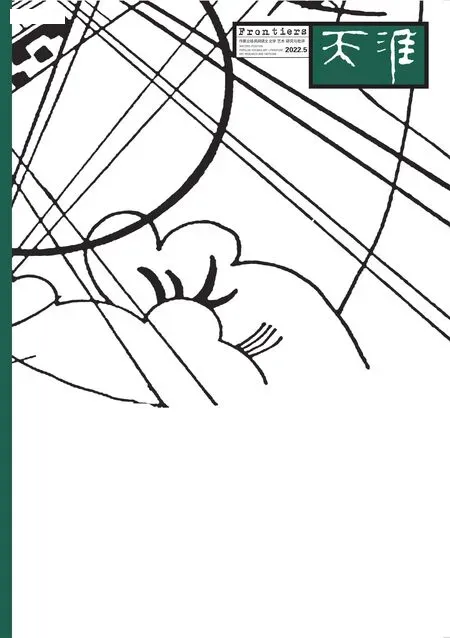新一代在如何對抗數字監控
肖芯妍
2022年6月2日《波士頓評論》的網站上,刊載了該網站記者對普林斯頓大學兩位研究者——肯妮婭·黑爾和佩頓·克羅斯基的訪談,題為《新一代在如何對抗數字監控》。
隨著數字技術的日益普及,我們也越發明白:我們的設備在監聽我們的談話,我們的個人數據在被追蹤和售賣,商家和有關部門在存儲我們的面部圖像,等等。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人在探討保護我們數字隱私的辦法——普林斯頓大學的“艾達·貝爾·韋爾斯‘只是數據實驗室”即致力于此,但它的關注點更為集中,即黑人和其他邊緣人群在數字監控時代所遭遇的挑戰和威脅。該實驗室試圖將學生、教育工作者、社會活動家和藝術家等集結起來,以共同探討針對數據生產和流通的批判性、創造性思考,黑爾和克羅斯基即在該實驗室工作。
面對數字監控的指控,系統和軟件的開發者們可能會回應說,情況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這是新技術,還有待進一步完善,而且隨著新技術的增多,情況會變得越來越好。但黑爾和克羅斯基并不認同這樣的說法,在她們看來,技術并非中性或無偏向的——我們將自己的價值觀和信仰編碼進技術之中,而技術之所以存在問題,是因為我們有對邊緣社群進行奴役和剝削的歷史,因此技術雖然是新的,但與技術有關的問題卻一點也不新:它們只不過是被重新塑形并被重新打包而已。新的軟件使得技術的運行速度更快,但它同時也使得歧視的運行速度更快,因此要解決技術的問題,我們還是要回到人和歷史那里。
從這一思考出發,黑爾和克羅斯基所在的團隊正在研發一款名為“我們的空間”的應用軟件。兩人對這款軟件做了介紹:一般流行的精神健康應用軟件都是針對個人的,它會問你今天過得怎么樣,或者追蹤你一周的情緒變化。但“我們的空間”要抵制的正是這一假設,即疾病的療治只能依靠身處資本主義重壓之下的你自己——“我們的空間”意在成為一個疾病療治的社群,比如:當你感到焦慮或者沮喪時,你和你所在的社群都知道如何能幫助你,這時有人就會告訴你,可以看看電視、吃點什么或者做點什么;你還可以在感到焦慮時向社群里的人發出警報,這樣其他人就會知道你的情況,并對你進行關照。
當然,從大的方面來說,這樣的對抗似乎于事無補:這就好像個體在對抗氣候變化——你大力踐行環保理念,但個人的努力在大規模排放的企業面前,簡直不值一提。同樣的道理,你在努力對抗數字監控,但相關的大型企業和機構似乎還越發壯大。對此,黑爾和克羅斯基回應說,我們的確無法指望一款應用軟件或者一項技術就能改變監控資本主義的現狀,但在現狀被徹底改變之前,我們還是得集體行動起來并匯集解放性力量,以求得生存,并矯正最終的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