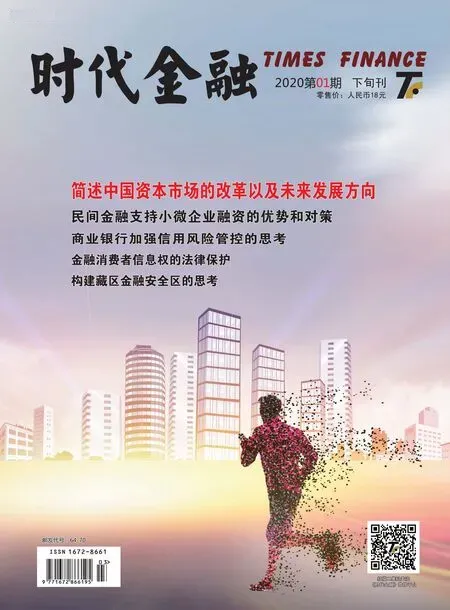化解地方政府存量債務風險創新機制研究
蘇振華

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礎設施缺乏有效的資產定價工具和市場化經營機制。目前監管部門、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之間就地方政府債務形式進行單向約束,而對化解內容、化解方式缺乏共識基礎,這也是造成地方政府債務堰塞湖遲遲無法有效疏解的主要原因。本文試圖探究一個化解地方政府債務的創新機制:在預算績效能力定價下的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權。依托現有政策及合規性文件充分闡述該機制的合理性。
一、我國公共財政與公共產品投資困境及其產生的成因
我國的財政政策被公共產品的錯配機制裹挾,鎖定在公共產品剛性兌付的財政資金池和“以收定支”的短期循環里,陷入錯配循環,地方財政的管理脫離目標導向,走向救濟式管理,“以收定支”的周期越來越短。剛性兌付和“表象公平”不僅造成各類公共產品的社會供給能力和生產供給邊界無法得到精確的識別和界定,公共產品也無法形成合理的定價結構。包括我國在內的許多國家均未建立與公共產品、公共服務及公共財政相匹配的獨立化、透明化機制。政府向民眾剛性兌付所需的公共產品,并以 “表象公平”的方式進行各種公共財政兌付;民眾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養老保險、免費醫療、義務教育等公共服務,并且建設更多的公共基礎設施。公共產品的剛性兌付使公共財政被短期目標所影響,導致公共資產配置與公共財政能力長期失衡。公共產品不是由公共權力憑空創造的,而是由人民群眾提供資金、資產或資源形成的社會供給能力創造的,這就回歸到使用者付費的本質。公眾通過納稅等形式形成公共財政,服務于公共產品等公共資產的供給,以社會供給能力為基礎的公共財政與公共產品提供機制的匹配性、獨立性和市場性越強,財政政策就越有效、越穩定。
構成公共產品投資與公共財政之間困境主要原因在于基礎設施缺乏有效的資產定價工具和市場化經營機制。一直以來,經濟學領域和政府公共管理領域都認為履行政府職能的公共產品和服務對于公眾來說都是免費的,因此忽略了其經濟屬性。 所有消耗人類財富的投資都應用得到精準測算,世界上沒有由政府提供的免費公共產品和服務,把“公共產品和服務對公民的公益性”覆蓋了其經濟屬性,覆蓋其投入和支出精準測算的必需性,是一個錯誤的定位。所有具有服務潛力的政府資產,都是具有經濟利益流入的經濟資源。
人民銀行《中國金融穩定報告(2018)》中明確:以某省為例,截至2017年末,該省銀行政府債務中約有65%用于基礎設施建設。我國地方政府債務形成的主要原因在于基礎設施缺乏有效的資產定價工具和市場化經營機制。由于對基礎設施投資形成的債務缺乏精準測算和比例分析,目前,監管部門、地方政府、金融機構之間就地方政府債務形式進行單向約束,而對化解內容、化解方式缺乏共識基礎,這是造成地方政府債務堰塞湖遲遲無法有效疏解的主要原因。
二、采用預算績效能力對存量基礎設施進行定價,打破公共財政與公共產品困境
根據《政府會計準則》將地方政府存量基礎設施按全生命周期(30年)的預算績效能力進行定價核算,對超出財政預算能力的負債進行識別和剔除,對滿足績效能力、確需財政進行支付的基礎設施按照《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進行特許經營。地方政府通過招拍掛方式,以15-30年期限進行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權有償轉讓,收回前期投資的資金,定向用于公益性項目的地方政府債務償還。定價對化解我國地方政府90%左右的地方政府債務,具有實際可行的積極作用。
假設:某城市共有ABC三條道路,長度均20公里,使用期限為30年。(為了便于理解,下例采用整數取數舉例。)
道路A總造價成本30億元,年通行車輛200萬輛;道路B總造價成本45億元,年通行車輛150萬輛;道路C總造價成本60億元,年通行車輛100萬輛。
經過核算,該城市道路的基準績效能力價格為100元/輛/次。道路A績效成本50元/輛/次低于基準績效能力價格;道路B績效成本100元/輛/次等于基準績效能力價格;道路C績效成本200元/輛/次高于基準績效能力價格,存在超額負債投資。
政府通過特許經營收回資金(扣除資金周期成本):道路A收回30億元以內;道路B收回45億元以內;道路C收回45億元以內,15億元超額投資部分超過基準績效能力價格,被剔除。
政府特許經營年度預算支出安排:道路A政府按實際績效成本進行預算支付購買服務,預算收大于支;道路B政府按基準績效能力價格進行預算支付購買服務,預算收支平衡;道路C政府按基準績效能力價格進行預算支付購買服務,剔除了超額投資。
地方政府債務實質上是基礎設施投資缺乏精算平衡,地方政府公共基礎設施的投資按3-8年的期限舉借債務,與公共基礎設施20-30年左右的服務能力期限無法形成期限匹配,存在3-6倍的時間周期杠桿,導致地方政府當期償付壓力巨大,不得不承擔未來30年左右的公共基礎設施服務能力負擔。
試點方案立足于從地方政府的財政能力出發,按預算績效對基礎設施資產進行定價,實現從內容上真正的化解債務。不僅能夠實現地方政府由長期舉債投資基礎設施的方式,轉變為根據績效購買基礎設施服務能力的方式,而且全面強化了基礎設施預算支出的硬化約束機制、長效匹配機制、精算平衡機制,實現基礎設施服務能力與財政能力一一對應,實現基礎設施服務周期與財政周期一一對應。
三、預算績效能力對存量基礎設施進行定價的政策依據和合規性分析
(一)在政府會計中基礎設施具有經營屬性和經營內涵
《政府會計準則——基本準則》中明確:“第二十七條資產是指政府會計主體過去的經濟業務或者事項形成的,由政府會計主體控制的,預期能夠產生服務潛力或者帶來經濟利益流入的經濟資源,服務潛力是指政府會計主體利用資產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以履行政府職能的潛在能力。”
通過《政府會計準則》可以明確:基礎設施資產的核心價值是“服務能力”,與財政能力匹配的“服務能力”才具有政府會計管理價值和財政預算支付的價值,所以基于財政預算績效能力定價是確定基礎設施投資與預算支付精算平衡的基礎。
能夠帶來經濟利益流入的資產,需要通過經營提高其經濟利益流入;能夠產生服務能力的基礎設施資產也需要通過經營提高其服務能力供給和服務。
因此基礎設施的經營內涵既不是簡單的表現為日常維護,也不是像高速公路一樣直接由使用者付費,其特許經營內涵包括:一是通過有償轉讓收回資金,政府對基礎設施短期的投資性、債務性支出轉變為基礎設施全生命周期的績效服務能力支出,政府的預算支出由資產成本定價方式轉變為績效能力定價方式;二是特許經營項目公司在經營期限內實現對基礎設施資產公共服務能力的有效保持;三是政府對基礎設施資產的服務能力進行監測和績效評價,不再按資產成本付費,而是按實際績效能力付費;四是在經營期限內,特許經營項目公司進行基礎設施維護效率的提升和財政預算費用的節約。
(二)建立全面績效管理的基礎設施一般公共預算支出是黨中央、國務院的明確要求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全面實施預算績效管理的意見》(2018年9月1日)中明確:“加快建成全方位、全過程、全覆蓋的預算績效管理體系。”
本方案的核心目標是根據國家預算法的核心“規范政府收支行為,強化預算約束,建立健全全面規范、公開透明的預算制度,保障經濟社會的健康發展”,理順政府預算支出的服務價格,按照基礎設施特許經營模式,建立基礎設施領域的預算績效標準,立足長遠、標本兼治,提高地方政府收入和支出的匹配度,健全長效機制的目標。
(三)現行政策明確公益性項目可以實行市場化經營
《國務院關于創新重點領域投融資機制鼓勵社會投資的指導意見》(國發〔2014〕60號)指出:“政府可采用委托經營或轉讓—經營—轉讓(TOT)等方式,將已經建成的市政基礎設施項目轉交給社會資本運營管理。”
2015年,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財政部、中國人民銀行等六部委頒發《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要求對能源、交通運輸、水利、環境保護、市政工程等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領域開展特許經營。
2018年《國務院辦公廳關于保持基礎設施領域補短板力度的指導意見》提出“規范有序盤活存量資產,鼓勵采取轉讓—運營—移交(TOT)、改建—運營—移交(ROT)等方式,將回收資金用于在建項目和補短板重大項目建設”。
2018年7月,相關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要求:“對于承擔公益性項目建設運營職能的融資平臺,轉型為基礎設施、公共事業、城市運營等領域市場化運作的國有企業,轉型后依法合規承接政府公益性項目,實行市場化經營。”
上述政策均清晰明確,政府公益性項目可以實行市場化經營。
(四)資產定價環節的政策依據
《政府會計準則》《政府綜合財務報告編制指南》《政府會計準則第 5 號——公共基礎設施》均要求各級政府對基礎設施進行核查登記。
(五)招拍掛環節的政策依據
《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特許經營管理辦法》第十五條“實施機構根據經審定的特許經營項目實施方案,應當通過招標、競爭性談判等競爭方式選擇特許經營者。”
2019年4月22日,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經認真研究,對定價和試點工作提供了書面復函,認為定價“對于優化完善地方政府存量公共基礎設施的資產核算、服務定價與績效評價等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為國家當前在公共服務領域鼓勵推廣運用的‘轉讓—運營—移交(TOT)方式提供了更為細化和可操作的實施標準及流程。”
四、預算績效能力對存量基礎設施進行定價的三大長效作用
(一)從地方政府端,定價能夠建立基礎設施全面績效預算控制和精算平衡機制
多年來,我國治理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的措施趨于表象,我國財政政策對基礎設施投資與城市發展需求、與有需求的財政能力三者之間缺乏精算平衡的量化控制工具和控制機制。
定價能夠建立精確到城市每一條道路、每一個公園、每一桿路燈等的資產核算、服務定價與績效評估為前提的基礎設施全生命周期預算管理、財務核算管理和績效管理機制。這樣不僅能夠實現地方政府由舉債投資基礎設施的方式,轉變為購買基礎設施服務能力的方式,使城市基礎設施運營管理實現專業化、效能化和陽光化;而且全面強化了基礎設施預算支出的硬化約束機制、長效匹配機制、精算平衡機制,實現基礎設施服務能力與財政能力一一對應,實現基礎設施服務周期與財政周期一一對應。
(二)從金融機構端,定價能夠建立基礎設施投融資量化信用控制機制,推進基礎設施領域金融供給側深化改革
定價能夠把城市基礎設施供給能力信用從寬泛的政府信用、地方平臺公司評級信用等模糊信用管理中獨立出來,改變金融機構按資產規模進行基礎設施融資定價的方式,建立按基礎設施服務能力和服務期限進行定價的方式,實現了按需求、按市場機制配置金融資源的量化信用控制機制,推動金融機構在地方政府投融資體系由單純的資產融資服務轉型為資產定價、資產配置、資產績效管理的綜合金融服務。這對化解地方政府債務風險、確保財政健康可持續、維護國家經濟金融安全、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大意義。
(三)定價能夠解除我國對房地產和基礎設施投資的依賴,解除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收入的依賴,為我國經濟發展建立可循環的財政資金
2021年,我國整體經濟指標趨向好轉,但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的結構尚在形成過程中,各級財政受到化解債務風險和產業減稅的雙向擠壓。現在尋找規模化、可釋放的資產以保持國民經濟投入的循環至關重要。
我國基礎設施固化了幾十萬億元的資金,占用了我國大量的財政能力,資金鎖定周期30年左右。定價能夠盤活地方政府幾十年來積累的債務化、固化基礎設施資產,提高財政資金在國民經濟中的周轉率,降低了財政對當期稅收收入、土地收入的依賴,降低經濟驅動對基礎設施、房地產投資的依賴。分3-8年能夠釋放20-30萬億元的非債務型、非超發型資金,使得各級政府有充裕的財政能力和財稅政策空間支持實體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1]張賀,秦沖.承做地方政府專項債對商業銀行的正向溢出效應[J].農村經濟與科技,2020(31):161-162.
[2]張賀,李體欣.鄉村振興戰略下地方政府專項債創新研究[J].全國流通經濟,2019(36):124-126.
[3]張賀.地方政府專項債政策變化中的商業銀行策略[J].中國集體經濟,2020,(19):108-109.
[4]張賀.農村金融的功能效應與普惠金融發展——嬗變中的“道德”與制度正義[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7,34(03):100-105.
[5]張賀,白欽先. 數字普惠金融減小了城鄉收入差距嗎?——基于中國省級數據的面板門檻回歸分析[J]. 經濟問題探索,2018,(10):122-129.
[6]張賀.全面推進鄉村振興背景下數字普惠金融對我國西部經濟增長的影響[J].云南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1,38(05):55-62.
作者單位:中國農業銀行云南省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