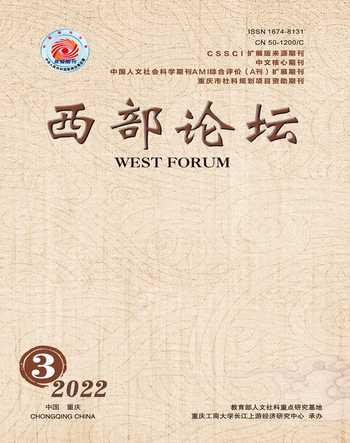我國家庭農場研究進展與展望
郭熙保 吳方 查科
主持人語
郭熙保: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是我國家庭農場迎來快速發展的標志性文獻,可以說,2013年是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的元年。首先,自2013年開始,國家和各地密集出臺了支持家庭農場發展的政策和措施;其次,近10年來,我國家庭農場如雨后春筍般在全國各地興起,至今已發展到300多萬家;最后,學術界關于家庭農場的研究爆發性增長,每年以千篇論文以上速度遞增。十年是一個值得總結的時間節點。為此,本專題從理論與政策兩個層面對我國家庭農場研究進行了梳理和總結。《我國家庭農場研究進展與展望》一文較為全面系統地梳理和歸納了我國學術界關于家庭農場的研究成果,并提出了未來的研究方向和研究課題;《家庭農場研究:知識圖譜、研究熱點與前沿趨勢》一文基于文獻統計從知識圖譜、研究熱點和前沿趨勢等方面刻畫了10年來我國家庭農場研究的演進和趨勢;《示范家庭農場認定標準評析》一文對21個省份和31個城市出臺的示范家庭農場認定文件進行歸類和比較,并提出改進建議。
DOI:10.3969/j.issn.1674-8131.2022.03.001
摘要: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的發布促進了我國家庭農場的快速發展,也掀起了家庭農場研究的熱潮并一直延續至今。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為家庭農場發展帶來新的機遇,如何在新時代實現家庭農場高質量發展給家庭農場研究提出了新的課題,因而有必要對已有的家庭農場研究文獻進行梳理總結,為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家庭農場研究提供啟示和方向。
本文通過回顧和梳理CSSCI收錄的題目包含“家庭農場”的382篇論文,從家庭農場的概念特征與地位作用、形成原因與發展條件、發展模式與經營模式、適度經營規模與經營效率(績效)、制約因素與應對策略等5個方面總結其主要研究成果:(1)家庭農場是介于企業和普通農戶之間的農業經營主體,既有“家庭”的特征,也有“農場”的屬性;當前,家庭農場是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生力軍,是推動農業現代化和鄉村振興的主要力量之一。(2)制度供給與制度需求的不均衡催生了家庭農場;我國家庭農場的產生與工業化和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密切相關,而制度改革是家庭農場形成機制中的關鍵因素;家庭農場的持續發展需要有相應的土地流轉和新型職業農民培育制度、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市場機制和政府支持、投資保障和社會保障等。(3)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適度規模經營是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模式;各地資源狀況和發展水平存在巨大差異,家庭農場實踐也形成了多樣化的發展模式和經營模式。(4)家庭農場經營規模要“適度”,而“適度”的標準對于不同地區、不同類型的家庭農場具有顯著差異;我國家庭農場的經營績效明顯高于普通農戶,但經營效率普遍不高,尤其是技術效率水平整體偏低;家庭農場的經營效率和績效受到農場主及其家庭特征、農場經營方式和技術水平、經營環境和配套設施、農業扶持政策和政府補貼等因素的影響。(5)我國家庭農場發展仍然面臨諸多制約因素,比如:農場主素質不高、經營管理能力欠缺,農場經營規模或方式不當、投資不足、技術水平不高,土地產權和流轉制度有待完善,融資較為困難,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不健全,政府扶持力度不夠等,應從土地流轉、農地改革、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農場主培育、金融支持、財政補貼等方面加以完善。
我國學者對家庭農場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并產生了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成果,但還存在一些問題有待進一步深化和拓展,如:截面分析較多,長期跟蹤分析不足;經濟學角度分析較多,多學科分析不足;國內分析較多,國際比較分析不足。
關鍵詞:家庭農場;適度規模;農地制度;新型職業農民;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22)03—0001—16
《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現代農業進一步增強農村發展活力的若干意見》(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的發布使“家庭農場”迅速成為我國學術界的研究熱點。雖然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學者對家庭農場的研究已有數十年的歷史,但2013年無疑是家庭農場研究的分水嶺。在中國知網的搜索結果顯示,家庭農場研究的論文數量從2012年的127篇激增至2013年的1316篇,此后每年發文數量穩定在1000篇以上。截至2022年4月25日,在中國知網數據庫中以“家庭農場”為主題的期刊論文有1.58萬余篇;在CSSCI數據庫中以“家庭農場”為主題的論文有706篇,其中篇名直接包含“家庭農場”的論文有382篇。
面對家庭農場研究的爆發式增長,一些學者對家庭農場研究進行了文獻回顧和綜述(韓朝華,2017;陳德仙等;2019)[1-2]。然而,現有關于家庭農場研究的文獻綜述仍需改進。首先,在研究主題上,有些文獻綜述主題不夠全面,涉及內容不夠廣泛,僅回顧了家庭農場研究的某一個主題,如家庭農場的最優適度規模或經營效率評價、制度環境對家庭農場的影響等。其次,很多文獻綜述涉及的話題和內容存在重復和雷同,主要集中在介紹家庭農場的內涵和特征、闡述其發展問題和對策、梳理其影響因素和規模效應等方面。最后,在研究時間上,沒有及時總結和反映最新研究成果,大多是2017年以前的文獻。本文綜述的內容不僅涵蓋了當前國內家庭農場研究的多個主題,而且及時吸收了相關研究的最新學術成果。
一、家庭農場的概念特征與作用地位
1.家庭農場的概念與特征研究
家庭農場顧名思義是以家庭為單位的農業經營主體,但不是所有以家庭為單位的經營主體都可以叫家庭農場。家庭農場是與現代農業聯系在一起的。在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傳統農業占支配地位,農戶一般不稱作家庭農場(family farm),而稱作小農(small peasant household)。我國學者從不同角度來 定義家庭農場。在早期的研究中,有學者把家庭農場定義為具有企業性質的經營組織(房慧玲,1999;黎東升等,202000)[3-4]。2013年以來,學術界普遍認為家庭農場不是企業,而是介于小農戶與企業之間的一種微觀經濟組織。例如,高強等(2013)基于農業生產要素的角度認為,家庭農場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融合科技、信息、農業機械、金融等現代生產因素和現代經營理念,實行專業化生產、社會化協作和規模化經營的新型微觀經濟組織[5]。黃新建等(2013)基于經濟收益的角度認為,家庭農場應當是以家庭經營為基礎、以適度規模經營為目標、以高效的勞動生產率從事農產品的商品化生產活動,并獲取與農戶從事非農產業收入相當甚至略高的經濟利潤的經濟單位[61。高帆和張文景(2013)基于組織方式的角度認為,家庭農場是介于小農戶和農業企業之間的中間型經營組織方式,而之所以介于二者之間,一方面是由于家庭農場以家庭成員為主要勞動力(與小農戶相似),另一方面是因為家庭農場具有法人性質和規模化生產機制(與農業企業相似)
西方發達國家雖然在定義家庭農場時不強調經營規模,但絕大多數家庭農場規模都比較大,因此,家庭農場大多數是規模經營單位。我國的家庭農場從一開始提出就是與經營規模聯系在一起的。早在1987年1月,中共中央發布的《把農村改革引向深入》(中發[1987]5號)就提出要在發達地區興辦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二十多年后,2008年10月,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把家庭農場作為規模經營主體提出來。2013年中央一號文件進一步提出,“鼓勵和支持承包土地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流轉,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不過,我國的家庭農場與西方的家庭農場在土地所有制上具有顯著差別。由于我國實行的是農村集體土地所有制,農村集體享有農用地所有權,而農戶僅享有農用地的承包經營權,導致“租地農場”成為我國家庭農場區別于大部分西方發達國家家庭農場的一個顯著特征(王貽術等,2013)[8]。
規模經營是家庭農場的主要特征,但不是唯一特征。郭熙保(2013)認為,家庭農場主要有以下四個特性:一是以家庭作為經營單位,二是勞動力主要是家庭成員,三是農地經營長期穩定并達到一定規模,四是農業經營收入是家庭的全部或主要收入來源[1。關付新(2018)將家庭農場的基本特征概括為三個方面:一是規模化經營,以此區別于小規模經營的小農戶和兼業農戶;二是以家庭勞動力為主,以此區別于雇工經營的農業公司和專業大戶;三是家庭主要收入來自農業(種植和養殖),以此區別于非農化的從事農產品加工和流通的農村工商戶以及以非農收入為主要收入的兼業戶[10]
從以上文獻可以看出,盡管不同學者對家庭農場的概念界定有不同的表述,但基本內涵大同小異,只是所強調的維度有所不同。與傳統普通農戶相比,家庭農場的特征概括起來主要有如下幾個方面:一是以家庭為經營單位,這是最基本特征,否則就不能冠名“家庭”二字;二是適度規模經營,要比小農戶經營規模大得多,否則就不稱其為“農場”,但也是在家庭勞動力能夠經營的范圍內;三是從事專業化、市場化生產,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這是其與小農戶的本質區別,后者主要是為滿足自己消費而進行農業生產,追求產量最大化。
2.家庭農場在我國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家庭農場在不同的國家、不同的發展階段具有不同的特征,且在農業生產乃至國民經濟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有所不同。2018年9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政治局第八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要突出抓好農民合作社和家庭農場兩類農業經營主體發展,賦予雙層經營體制新的內涵,不斷提高農業經營效率。之后,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都提出要重點抓好家庭農場和農民合作社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發展。可見,中央非常重視家庭農場的發展,強調家庭農場在鄉村產業振興中的重要作用。相關研究也基于家庭農場的性質和特點認為,家庭農場必將成為主導我國現代農業的新型市場主體,是實現農業現代化和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力軍。
郭熙保(2013)較早提出規模經營是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實現農業現代化的主要途徑,而家庭農場是實施農業規模經營的最重要主體[]。郭慶海(2013)分析了家庭農場在家庭經營、規模經營方面的優勢,指出家庭農場作為新型農業經營主體中的基本主體,具有提高農業綜合效益、推廣農業科技等重要作用。杜志雄和王新志(2013)通過對多元化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特征辨析認為,家庭農場體現著改造傳統農業的歷史規律性,引領著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代表著中國農業的先進生產力,其理應成為未來我國農業經營體系當中最主要的形式[121。姜濤(2017)指出,家庭農場的一系列特征決定了其具有新型農業經營主體“樞紐”地位,并在提高農業綜合效益、推廣農業科技、保護耕地、傳承農耕文明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王新志和杜志雄(2020)認為,家庭農場具有內在的制度優勢,是現階段中國“最適宜”“最合意”的新型農業經營主體
[14]。陳德仙等(2021)指出,家庭農場保留了家庭在農業生產中的“監督成本優勢”,既具有土地規模適度擴大帶來的“規模經濟優勢”和“市場競爭優勢”,還具有產業疊加和融合帶來的“多層利益優勢”,是一種有效的農業經營主體發展方式,并在實踐中取得了良好的經濟成效,為新時代鄉村振興注入了強勁的內生動力[15]。此外,家庭農場也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主體。肖望喜等(2018)提出,家庭農場可以在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發揮多種積極的作用,包括以市場為導向改善農產品供給結構、促進農業產業體系整合與“三產”融合、推動農業生產技術與基礎設施的現代化等[16]。
二、家庭農場形成原因與發展條件
1.家庭農場的形成原因研究
學術界對家庭農場形成原因的探究大都是從制度層面展開的。有學者基于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觀點分析家庭農場形成的原因。例如,屈學書(2016)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農業生產二重性理論、制度變遷理論、規模經濟理論分析認為,家庭農場是與當前生產力發展相適應的一種生產關系,是符合農業生產二重性特點要求的農業生產方式。王春來(2014)也認為,家庭農場的興起和發展是我國農村生產關系與生產力相適應的結果[18]。也有不少學者根據新制度經濟學理論闡述家庭農場形成的原因。例如,高強等(2013)、何勁和熊學萍(2014)認為,制度的供給與需求均衡是家庭農場形成的主要動因,制度安排與環境相容是家庭農場形成的必要條件,而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了漸進式發展是家庭農場的必然選擇[5][19]。伍開群(2014)則認為,國家強制性制度變遷與農民誘導性制度變遷共同促進和實現了家庭農場的制度變遷[20]。程軍國等(2020)也認為,我國家庭農場的形成是需求誘導和政府引導兩種路徑共同作用的結果,其中,需求誘致來源于農業產業的宏觀發展需求和微觀農戶為節約自身交易成本所做的努力,政府引導則是通過制度改革創造有利于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環境而發揮作用[2]。蘭勇(2015)認為,從傳統農民到家庭農場的演變是一個多因素相互作用和演變的過程,包括環境、制度和農民行為等,它們的相互作用和演化是家庭農場產生的基本動力機制[22]。楊成林(2014)指出,家庭農場形成的根本驅動力來自農民對經濟激勵的自發反應,政府的作用主要在于如何為這一生成掃清障礙,降低農民在其生成過程中付出的“交易成本”,同時降低農業經營風險,使農業生產更具可預測性
還一些學者從經濟發展和結構變化的角度探討家庭農場形成和規模擴大的原因。郭熙保和馮玲玲(2015)運用動態均衡理論分析發現,隨著工業化進程的加快,非農就業機會不斷增加,導致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和農場生產機械化程度提高,從而使農場規模不斷擴大[24]。其他學者也持有類似的觀點,如陳楠和王曉笛(2017)認為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是影響家庭農場發展的主要環境因素,工業化和城鎮化將農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出來并解決土地集中問題,進而為新型職業農民和家庭農場的發展提供可能,因此,工業化與城鎮化是家庭農場發展的經濟基礎與前提,家庭農場的發展需要與工業化和城鎮化同步推進[25]。何勁和熊學萍(2014)指出,工業化、城鎮化的快速發展和勞動力市場制度的創新不僅為農村勞動力提供了廣闊的就業空間,而且也為家庭農場的形成與發展創造了生產專業化、農民職業化的前提條件。王振等(2017)基于我國家庭農場發展較好的地區大多城鎮化水平較高的客觀事實認為,在人多地少的中國發展家庭農場必須以工業化和城鎮化為開拓力量[26]。
2.家庭農場的發展條件研究
作為一種全新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家庭農場的發展需要一定的基礎和條件。高強等(2013)認為,家庭農場形成和發展所需的制度條件至少應包括:以專業化分工為基礎的勞動力市場制度,穩定和明晰的土地產權制度,以農機作業服務、金融服務、市場信息服務、農技服務為主的社會化服務制度等[5]。朱 啟臻等(2014)指出,家庭農場的發育需要政府的支持和特定的社會條件,包括新型職業農民培育、高效的土地流轉制度和政府的配套支持等[27]。王振和李凡(2014)基于對上海松江地區的考察認為,家庭農場的發展應滿足幾個基本條件:一是農業人口減少且土地流轉順暢,二是政府有效的財政支持和政策引導,三是良好的社會化服務和外部環境[28]。屈學書和矯麗會(2014)指出,工業化發展、社會保障體制健全、土地流轉市場完善是家庭農場發展的條件[291。郭熙保和冷成英(2018)認為,市場化環境是家庭農場產生和興起的關鍵,工業化和城市化催生了家庭農場的繁榮,土地流轉市場的形成是家庭農場發展的基礎,大規模投資是家庭農場快速發展的重要保障,政府扶持對家庭農場發展有重要推動作用301。陳軍民和翟印禮(2015)從交易成本的角度認為家庭農場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契約性質,契約各方的行為對家庭農場的產生具有很大的影響,因而降低家庭農場運行的交易成本是該制度順利實施的關鍵,同時,政府和中介組織在降低農民適應制度成本方面也發揮著重要作用3。
通過以上文獻梳理可知,學術界對家庭農場產生的原因進行了多角度探討,其中的主要觀點是制度變遷是家庭農場產生的主要動因,但從經濟發展角度考察家庭農場產生的原因更為恰當。家庭農場形成和發展的根本動因是工業化和城鎮化。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導致大量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非農部門轉移,留守在農村的人口越來越少,使得每個農業勞動者經營的農地不斷增加,于是促進了農地的流轉和集中,家庭農場應運而生并持續發展。如果說制度變遷導致家庭農場產生和發展,其也是通過促進工業化和城鎮化來發揮作用的。例如,家庭承包經營制的實施解放了農村剩余勞動力,而勞動力市場的開放促使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轉移到非農部門,推動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加快,從而導致土地流轉和集中,使得家庭農場發展成為可能。
三、家庭農場發展模式與經營模式1.家庭農場的發展模式研究
家庭農場發展模式是指家庭農場在發展過程中所形成的具有鮮明特色的發展方式與發展路徑(冷成英,2020。家庭農場發展模式的形成是基本經濟條件、制度環境、經營主體、社會資源等相互作用的結果(高強等,20014)[33]。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家庭農場發展模式選擇主要取決于其土地、勞動力等資源稟賦和工業化水平。從經營規模角度看,發達國家的家庭農場發展大致有三種主要模式:以美國為代表的大型家庭農場發展模式、以法國為代表的中型家庭農場發展模式和以日本為代表的小型家庭農場發展模式(張紅宇等,
2017)[34]。人少地多的國家,農業發展首先從生產工具上進行革新,通過機械化等路徑節約勞動力;人多地少的國家,則需要更多地投入勞動力和運用生化技術,通過提高單產來充分利用土地資源。因此,以美國為代表的大型家庭農場發展模式是規模化、機械化和高技術的模式,以法國為代表的中型家庭農場發展模式是生產集約加機械技術的復合型模式,以日本為代表的小型家庭農場發展模式則是資源節約和資本技術密集型模式(高照軍等,2008)。
適度規模經營是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的基本方向和主要模式,這是由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決定的。郭熙保(2013)認為,我國地域遼闊,各地人口密度、地形差異大,因此應該走多元化的農業發展道路,比如:像東北和西北的平原地區,人均耕地面積與歐洲國家相當,應該借鑒歐洲農業發展模式,選擇機械化與生化技術混合的技術進步路徑;而像東部與中部人口稠密的地區,人均耕地面積與日本和韓國差不多,應借鑒日韓的農業發展模式,選擇以生化技術為主的技術進步道路;受制于人均耕地面積,我國無論如何也不適合采取美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國以機械化為主的農業發展模式[9]。
事實上,在我國的家庭農場發展過程中,各地因地制宜的實踐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發展模式。王新志和杜志雄(2014)總結了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的五種典型模式,即“上海松江模式”“浙江寧波模式”“湖北武漢模式”“吉林延邊模式”“安徽郎溪模式”:(1)上海松江的家庭農場發展模式是上海市高度城市化和后工業化的產物,其主要特征是建立規范統一的土地流轉方式,促進農村土地的適度規模化經營;(2)吉林延邊地區通過發展勞務經濟實現農業人口轉移從而推動家庭農場發展,其主要特征是加快土地流轉,創新融資模式;(3)浙江寧波的家庭農場發展模式是由寧波地區民營經濟快速發展帶來的農業勞動人口轉移所催生的,其主要特征是成立基金引導家庭農場發展;(4)湖北武漢依托工業化和城市化發展推動城郊家庭農場發展,其主要特征是細化扶持政策,著重引導家庭農場的發展與促進產業化和環境保護相結合;(5)安徽郎溪的家庭農場發展模式則是傳統農業地區通過創新農業生產經營體制發展家庭農場的代表,其主要特征是“三駕馬車”(指農民主體、政府扶持、協會幫助)拉動家庭農場發展(王怡術,2015)。高強等(2014)將我國家庭農場歸納為“上海松江自耕農模式”“吉林延邊城鎮化聯動模式”“安徽郎溪協會帶動模式”“山東諸城分類管理模式”等四種典型模式[33]。郭家棟(2017)則辨析了“上海松江”“浙江寧波”“安徽郎溪”“河南民權”四種家庭農場發展模式的具體實踐、實際效果和優缺點[38]。在諸多家庭農場發展模式中,一些學者重點研究了家庭農場的一種或幾種發展模式。例如,呂惠明和朱宇軒(2015)根據問卷調查數據,分析了寧波家庭農場發展模式的現狀、問題及對策[31;郭熙保和冷成英(2018)對比分析了湖北武漢和安徽郎溪的家庭農場發展模式,并總結了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的十大特征[30][40]。
2.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研究
與家庭農場發展模式側重于從宏觀層面描述家庭農場的發展方式和發展路徑不同,家庭農場經營模式側重于從微觀層面描述家庭農場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是指單個家庭農場為了規避風險、實現利益最大化而選擇與其他經營主體(包括農民合作社、農業龍頭企業和社會化服務組織等)聯合和合作的生產組織形式和經營方式。學術界根據家庭農場與其他經營主體的聯合和合作方式提出了不同的家庭農場經營模式。例如:趙維清和邊志瑾(2012)通過對浙江省家庭農場的實地調查,提出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的創新路徑,包括“家庭農場+合作社+合作社參與龍頭企業”“家庭農場+合作社+加工企業”“家庭農場+合作社+超市”等模式[41];劉倩(2014)則提出我國家庭農場主要有“單打獨斗”“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家庭農場+龍頭企業”“家庭農場+專業合作社+龍頭企業”等經營模式[;蔡穎萍和杜志雄(2017)指出,我國家庭農場已經呈現出多元化、多類型的發展趨勢,包括“家庭農場+農業社會化服務”“發揮集體功能培育適度規模的家庭農場”“家庭農場+合作社+龍頭企業聯合經營”“家庭農場聯合合作”等多種經營模式[43]。還有一些學者比較分析了不同家庭農場經營模式的優缺點。例如:張樂柱等(2012)分析了溫氏集團“公司+家庭農場”的生產經營模式,認為該模式與“公司+農戶”模式相比,化解了后者利益分配難題,實現了龍頭企業與農戶間更緊密的聯結機制;曹林奎(2013)通過分析“公司+農戶”經營模式認為,“合作社+家庭農場”是一種新型的農業產業化模式,應該給予重點關注[45];張瀅(2015)則認為,“家庭農場+合作社”經營模式不僅避免了“公司+農戶”模式下交易成本高、違約風險頻繁的問題,還利用合作社的聚合效應和農場主的高度利益同質性,解決了“合作社+農戶”模式下“小農需要合作,但不擅長合作”造成的合作困境[46]。
綜上所述,學術界對我國家庭農場發展和經營模式的研究主要基于三個不同的層次展開:一是從國際比較角度提出我國的家庭農場發展模式,主要是以經營規模為劃分準則,例如北美大型農場模式、歐洲中型農場模式和日韓小型農場模式,認為我國的家庭農場發展應該借鑒歐洲和日韓模式,而不能走北美發展道路。二是從地區角度劃分不同的家庭農場發展模式,例如“上海松江模式”“浙江寧波模式”“湖北武漢模式”“安徽郎溪模式”和“吉林延邊模式”,這些模式是基于各地資源稟賦、發展水平和政府支持等情況總結出來的發展經驗,各有特點,對于類似地區具有重要的推廣價值。三是從經營主體之間的聯合和合作角度劃分家庭農場的經營模式,如家庭農場獨立經營模式、與合作社合作模式、與龍頭企業合作模式以及幾種經營主體聯合經營模式等,這些模式對于各地家庭農場經營效率和效益的提高具有重要的學習價值和借鑒意義。
四、家庭農場適度經營規模與經營效率和績效
1.家庭農場的適度經營規模研究
從我國農業人口多、耕地面積少、戶均經營規模較小的特殊國情出發,官方和學術界都認為家庭農場的經營規模應該適度。2013年9月,原農業部部長韓長賦指出,中國也需要在家庭承包經營的基礎上發展家庭農場,但中國的家庭農場要強調適度規模,不可能搞到像美國、阿根廷和巴西那么大的規模。黃宗智(2014)認為,適度規模的、“小而精”的家庭農場才是中國農業正確的發展道路[47。影響農場經營規模的因素非常復雜,除了技術水平之外,交易成本、市場的完善程度、稅收政策和農戶的風險規避能力等都會對農場經營規模產生影響(林萬龍,2017)[48]。朱啟臻等(2014)提出,家庭農場的具體規模是由自然和社會條件、技術水平、經營內容、經營方式與地理環境等因素綜合決定的,在其他條件一定的情況下,家庭農場規模最重要的限制因素是家庭勞動力的數量[27]。王春來(2014)也認為,自然稟賦、生產傳統、科技水平和社會化服務等共同決定了家庭農場的適度規模[18]。丁建軍和吳學兵(2016)基于對湖北荊門市家庭農場的調查認為,影響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因素有資源稟賦、土地流轉、雇工狀況、農場主的經營能力以及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的完善程度等[49]。
關于家庭農場經營規模的適度標準,相關文獻的觀點可以概括為“收入標準論”和“效率標準論”(也稱為“勞動標準論”)。郭熙保(2013)認為,農業經營規模化是指農業生產者經營足夠面積的農地,產生規模效應,使勞動生產率大幅度提高到接近非農業部門的水平,其所獲得的收益也不低于從事其他行業的收益。朱啟臻等(2014)認為,家庭農場的適度規模有兩個標準:一是生計標準,即家庭農場的規模收益能滿足家庭人口的基本需要;二是生產力標準,即在現有技術水平下家庭勞動力所能經營的最大面積27。郭慶海(2014)則認為,農戶的最優經營規模應確保以下兩點:從效率的視角看能夠實現農戶收益最大化,從收入的視角看農戶能夠獲得與城市居民(或外出務工農戶)大體相當的收入水平[50]。從上述學者的論述中可以看出,在確定家庭農場的適度經營規模時,“收入標準”和“效率標準”是同樣重要的。然而,一些學者提出“收入標準”是確定農場適度規模的首要因素,適度規模的核心是使務農者能夠獲得與打工收入相當的收入(何秀榮,2016)[51]。對此,關付新(2018)認為,“收入標準”判定的是最小適度經營規模,而“效率標準”確定的是最大適度經營規模,因而適度的土地經營規模處于由“收入標準”和“效率標準”確定的下限和上限之間0。此外,也有學者基于公平的角度來看待家庭農場的適度經營規模,如陸文榮等(2014)指出,村莊強大的集體制傳統、基于村落成員權的土地福利分配、形式平等與事實平等兼顧的村莊大公平觀等與政府和市場共同建構了家庭農場的適度經營規模[52]。
然而,在具體規模測算上,相關文獻對家庭農場適度經營規模的估算值差異很大。例如:農業部經管司及經管總站研究組(2013)認為,從土地生產率和勞動生產率的雙重標準來衡量,北方單季地區的適度經營規模在6.67公頃,南方兩季地區則為3.33公頃[53;朱啟臻等(2014)認為,家庭農場適度經營規模的下限為家庭成員的生計需要,上限則為家庭成員經營能力最大化所對應的規模,據此推算,山東一對種植蘋果的夫婦所適合的經營規模為0.33公頃,而黑龍江一個種糧戶最多可耕種20公頃左右的土地[27];黃新建等(2013)根據江西水稻種植的經驗,基于規模效率邊際報酬計算出的家庭農場最佳經營規模為4.73~10公頃[61;孔令成和鄭少鋒(2016)運用DEA模型的測度結果顯示,上海松江區家庭農場的最佳土地投入規模為8.13~8.40公頃;韓蘇和陳永富(2015)運用DEA模型的分析則發現,浙江省果蔬類家庭農場的最優經營面積為1.33~2.0公頃[55]。蔡瑞林和陳萬明(2015)基于江蘇省13市糧食生產型家庭農場測算出的最優經營規模約為5.17公頃[56];根據蘇昕等(2014)的推算,到2030年,我國勞均耕作面積將達到0.67公頃,而家庭農場的平均規模將達到26.7公頃(57)。
[47]黃宗智.“家庭農場”是中國農業的發展出路嗎?[J].開放時代,2014(2):176-194+9.
[48]林萬龍.農地經營規模:國際經驗與中國的現實選擇[J].農業經濟問題,2017(7):33-42.
[49]丁建軍,吳學兵.家庭農場經營規模及其效益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湖北省荊門市66家種植類示范家庭農場的調查[J].農業經濟,2016(10):9—11.
[50]郭慶海.土地適度規模經營尺度:效率抑或收入[J].農業經濟問題,2014(7):4-10.
[51]何秀榮.關于我國農業經營規模的思考[J].農業經濟問題,2016(9):4-15.
[52]陸文榮,段瑤,盧漢龍.家庭農場:基于村莊內部的適度規模經營實踐[J].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3):95-104.
[53]農業部經管司、經管總站研究組.構建新型農業經營體系穩步推進適度規模經營—“中國農村經營體制機制改革創新問題”之一[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3(6):38-45+91.
[54]孔令成,鄭少鋒.家庭農場的經營效率及適度規模—基于松江模式的DEA模型分析[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5):107—118.
[55]韓蘇,陳永富.浙江省家庭農場經營的適度規模研究—以果蔬類家庭農場為例.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5(5):89-97.
[56]蔡瑞林,陳萬明.糧食生產型家庭農場的規模經營:江蘇例證[J].改革,2015(6):81-90.
[57]蘇昕,王可山,張淑敏.我國家庭農場發展及其規模探討—基于資源稟賦視角[J].農業經濟問題,2014(5):8-14.
[58]高鳴,習銀生,吳比.新型農業經營主體的經營績效與差異分析—基于農村固定觀察點的數據調查[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5):10-16+161.
[59]蔡鍵.我國家庭農場形成機制與運行效率考察[J].商業研究,2014(5):88-93
[60]錢忠好,李友藝.家庭農場的效率及其決定—基于上海松江943戶家庭農場2017年數據的實證研究[J].管理世界,2020(4):168-181+219.
[61]李紹亭,周霞,周玉璽.家庭農場經營效率及其差異分析—基于山東234個示范家庭農場的調查[J].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2019(6):191-1
[62]張德元,宮天辰.“家庭農場”與“合作社”耦合中的糧食生產技術效率[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8(4):64-74.
[63]吳方.基于SFA的家庭農場技術效率測度與影響因素分析[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48—56+163.
[64]蔡榮,汪紫鈺,杜志雄,示范家庭農場技術效率更高嗎?—基于全國家庭農場監測數據[J].中國農村經濟,2019(3):65-81.
[65]高雪萍,檀竹平.基于DEA—Tobit模型糧食主產區家庭農場經營效率及其影響因素分析[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5(6):577-587-584.
[66]孔令成,余家鳳.家庭農場適度規模測度及影響因素分析[J].江蘇農業科學,2018(16):301—305.
[67]高思涵,吳海濤.典型家庭農場組織化程度對生產效率的影響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21(3):88—99.
[68]何勁,祁春節.中外家庭農場經營績效評價比較與借鑒—基于湖北省武漢市家庭農場經營績效評價體系構建[J].世界農業,2017(11):34-39+178
[69]任重,薛興利.家庭農場發展效率綜合評價實證分析—基于山東省541個家庭農場數據[J].農業技術經濟,2018(3):56-65.
[70]張琛,黃博,孔祥智.家庭農場綜合發展水平評價與分析—以全國種植類家庭農場為例[J].江淮論壇,2017(3):54-60.
[71]關迪,陳楠.基于AHP—FCE的家庭農場經營績效綜合評價研究[J/OL].中國農業資源與區劃:1—12(2021—09—01).http://kns.cnknet/kems/detail//11.3513.S.20210901.1052.010.html
[72]郭廈,王丹.我國家庭農場發展質量評價與分析[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2(3):22—35
[73]張德元,李靜,蘇帥.家庭農場經營者個人特征和管理經驗對農場績效的影響[J].經濟縱橫,2016(4):77-81
[74]蘭勇,謝先雄,易朝輝,等.農場主經歷對農場發展影響的實證分析[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4):92-97.
[75]劉同山,孔祥智.加入合作社能夠提升家庭農場績效嗎?—基于全國1505個種植業家庭農場的計量分析[J].學習與探索,2019(12):98—106.
[76]來曉東,杜志雄,郜亮亮,加入合作社對糧食類家庭農場收入影響的實證分析—基于全國644家糧食類家庭農場面板數據[J].南京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143-154
[77]袁斌,譚濤,陳超.多元化經營與家庭農場生產績效—基于南京市的實證研究[J].農林經濟管理學報,2016(1):13-20.
[78]朱紅根,宋成校.家庭農場采納電商行為及其績效分析[J].華南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6):56—69.
[79]耿獻輝,薛洲,潘超,等.品牌資產對家庭農場經營績效的影響—基于江蘇省的實證研究[J].農業現代化研究,2020(3):435-442. [80]
[80]郭熙保,龔廣祥,新技術采用能夠提高家庭農場經營效率嗎?—基于新技術需求實現度視角[J].華中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1):33-42+175.
[81]陳德仙,胡浩.經營環境對家庭農場經營績效的影響研究—以長江三角洲3市為例[J].長江流域資源與環境,2021(4):1003-1015.
[82]曾福生,李星星,扶持政策對家庭農場經營績效的影響—基于SEM的實證研究[J].農業經濟問題,2016(12):15—22+110.
[83]劉同山,徐雪高.政府補貼對家庭農場經營績效的影響及其作用機理[J].改革,2019(9):128—137.
[84]鮑文,張恒,中國家庭農場發展的障礙及其路徑選擇[J].甘肅社會科學,2015(5):204—207.
[85]顧群.我國家庭農場的發展困境及破解對策[J].人民論壇,2016(11):83—85.
[86]陳明鶴.論新型農業生產經營主體:家庭農場[J].農村經濟,2013(12):42—45.
[87]陳永富,曾錚,王玲娜.家庭農場發展的影響因素分析—基于浙江省13個縣、區家庭農場發展現狀的調查[J].農業經濟,2014(1):3—6.
[88]王建華,楊晨晨,徐玲玲.家庭農場發展的外部驅動、現實困境與路徑選擇—基于蘇南363個家庭農場的現實考察[J].農村經濟,2016(3):21—26.
[89]湯文華,段艷豐,梁志民,促進我國家庭農場發展的對策研究[J].求實,2013([90]林雪梅.家庭農場經營的組織困境與制度消解[J].管理世界,2014(2):176-1
[91]楊建利,周茂同.我國發展家庭農場的障礙及對策[J].經濟縱橫,2014(2):49
[92]陳金蘭,王士海,胡繼連,家庭農場的傳承障礙及支持政策研究—基于山東省的微觀數據和案例分析[J].農業經濟問題,2021(4):121—131.
[93]劉文勇,張悅.家庭農場的學術論爭[J].改革,2014(1):103-108.
[94]周忠麗,夏英.國外“家庭農場”發展探析[J].廣東農業科學,2014(5):22-25.
[95]肖衛東,杜志雄,家庭農場發展的荷蘭樣本:經營特征與制度實踐[J].中國農村經濟,2015(2):83—96.
[96]朱學新.法國家庭農場的發展經驗及其對我國的啟示[J].農村經濟,2013(11):122—126.
[97]徐會蘋.德國家庭農場發展對中國發展家庭農場的啟示[J].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4):70—73.
[98]郎秀云.家庭農場:國際經驗與啟示—以法國、日本發展家庭農場為例[J].毛澤東鄧小平理論研究,2013(10):36-41+91
[99]何勁,YIRIDOEEK,祁春節.加拿大家庭農場制度環境建設經驗及啟示[J].經濟縱橫,2017(5):118—122.
Progress and the Prospect of Family Farm in China
GUO Xi-bao, WU Fang, ZHA K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Wuhan University,Wuhan 430072,China)
Abstract: The release of the No. 1 Central Document in 2013 promoted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and also set off a boom in family farm research, which has continued to this day.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has brought new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How to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n the new era has raised new topics for family farm research. There fore,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and summarize the existing literature on family farm research to provide inspiration and direction for further deepening and expanding family farm research.
By reviewing and sorting out 382 papers with the title of “family farm" included in CSSCI,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main research results of family farms from five aspects: the conceptual characteristics and status function, the reasons for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conditions, development mode and management mode, moderate management scale and management efficiency (performance),the constraints and coping strategies. Specifically,(1) family farm is the main body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between enterprises and ordinary farmers, which has bo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mily” and the attributes of “farm”; at present, family farms are the new force of new agricultural business entities and one of the main forces promoting agricultural moderniz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2) The imbalance between institutional supply and institutional demand gave birth to family farms; the emergence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rapid advancement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reform is a key factor in the formation mechanism of family farms;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requires corresponding land transfer and new professional farmers cultivation system,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system, market mechanism and government support, investment security and social security. (3) The basic national conditions of more people and less land determine that moderate scale management is the basic direction and main mode of 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there are huge differences in resource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level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the practice of family farms has also formed a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model and business model. (4) The seale of family farm operation should be “moderate”, and the standard of “moderation” has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for different region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family farms; although the operating performance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is obviously higher than that of ordinary farmers,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is generally not high, especially the overall low level of technical efficiency; the operating efficiency and performance of family farms are affected by factors such 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armers and their families, farm management methods and technical levels, ?operating environment and supporting social facilities, agricultural support policies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5)The development of family farms in China still faces many constraints, such as, the quality of farmers is not high, the management ability is lacking, the scale or mode of the farm operation is improper, the investment is insufficient, the technical level is not high, the land property rights and circulation system needs to be improved, financing is more difficult, the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 govermment support is not enough. Thus, reform and improvement should be carried out in terms of land transfer, farmland reform, agricultural socialization service system, farmer cultivation, financial support, and financial subsidies.
Chinese scholars have conducted extensive and in-depth research on family farms, and produced a large number of fruitful research results,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that need to be further deepened and expanded. For example, there are too many cross-sectional analyses, and long-term tracking analysis is insufficient; there are too many analys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nomics, but the multidisciplinary analysis is insufficient; there are too many domestic analyses, but the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analysis is insufficient. Key words: family farm; moderate scale; farmland system; a new type of professional farmers; agricultural socialized service system; a new type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entity
CLC number:F325 Document code: A Article ID:1674-8131(2022)03-0001-16
(編輯:黃依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