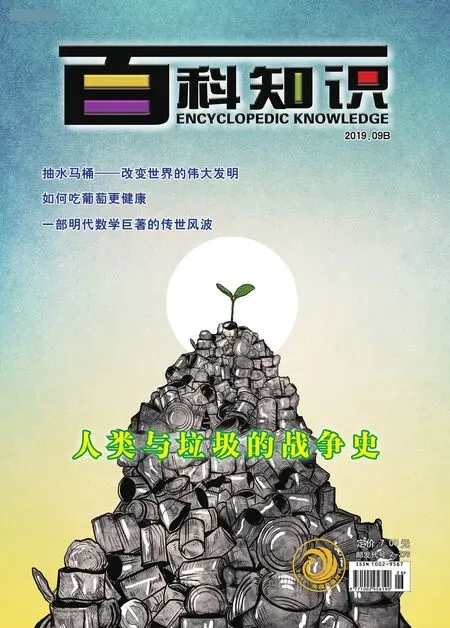太空太陽能發電站
沈羨云
據國際權威機構的統計,地球上的煤炭還能用200年左右,化石燃料(石油和天然氣)還能用五六十年。為此,人類需要抓緊時間尋找可持續、無污染、低成本的替代能源。現在,人們的目光已經開始聚集到太空,太空太陽能也許可以成為一種可被利用的新能源。
太空太陽能發電站的最初構想
早在1941年,科幻小說作家伊薩克·阿西莫夫就在他的短篇小說《理性》中寫到,空間站可以利用微波束從太陽收集能量傳輸到各個行星。1968年,美國航空航天工程師彼得·格拉塞在《科學》雜志上發表了《來自太陽的能量:它的未來》,文中提出了“太陽能發電衛星”的概念。格拉塞提出,先在太空建設一個太陽能發電站,將收集到的太陽輻射能轉變成電能后再轉變成電磁能,然后將電磁能通過無線傳輸裝置傳輸到地面的接收站,接收站將電磁能轉變回電能后,便可提供給供電網。在當時,格拉塞的想法可謂非常大膽,但他提出這一構想時,全球正面臨著石油危機,太空發電站的設想就顯得非常誘人。美國科學家在經過10年的論證后,終于在1979年提出了一個名為“1979SPS基準系統”的太空發電站方案,并計劃斥資2500億美元實現這個計劃。然而這個計劃中的太空發電站重達5萬噸,僅太陽能電池板的空間面積就超過了50平方千米,向地球運輸電力的微波發射天線的直徑甚至寬達1千米。別說當時美國的航天飛機還未正式投入使用,即使能夠使用,50噸載量的航天飛機也需要運送約1000次才能完成太空發電站組件的運送工作。于是這個項目不得不擱置。

20世紀末,太空發電站的構想再次被美國軍政當局提上了議事日程,并計劃于2050年前將自己的太空發電站部署在太空軌道上。在美國忙于研究的這20多年里,其他國家也對太空發電站的構想很感興趣,歐盟及俄羅斯、日本等國家都紛紛啟動了自己的太空發電站計劃。
太空太陽能發電站的優勢
首先,與地面太陽能發電站相比,太空太陽能發電站不受晝夜、天氣等自然因素影響,對太陽能的利用率更高,是充分利用太陽能的最佳選擇。相比于地面太陽能供電系統,太空太陽能發電站有更高的發電效率,這不僅是因為太陽能發電站在太空中能夠24小時持續工作,而且因為太空太陽能發電站的陽光不會受到地球大氣層的削弱和干擾,從而使每塊太陽能電池板都能發揮出數倍于地面同類的能效。
其次,太陽能屬于綠色清潔和可再生能源。如果太空太陽能發電站能夠成熟使用,便可以克服化石能源帶來的各種問題。
此外,太空太陽能發電站可實現超遠距離能量傳輸和調度。太空太陽能發電站利用無線能量傳輸技術,可以快速將能量聚焦傳輸到偏遠的環境,比如海洋、沙漠等缺乏電網設施的地區。不僅如此,還可以在飛機、衛星、深空探測器甚至在其他星球上搭載接收微波能量的天線設備,讓這些移動平臺在需要時方便地接收來自太空的微波能量,實現“充電自由”。
如何建立太空太陽能發電站
建立太空太陽能發電站,其實就是在地球赤道上空3萬多千米的地球靜止軌道上,建造一個太陽能電池矩陣,并通過無線輸電裝置進行傳輸。太空發電站相對地球靜止,這也為無線輸電裝置的使用創造了有利條件。就目前來看,太空發電站的理想位置有兩個,分別位于西經123°和東經57°附近,這兩個地方日照時間長,不受天氣、氣候影響,穩定性強,總的發電時間可以達到99%。


具體地講,太空太陽能發電站包括以下3個部分:能量收集平臺,能量轉換和傳輸過程,能量接收與利用終端。
能量收集平臺就是在太空中收集太陽能的航天器。從本質上看,太空太陽能發電站是一顆衛星,主要由太陽能電池板組成。太陽能電池板是通過吸收太陽光,將太陽輻射能通過光電效應或者光化學效應直接或間接轉換成電能。
能量轉換和傳輸過程存在諸多技術方案,討論最多的是用微波或激光的方式,將在太空中收集的太陽光能量轉換成電磁波,然后傳到地球表面。目前,高精度的激光傳輸技術已經被用于從衛星到地面的激光通信,但是激光在大氣層中的傳輸容易受到云層和降水的影響。利用微波傳送電力的手段相對更加成熟。微波是一種電磁輻射,在環境好的狀況下,通過微波將電能送回,其電能僅僅損失2%。
能量接收與利用終端一般可以認為是地面的接收裝置,當然也可以是飛機、衛星甚至月球上需要用電的其他終端。總體來看,地面的微波接收裝置(整流天線)周圍的安全是可控的:在地表可以建造圍欄等防止人員進入;在飛機上可以安裝保護性的金屬外殼(法拉第籠)來防止乘客受到微波光束照射;此外還需要控制微波束的功率,防止對鳥類等動物造成傷害。
建立太空太陽能發電站面臨哪些挑戰
既然太空太陽能發電站有這么多優點,為什么至今沒有建成呢?這是因為建成它要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主要表現在以下4個方面。
第一,建造成本高。從歷史上看,將這樣一個發電站送入軌道的成本是天文數字,使其目前在商業上還不可行。按照目前一塊1平方米的太陽能電池板重5千克計算,最終建成的太空太陽能發電站將重約2000噸。這里可以參考一下英國設想2040年落成的太空太陽能發電站方案,成本逾160億英鎊(約1300億元人民幣),其中有90億英鎊(約740億元人民幣)是發射成本。
第二,裝備容易受損和老化。太空環境非常復雜,環境輻射強烈,溫度變化劇烈,所以發電光伏板在太空中的老化速度遠遠超過在地球上的速度。另外,太空太陽能發電站需要非常龐大的體積,特別是展開的光伏板或者反射鏡面等,因此更容易受到空間碎片的碰撞。
第三,難以組裝、建設和維修。在地面維護和更換太陽能電池板是非常簡單的事,但是在太空中往往需要通過遙控機器人來實現太空太陽能發電站的組裝和維修。此前美國曾經多次通過航天員的太空行走,實現對哈勃空間望遠鏡(軌道高度在570千米左右)的維修,但是如果在地球同步軌道(約3.6萬千米)建設和維修太空太陽能發電站,其難度和風險都遠遠超出以往的太空維修任務。

第四,微波傳輸可能干擾通信波段。目前,典型的無線能量傳輸設計是利用在1GHz~10GHz頻率范圍內的微波,例如常用的2.45GHz(微波爐的常用頻率)或5.8GHz微波,因為該頻段是大氣微波傳輸的窗口,微波能量損耗最小。但是藍牙、無線網絡(WiFi)以及一些特殊的微波通信頻率也在這個范圍內,還有一些天文觀測可能也會針對這個頻段,這樣就可能產生頻譜干擾問題,需要通過管理來協調。
由于以上原因,目前太空太陽能發電站還處于探索階段,至于何時實現還是個未知數。
我國太空太陽能發電站計劃
2010年我國提出太空太陽能發電站“三小步”“兩大步”計劃。“三小步”即技術測試。首先開展地面及浮空器試驗驗證,然后開展高空超高壓發電輸電驗證,最后開展空間無限傳播能量試驗。從地面到太空,分三步解決輸電技術問題。“兩大步”則為建設太空發電站兩個階段:第一階段計劃到2030年前,在距離地面3.6萬千米的高軌道建設一個兆瓦級小型太空發電站,第二階段計劃到2050年前,建造兆瓦級空間太陽能電站驗證系統和吉瓦(GW)級商業空間太陽能電站。
2018年12月,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段寶巖院士團隊提出了歐米伽空間太陽能電站設計方案:首先以75米高的鋼結構支撐塔為底座,根據太陽高度角確定聚光鏡需要傾斜的角度,在接收到聚光鏡反射的太陽光后,位于聚光鏡中心的光伏電池陣,將其轉化為直流電能。隨后,通過電源管理模塊,4個聚光系統將轉換得到的電能匯聚到中間發射天線,經過振蕩器和放大器等模塊,電能被進一步轉化為微波,利用無線傳輸的形式發射到接收天線。最后,接收天線將微波整流再次轉換成直流電,供給負載。這一設計方案被命名為“逐日工程”。與美國的阿爾法設計方案相比,我國的“逐日工程”具備3個優勢:控制難度下降,散熱壓力減輕,功質比(天上系統的單位質量所產生的電)提高約24%。
2022年6月13日,段寶巖院士帶領的“逐日工程”研究團隊傳來好消息,世界首個全鏈路全系統的空間太陽能電站地面驗證系統順利通過專家組驗收。這一驗證系統突破并驗證了微波轉換、微波發射等多項關鍵技術。該成果對我國下一代微波功率無線傳輸技術、空間太陽能電站理論與技術的發展具有支撐性、引領性,應用前景十分廣闊。
此外,2021年6月,我國首個空間太陽能發電站實驗基地在重慶璧山正式開工建設,該基地將重點進行空間太陽能發電站、無線微波傳能以及空間信息網等技術的前期演示模擬與驗證等。建成后,“璧山電站”將會成為中國第一個集試驗、技術集成攻關、科學數據野外觀測及新產業培育為一體的大型綜合實驗基地,將對“改變傳統能源傳輸方式、破解能源供給難題”等產生重大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在所有太空發電站構想中,只有中國真正進入到了地面驗證階段,中國或將領先一步成為首個擁有太空發電站的國家。但太空發電站的運行依舊充滿挑戰:在滿是空間碎片的太空中,如何保護太陽能發電光伏板不受太空碎片的損害?脫離了大氣層的保護受到強烈太陽輻射影響,太陽能發電光伏板的退化速度加快,如何延長它的使用壽命?當然,還有大眾最關心的電價問題,畢竟成本高昂,太空發電站的電價會不會很貴?據推算,太空發電電價成本是一般電價的10倍,但隨著太空太陽能發電站的普及,價格會慢慢降至一般電價水平。太空太陽能發電站點亮未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