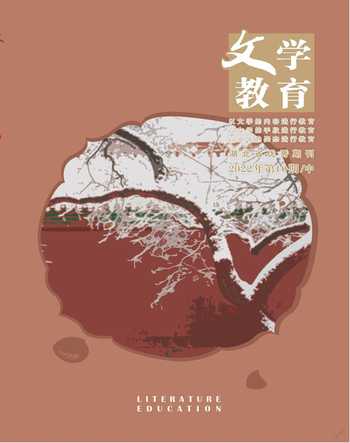苔絲和房思琪的女性悲劇追問
晏浩婷 彭石玉
內容摘要:本文基于文本細讀法,對《德伯家的苔絲》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兩部作品進行平行研究。二者都以男權社會為文化背景,揭露導致兩位女主人公苔絲和房思琪遭受誘奸悲劇的共同原因:男女雙重道德標準、女性羞恥感和社會性謀殺。本文通過解讀苔絲和房思琪的命運悲劇,探討兩部作品對現代兩性關系的現實意義和深刻啟發。
關鍵詞:《德伯家的苔絲》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比較文學 平行研究 女性悲劇
《德伯家的苔絲》(以下簡稱《苔絲》)和《房思琪的初戀樂園》(以下簡稱《房思琪》)是世界文學史長河中的兩部佳作。二者分別以英、中兩國不同時代的社會歷史風貌為背景,但筆者認為二者之間存在諸多相似之處:以女主角遭受性侵為主題,揭露父權社會遵循不平等的男女雙重道德標準;通過對女性施加羞恥感和社會性謀殺,女性在文化熏染中自覺內化不平等的性道德觀,進而將自己置于他者地位。由此可見,兩位作者筆下懸殊的兩性地位和失衡的兩性關系,不約而同為人類兩性社會敲響警鐘。
《苔絲》是英國19世紀現實主義小說家托馬斯·哈代的經典作品之一。哈代筆下的苔絲是“一個純潔的女人”,為了改變家庭貧困敗落的現狀,被迫與靠資本發家的德伯家認親,不幸遭到亞雷的奸污。而后遇到真愛克萊卻因有罪的過往慘遭拋棄,為生所迫再度委身于亞雷。最終因殺害亞雷被捕,結束短暫而悲劇的一生。
《房思琪》是中國臺灣作家林奕含的長篇小說,于2017年出版。小說講述了房思琪被國文老師李國華性侵多年直至精神崩潰的成長歷程。小說篇名包含了故事的三個要素:房思琪,故事的主人公——一個用文學為遭受性侵的少女們發聲的受害者,少女們指與思琪有相同遭遇的女孩——以餅干和郭曉奇為代表;初戀,即思琪在少女時期與李國華的被迫“戀愛”;樂園,指故事以“樂園——失樂園——復樂園”的時空順序展開。
苔絲和房思琪是兩位集美麗、純潔、善良、堅韌等優秀品質于一身的女性,跨越時空界限,卻雙雙遭受男權社會施加于女性生理和心理的雙重侵害,短暫的一生飽受壓迫和暴力,成為男權文化的犧牲品。本文基于文本細讀法和女性主義理論,從男女雙重道德標準、女性羞恥感和社會性暴力三個層面對《苔絲》和《房思琪》進行平行研究。
一.男女雙重道德標準
父權制度主張男性在社會中享有絕對權威,女性則處于社會邊緣且被視為男性的附屬品。維多利亞時代英國的性道德觀和婚姻觀均以男性為中心,具有典型的父權制特征。一方面,女性的絕對純潔是丈夫的特權,一旦失貞就淪為不道德的女人;另一方面,男性不僅沒有任何貞潔要求,還隨意對待兩性關系、肆意壓迫或侵犯女性,無需承擔后果。
誘奸苔絲的施暴者——亞雷,他從始至終只把苔絲當做滿足肉欲的玩物,隨意玩弄女性且不以為恥。亞雷的思想代表了同時代男性的普遍認知,即將女性視為屈從于男性金錢和社會地位的附屬品。勞倫斯(1979)認為:“阿歷克把苔絲視為滿足欲望的象征:一件屬于他的物品”。亞雷把苔絲誘人的美貌當做他犯錯的說辭,導致苔絲經歷失貞、懷孕、喪子的同時飽受非議,無疑是肉體創傷之上的精神折磨。而亞雷自己的名聲卻毫發無損,還成為了一個道岸偉然的傳教士。亞雷利用宗教指責苔絲的性誘惑,要求她發誓不再用美貌誘惑自己;隨后卻出于自己欲壑難填的性欲,用盡卑鄙手段把苔絲娶進門。除了來自宗教的精神壓迫,亞雷對苔絲的迫害也象征著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愈發加重男權社會對苔絲的控制。
安璣·克萊,一個戴著自由資產階級面具的知識分子,表面上反對舊道德,實際上腐朽的男女雙重道德觀已在其觀念中根深蒂固。聶珍釗(1982)認為,克萊的思想重幻想而輕現實,這種靈與肉的矛盾普遍反映了19世紀英國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時代變化中尋找出路的困境。克萊視苔絲為“大自然的女兒”即表示克萊崇尚理想化的愛情,本質上仍要求女性的絕對純潔。苔絲因愛而原諒克萊浪蕩的過往,克萊卻把苔絲被迫失貞的經歷視為不可原諒的罪過,狠心將其拋棄。
文學少女房思琪的故事發生在當代中國臺灣,社會對男女貞潔觀也呈雙重化標準,以男權為主導的倫理道德規范仍秉持傳統的男尊女卑思想。首先,男權文化要求女性絕對貞潔。出生于一個普通三口之家,思琪從小在家庭和鄰里家長們的教育下,以“仁慈善良、富有同理心,女孩子要有羞恥感”為目標長大。正如現代家庭中的性教育,家長們在孩子面前對性避而不談,自己卻在公共場合談性百無禁忌。吳奶奶教導思琪仁慈善良,自己卻對晚輩開“剩嘴也不是不行”的玩笑話,其他人還附和到“姜還是老的辣”。如此表里不一的性教育,試問如何真正讓女性成為仁慈善良的人?
房思琪、餅干和郭曉奇于李國華而言不過是泄欲的工具。李國華對同樣以誘奸學生為樂的“狼師”們說:“我喜歡與她們談戀愛……她們讓我的中年重煥生機,有了這樣的愛情才有了現在的我。”占有少女的貞潔,是他們獲得虛偽滿足感的勝利勛章。當李國華的秘密敗露,他和亞雷一樣把一切罪責推到女性身上,稱“是她在誘惑我,我沒能自控……”而他作為國文老師的正面形象讓受害者家屬、鄰里街坊以至于整個社會都將罪責一同指向女性的不自尊自愛。當餅干把自己被強暴的事告訴男友時,男友用三根煙的時間做出與她分手的決定,并用一句“我干嘛跟臟掉的餅干在一起”為理由棄之而去。自尊自愛的教育只能讓女性保持單方面的性純潔,卻無法讓男性樹立起對女性貞潔的尊重和保護,最終的結果只會是女性在兩性關系中周而復始地成為受害者。
二.女性羞恥感
當男權文化如同一種社會制度在人們的思想中根深蒂固,深陷其中的女性便潛移默化地將此思想內化,出現一種主動他者化的現象,為男性更加肆無忌憚地利用和侵犯女性提供便利。正如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言:“一個人之為女人,與其說是‘天生的不如說是‘形成的”。
當亞雷以宗教之名要求苔絲停止用美貌誘惑男人時,苔絲就開始潛意識地對自己的性別心生罪惡感,甚至認為克萊的離開是對她過去罪惡的懲罰。盡管苔絲認定與克萊的愛情是自由平等的,一旦步入婚姻她就將兩人視為主人與奴隸的關系,這是根深蒂固的傳統婚姻觀念指引苔絲將自己隸屬于男性。面對兩人同樣有罪的過去,苔絲對克萊的寬容一方面出于她真誠的愛,另一方面則是遵守男權文化的表現。而苔絲坦白過往后遭克萊拋棄,她將此視為一種對自己罪行的審判,原諒或是拋棄的結果全權由克萊決定,苔絲在本應以雙方意愿為主體的愛中主動關閉了自己的話語權。在資產階級傳統道德觀和法律的庇護下,克萊拋棄妻子的行為沒有受到任何譴責或懲罰,反而是無辜的受害者苔絲獨自承受失貞、不道德的罪名。在女性受到來自施暴者本身帶來的傷害時,原本就孤立無援的受害者還要承受來自社會的譴責與聲討(亓辰露,2019:81)。社會的指責是苔絲被迫再次回到亞雷身邊的催化劑,語言侮辱和暴力是苔絲悲劇真正的劊子手。
初次受到侵犯的房思琪想到的第一個辦法是“我不能只是喜歡老師,我要愛上他。你愛的人對你做什么都可以……我是從前的我的贗品。我要愛老師,否則我太痛苦了。”對于深受恥感教化的未成年少女來說,接受社會的界定,在默默隱忍中愛上施害者,無疑是社會壓力最小的選擇(王佳鵬,2020:125)。在羞恥心教育下,思琪被強暴后不愿接受同齡男生的追求,她視自己為“餿掉的柳丁汁和濃湯,爬滿蟲卵的玫瑰和百合,一個燈火流麗的都市里明明存在卻沒有人看得到也沒有人需要的北極星。”這是一種用美好事物的腐敗化象征自我的表達,揭露出思琪對男權觀念的服從,由此把被迫受害轉化為深深的自我否定和自我墮落,即女性通過內化男權文化將自身置于他者地位。由自覺內化產生的“羞恥感”進而為李國華對其利用提供了更大的便利。作者借全知敘述者之口向這種無恥行為發出控訴:“他發現社會對性的禁忌感太方便了,強暴一個女生,全世界都覺得是她自己的錯,連她都覺得是自己的錯。罪惡感又會把她趕回他身邊。”因此,羞恥感無疑是反復將思琪推向李國華魔爪的兇手,也是李國華不費吹灰之力長期掌控思琪的武器。
三.社會性謀殺
苔絲的悲劇是人與社會間矛盾的產物,她的悲劇命運是她所生活的那個社會的必然(譚曉援:2002:42)。如果男女雙重道德觀是人們的精神枷鎖,那么資本主義制度則是百姓生存的牢籠。19世紀是英國由農業文明向工業文明的轉型期,資本主義大機器生產迅速取代原始小農經濟,苔絲的家庭作為農民階級的典型代表,經歷了經濟破產、土地和生產資料被剝奪。貧窮將代際親情關系異化,父母帶著強烈的功利主義養育子女(張曉曉,2018:31)。在大變革時期,不作為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弟妹迫使苔絲外出工作,出賣勞動力獲得全家唯一的經濟來源。亞雷作為新興資本家代表,通過經濟手段控制苔絲,左右其命運,象征著資產階級的財富和權力對人們的剝削與壓迫。
工業革命浪潮極大沖擊了農村經濟,但封建思想仍深深植根于在人們心中,苔絲父母深受封建門第觀念毒害,破產后還妄想以認親榮登名門望族。他們把苔絲的美貌當做改變家庭命運的搖錢樹,卻絲毫不顧她的安危和人生。父母既是世俗偏見的推波助瀾者,也是悲劇的始作俑者。他們利用女兒勞動、認親和婚姻解決經濟困難,卻未曾給她建立自我保護的意識,致使她輕易受到男人的誘騙,一失足成千古恨。苔絲離開亞雷后,失貞如同“罪”一般刻印在她的身上,再也無法擺脫。對待身心遭受重創的女兒,他們同旁人一樣以她的失貞為恥,卻不曾停止壓迫她為家庭創造財富。她不但沒有得到來自家人的理解,還在威塞克斯村受盡辱罵和驅逐。由此可見,苔絲的悲劇源于整個社會的冷漠與殘酷。
倘若苔絲的悲劇是她所處社會的必然命運,同理,房思琪的悲劇也能定義為一個社會悲劇嗎?陷入絕境的思琪并非沒有嘗試向外界尋求幫助,而是多次求助無果后最終放棄。思琪向母親詢問性教育,母親回答“性教育是給那些需要性的人”,她“一時間明白了,在這個忽視中父母將永遠缺席,他們曠課了,卻自以為是還沒開學”。此外,她還不經意向母親提起女同學和老師在一起的事,母親卻回答“這么小年紀就這么騷?”從此,思琪關閉了求助的心門。郭曉奇父母得知女兒失貞的反應則是“你破壞別人的家庭,我們沒有你這種女兒”。他們與李國華夫婦見面,唯唯諾諾地不停向對方道歉,竟為一頓飯錢贊賞李國華大方慷慨。父母對性教育本身的誤解和對孩子性教育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是與侵犯未成年的不法犯罪站在了一起(寧微雅,2021:108)。兩個家庭不謀而合地忽視了女性在性侵中的被動地位,各種指責都顯現出“性別即原罪”和“受害者有罪”的普遍社會認知,而男性在其中的主動傷害性卻悄無聲息地消失了。
劉怡婷作為小說中唯一未受傷害的少女,是樂園的擁有者,也是思琪的靈魂好友。她得知思琪的遭遇后第一反應是:“你真的好惡心,我沒辦法跟你說話了”。在長期受男權文化統治的社會,人們幾乎無一例外地把矛頭指向女性本身的不潔。周遭環境不僅為暴力行為推波助瀾,更可能就是施暴者本身(陳蓮蓮,2019:54)。孫潔雨(2020)將其稱為“對性暴力受害者的污名化”。思琪最終發現:“直到現在,我才知道這整起事件很可能化為這一幕:他硬插進來,而我為此道歉。”社會的指責和非議,讓受害者也將自己定義為有罪方。而社會眾多看客和劉怡婷一樣,未知全貌就對受害女性施以語言暴力:“這么小年紀就當小三”“你拿了他多少錢?”“當補習老師真爽”“第三者去死!”親人、朋友乃至全社會對受害者的惡意都將“房思琪們”一步步推向絕望的深淵,不愿也無力掙扎。復樂園中“所有的人都笑了,所有的人都很快樂”,除了被傷得體無完膚的思琪,她永遠與快樂缺席了,這個社會原諒了施暴者,也忘記了受害者。
綜上所述,《苔絲》和《房思琪》都以男權社會為文化背景,男女雙重道德標準、女性羞恥感和社會性謀殺是導致苔絲和思琪悲劇的共同原因。這兩部作品跨越時空界限展示出獨具特色的藝術魅力,它們所揭示的主題都具有引人深省的力量,通過揭露男權社會對女性的種種壓迫,為人類兩性關系的現狀與未來敲響警鐘。
林奕含曾在一次訪談中說:“在書寫的時候我很確定,這件事不要說在臺灣,在全世界,現在,此刻,也正在發生。”因此,本文通過解剖苔絲和房思琪的命運悲劇,呼吁現代社會建立平等的兩性關系,喚醒女性自主意識和男性同理心的覺醒,為挽救和避免此類悲劇重現貢獻綿薄之力。
參考文獻
[1]陳蓮蓮.文學少女烏托邦的坍塌——淺評《房思琪的初戀樂園》里女性遭受的雙重暴力[J].北方文學,2019(02):52+54.
[2]D.H.勞倫斯.權威文本《德伯家的苔絲》中的男性和女性原則 哈代與小說批評[M].紐約,倫敦:諾頓公司出版社,1979.
[3]林奕含.房思琪的初戀樂園[M].臺北:游擊文化,2017.
[4]寧微雅.記憶還是忘卻:《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的創傷敘事解讀[J].美與時代(下),2021(02):107-110.
[5]聶珍釗.苔絲命運的典型性和社會性質[J].外國文學研究,1982(02):118- 122.
[6]亓辰露.女性的抗爭與社會的救贖——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所思[J].作家天地,2019(05):81-82.
[7]孫潔雨.“他者”的自述——從波伏瓦女性主義視角看小說《房思琪的初戀樂園》[J].參花(上),2018(12):66-68.
[8][英]托馬斯·哈代.德伯家的苔絲[M].王忠祥、聶珍釗譯,廣州:花城出版社,2015.
[9]譚曉援.社會、人性、人生——苔絲的悲劇剖析[J].成都教育學院學報,2002(11):41-44.
[10]王佳鵬.“羞恥心是不知羞恥的淵藪”——從《房思琪的初戀樂園》看性侵和家暴的文化心理根源[J].天府新論,2020(05):121-129.
[11]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M].鄭克魯,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11.
[12]張曉曉.論哈代“性格與環境小說”中的家庭倫理[D].山東師范大學,2018.
(作者單位:武漢工程大學外語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