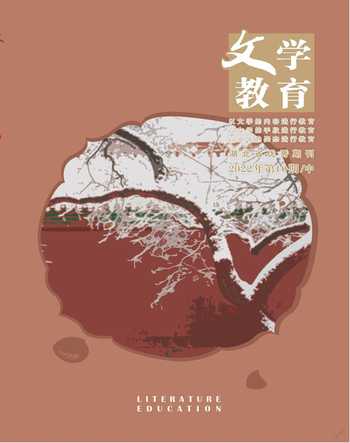論楚劇《葛麻》的楚風楚韻
談太輝
內容摘要:楚劇《葛麻》具有人物的智慧性、語言的趣味性、文化的地域性和思想的平民性,正是這些特色,促使《葛麻》成為享譽全國的典范之作。
關鍵詞:《葛麻》 楚劇 特色 地域
《葛麻》是傳統楚劇中的典范之作。這個劇目是根據傳統戲《打葛麻》改編的。該劇于1952年獲得全國首屆戲曲觀摩會的劇本獎和二等表演獎,1956年由上海天馬制片廠拍攝成藝術影片而享譽全國,劇本收入《戲曲選》第5卷。該劇還于1976年第二次被拍攝為舞臺戲曲藝術電影。一時間,能站著睡覺的葛麻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在戲曲界有很大的反響,其他地方戲曲也紛紛加以改編上演,一時形成了影響極大的“葛麻風”(或稱“葛麻現象”),成為影響楚劇風格50年之久的重要劇目。只要提到楚劇便會想到《葛麻》,就像提到黃梅戲便會想到《天仙配》,提到越劇便會想到《梁祝》一樣。晉劇、祁劇、贛劇、桂劇、廬劇、皖南花鼓戲、黃梅采茶戲、鄖陽花鼓戲皆有此劇目。
葛麻是個正直、機靈、有膽識的青年。他在地主馬鐸家做工,馬鐸在未發跡前,曾把女兒許配給窮書生張大洪。后來馬鐸發了橫財,就嫌張家窮,企圖退掉這門親事,將女兒另配高門。一天,馬鐸叫葛麻將張大洪找來,想當場逼張大洪寫下退婚字據。張大洪是葛麻的表弟,為人忠厚老實,看到馬鐸這樣嫌貧愛富,要他退婚,一時沒了主意。葛麻決心幫助表弟。他為張大洪想辦法,設下圈套,準備狠狠地教訓馬鐸。張大洪到了馬家,葛麻在一旁見機行事,葛麻十分機靈地使馬鐸送張大洪一件最漂亮的衣服和二十兩銀子,還假裝幫馬鐸打張大洪,而拳頭卻落在馬鐸身上。葛麻憑著他的機警、聰明和口齒伶俐,使馬鐸無法逼張大洪寫退婚字據。隨后,葛麻又到后花園,巧妙地探出馬小姐的心事。馬小姐深愛張大洪,憎恨父親嫌貧愛富的行為。在葛麻的幫助下,馬小姐逃出家門,與張大洪結成夫妻。
楚劇《葛麻》的成功之處,在于其人物的智慧性、語言的趣味性、文化的地域性和思想的平民性。
一.人物的智慧性
一部優秀的戲劇作品,無論是主題的高度提煉、結構的精心安排,還是情節的巧妙設置、場面的合理布局,都離不開人物形象的個性化塑造。只有把人物塑造好了,主題才能突出,劇情才能集中,矛盾才能尖銳,高潮才能迭起,吸引觀眾的強烈的戲劇效果才能得以充分顯現。
從這個角度言,葛麻雖是個小人物,卻因其鮮明的個性特征區別于其他人,具有獨立的魅力。他的個性正在于其智慧。以其機智詼諧妙趣橫生,并且古道熱腸助人為樂,打抱不平懲惡揚善,深得廣大觀眾的喜愛。
仔細分析作品后,我們不難發現,葛麻身上表現出來的智慧是超乎尋常的。他在整個故事中出的點子充滿了創意,言行舉止間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定位、人心理活動的把握、事情趨勢的判定都是極其精準。
當葛麻聽馬鐸說出逼寫退婚文書的打算時,立即毛遂自薦去尋找張大洪,從而取得掌控事態發展的主動權。張大洪是一介書生,文弱迂酸,人窮志短,一聽說馬鐸要他寫下退婚文書,頓時方寸大亂、六神無主。葛麻見狀,幫他謀劃出一個擺布馬鐸的妙計,不但告訴張大洪如何應對馬鐸的問話,還模擬演練了一出戲中戲,這才放心帶他來到馬府。
在葛麻設計的應答對話中,最能體現了葛麻的見多識廣和聰明機智的特征。當張大洪問他如何回答馬鐸“你寫是不寫?”的問話時,葛麻告訴他:“你說‘小婿告辭了。他問你‘哪道而去?你就說‘我去到大市長街,化幾文銅錢,買一陌紙錢,去到爹娘墳前,燒得一燒,叫得一叫,再把棺木撬開,爹娘答應兒寫兒就寫,不答應兒就寫他不成!這樣該推得干凈吧”葛麻又推測說:“他一定會問你‘哪有人死又復生?”張大洪又問“那我怎么說?”葛麻告訴他:“嗯,你就說‘哪有定親又退親?”葛麻還告訴他,馬鐸要是問他“哪個與你有親?”“既然有親,何人的媒證呢?”“既有媒證,何曾見你三茶六禮?”這三個問題時,就別的話不說,只回答三個“這個——”。葛麻不僅能根據馬鐸的個性揣測出他要問的問題,還針對這些問題設計出如此絕妙的回答,足見葛麻的才思之聰明和人情世故之老練。
張大洪與馬鐸吵翻,跑出馬府,葛麻又借機追趕出去,聽張大洪說:“我與她從前是青梅竹馬,兩小無猜。如今怎樣舍得?”葛麻又給他定下對策,說:“依我之見,你在馬房等候,我到繡樓去會一會小姑娘,探聽她的口氣如何,她若念前情,就會贈銀子與你,那我就來跟你想法子迎親。要是她與她老子一條心,那時再退也不遲!”在此對白中,張大洪的文弱無能與葛麻的足智多謀再次形成對比,葛麻的個性形象也得到了突出的展示。
在與馬鐸的周旋過程中,葛麻見多識廣、聰明機智的個性特征同樣使他處在有利的位置并掌控了事態發展的主動權。利用馬鐸嫌貧愛富、好面子的特點,不但幫張大洪“借”到了二十兩銀子,還順帶要了一件新衣裳。張大洪跑出馬府,馬鐸要去追、去告張大洪,葛麻也及時阻止了他,同樣顯示出他的見多識廣和聰明機智,還借機嘲諷了馬鐸的愚蠢無知,取得了很好的諷刺效果。
葛麻阻止馬鐸去追的理由是:“張大洪在前面跑,你在后面趕,少不得他張家還有幾個人,再加上你的那些種田借錢住房子的一些窮人,攔住張大洪就問為么事,他就說你們從前兩家貧窮開親,如今他家發富,把我誑進府去,逼寫退婚文書,有錢的該生,無錢的就該死。話沒有說完,你就趕得去了,人家心里本來就有些不服,加上平日吃你的虧又吃得多,哪里能找到一個機會出氣呀,說的說,推的推,扎的扎袖子,扯的扯鞋子,塞的塞你的冷砣子(趁混亂之際打你)。”葛麻不但阻止了馬鐸去追張大洪,還借機痛打他了一拳,但是又聲明說:“我這是做得你看的,你去不得的。”馬鐸追不成,又想要去告張大洪,葛麻又找了個理由阻止了他。葛麻說:“你與張大相公打官司,張大相公見了老爺站倒(著,語語氣詞),你見了老爺就要跪倒。”馬鐸表示不解,說:“他們窮鬼站倒,我是有錢的員外,還要跪倒?”于是葛麻又趁機挖苦他說:“我說你又不懂!”“他是黌門秀才,他有功名當然站倒。你沒有功名,頭上一摸是個大光頭。”馬鐸又后悔說:“曉得這樣,從前拿幾個錢捐個功名。”葛麻再次嘲笑他說:“捐個功名?教你讀書,你要逃學哩。”
同樣,在與馬小姐的對活中,葛麻借談論《賣水記》的戲情時,講出了馬鐸打算將她“另行擇配”的事,馬小姐也是急得不知所措,請葛麻想辦法化解。葛麻趁機又幫她出主意:“讓張大洪打轎子接人,立馬成親。”從而成功化解了一場危機,促成了馬金蓮與張大洪的婚事。
由此可以看出,無論是在與土老財馬員外的周旋過程中,還是在與張大洪的謀劃計議之時,抑或是在試探馬府小姐金蓮的情感態度和立場之時,葛麻不但生性詼諧、言語風趣,而且見多識廣、聰明機智這一喜劇性格,在全劇中自始至終都發揮得淋漓盡致,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二.語言的趣味性
本劇是楚劇丑角代表劇目之一,以念白和做功為主。劇中的對話短兵相接,節奏明快,生活氣息濃厚,使人物性格更加鮮明、生動。
作為表現丑角行當的藝術表現方式,最常見的自然是插科打諢了。“科諢”是中國古典喜劇的構成要素之一,歷來為劇作家和戲劇理論家所重視。李漁在《閑情偶寄·詞采第二·重機趣》中道:“‘機趣二字,填詞家必不可少。‘機者,傳奇之精神;‘趣者,傳奇之風致。少此二物,則如泥人土馬,有生形而無生氣。”《閑情偶寄·編劇論》亦有:“插科打諢,填詞之末技也。然欲雅俗同歡,智愚共賞,則當全在此處留神。文字佳、情節佳而科諢不佳,非特俗人怕看,即雅人韻士,亦有瞌睡之時。”許渭森在《綴白裘十一集序》講道:“有時以鄙俚之俗情,入當場之科白,一上氍毹,即堪捧腹。此殆如東坡相對正襟捉肘,正爾昏昏欲睡,忽得一次諧汕笑之人,為我持羯鼓解酲,其快當何如哉?”王驥德《曲律》亦說:“插科扣‘諢,須作得極巧,又下得極好,如說笑話者,不動聲色,而令人絕倒方妙。大略曲冷不鬧場處,得凈、丑間插一科,可博人哄堂,亦是戲劇眼目。”
葛麻就是這樣一個“詼諧訕笑之人”,最擅長捕捉時機、在不動聲色的插科打諢之中給人帶來令人絕倒的喜劇藝術效果。《葛麻》中的科諢,通常采用的藝術手段有借題發揮、明知故問、諧音與接話頭以及用借用俗語、諺語等。
葛麻剛出場的時候,就借問候馬鐸之機發揮開來,諷刺員外馬鐸為人慳吝刻薄。葛麻說:“見了員外丟揖(見禮)。”他還解釋說:“見了旁人一禮要還我一禮,見了員外昂昂不動,豈不丟了一個揖?”
再如明知故問藝術。馬鐸讓葛麻去找張大洪,葛麻跟張大洪本是表兄弟,卻故意問道:“員外叫我找張大洪,到哪里去找呢?”馬鐸告訴他:“到他家里去找。”葛麻又說:“哪個人不出外呢?”馬鐸就說:“你到黌學去找。”葛麻就反問說:“他那窮,哪有錢讀書呢?”馬鐸又不耐煩地說:“到大街去找。”葛麻仍是故意激他,說:“他差(欠)人家的錢,還敢上街?”葛麻之所以明知故問,目的有二:一是替張大洪的“窮”作了辯護,意在張大洪并沒有窮到落魄的地步,你馬鐸不應該起這樣“嫌貧愛富”的心思;二是對馬鐸“嫌貧愛富”的不滿,通過此番明知故問來逗馬鐸生氣、拿他開心。
三.文化的地域性
楚劇是湖北省有代表性的劇種之一。它發源于農村,發展在城市,農民和城市平民百姓是它的忠實觀眾。受民風、民俗的長期熏陶,楚劇形成了既有黃陂孝感鄉下味,又有漢口都市風的獨特藝術風格。俗話說:無陂不成鎮。由此推斷,漢口成為四大名鎮之一與黃陂人下漢口謀生、創業有關。家鄉人愛聽家鄉戲,楚劇能在漢口立足,一晃就是上百年,也就不奇怪了。從這個意義上講,楚劇是都市里的鄉土戲。
楚劇演的是湖北佬,唱的是漢水情,舉手投足間散發著濃郁的漢味風情,彰顯著鮮明的地方特色。楚劇還是通俗的戲劇。生長于民間,活躍于山鄉的楚劇,由于它的觀眾大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勞動人民,從而決定了它尤以通俗見長。半個世紀以來,楚劇吸吮鄉土文化的乳汁、市民文化的營養,不僅從大量演義、戲說、說唱之類的文本中搜尋改編,而且從現實生活中提煉創作了一大批通俗化大眾化久演不衰、至今保持魅力的劇目。《葛麻》正是代表之一。
劇種的地域性,也就意味著《葛麻》一劇充溢著濃厚的楚風楚韻文化。這表現在該劇大量運用了民間俗諺、歇后語與地方方言。
比如葛麻占了馬鐸的便宜,還要說:“上說下應,越說越有勁。”這句話就是一句俗語。葛麻表示自己有能力找到張大洪時,就借用了一句歇后語:“好比藥鋪的甘草一抓就來了。”此外,還有一句“你真是三十斤的鳊魚,把我側看了。”靈活運用方言,這是地方戲的共同特色。
盡管歷來都有反對方言入曲的學者專家,但是,各時代的戲曲里,大量地雜入了方言、俗語卻是顛撲不破的事實。葛麻向馬鐸要茶盅,就利用方言“茶盅”與“雜種”音近的特點,借機罵他說:“員外,雜種!”一句“窮要窮得干凈,富要富得寧凈(干凈)”的方言俗語,看起來是在批評張大洪,實際上是諷刺、批評馬員外為富不仁、財路來得不正。此外,在與馬金蓮的聊天取樂中,“打鬧臺”“毛痞”“搭架子”等方言詞匯的運用,也給該劇增添了濃郁的地方風情。
四.思想的平民性
楚劇《葛麻》是以劇中葛麻這個丑角行當為主角的喜劇。該劇的主人公葛麻是一個小人物,是勞動人民的縮影。他代表著千千萬萬的勞苦大眾,因而其一言一行更易引起共鳴。
所謂“小人物”,是指與傳統詩文中經常出現的士大夫形象不同的普通人物。中晚唐文學中出現了許多“小人物”形象,作者將其作為正面人物加以刻畫,體現出一種新的文學趣味。后來的戲劇和小說等通俗文學,深受中晚唐傳奇的影響,大量書寫小人物的故事。楚劇《葛麻》也是一脈相承,繼承了這一傳統。
《葛麻》作者禮贊小人物的品行與智慧,在創作思想上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和平民性。
思想的平民性也是由楚劇的地域性決定。楚劇是地方劇,平民的戲劇,也是生活的戲劇。楚劇藝術來自民間,其傳統劇目,多是反映平民生活中的人和事,反映平民百姓的審美視角和情趣,表現平民百姓的喜怒哀樂,尤以表現平民百姓如泣如訴的悲怨和幽默風趣見長。而且因為楚劇孕育于農村、成長于城市,是鄉土文化和市民文化相結合的產物,所以其觀念形態充滿著超前的民主意識。
立意是劇本的靈魂。一部優秀劇作的立意,是藝術家對現實生活觀察、體驗、感受的結晶。只有對社會生活的熱點、社會生活的心理情結有深層把握,作品才能撥動觀眾心弦。
《葛麻》立意出發點為:為人正直、好打抱不平的雇工葛麻,幫助窮酸書生張大洪同“嫌貧愛富”“慳吝刻薄待窮人”的暴發戶馬鐸周旋、斗智。
“能喚起當代人共鳴與思考的立意是劇本成功的前提。”楚劇《葛麻》之所以受到當代觀眾的歡迎,在于它積極用當代意識(批判嫌貧愛富行為)觀照藝術創作,使當代觀眾產生情感共鳴。
魯迅先生說:“俗文之興,當由二端,一為娛心,一為勸善,而尤以勸善為大宗。”楚劇《葛麻》正體現了這樣的通俗藝術的審美追求。
《葛麻》通過對民俗與地緣感情的提練,虛實兼顧地以“平民風格”表現民眾耳熟能詳的“小人物形象”,使楚劇此后生產出“葛麻”風格系列的藝術精品,呈放射狀地進行著傳播。
(作者單位:湖北工程學院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