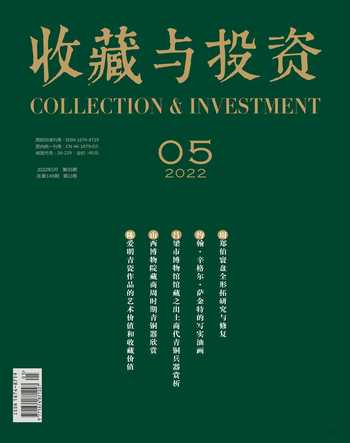東陽市博物館館藏人首魚身俑賞鑒及發展分析
摘要:陶俑是古代墓葬雕塑藝術品的一種,飽含古人對陰間和后代生活的美好期許。對出土的神煞明器進行研究有利于我們更好地了解古代人的現實生活、精神追求和風俗文化。本文以東陽市博物館館藏人首魚身俑為引,淺析人首魚身俑這種隨葬明器的發展演變及其在變化中反映的文化風俗演變。
關鍵詞:陶俑;人首魚身俑;唐宋時期
俑負載了古代社會的各種信息,對研究古代的輿服制度、生活方式乃至中外文化交流融合都有重要的意義,同時也為現代梳理古代雕塑藝術發展的脈絡以及朝代變遷中風俗文化的發展軌跡提供幫助,成為了解和研究中國古代雕塑藝術和風俗文化不可或缺的珍貴實物史料。現以東陽市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外形完整、文化內涵豐富的人首魚身俑為例,展開論述。
一、藏品基本信息
東陽市博物館這件人首魚身俑,制作時間為兩宋時期,外在表現為人首與魚身結合為一體的陶俑,尺寸為6厘米長、2厘米高,形象頗為奇特。頭部形象為人首,面孔表現為男性,光頭,慈眉善目,昂首向上;身作魚形,魚鱗呈現月牙狀,好似眉月,鱗次櫛比;尾部魚鰭紋路線條如真,動狀表現,似在搖擺游動。陶俑整體呈現“C”型,神態動靜結合,似一種超自然神獸在水中慢慢游動嬉戲(圖一、圖二)。
二、藏品淺析
對于人首魚身俑的命名,學界一般認為是儀魚,這一說法出自考古學家徐蘋芳先生1963年發表的《唐宋墓葬中的“明器神煞”與“墓儀”制度—讀<大漢原陵秘藏經>札記》,他認為唐宋墓中出現的人首魚身俑就是《大漢原陵秘藏經》中的“儀魚”。

從現有考古資料來看,儀魚最早出現于隋唐時期的北方區域,主要流行于山西、陜西等地,多出現于中下層的墓葬中,南方則極少出現。1961年4月,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晉東南文物工作組在長治市東郊清理兩座唐墓時出土了一件儀魚①。1986年10月,長治市博物館在西郊瓦窯溝發掘一座唐墓,出土了一件儀魚②。至晚唐五代時期,儀魚在北方墓葬神煞明器中逐漸消失,傳播至南方,在江蘇和福建等東南地區比較流行,并開始出現于高等級墓葬中。如1950年,南京郊外祖堂山發現了南唐第一位皇帝和皇后的合葬墓—李昇陵,出土了一件非常精美的人首魚
身俑(圖三),現藏于南京博物院。后在南唐李璟陵中出土了一件外形不同的人首魚身俑(圖四),現藏于南京博物院。至宋代,只有江西、四川和湖北等地零星發現人首魚身俑,隨時間推移,后來發掘的墓葬中再也見不到儀魚了,推測它可能退出喪葬明器之列了。
就考古發掘來看,出土的儀魚不算多。2013年崔世平所作《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總結全國只有三十多所墓葬中出土過儀魚,共計四十余件。按外在表現的差異,儀魚大致分為三類:(1)人首與魚身呈直線形,如南唐李昇、李璟二陵出土的儀魚;(2)人首與魚身呈字母擺動形,如崔世平在《唐宋墓葬所見“儀魚”與葬俗傳播》中所述遼寧朝陽黃河路唐墓出土的“S”形儀魚(圖五),以及東陽市博物館收藏的“C”形儀魚;(3)兩人首魚身連體形,如現藏于安陽博物館的唐代人面連體魚身俑(圖六)。
對于儀魚在喪葬明器的精神內涵,大致有三種認知:(1)一種祈福方式,寓意逝者子孫后代繁衍不息,多子多福;(2)作為一種鎮墓獸,鎮邪祛惡,保佑墓主人;(3)是一種指引升天、登臨極樂的寓意,希望逝者能夠在儀魚的幫助下到達遙遠的仙界,羽化成仙,這是后人對先人的一種美好祝愿。
儀魚作為隨葬明器出現于唐宋時期,其蘊含著古人特殊的精神寄托,然而這種形制的隨葬明器如曇花一現,在歷史長河中存在時間較短,同時,它的外在表現,尤其是人首形象發生了很大轉變,是什么外在因素促成或推動儀魚的變化還有待考察。
首先,筆者就儀魚曇花一現,宋以后逐漸退出喪葬禮制之列的情況,分析其影響因素主要有以下幾點:
(一)宋代薄葬之風盛行
宋代竭力提倡薄葬,朝廷明確制定了喪葬令,規定不可將金銀財寶放入棺木墓室內。如宋仁宗天圣年間曾頒布《天圣令》,其中的《喪葬令》對各級官員的墓田面積、墳塋高度、墓葬規格、棺槨材質、石獸數量、陪葬品等都進行了詳細規定,如《喪葬令》第二十一條規定:“品官諸葬不得以石為棺槨及石室,其棺槨不得雕鏤彩畫、施方牖檻,棺內不得藏金寶珠玉。”宋高宗紹興二年(1132年),針對兩廣地區“婚姻喪葬,習為華侈,夸競相勝,有害風俗”的厚葬現象,朝廷專門下令“委帥守、監司常切覺察,如違,重置典憲”。通過三令五申,強化制度執行,唐朝的厚葬之風逐漸淡去,薄葬習俗逐漸成為宋朝社會的主流。同時,士大夫自覺自發,通過遺訓或著書立說,倡導薄葬之風。如翰林學士宋祁告誡其子:吾逝后三日殮,三月葬,不受陰陽流俗擺布,棺材僅用雜木,不可放置任何金銀財物。更有南宋理學家李衡在遺訓中稱棺木以小為貴,僅能周身足以,其余連衣裳帽子都一概不用,只消一張草席墊背。
從考古發掘來看,四川地區宋墓中很少有金屬器物,幾乎全是陶制明器,瓷器偶有發現。雖然也常有銅錢或鐵器殉葬,但一般不過數枚③。河南陜西一帶發現的許多宋墓,隨葬物品也不多,只有一方墓志或買地券,幾十枚銅錢,一兩只瓷碗或陶罐而已④。江浙一帶的宋墓往往隨葬陶罐、瓷碗、銅錢等,數量不多,另加一塊墓志。如上海市嘉定區北宋夫婦墓僅出土四系陶罐一只、陶壇一只、陶瓶兩只、銅錢三百余枚、墓志一方⑤。
(二)紙錢和紙質明器的流行

傳統的實物明器由唐代的登峰造極至宋代日趨衰落,與此同時,紙錢和紙質明器大為盛行,在宋代的喪葬活動中得到廣泛使用。人們通過焚化紙錢和紙質明器,以慰先人之靈或以禱神。話本《快嘴李翠蓮記》中有“沙板棺材羅木底,公婆與我燒錢紙”。北宋初年,福州的“東岳行宮,偽閩所建東華宮之太山廟也”[見淳化四年(993年),節度掌書記、承直郎、試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裴詢所作《福州東華宮太山廟記》,首云:“四時代謝,東方立生殺之權;五岳辨方,太山掌生死之籍。”蓋本宮中之廟也。]錢氏時,廟祀始盛,《記》云:“王氏既滅,斯師治民。斯廟也,玉宇恢廓,金殿崢嶸。乞福人多,紙錢飛雪;祭神客眾,竹葉成池。”⑦再者,同時期長安民間遇喪葬時,陳列偶像,其中外表用綾絹金銀做成的偶像稱“大脫空”,外表用紙并著色的偶像稱“小脫空”。長安城里有許多專門生產和經銷“脫空”的店鋪,組成“茅行”。“長安人物繁,習俗侈,喪葬陳拽寓像,其表以綾綃金銀者,曰‘大脫空,褚外而設色者,曰‘小脫空,制造列肆茅行,俗謂之‘茅行家事。”⑦
由此可見,宋代薄葬之風和紙質明器的流行改變了自秦以來的厚葬習俗,對實物明器隨葬產生了很大的沖擊,是推動儀魚這種隨葬明器逐漸消失的重要影響因素。
(三)儀魚外觀表現的變化
唐代儀魚人首表面幾乎都是有裝飾的,南唐李昇時期,魚人首確立為道士形象,頭戴道冠,形似純陽巾,面容清秀;到南唐李璟時期,人首形象發生變化,頭部無任何毛發存在的痕跡,是為僧侶形象,慈眉善目。東陽市博物館收藏的這件儀魚也如李璟陵的儀魚一樣,在人首表現上一致。儀魚這種形制的變化很可能與唐宋時期的宗教格局和宗教信仰存在關聯性。
唐代皇室尊崇道教以神化自己,鞏固皇權;高祖李淵以老子為祖先,太宗、高宗也肯定了道教的優先地位,高宗還尊稱老子為“太上玄元皇帝”。南唐李昇在位時,自命繼承李唐正統,為表現自身順應天命,竭力將皇室與道教聯系在一起。當時,南唐大盛崇道之風。道士大受寵信,得以出入宮廷,同時李昇對待佛教采取包容的態度,使其為政權服務。到李璟時期,金陵佛教空前繁榮,李璟喜與高僧往來,廣建佛寺,至后主李煜即位后大肆奉佛,其虔誠比李璟尤勝。《南唐書》中記載“南唐有國,蘭若精舍,漸盛于烈祖、元宗之世,而后主即位,好之彌篤,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由此可見,從唐到五代十國時期,釋、道盛行。在南唐李昇、李璟時期,宗教格局和宗教信仰由崇道轉變為崇佛,這或許就是儀魚人首形象發生變化的外在影響因素。
三、總結
儀魚作為一種特殊的喪葬明器,是研究我國古代民俗風情的重要資料,是古人留給我們的寶貴歷史文化遺產,其濃郁的民俗氣息、豐富的文化內涵以及美好的生活寓意,透過悠悠的歷史長河向我們表達古人對死亡的一種態度,承載著先人們無窮的智慧和美好的愿望,同時向我們展示了古時民俗民風和精神文化的轉變,以及外在社會因素、政治因素以及宗教信仰的變化對喪葬習俗變遷的影響,讓我們更好地通過實物史料了解和認知古代社會和宗教民俗的發展。
作者簡介
陸勇,1987年3月生,男,安徽合肥人,東陽市博物館助理館員,本科,研究方向為文物研究。
注釋
①沈振中:《山西長治北石槽唐墓》,《考古》,1962年第2期。
②侯艮枝,朱曉芳:《山西長治市唐代馮廓墓》,《文物》,1989年第6期。
③王家佑:《四川宋墓札記》,《考古》,1959年第8期。
④何鳳桐:《洛陽澗河兩岸宋墓清理記》,《考古》,1959年第9期。
⑤王正書:《上海嘉定宋趙鑄夫婦墓》,《文物》,1982年第6期。
⑥(宋)梁克家:《淳熙三山志》卷8,《公廨類二·祠廟》。
⑦陶榖:《清異錄》卷下,《第九事喪葬門·大小脫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