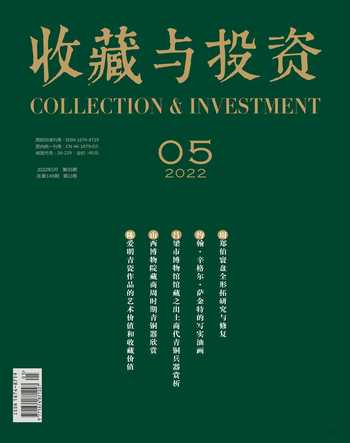西夏陶瓷扁壺設(shè)計(jì)的實(shí)用性和審美性芻議
秦文濤 侯昀

摘要:在人類文明發(fā)展進(jìn)程中,陶瓷是一種比較特殊的文化形態(tài),具有物質(zhì)和文化雙重屬性。自古以來(lái),陶瓷就具有實(shí)用功能和審美功能,它在人類的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雙重領(lǐng)域都充當(dāng)著重要的角色。西夏陶瓷扁壺反映了西夏黨項(xiàng)族人文明進(jìn)步的程度和生活面貌。本文簡(jiǎn)要介紹了西夏瓷器中扁壺的類型,分析了它的實(shí)用性設(shè)計(jì)及審美意味。此外,還對(duì)西夏陶瓷扁壺對(duì)現(xiàn)代藝術(shù)的啟發(fā)進(jìn)行了探討。
關(guān)鍵詞:西夏陶瓷;黨項(xiàng)族;實(shí)用性;審美性
西夏是中國(guó)歷史上由黨項(xiàng)人于1038—1227年間在中國(guó)西部建立的一個(gè)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黨項(xiàng)一族本是古老民族羌族的一個(gè)部落分支,早期居住于青藏高原東北部,后因?yàn)橥罗瑒?shì)力入侵而北遷到今甘肅東部、寧夏地區(qū)和陜西西北一帶,隨后勢(shì)力逐步增大,到宋仁宗寶元元年(1038年),李繼遷其孫李元昊正式稱帝建國(guó),國(guó)號(hào)大夏,史稱西夏。西夏疆域,東據(jù)黃河,西至玉門關(guān),南臨蕭關(guān)(今寧夏同心縣南),北控大漠。這一時(shí)期,黨項(xiàng)族建立的西夏政權(quán)與宋并存,在各民族的長(zhǎng)期對(duì)峙下,游牧文明與農(nóng)耕文明不斷交流和轉(zhuǎn)變。最后,蒙古大軍橫掃全境,結(jié)束了西夏近200年的統(tǒng)治。在這場(chǎng)王權(quán)變更的殘酷戰(zhàn)爭(zhēng)中,西夏的建筑物損毀殆盡,西夏的文獻(xiàn)典籍也遭到嚴(yán)重破壞,從此西夏文明湮沒(méi)于歷史長(zhǎng)河中,鮮為人知。直到俄羅斯海軍挖盜的西夏文物公布于世,西夏王朝神秘的面紗才逐漸被揭開(kāi),而西夏陶瓷扁壺作為西夏游牧民族的生活用具,對(duì)黨項(xiàng)人生活方式的研究、精神面貌的探尋以及西夏王朝殘缺歷史的填補(bǔ)都具有彌足珍貴的作用。
一、西夏陶瓷扁壺的實(shí)用設(shè)計(jì)
黨項(xiàng)族在北遷之前,其生產(chǎn)方式不同于中原的農(nóng)耕,而是以游牧業(yè)為主,基于這樣的生存方式,其生活用品的設(shè)計(jì)自然與黨項(xiàng)族人游牧的生活需求相適應(yīng),因此,西夏陶瓷扁壺具有經(jīng)典的形態(tài)特征。它是一項(xiàng)實(shí)用性與審美性合一的智慧產(chǎn)物。
就目前出土的文物來(lái)看,西夏陶瓷扁壺主要有盆形扁壺、罐形扁壺以及碗形扁壺這三種類型。盆形扁壺采用的制作方式是將兩個(gè)盆坯對(duì)口黏合在一起燒制而成,其屬于可攜帶的扁壺形瓷器,但是體型相對(duì)較大,厚重粗糙,目前出土的均為素面,無(wú)刻花裝飾。罐形扁壺是由罐形坯體加工而成,故名罐形扁壺。這類扁壺的制作方式是直接將圓形罐體兩邊粘貼耳系,并用鉚釘加固,以便提攜。碗形扁壺制作工藝是將兩個(gè)拉好的碗坯扣合,扣槽處根據(jù)需要,或用手指、木棍壓實(shí)一圈,形成凹凸堆積的裝飾紋樣,或者直接抹平堆紋而產(chǎn)生一種簡(jiǎn)潔的效果,之后再對(duì)合成的坯體開(kāi)壺口,安裝耳系、上釉,或進(jìn)行剔、刻、釉等裝飾工藝。各項(xiàng)工藝完成之后,再將壺放入特定的烘干房烘干,最后裝窯燒制。碗形扁壺是西夏陶瓷扁壺中的典型代表,出土數(shù)量多且種類多樣,由此可見(jiàn)它對(duì)于黨項(xiàng)族生活的重要程度。
不管西夏陶瓷扁壺的形狀何如,實(shí)用性都是其設(shè)計(jì)準(zhǔn)則,如壺身的耳系,呈橋形穿帶狀,粘燒在壺的肩部和腹部,便于系繩拎置。因自然條件的制約,黨項(xiàng)游牧民族的生活對(duì)水源有著很大的依賴性,因此,西夏陶瓷扁壺的設(shè)計(jì)都圍繞著用水便捷這一原則。首先,壺身扁平這一設(shè)計(jì)非常方便水注入壺內(nèi),而且圓鼓的壺腹部設(shè)計(jì)既可以使其蓄水容量最大化,又可以使扁壺與馬背的貼合面積更大,在顛簸的路途中保證壺的穩(wěn)定。另外,圓的壺身設(shè)計(jì)提高了安全性,易于行進(jìn)。西夏陶瓷扁壺的頸口有意設(shè)計(jì)為短窄口以及口卷沿的結(jié)構(gòu)模式,目的是增加壺口的密閉性,可以有效地阻隔塵土對(duì)壺水的污染,這一設(shè)計(jì)是基于黨項(xiàng)人生活環(huán)境多風(fēng)沙的考慮。同時(shí),西夏扁壺底部或正面有足圈,可以起到穩(wěn)定放置與加固胎體的作用,黨項(xiàng)人在游牧途中可將其立于地面。西夏扁壺任何一處細(xì)小的設(shè)計(jì)都體現(xiàn)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智慧。
二、西夏陶瓷扁壺的審美意味
西夏陶瓷扁壺的設(shè)計(jì),首先是為了實(shí)際生活的需要,但是它又在此基礎(chǔ)上體現(xiàn)了黨項(xiàng)民族的審美偏好及精神追求。西夏瓷器的裝飾紋樣、生產(chǎn)工藝以及在題材的選擇上都展現(xiàn)了民族特色。例如扁壺上的牡丹裝飾紋樣,雖然深受宋瓷的影響,但它的整體藝術(shù)風(fēng)格依然體現(xiàn)了獨(dú)具特色的民族性,展現(xiàn)了北方民族豪邁雄壯、率真淳樸的精神風(fēng)貌,體現(xiàn)了西夏民族多層次的社會(huì)生活。
西夏陶瓷兼具實(shí)用性和美觀性,在裝飾花紋的使用方面各有特點(diǎn)。例如寧夏海原縣征集收藏的一件四系剔刻花扁壺(圖1),用一枝花開(kāi)四朵的纏枝牡丹作裝飾。該壺高37.5 cm,口徑為7.0 cm,腹徑為30.0 cm,底圈足徑為10.0 cm。直唇口,長(zhǎng)頸,通體施茶葉末釉,腹部不施釉,露米黃胎。面部有凸起的圈足,并以圈足為中心,剔刻出一圈纏枝牡丹紋飾。西夏瓷器上的纏枝牡丹花紋是藤蔓牡丹花形象的再現(xiàn)。纏枝牡丹花為藤科草本,屬多年宿生根、耐高寒的植物。當(dāng)時(shí)西夏國(guó)部分寒冷地區(qū)有野生資源分布,單花品種居多。植物紋樣在壺身的運(yùn)用體現(xiàn)了西夏人順應(yīng)自然、與自然相融的生存觀。
早在舊石器時(shí)代,我們的先人就將植物形態(tài)的紋樣描繪在陶器上,這反映了植物對(duì)人類生存的參與,大自然以植物為中介實(shí)現(xiàn)對(duì)人類生存的營(yíng)養(yǎng)供給,人從植物中獲得生存能量。這種依存關(guān)系使人類對(duì)植物有一種特殊的感情。部分植物雖然不能食用,但能滿足人的審美需要,給生活增加美感,起到裝飾生活空間的作用。對(duì)于植物紋樣的應(yīng)用體現(xiàn)了西夏人的泛愛(ài)觀,他們將植物視為與人平等的生命體,都是得天地之靈而生的生命組織體,植物與人類同屬生命之象,共同運(yùn)轉(zhuǎn)于世界生命共同體之中。古人認(rèn)為萬(wàn)物相通,雖然植物與人的形態(tài)不同,卻能找到與人共通的內(nèi)在品質(zhì),這是一種本源上的共通,因此這些壺身上的植物紋樣具有反映人類生存環(huán)境的特殊寓意。如圖1所示,壺身上的牡丹紋樣婉轉(zhuǎn)多姿,生動(dòng)優(yōu)美,富有動(dòng)感,具有流暢和諧的美感。人們從此花的生長(zhǎng)特點(diǎn)中感受到了活潑延綿的生命狀態(tài),因此這種花紋被廣泛用于表達(dá)生生不息、萬(wàn)代綿長(zhǎng)的美好寓意。這一抽象紋樣也是西夏人以心靈體物、與世界萬(wàn)物相容的結(jié)果。纏枝牡丹花也是象征愛(ài)情的花卉紋飾之一,這件西夏瓷壺上的纏枝牡丹繞過(guò)開(kāi)光,不受其阻斷,花枝環(huán)繞于壺身,次第綻放,意味綿長(zhǎng)。
圖2是寧夏海原縣關(guān)橋鄉(xiāng)龍池村西夏遺址出土的白釉剔刻花小扁壺,此壺高13.0 cm,口徑為2.7 cm,腹徑為10.6 cm,小唇口,短徑扁圓,肩部安有耳系,此壺施白釉成為其獨(dú)特之處。白釉在西夏瓷器中頗具特色,西夏的開(kāi)國(guó)皇帝李元昊稱帝后,衣著白衫,戴白高氈帽,以示尊貴。于是西夏的民俗也具有崇白的風(fēng)尚,把白色視為崇高的顏色。受政治因素影響,瓷器的生產(chǎn)制作也受尚白習(xí)俗的影響,但是因西夏的地理位置,其土質(zhì)發(fā)黃發(fā)灰,并不利于白色瓷的生產(chǎn)。黨項(xiàng)族人發(fā)揮智慧,經(jīng)過(guò)探索,形成了先上一層化妝土,對(duì)胎體本身的顏色進(jìn)行覆蓋,再掛釉形成白瓷的獨(dú)特?zé)品绞健1M管如此,西夏純白色瓷器依然不多,大都呈灰白色或牙黃色。除了獨(dú)特的釉色外,這件扁壺的壺身設(shè)計(jì)采用了折枝牡丹紋樣作為裝飾。折枝牡丹紋是西夏瓷器擅用的一種裝飾紋樣,因其不畫全株牡丹只選取部分花枝刻畫而得名。牡丹花紋飾在西夏瓷中應(yīng)用廣泛,它有幸福吉祥的美好寓意。這枝折枝牡丹被巧妙地布于壺身的中心位置,牡丹從側(cè)邊出枝的方式為扁壺增加了活潑的氣息,使它呈現(xiàn)質(zhì)樸風(fēng)格的同時(shí)又不顯呆板。壺身花枝繁盛,花朵盛開(kāi),花瓣圓潤(rùn),刀法流暢自如。為了保留扁壺牡丹紋樣的整體性,這件扁壺把圈足設(shè)在腹下內(nèi)部,正面沒(méi)有圈足,牡丹花紋凸起,具有淺浮雕的質(zhì)感。這樣的剔刻方式為小扁壺的紋樣增加了豐富性與美感,可見(jiàn)生產(chǎn)者在遵照實(shí)用性準(zhǔn)則的同時(shí)又十分重視它的裝飾美。

與白釉剔刻牡丹扁壺不同,這件高33.3 cm、口徑為9.0 cm、腹徑為32.0 cm的黑釉剔刻花瓷扁壺(圖3)外觀透著一種更為豐富、剛毅的美感,這樣一種美感傳達(dá)體現(xiàn)在它的線條設(shè)計(jì)和釉的設(shè)色上,壺身的牡丹紋樣以野牡丹為材并設(shè)了重色,可見(jiàn)設(shè)計(jì)者意不在使之嬌巧。制作者對(duì)壺腹壁黏合處的處理并沒(méi)有選取抹平的方式,而是將黏合處捏塑成波浪曲線的裝飾紋樣。壺身上開(kāi)光外畫了對(duì)稱牡丹。對(duì)稱牡丹紋樣是西夏瓷器中常見(jiàn)的一種對(duì)稱紋樣,一般分為兩種,其中一種為開(kāi)光內(nèi)對(duì)稱,這種紋樣對(duì)開(kāi)光的大小范圍有一定的要求,因此一般應(yīng)用于大型的器具,另外一種為開(kāi)光外對(duì)稱,多應(yīng)用于扁壺之類的小器物。正如這件扁壺,兩枝牡丹于開(kāi)光外對(duì)稱。縱觀整壺,剔刻紋樣深淺色調(diào)對(duì)比鮮明,其中側(cè)緣波浪曲線、剔刻的直線、旋繞的牡丹枝葉等各元素俯仰相錯(cuò),對(duì)稱之下又不盡相同,體現(xiàn)出中國(guó)“和而不同”的傳統(tǒng)精神,展示了西夏瓷器質(zhì)樸、粗獷、豪放的藝術(shù)品質(zhì)。
從三種具有不同審美特征的扁壺來(lái)看,我們能深刻地認(rèn)識(shí)到西夏陶瓷扁壺除了實(shí)用功能外,還具有豐富的美學(xué)特征。在這個(gè)流動(dòng)不息的宇宙、包羅萬(wàn)象的生命空間中,黨項(xiàng)人以詩(shī)性的目光看待萬(wàn)物,把客觀事物情感化,把它們看作獨(dú)具性靈活潑的生命實(shí)體。扁壺一方面反映了黨項(xiàng)民族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也揭示了西夏民族的生命哲學(xué)觀。西夏民族不僅具有理性的生活智慧,還具有對(duì)于生命形態(tài)的感知力。
三、西夏瓷器扁壺對(duì)當(dāng)代藝術(shù)的啟示
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中,藝術(shù)品作為一種獨(dú)特的文化形式,受到廣泛關(guān)注,并逐漸被獨(dú)立出來(lái),與其他實(shí)踐活動(dòng)相脫離。當(dāng)人們談及藝術(shù)時(shí),不自覺(jué)想到的是它獨(dú)立的審美性,也就是其藝術(shù)性。然而,不管是過(guò)去實(shí)用性與審美性相統(tǒng)一的藝術(shù)品,還是現(xiàn)在獨(dú)立存在的藝術(shù)作品,人們對(duì)其都應(yīng)該持有正確的審美態(tài)度,即藝術(shù)品的價(jià)值并不會(huì)因它具有實(shí)用目的而削弱一分,也不會(huì)因它少了那份實(shí)用性而增強(qiáng)一分。正如實(shí)用性與審美性兼具的西夏陶瓷扁壺,當(dāng)人們面對(duì)它時(shí),并不知道其制作者是誰(shuí),但卻可以靜下心來(lái)感受它的美。現(xiàn)代社會(huì)的一個(gè)普遍現(xiàn)象是,人們談及藝術(shù)作品往往會(huì)過(guò)多地關(guān)注藝術(shù)家,而忽視作品自身的獨(dú)立性,甚至還會(huì)因?yàn)橐粋€(gè)作品是否由知名藝術(shù)家創(chuàng)造而影響自身的鑒賞標(biāo)準(zhǔn)。這樣就導(dǎo)致了一個(gè)令人諷刺的現(xiàn)象—藝術(shù)品之所以被稱為藝術(shù)品,并不是因?yàn)樗哂歇?dú)立的藝術(shù)價(jià)值,而是因?yàn)樗撬囆g(shù)家創(chuàng)造的。這些藝術(shù)作品的價(jià)值是由藝術(shù)家的稱謂附加而來(lái)的,致使人們?cè)谟^看藝術(shù)作品時(shí)往往被所謂的“權(quán)威”以及各種功利的社會(huì)因素所干擾,喪失了個(gè)人的藝術(shù)審美感受力。或許是現(xiàn)代討巧的東西太多,相比面面俱到的繪畫作品,筆者反而更喜歡這些簡(jiǎn)單、質(zhì)樸的西夏扁壺,這些器物透露出純樸、真誠(chéng)的氣質(zhì)。作為生活器皿,它們看似粗糙簡(jiǎn)單,可是當(dāng)你切實(shí)地去鑒賞時(shí),就會(huì)改變對(duì)它們的刻板印象,從而發(fā)現(xiàn)其質(zhì)樸下豐富的美。黨項(xiàng)族人在生活的同時(shí)也在極力裝點(diǎn)他們的生活,這或許就是藝術(shù)的健康狀態(tài),不偏不倚,既不矯揉造作又不無(wú)病呻吟,達(dá)到實(shí)用性與審美性的統(tǒng)一。沒(méi)有因?yàn)槠渲幸环蕉魅趿硪环剑瑑烧呦嗷コ删停质孢m自然,簡(jiǎn)單純粹。創(chuàng)作達(dá)到這樣舒適的境地就很好,既不過(guò)分喧張,又能表現(xiàn)出它內(nèi)在的精神力量。
四、總結(jié)
西夏瓷器因?yàn)槠洚a(chǎn)生于獨(dú)特的地理位置、民族文化、時(shí)代背景,而形成了獨(dú)特的藝術(shù)風(fēng)格,其在中國(guó)古代瓷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與黨項(xiàng)游牧生活密切相關(guān)的器物中,扁壺最具特色,它兼有實(shí)用價(jià)值及審美價(jià)值,反映了西夏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這些西夏陶瓷使我們能夠看到藝術(shù)品的雙重屬性,即實(shí)用性與審美性,這兩種屬性在人們的智慧安排下自然地凝合在一件器物上。西夏扁壺瓷器凝結(jié)了時(shí)代精神,具有一種純粹美,是人類的主觀智慧和客觀生存環(huán)境的有機(jī)統(tǒng)一,展現(xiàn)了黨項(xiàng)人樸實(shí)、自然的品質(zhì)。人們可以透過(guò)這小小器物了解西夏民族的生活方式,體會(huì)黨項(xiàng)族人在漂泊不定的游牧生活中對(duì)于生存、生活的渴望及其對(duì)美的熱愛(ài)與追求。
作者簡(jiǎn)介
秦文濤,1996年8月生,漢族,河南商丘人,寧夏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2020級(jí)美術(shù)專業(yè)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橛彤嫛?/p>
參考文獻(xiàn)
[1]鐘侃,吳峰云,李范文.西夏簡(jiǎn)史[M].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2005.
[2]韓小忙,孫昌盛,陳悅新.西夏美術(shù)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
[3]唐榮堯.西夏王朝[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5.
[4]李進(jìn)興.西夏瓷器造型探析[J].蘭州學(xué)刊,2009(9):211-213.
[5]山丹.淺論西夏扁壺[J].內(nèi)蒙古大學(xué)藝術(shù)學(xué)院學(xué)報(bào),2008(2):85-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