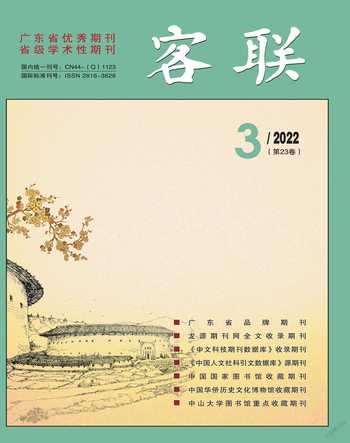女性的困境:亨利·詹姆斯早期小說中的“女性氣質”
劉軍
摘 要:本文通過文本細讀,分析了詹姆斯早期小說中的“女性氣質”,剖析了其道德、婚姻和家庭三個層面的內涵,指出父權意識形態通過構建“女性氣質”,營造了女性困境,束縛和剝奪了女性的主體性。
關鍵詞:女性氣質;亨利·詹姆斯;父權
亨利·詹姆斯是英美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人物,創作了包括《黛西·米勒》、《華盛頓廣場》、《一位女士的畫像》等為數眾多的小說,塑造了一系列熠熠生輝的女性形象,更被杜彼贊為“女性文學時代偉大的女性小說家”[2]。
從出版伊始,批評界就注意到詹姆斯作品中十分明顯的“女性氣質”。有學者認為這是對同時期女性作家作品的有意扭曲[3];還有國外學者認為是他對19世紀主流性別、階級觀念的妥協[6]。筆者以為,上述研究對“女性氣質”語焉不詳,有必要結合尤其早期作品文本加以探討。
一、關于“女性氣質”
女性主義批判父權制生物決定論,認為所謂的“女性氣質”不過是父權社會文化的構建物。在《第二性》中,波伏娃指出,盡管在生物和生理結構上,男性和女性的確存在差異,但是社會按自己的目的來對之做出解釋[1]。換言之,“女性氣質”是父權社會通過闡釋性活動,外部強加給女性的、要求女性必須扮演的社會角色內涵,以此強化男性自己的主體性,將女性降低到他者地位,實現對女性的控制。
19世紀晚期的歐美社會,父權制度意識形態根深蒂固。關于女性氣質的一系列社會觀念,也在道德、婚姻和家庭等多方面束縛著深陷其中的女性。詹姆斯早期小說中的眾多女性角色就是她們的代表者。然而,詹姆斯對這些女性角色的氣質內涵進行了再書寫和再闡釋,展現了她們所處的困境。
二、道德層面:純真
在道德方面規定女性氣質時,父權話語是矛盾的。一方面,女性被認定為純真無辜的天使,是人類社會道德的守護者;另一方面,女性又被認為在道德上發展不完整,無法像男性一樣,以“頭腦”控制“心靈”。這種看似互相抵牾的邏輯背后,其實大有深意。
《黛西·米勒》中,年輕的黛西就被描述為氣質上純真的女性。她善良真誠,與人交往簡單明快,在旅居歐洲時熱情地學習體驗舊大陸的文化和風情。這些都令男主人公溫特博恩為之著迷。然而,黛西帶著同樣的純真進入社交圈時,卻遭到了鄙視、質疑和最終的否定。因為在沒有監護人在場就與男子交談,因為與溫特博恩單獨出游,科斯特洛夫人拒絕與她見面;因為與下層階級“隨隨便便”就交往,更被包括溫特博恩在內的其他人,視為非正當行為。于是,詹姆斯天才地將父權道德性定義女性氣質的矛盾呈現在了我們面前:男性因為女性的純真而愛上女性,但又因為女性將純真貫徹于生活而質疑和否定女性。在這個矛盾的父權話語中,“純真”這一女性氣質,要求女性適時、適地扮演角色內涵,這是父權主體對女性的凝視,實質上就是一個使女性客體化的陷阱。
可以說,將“女性氣質”道德化,并操控其內涵賦予的權力,正是父權社會制度化控制女性的企圖。
三、婚姻層面:順從
父權觀念關于“女性氣質”的第二個迷思就是婚姻。盧梭在《愛彌兒》中說,女人的存在依附于男人,依靠男人“對她們的美德所設定的價值而活”。男性對女性美德設定的價值,突出地體現在了婚姻中。叔本華更直接地說,“女人從本性上來說意味著服從”,“這是因為她需要一位丈夫和主人”[4]。可見,父權對“女性氣質”在婚姻層面的規定就是順從,或者同義表述:溫柔。
諷刺地是,要求女性順從男性,又與要求女性有道德是矛盾的。如《波士頓人中》的伯宰小姐,有著“八十歲的純真”,是“道德熱忱”的新英格蘭精神的最后代表,然而在男主角奧利夫的敘述中,充滿了可憐她、譏諷她的復雜情感。另一位男性角色蘭塞姆則直接了當地說:“可憐的伯宰小姐根本就沒有一點女性的輪廓。”
要理解這一矛盾看法,我們只需注意到:和另一位被認為乖僻的職業女性普蘭斯醫生一樣,伯宰夫人終身未婚,“沒有健全的生活”。換句話說,沒有進入婚姻的伯宰夫人,不具備婚姻賦予女性的氣質,即“順從”,因而她在道德上的無可挑剔性,反而使她可以凌駕于男性之上,這才是她不被男性角色喜愛的真正原因。
四、家庭層面:責任
父權社會規定,女性對家庭的責任就是盡到母職和妻職,給予家庭成員各種“關懷”。恩格斯在分析資產階級社會的家庭時,犀利地指出:一夫一妻的對偶家庭是權力高壓和經濟迫切需求的產物[5]。因此,“責任感”作為一種女性氣質內涵,實際上就是要求女性在家庭內部,完全以男性(丈夫)為中心,自覺接受男性的剝削。
“關懷”的剝削性本質,使得父權價值體系必然鼓吹:婦女有能力關懷別人、一向關懷別人。這自然會產生更明確要求:女性應該承擔關懷的責任,無論她們為此要付出何等代價。于是,正如巴特基指出的那樣,婦女的責任以及她們對男人的關懷,就變成了“婦女對男人集體性的屈從、對男性重要性的肯定”[5]。婦女的責任感越強,對男人的關懷越多,就越會舍棄自己、進入他的議程,僅僅為他的利益服務,從而喪失了對自我的感覺,也喪失了對現實的觀感和對真理的思考。亦即,在父權式家庭模式里,要求女性具有責任感,要求女性服從“關懷”氣質,實際上就是在剝奪女性的作為主體性個人的自由。
這一困境,也正是詹姆斯筆下諸多女性角色所面臨的,典型地如《一位女士的畫像》的女主人公伊莎貝爾。伊莎貝爾拒絕了英國貴族沃伯頓勛爵和美國企業家格德伍德,拒絕了權力和財富,選擇了無權無產甚至無職業的奧斯蒙德,就是因為她相信,與奧斯蒙德的結合,會使她能在婚姻和家庭中繼續保持一貫追求的獨立和自由。然而,當奧斯蒙德的背叛造成她的理想破滅后,她卻拒絕了格德伍德讓她離開丈夫的熱烈請求,義無反顧地回到了羅馬,回到了丈夫身邊。其原因正是她強烈的家庭責任感。她對家庭的維系,對丈夫的關懷,是以放棄個人對自由的追求為代價的。
五、結語
詹姆斯在早期小說中,通過塑造一系列女性角色,講述她們的故事,敏銳而又深刻地捕捉和再現了19世紀晚期歐美社會中女性所面臨的困境:保持自己的“女性氣質”,就無法保持自己作為“自為的自我”的主體性。他對父權社會關于“女性氣質”闡釋的虛偽性、矛盾性和壓迫性的揭露,使他當之無愧地位列最偉大的女性題材小說家中。
參考文獻:
[1]de Beauvoir, Simone. The Second Sex [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4: p24.
[2]Fowler, Virginia C.. Henry James’s American Girl: The Embodiment on the Canvas [M].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p2.
[3]Habegger, Alfred. Henry James and the "Woman Busines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
[4]李銀河. 女性主義[M]. 濟南:山東人民出版社,2005: p9.
[5][美] Putnam Rosemarie Tong.女性主義思潮導論[M]. 艾曉明,等,譯.武漢: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 2002: p152, p235.
[6]Wichelns, Kathryn. Henry James's Feminist Afterlives: Annie Fields, Emily Dickinson, Marguerite Duras [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