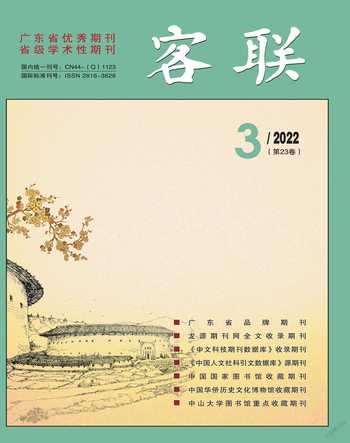環境規制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機制分析
周心秀
摘 要:環境規制是協同我國推進綠色經濟高質量發展和實現生態環境高水平雙重保護任務的關鍵所在。從經濟可持續發展角度而言,綠色全要素生產率是兼顧經濟效應與環境效應的綜合指標,其深入研究也更符合當代經濟發展的現實需求。本文力圖探討環境規制影響綠色全要生產率的內在機理,得出環境規制主要通過技術創新和產業結構優化這兩方面的因素對綠色全要素產生影響。
關鍵詞:環境規制;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作用機制
一、引言
Solow(1956)首次提出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概念,他把經濟增長中扣除資本和勞動后的投入要素叫做全要素,并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進行了測算,它能夠實際反映出經濟增長的總體質量。隨著環境污染的惡化,環境質量已逐漸發展為制約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另一關鍵性因素,環境不只是是經濟的內生變量,也是經濟發展程度的政策剛性約束。Chung等(1997)指出利用DDF函數和ML生產率指數定量的測度了瑞典紙漿廠的全要素生產率,將非期望產出納入框架,首次從方法上擬合了污染排放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得出了真正意義上的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因此,本文有必要充分考慮經濟增長對環境產生的損耗和環境污染對經濟發展產生的剛性約束,考慮非期望產出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來討論環境規制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機制。對現階段面臨著污染治理和經濟綠色轉型雙重壓力的中國而言,探討這一問題十分重要。
二、環境規制通過技術創新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環境規制通過技術進步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一定作用,主要有以下兩種觀點:一些學者認為,環境規制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發揮阻礙作用。如孫玉環,劉寧寧等(2018)指出,廠商在生產環節尾端的治理成本和效率配置的環境成本會由于環境規制政策的實行而上升,這樣一來的話就會對廠商的生產性投資產生擠占作用,致使企業會減少科研的創新投入和技術改良投入;也有許多學者持相反的觀點,即環境規制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路徑發揮促進效應。Poter(1995)等提出“波特假說”有力的論證了這一觀點。波特認為,在短期內廠商不可避免的會受限于環境規制政策所帶來的額外成本增加,而削減創新投入。但站在長期發展的視角來看,技術進步最終會降低環境治理成本。主要體現在環境規制政策的實行,會倒逼企業進行生產創新,由此帶來的創新補償效益會對沖或者超過環境的遵循成本。呂康娟,程余等(2017)的研究也都力證了“波特假說”的合理之處,認為環境規制有利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具體的作用機制如下:
(一)投資擠出效應
傳統新古典理論認為,環境保護勢必會以廠商的生產成本增加為代價來提高整個社會的福利,這樣的話則會抑制廠商內部的創新與研發能力。在諸多假定不變的條件下,如消費需求和企業技術水平,環境管制對企業的技術創新不利。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創新資金的擠出效應。原始投入在企業技術創新過程中必不可少,而環境規制會增加污染的治理技術成本,從而會減少企業的研發投入;二是投資需求的擠出效應。一些企業在環境規制的嚴格政策背景下,會傾向于選擇規制程度相對低的地區進行生產和投資,這樣會導致規制程度稍低的地區成為“污染天堂”。而且,高環境規制約束下的廠商往往背負著更多的稅收負擔,這會增加公司的運營成本,企業則會偏向于重新選擇環境規制成本稍低的地區進行投資,進行低污染產業的梯度轉移。
(二)創新補償效應
也有學者從動態角度分析,提出了捍衛綠色環保的理念(Porter,1995)。他們認為一方面環境規制會加重企業的生產成本,另一方面也會激勵企業提升技術創新水平。政府通過實施嚴格的環境規制措施,對生產廠商污染物的排放量進行限制,如工業廢氣、廢水及附屬品等,要求各廠商通過執行嚴格的環境規制措施或者進行污染治理技術的改良,這將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企業的污染治理成本。我們都知道,廠商是逐利的,因而在面臨環境規制時會通過改良生產工藝或者技術水平,以求企業生產效率的提升,這一過程最終會減弱甚至抵消環境規制給企業增加的環境成本,這就是環境規制的“創新補償效應”。雖然這一過程可能會增加污染物的排放量,但由于企業創新技術的研發水平的提高則會促進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增長。
三、環境規制通過結構優化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環境規制通過結構優化會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產生一定的影響,具體路徑如下:一是產業轉移效應,二是產業轉型效應。具體作用機制如下:
(一)產業轉移效應
產業轉移本質上來看是國家或地區間的資源或需求的空間移動現象(李虹,鄒慶,2018)。根據“污染避難所假說”的規定,環境政策的規制將會導致一些具有較高排放污染率的企業由過去相對發達地區逐步轉向其它經濟欠發達地區(FANG等,2020)。相反,經濟發達地區則會更注重本區域的生態環境,環境規制的強度會更高。同時,欠發達城市也會實行相對寬松的環境政策來吸引高污染產業的轉移,來換取經濟的高速增長。但是隨著整個城市經濟的加速發展,重污染的產業會逐漸被淘汰掉,部分產業則會開始創新轉型的升級,產業結構就必然地會的隨之的逐步地優化。錢爭鳴和劉曉晨(2014)發現,環境規制從長期的角度來看,是有利于產業結構調整的。總的來說,隨著環境規制程度的加強,高耗能和高污染型的企業會由進行環境規制相對寬松地區的轉移,而且環境規制程度高的地區會著重發展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的產業。
(二)產業轉型效應
微觀層面所指的產業經濟轉型是指行業內部資源和行業內要素的交換和再配置,從而導致其從原來衰退性產業轉向新興戰略性產業(杜龍政,趙云輝等2019)。根據“波特假說”原則,環境經濟規制通過創新技術的研發帶來企業經營效益提高,從而實現企業自身結構的優化調整(陳素梅,李鋼,2019)。經濟相對發達穩定的地區會進行技術改造,提高對企業和生產設施的生產環境標準,部分技術落后的企業將會選擇被關停出局;另一些在原有生產效益高的企業可能會重新進行產品技術工藝革新改進以逐步達到企業新設計的技術環境標準要求,從而仍然可以安全繼續生產。企業本身進行技術創新獲取的最終收益必然會顯著大于企業創新研發產生帶來的運營成本,這是新環境下規制政策引起企業的新產業轉型。同時,由于生態環保理念的不斷踐行,消費者對產品的需求也相應的轉向環保品。需求結構的變動也會使企業調整產業結構進行轉型,來更好的適應市場發展的需求。此外,環境規制嚴的地區高新技術產業的比重會不斷上升,耗能高和污染重的產業比重會逐步下降。因此,環境規制通過產業轉移和產業轉型促進產業結構的高級化及合理化,因而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
四、結論
總的來說,環境規制主要將通過產業技術創新效應和技術產業結構效應這兩個主要方面來影響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一是環境規制與技術創新大體上呈“U”型關系,即前期主要是規制的擠出效應作用于技術創新降低綠色全要素生產率,而后期主要是技術創新的補償效益來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二是隨著環境規制嚴厲程度的增強,通過產業結構更高級化發展及經濟合理化都趨于積極有利的調控機制來有效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因此,各企業或各地區在環境規制背景下想要提高綠色全要素生產率,可以從以下兩方面入手。首先,各地區可以加大技術創新的投入強度,加大創新成果的轉化力度,政府也應該增加對創新投入的補貼,來促進新知識和新技術的產生,增強技術進步對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基石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自發的進行產業轉型升級,降低高污染產業的比重,逐漸淘汰傳統的“三高”企業,為一些低耗能和高附加值的產業騰挪部分空間,提升高新技術產業的效率,充分發揮結構優化的綠色增長作用。
參考文獻:
[1]Solow R.M.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J].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1956,70(1):65-94.
[2]Chung,Yangho,Rolf Fare Shawna Grosskopf.Productivity and Undesirable Outputs: A Directional Distance Function Approach[J].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1997(51):229-240.
[3]孫玉環,劉寧寧,張銀花.中國環境規制與全要素生產率關系的區域比較[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18(1):33-40.
[4]Porter M E,Linde C V D.Toward a new con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competitivenes relationship[J].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1995,9(4):97-118.
[5]呂康娟,程余,范冰潔.環境規制對中國制造業綠色全要素生產率的影響分析[J].生態經濟,2017,33(4):49-52.
[6]李虹,鄒慶.環境規制、資源稟賦與城市產業轉型研究———基于資源型城市與非資源型城市的對比分析[J].經濟研究,2018,53(11):182-198.
[7]FANG Z,HUANG B H,YANG Z X.Trade openness and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vidence from Chinese cities[J].The World Economy,2020,43(10):2622-2649.
[8]錢爭鳴,劉曉晨.環境管制.產業結構調整與地區經濟發展[J].經濟學家,2014(7):73-81.
[9]杜龍政,趙云輝,陶克濤等.環境規制、治理轉型對綠色競爭力提升的復合效應———基于中國工業的經驗證據[J].經濟研究,2019,54(10):106-120.
[10]陳素梅,李鋼.環境管制對產業升級影響研究進展[J].當代經濟管理,2020,42(4):49-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