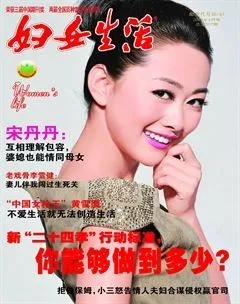這么多年,她一直都在
我小的時候,父親是生產隊隊長,每次從村里開會回來,都會帶一本雜志,她便是《婦女生活》。有一期,刊登了一個農村女孩被拐賣,跟人販子斗智斗勇的故事,看得我緊張得直冒汗。我最關注的,還是心理、情感問題和法律知識。那個年代,由于課外書極度匱乏,《婦女生活》為我打開了另一扇知識的大門。
父親不任職后,我很難再看到《婦女生活》。有時候實在想看,我會把希望寄托在婦女隊長身上,碰上她去村里開會,我就候在大路上,眼巴巴地等她回來。可失望總是居多,她也很歉意,說書被誰誰給拿去了。也有喜出望外的時候,我會拿著雜志跟二哥炫耀:“看,《婦女生活》。”他嘿嘿一笑:“拿來我看看。”我舍不得,只向他展示封面,他卻劈手奪去,跑到遠處的池塘邊盡情欣賞。我遠遠地跟他要,要不到就哭,母親就會命令他:“快還給你妹妹!”二哥孬得很,不但不還我,還惡作劇地隨手把書往池塘里一扔,撒腿就跑。我心疼自己的寶貝,哪顧得水深水淺,撲通一聲跳進水里就去撈……
長大后,我定居深圳,戀愛、結婚,家鄉離我越來越遠。我生孩子那年,娘家裝了電話,母親最先打給我,絮絮叨叨地說起了小時候我跟二哥搶雜志的往事,末了還說:“你那些寶貝,我都收著呢,放在閣樓的小木箱里。”我突然哽咽——謝謝不識字的媽媽!這么多年,愛原來一直都在。
再經過報攤,我的目光忍不住在一本本雜志的封面上游移。這么多年了,她還好嗎?
無數次的留意,終于讓我重逢久違的她。2012年5月15日下午,在一個比較冷清的報攤上,我發現了兩期《婦女生活》,當即每期買了一本。多年未見,心里還真有些忐忑:她還是我記憶中的模樣嗎?她是否還能夠滿足我這個現代都市女性挑剔的審美眼光?萬沒想到,封面上依舊是那熟悉的四個字,內容卻與時俱進:《朝夕相處的夫妻:如何繞開亞婚姻雷區》《哈文:事業型女人也能做個好媽媽》……她完全跟上了現代女性生活的節奏,她仍是女人的心頭好,而且內容更豐富,案例更鮮活,知識面更廣。更令我驚喜的是,她還出了姊妹刊《現代家長》,我豈不又多了一個教育孩子的好幫手?
再往下看,我看到了“我與《婦女生活》30年”征文活動的啟事,激動中我跟丈夫說:“我是她的老讀者呢!”丈夫聽了,半天沒吱聲。我抬眼一看,素來不看雜志的他,竟捧著《婦女生活》看得津津有味。突然,我有了一個主意,拿起手機打給媽媽:“把咱家收藏的《婦女生活》,都贈給村里的農家書屋吧!今年是她創刊30周年,我想讓更多的人看到她!”
〔編輯:馮士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