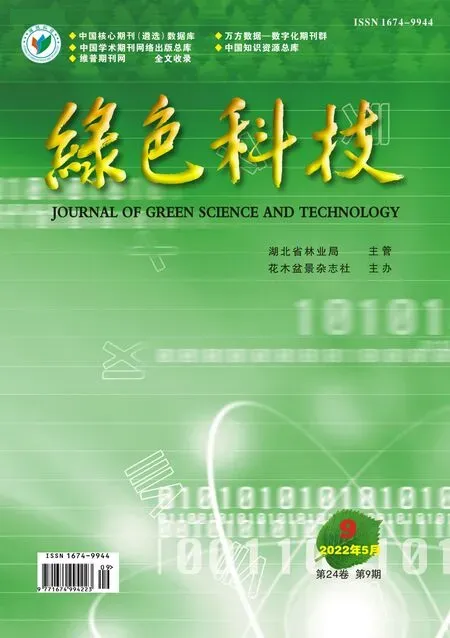成渝地區城市間交通可達性演變分析
何 紅,李孝坤
(重慶師范大學 地理與旅游學院,重慶 401331)
1 引言
可達性或通達性,通常表示使用一種交通工具從某個特定城市通往另一個城市的便捷程度[1]。可達性是一個常用概念,在城市規劃和交通規劃、經濟學和地理學領域被廣泛使用,可達性作為有效分析的綜合性指標,在衡量交通網絡結構有效性、測度區域獲取發展機遇及市場影響強度等方面是重要影響要素之一,因此成為國內外研究的熱點內容[2,3]。Linneker和 Spence在研究區域經濟發展的有效影響機制中表明,倫敦M25環形公路所引起的交通可達性變化促進所經區域經濟快速發展[4]。可達性對某種社會服務的接近度也會有影響,Gimpel和 Schuknecht在研究居民參與政治投票的意愿與投票箱可達性之間的關系時發現,到投票箱的可達性與居民參與政治投票率呈正比[5]。國內學者在可達性研究方面頗有建樹,金風君等學者基于我國航空網絡的空間拓展和鐵路網的空間演變,對我國不同區域可達性進行研究,結果表明交通網的完善推動我國區域間經濟交流與合作,縮小區域經濟差異[6,7]。交通網的完善也代表該區域有更多的機會、更大的潛力與其他區域進行經濟技術和社會文化交流[8],同時可以擴大供應商的選擇區域和投資范圍,促使區域內企業獲得更大范圍其他地區的知識和技術[9~11]。
有多種方法測算可達性,成熟的方法如最小距離法、緩沖區分析法、空間插值法等計算方法,但由于實際交通網絡的復雜性使得以上方法度得出的區域交通可達性與實際情況之間誤差較大[12,13]。隨著科學技術發展,交通基礎設施建設逐漸打破了地形、氣候等因素的限制,交通網絡漸趨網絡化、復雜化,交通工具更加多樣化;隨研究不斷深入發展,在區域經濟、城市物流、跨區域旅游等領域均有可達性的相關研究,可達性的測度方法也更加多元。加之諸多數理方法的引入與GIS技術的不斷完善普及,GIS技術成為有效且簡便的分析可達性的有力工具[14],雖然計算量大,時耗長,但是所得結果與實際值差異較小,使得研究更具價值。
分析城市間的可達性,通常以區域間最短路徑旅行時間作為交通可達性評價指標,其不僅影響該區域內空間經濟角色定位與調整,也是促使區域經濟不平衡的眾多因素之一[15]。在其他要素不變的情況下,區域可達性越好,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城市間經濟交流與合作更加頻繁深入。本研究將研究區內各市(區/縣)人民政府抽象地視為交通網絡中的節點,借助ArcGIS10.4軟件計算出2010年、2015年、2019年各人民政府間交通最短旅行時間,進而對比分析城市間的可達性狀況。
2 數據來源與研究方法
2.1 研究對象
參考《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規劃綱要》規劃范圍,考慮成渝地區城市經濟發展聯系的復雜性及保證研究區域的完整性,本文選擇四川省15個完整地級市(成都、德陽、綿陽、雅安、樂山、眉山、宜賓、瀘州、自貢、內江、資陽、南充、遂寧、達州、廣安),和重慶市中心區等21個區縣(重慶中心城區、合川、豐都、璧山、云陽、潼南、忠縣、大足、綦江、榮昌、銅梁、南川、江津、長壽、永川、梁平、涪陵、開州、墊江、萬州、黔江)作為研究對象,共36個研究單元。
2.2 數據來源
以2011年、2016年和2020年四川省和重慶市的公路圖(《中國公路交通史叢書、四川交通年鑒、重慶交通年鑒》),及2016年、2021年全國高鐵規劃圖作為基礎地圖,對地圖進行空間校正、投影處理和矢量化,處理后得到3個年份的交通路網數據作為本研究的基礎數據。
2.3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ArcGIS10.4軟件對成渝地區內36個研究單元進行可達性測算,并構建成渝地區城市可達性OD時間成本矩陣。操作步驟如下:對地圖空間校正、高斯——克呂格投影轉換和矢量化處理,獲取3個年份的城市交通路網數據(包括高鐵/動車、高速、鐵路、國道、省道、縣鄉道),形成交通網絡數據庫,進而參照國家道路限速標準和川渝地區交通行駛情況,對不同層級的交通網絡系統賦相應的時間成本值,最后借助OD成本分析模型,計算每個城市與其他城市的最短路徑可達性時間,建立OD成本矩陣。受地形影響,截至2019年川渝地區高鐵行駛速度在300 km/h左右,加上動車和城際列車行車速度可達250~300 km/h,故研究區內部分城市雖沒有通高鐵,但是開通城際列車或動車的,行駛線路也算在高鐵一類,各類交通通行速度如表1所示。

表1 川渝各類交通通行速度 km/h
3 節點城市交通網絡分析
交通是區域聯系的重要媒介,道路網絡的完善程度與城市間的通行時間呈負相關,節點間通行時間越短可達性越高,交通網絡是城市間要素流通的橋梁,完善的交通網絡能夠增強要素流通的便捷性,并導致集聚城市群內經濟發展分布格局變化[16]。基于此,本研究運用ArcGIS10.4軟件,將2010年、2015年、2019年3個年份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內36個研究單元的道路路網分布圖進行可視化,如圖1所示。

圖1 交通網絡
結果顯示:路網漸趨完善、密集程度不斷提高,核心——邊緣的放射狀結構明顯,路網“空心區”和邊緣區交通條件有待改善。①由圖1可知,近10年來,成渝地區道路交通快速發展,交通網絡體系和網絡結構不斷完善,網絡密度漸趨增大;結合表1數據,隨著交通網絡的完善和道路通行路況改善,公路和鐵路通行速度不斷提高,川渝地區整體交通建設成效顯著;②成渝地區道路網絡空間格局呈現出以成都和重慶中心區為中心,網絡密度和網絡體系完善程度向外逐漸遞減的放射狀模式,呈明顯“核心——邊緣”結構;③在交通網絡漸趨完善的過程中,內江、遂寧、南充、涪陵、合川等節點城市在交通網絡中的中介節點地位越來越突出,網絡覆蓋面逐漸擴大,然而地處研究區東北片區的達州、云陽、開州,西部片區的雅安和南部片區的瀘州等城市網絡分布覆蓋度低,處在邊緣地帶;同時,圖1顯示,成渝中軸線附近高速路網和鐵路網分布均較稀疏,路網仍存在“空心區”,故邊緣區和成渝中軸線附近地區交通網絡有待進一步完善。④從鐵路分布來看,鐵路網絡漸趨完善,綿陽、內江、遂寧、永川、涪陵等城市成為鐵路網絡中的重要次級樞紐,是鐵路網絡重要中轉城市;從高速公路分布來看,高速路網完善程度比鐵路更高,密集程度更高,靈活性更強,成為短距離城市間聯系的重要選擇。
4 節點城市交通平均可達性時間
借助ArcGIS10.4軟件,對成渝地區的36個研究單元進行以時間成本為阻抗的OD成本分析,測算了匯總后的各單元平均可達性時間如表2所示,并將其可視化如圖2所示。

圖2 平均可達性時間

表2 各城市平均可達性時間 min
從成渝地區各研究單元3個年份平均可達性時間表中可以得出:隨著各城市高速公路、高鐵、城際列車、動車的開通運營,各城市間的可達性不斷提高。①2010年、2015年、2019年3個年份成渝地區各個城市平均可達性時間匯總值分別為7585.12 min、4547.92 min、3318.30 min,數據顯示2010~2019年交通平均可達性時間不斷降低,2019年相比2010年總平均時間減少了4266.82 min,減少幅度大于56%,這與成渝地區高速路網完善、鐵路路網完善和路況改善提升運行速度,及諸多城市開通運營城際列車和動車息息相關,鐵路和高速路網的完善大大降低了城市間通行時間;②2015年比2010年總平均可達性時間減少了3037.21 min,降幅大于40%,其中降低最多的是德陽、綿陽、眉山、樂山、資陽等高鐵、動車或城際列車開通運營的城市,以及雅安、開州、黔江、云陽、忠縣等高速開通的城市,還有豐都等鐵路投運的城市,這些城市在道路完善的過程中克服了城市間的空間距離,縮短了與其他城市的通行時間。③2019年比2015年總平均可達性時間減少了1229.61 min,降幅為27%,降幅從40%到27%,表明成渝地區城市在前期大力修建高速公路、鋪建鐵路道路,較短時間內道路從無到有,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提高了城市間的可達性,后期路網不斷延伸、加固、拓寬,可達性時間降幅自然降低;同時還有諸多城市路網完善程度較高,如遂寧、南充、達州、宜賓等動車、城際列車或高鐵開通的城市,渝萬動車沿線城市,以及成渝客運專線沿線城市總平均時間有不同程度降低。以上說明,隨著高鐵、城際列車、動車、高速的開通運營,對成渝地區城市的交通可達性產生“乘數效應”,同時,高速公路、高鐵、城際列車、動車對研究區內城市可達性影響程度相當高,是區域整體可達性提升的中堅力量。
成渝地區大部分城市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獲得了較大成功,交通網絡漸趨完善,城市間平均可達性顯著增強,重要次級交通樞紐漸趨形成;而可達性較低的城市多分布在研究區四周,交通發展建設不均衡的局面并未打破,成渝中軸線附近地區和邊緣地區交通條件改善力度總體較弱。圖2顯示,隨著時間的發展,成渝地區城市平均可達性顯著提高,其中值得注意的是,2010年成都和重慶中心區可達性是區域內高水平區,但隨著交通條件的完善,成渝中部大部分城市可達性反超成渝兩大核心城市,成為重要次級交通樞紐,如內江、永川、合川、遂寧、長壽等城市,這與成渝兩大核心城市所處的地理位置密切相關,由于這兩個城市并非處于研究區中間位置,故到各城市的距離自然增加,從而導致其并非是可達性值最高區域;但是,地處成渝中部的城市,如資陽、大足、潼南等城市,平均可達性并不高,出現可達性“空心區”,這與交通網絡結構圖相吻合。所以,在今后的建設中,仍需提高川西、川北、川東南、川渝東北以及中軸線附近地區城市的交通便捷度,加強可達性邊緣地帶城市的交通建設,完善交通體系,將1 h出行圈向外圍拓展,切實促進中心城市與周邊城市的聯系,從而推動整體實力提升。
5 結論與討論
交通要素是連接各城市的橋梁,是經濟活動主體進行經濟聯系不可或缺的載體,本文選擇各城市作為經濟活動主體,通過ArcGIS10.4軟件對成渝地區路網進行處理,并借助OD成本模型,對2010年、2015年、2019年成渝地區36個行政單元交通平均可達性進行測度,進而分析各城市間交通要素的演變特征。
研究結果顯示:①近10年來,成渝地區道路交通建設快速發展,道路通行路況改善,交通網絡結構不斷完善,特別是鐵路網絡和高速公路網絡的完善,為整個交通網絡體系架構了網絡骨架,網絡漸趨復雜,網絡密度逐漸增大,為城市間聯系提供了良好的條件。②“核心—邊緣”結構凸顯,道路網絡空間格局呈現明顯雙極核分布模式,成都和重慶中心區始終為區域交通樞紐城市,交通網絡以兩大核心城市為中心呈放射狀空間布局,但受地理位置限制,兩大核心城市并非始終是可達性最高的區域,且成渝中軸線附近路網仍存在“空心區”,導致該區域平均可達性低于周圍城市。所以,在建設核心城市對外交流渠道的同時,成渝中軸線地區交通網絡急需構建和完善,才能進一步打造成渝合作通道。③隨高鐵、城際列車、動車、高速的開通運營,對成渝地區城市的交通可達性產生“乘數效應”,交通平均可達性時間不斷降低,形成重要次級交通樞紐,加強了城市間交流;但是處于邊緣區的城市,要真正完全融入到成渝整體發展格局中,提高其與周邊城市乃至核心城市的交通通達性至關重要,這樣才能擁有更多的資源、更廣闊的市場,以發展自身經濟,進而參與到更高層級的競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