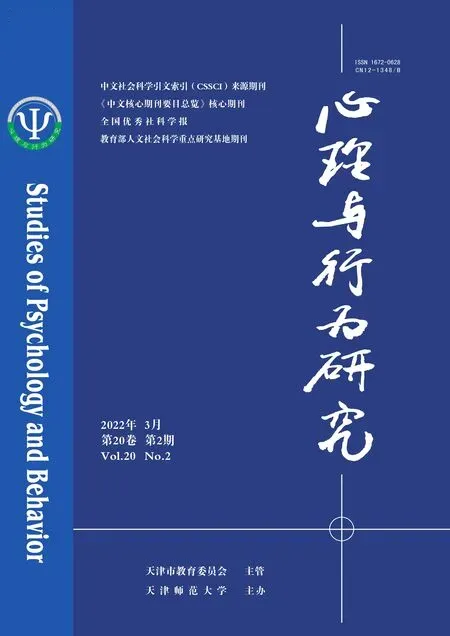父母自主支持、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網絡成癮的關系:一項交叉滯后研究 *
鄧林園 楊夢茜 楊雨萌 周 楠 李蓓蕾
(1 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北京 100875) (2 成都天府第七中學,成都 610218)
1 引言
青少年時期被認為是發展獨立人格、具有強烈內部動機對未來發展方向進行自主選擇的重要時期,他們特別需要重要他人(如父母)的理解、認同和支持。根據網絡成癮的“需要-滿足理論”,當青少年在現實生活中的心理需要得不到滿足的時候,他們更容易在虛擬的網絡世界中尋求快樂、安慰和滿足,并在惡性的循環中產生成癮行為。網絡成癮表現為個體過度使用網絡,無法控制自己的上網行為,導致心理和社會功能嚴重受損(Davis, 2001)。大量研究發現,有更多網絡成癮行為的青少年會有更多的問題性心理癥狀(Cao et al., 2007)、更高的社交焦慮(Liu & Kuo,2007)和抑郁水平(Huang & Leung, 2009),以及較多的學業問題和人際問題(Jiang, 2014)。
青少年網絡成癮的消極影響引起了研究者對其發生機制的廣泛探討,過往研究發現父母教養方式是不可忽視的環境因素(Chen et al., 2016)。根據自我決定理論(SDT)(Branie et al., 2008),父母心理控制與父母自主支持這兩種不同的教養方式都可以對青少年心理和行為問題的發展產生影響。父母心理控制指父母采用言語或非言語的方式對青少年的感受和想法進行侵犯性控制,忽視孩子的自主、情感或其他心理需要的一種控制行為(Barber & Harmon, 2002),父母自主支持是指父母支持孩子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發展,積極傾聽并理解孩子的想法,鼓勵他們自由選擇的行為。自我決定理論強調了家庭環境和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要(自主、關系和能力)相匹配的重要性,當青少年所處的家庭環境能夠滿足他們的基本心理需要,其可以促進孩子的適應性水平發展;反之,當父母的教養行為難以滿足青少年的基本心理需要,可能會導致青少年的生理或心理問題(如網絡成癮)(Ryan & Deci, 2002)。一些研究發現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出現的外化問題行為相關,如攻擊行為、藥物濫用、違紀行為以及反社會行為等(Barber & Harmon, 2002; Hoeve et al., 2009),而父母自主支持對青少年外化問題行為的發展具有保護作用(陳云祥 等, 2018),更容易促進青少年良好的心理適應性發展(Griffith &Grolnick, 2014)。目前關于父母心理控制、父母自主支持與青少年網絡成癮的關系的研究較少,部分研究發現父母心理控制對網絡成癮的消極影響,比如母親心理控制可顯著正向預測青少年網絡成癮(李丹黎 等, 2012),申子姣等(2012)發現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與網絡成癮呈正相關,也有研究發現父母的情感溫暖和支持可以有效緩解網絡成癮癥狀(Schimmenti et al., 2012),但是這些橫斷研究的數據所提供的信息對于發展變化中的個體來說是有限的(Kraemer et al., 2000),不能說明父母心理控制、父母自主支持和青少年網絡成癮之間的動態預測關系。另一方面,陳艷等人(2021)發現青少年的手機使用可以預測一年后親子間對手機的共同使用,可能當父母認為其子女的手機成癮越來越嚴重時,他們更愿意陪同孩子一起使用手機,以便監控孩子的使用內容,避免孩子進行非必要的網絡活動,并且共同使用與其他父母干預策略可能有共存的現象,比如父母可能會通過控制的方式減少青少年對手機和網絡的使用,也就是說青少年的成癮行為還可能反過來引發父母教養方式的改變,兩者之間可能存在著互相預測的關系。以往研究基于追蹤研究對親子影響的關系方向提出了不同的理論模型,包括父母效應模型、兒童效應模型和互惠效應模型三種作用模型(Loulis & Kuczynski, 1997)。
父母效應模型(the parent effect model)認為父母行為可以預測兒童青少年適應性行為,有研究發現父母較高的心理控制可以預測青少年較差的情緒功能和消極的自我評價(Wang et al., 2007)。一項關于父母心理控制、行為控制與青少年網絡成癮的關系的縱向研究中發現,父母心理控制可以預測青少年一年后的網絡成癮傾向(房超 等,2012)。這些研究證實了父母效應模型。兒童效應模型(the child effect model)認為青少年的問題行為能夠影響父母的反應和行為方式。比如有研究者發現兒童的焦慮水平越高,越有可能導致父母控制水平的提高(Wijsbroek et al., 2011)。一項關于青少年抑郁和違紀行為與父母心理控制的關系的追蹤研究發現,青少年的心理問題或行為問題可以預測一年后的父母心理控制水平(Barber,1996)。這些研究證實了兒童效應模型的存在。而互惠效應模型(the reciprocal effects model)認為青少年的社會化過程是青少年與父母相互影響的過程(Sameroff, 1975)。Koning 等人(2018)追蹤了兩次的研究數據發現青少年網絡游戲成癮和父母教養方式基本符合互惠效應模型,青少年的網絡游戲成癮會引發父母無效的教養方式,從而加劇成癮癥狀。父母心理控制、自主支持對于網絡成癮分別是風險和保護因素,但鮮有研究探討青少年網絡成癮對父母心理控制、自主支持的影響,父母教養方式和網絡成癮的相互預測模型還需要進一步檢驗。因此,本研究將采用追蹤研究的方式建立交叉滯后模型,探索父母心理控制、父母自主支持和青少年網絡成癮之間的相互預測關系。
綜上所述,本研究將建立穩定性模型判斷父母教養方式和網絡成癮在青少年發展過程中的持續性和穩定性,并通過建立交叉滯后模型的方式,分別建立父母效應模型、兒童效應模型和互惠效應模型,最后以模型比較的方式,探討父母自主支持、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的縱向影響關系。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通過整群抽樣的方式選擇北京市、河南省、四川省五所中學的初高中學生作為研究對象,進行為期六個月的兩階段追蹤測查。2019 年3 月(T 1)進行第一次數據采集,共發放問卷1570 份,有效收集1457 名學生的數據,回收率為92.80%;2019 年9 月(T2)進行第二次數據采集,127 名學生由于轉學、分班、生病等原因未參與問卷填寫,共發放問卷1443 份,取全部完成2 次調查的樣本為最終有效樣本。有效被試為1222 人,回收率為84.68%。被試在T1 時期的平均年齡為15.22±1.71 歲,在T2 時期的平均年齡為15.72±1.71 歲,其中男生 555 人(45.42%),女生667 人(54.58%),初中生 702 人(57.45%),高中生520 人(42.55%)。被試在兩個時間點的流失率是16.27%。經統計檢驗發現,有效樣本與流失樣本在T1 父母自主支持得分[t(1457)=2.15,p<0.05]和年齡 [t(1457)=-2.25, p<0.05]存在顯著性差異,有效樣本的父母自主支持得分顯著高于無效樣本的得分,有效樣本的年齡顯著低于無效樣本的年齡,在其他變量上沒有顯著差異。
2.2 研究工具
2.2.1 父母自主支持量表
采用Wang 等人(2007)修訂的父母自主支持量表,該量表在國內應用中表現出良好的信效度(唐芹 等, 2013)。該量表共12 個題項,例如“當我遇到問題的時候,父母會傾聽我的意見和觀點”。量表采用5 點計分法,1 代表“非常不符合”,5 代表“非常符合”。量表得分為所有題目得分的均分,均分越高,說明父母提供的自主支持以及子女感知到的父母自主支持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T1 和 T2 時該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是0.90 和0.90。
2.2.2 父母心理控制問卷
采用Shek(2005)編制,夏苗卉(2018)修訂的父母控制問卷中的父母心理控制中文版問卷,該問卷經過中國青少年的測量,顯示出良好的信效度。該問卷包括父親分量表和母親分量表,測量學生感知到的父母侵犯性地控制他們的想法和行為的水平。父母心理控制量表共10 個題項,例如“我的父親(母親)總是想改變我的想法”。量表采用5 點計分法,1 代表“從不這樣”, 5 代表“總是這樣”,10 道題目的均分表示父母心理控制水平,得分越高說明父母心理控制水平越高。在本研究中,T1 和T2 時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是 0.94 和 0.94。
2.2.3 網絡成癮量表
采用Young(1998)編制的網絡成癮量表(IAT),用于測量被試的網絡成癮程度。蘇文亮和林小燕(2014)對國內應用網絡成癮量表的文獻進行統計,結果顯示Young 編制的IAT 在國內使用廣泛,且信效度良好。該量表共20 個題項,例如“我覺得上網的時間比我的預期要長嗎”。量表采用5 點計分法,1 代表“完全不符合”,5 代表“完全符合”。所有題項的總分代表網絡成癮程度。總分5 0 分以下表明無網絡成癮問題;50~79 分代表輕度網絡成癮;80~100 分代表重度網絡成癮。在本研究中,T1 和T2 時該量表的Cronbach’s α 系數分別是 0.90 和 0.92。
2.3 數據處理
使用SPSS22.0 軟件進行數據預處理、描述性統計和相關分析等,采用Mplus7.0 程序進行交叉滯后模型的參數估計。參照Yu 和Shek(2018)的分析程序,為了檢驗父母自主支持(或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網絡成癮的穩定性,以及二者的相互預測關系,本研究構建了四個模型。模型1(M1)為穩定性模型,該模型只檢驗變量的自回歸效應,而不檢驗交叉滯后效應;模型2(M2)是父母效應模型,既包括M1 的自回歸效應,也包括從T1 父母自主支持(或T1 父母心理控制)到T2 網絡成癮的滯后效應;模型3(M3)是兒童效應模型,既包括M1 的自回歸效應,也包括從T1 網絡成癮到T2 父母自主支持(或T2 父母心理控制)的滯后效應;模型4(M4)是互惠效應模型,結合了M2 和M3,父母自主支持(或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在追蹤中可以相互預測。嵌套模型的相對擬合采用卡方檢驗的方式(Satorra &Bentler, 2009)。
3 結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控制與檢驗
由于父母自主支持、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都是由青少年報告,可能會產生共同方法偏差。采用Harman 單因子檢驗法進行共同方法偏差的檢驗(周浩, 龍立榮, 2004)。檢驗結果表明,在兩次測量中,特征值大于1 的因子分別有10 個、9 個,第一個因子的解釋的變異量分別為26.30%、26.67%,均小于40%的臨界標準。因此,可認為本研究不存在明顯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青少年網絡成癮檢出率及非網癮組和網癮組在各變量上的差異分析
根據網絡成癮量表(IAT)的診斷標準,將被試分為非網癮組(得分小于50 分)和網癮組(得分大于等于50 分),結果表明,T1 時期符合網絡成癮標準的被試有200 人,網癮檢出率為16.37%,T2 時期符合網絡成癮標準的被試有261 人,網癮檢出率為21.36%。采用獨立樣本t 檢驗分別考察兩組父母自主支持和父母心理控制的差異,結果表明,T1 和T2 時期網癮組的網絡成癮得分和父母心理控制得分均顯著高于非網癮組,而前者父母自主支持得分顯著低于后者。見表1。
3.3 父母自主支持、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的相關分析
如表2 所示,相關分析結果表明,T1 和T2 時期青少年網絡成癮顯著正相關(r=0.62, p<0.001),T1 和T2 父母自主支持顯著正相關(r=0.57, p<0.001),T1 和T2 父母心理控制顯著正相關(r=0.63,p<0.001)。說明網絡成癮、父母自主支持、父母心理控制在六個月內表現出一定的穩定性。另外,網絡成癮和父母自主支持、網絡成癮和父母心理控制的同時性相關顯著,前測時,前兩者的相關為-0.20(p<0.001),后兩者的相關為 0.33(p<0.001);后測時,前兩者的相關為-0.24(p<0.001),后兩者的相關為 0.29(p<0.001)。
3.4 父母自主支持、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的交叉滯后模型分析
在相關分析的基礎上,采用Mplus7.0 分別建立父母自主支持和網絡成癮、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的交叉滯后模型,以考察父母自主支持和網絡成癮、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的相互預測作用。其中,允許相同時間點不同變量的殘差相關,將性別編碼為虛擬變量(男=1, 女=0)后作為控制變量加入模型。采用極大似然法考察模型擬合情況,模型擬合和模型差異比較結果見表3。首先,檢驗兩次測量父母自主支持和網絡成癮的關系的方向,第一,相較于穩定性模型(M1),父母效應模型(M2)增加了父母自主支持到網絡成癮的交叉滯后效應,模型擬合顯著提升(Δχ2=5.70,Δdf=1, p<0.05);第二,兒童效應模型(M3)增加了網絡成癮到父母自主支持的交叉滯后效應,模型擬合相較于穩定性模型(M1)也獲得了顯著提升(Δχ2=5.63, Δdf=1, p<0.05);第三,互惠效應模型(M4)既包含了父母自主支持到網絡成癮的交叉滯后效應,也包含了網絡成癮到父母自主支持的交叉滯后效應,模型擬合顯著優于M1(Δχ2=10.96,Δdf=2, p<0.01)、M2(Δχ2=5.26, Δdf=1, p<0.05)、M3(Δχ2=5.33, Δdf=1, p<0.05)。因此,父母自主支持和網絡成癮的縱向預測關系符合互惠效應模型,即T1 父母自主支持可以預測T2 網絡成癮,T1 網絡成癮也可以預測T2 父母自主支持。

表 1 被試網絡成癮的基本情況

表 2 父母自主支持、父母心理控制與網絡成癮的相關分析

表 3 交叉滯后模型的模型擬合指標和卡方檢驗
其次,檢驗兩次測量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的關系的方向。第一,父母效應模型(M2)在增加父母心理控制到網絡成癮的交叉滯后效應后,模型擬合顯著優于穩定性模型(M1)(Δχ2=4.48,Δdf=1, p<0.05);第二,兒童效應模型(M3)與穩定性模型(M1)的擬合指數差異不大(Δχ2=1.68,Δdf=1, p>0.05);第三,互惠效應模型(M4)的模型擬合顯著優于 M3(Δχ2=4.16, Δdf=1, p<0.05),但沒有顯著提升穩定性模型以及父母效應模型的擬合指數。因此,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的關系符合父母效應模型(M2),即T1 父母心理控制可以預測T2 網絡成癮,但T1 網絡成癮不能預測T2 父母心理控制。
父母自主支持和網絡成癮之間的交叉滯后模型見圖1,為了簡化模型,未將控制變量的路徑系數顯示在模型中,性別可顯著負向預測T2 網絡成癮(β=-0.05, p<0.05)。如圖1 所示,自回歸路徑系數分別為0.56、0.61。控制了T1 父母自主支持、網絡成癮的自回歸相關和同一時間點的相關后,T1 父母自主支持可以顯著負向預測T2 網絡成癮(β=-0.05, p<0.05),T1 網絡成癮也可以顯著負向預測 T2 父母自主支持(β=-0.06, p<0.05)。
采用同樣的方式建立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之間的交叉滯后模型(見圖2),同樣,為了簡化模型,未將控制變量的路徑系數顯示在模型中,性別可顯著負向預測T2 網絡成癮(β=-0.04,p<0.05)。如圖2 所示,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在兩個測量時間點均具有較強穩定性,自回歸路徑系數分別為0.63、0.60。在控制了T1 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的自回歸相關和同一時間點不同變量的相關后,T1 父母心理控制可以顯著正向預測 T2 網絡成癮(β=0.05, p<0.05)。

圖 1 父母自主支持和網絡成癮的互惠效應模型

圖 2 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的父母效應模型
4 討論
本研究通過為期六個月的追蹤研究檢驗了父母自主支持和青少年網絡成癮以及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網絡成癮的相互預測關系,研究發現二者和網絡成癮的關系存在差異,并進一步為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干預提供依據。
交叉滯后分析結果表明,父母自主支持和網絡成癮符合互惠效應模型,父母自主支持可以預測六個月之后的網絡成癮,相反,網絡成癮也可以預測六個月之后的父母自主支持。首先,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家庭環境和青少年日益增長的自主、關系和能力等基本心理需求的匹配對于青少年的發展至關重要,如果個體賴以生存的現實環境不能滿足這些心理需要,個體將出現適應不良或者轉向其他環境尋求滿足(Ryan & Deci, 2002),而Suler(1999)提出關于網絡成癮的需要-滿足模型也認為網絡成癮是由于個體在現實中的基本心理需要無法得到滿足,轉而通過網絡使用得到直接或間接的滿足而形成的。因此,父母自主支持有助于青少年自主等基本需要的滿足,從而負向預測網絡成癮。以往研究發現,如果青少年無法感知更多的支持、關愛和溫暖,他們會有更多的耐受性、戒斷反應和無法控制網絡使用時間等癥狀(Chen et al., 2015)。其次,網絡成癮的發生一方面可能會導致青少年花費過多時間在網絡中尋求心理安慰和釋放,減少和父母的溝通交流,惡化親子關系(陳國華, 2011),同時青少年可能更難感受到父母的理解和關愛(蔣敏慧 等, 2017),他們所感知到的父母自主支持也會變少;另一方面,當孩子網絡成癮之后,父母可能會反思自己的教養方式,是否給孩子的自由度太高,而忽略了對其行為的指導和管束,導致孩子無法控制自己對于網絡的依賴,最終父母可能會調整教養方式,減少對孩子的自主支持。
研究也發現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的關系符合父母效應模型,即父母心理控制可以預測六個月后的網絡成癮,網絡成癮卻不能預測六個月后的父母心理控制。根據自我決定理論 (Ryan &Deci, 2002),當父母教養行為(如心理控制)與孩子的心理需求不匹配時,比如高心理控制的父母采用過渡干涉和內部控制的方式將自己的要求和意愿強加于子女,會與青少年自主感和獨立性的需要產生沖突,而青少年無法獨立地表達自己的想法,在生活中就更容易產生失控感和習得性無助等負面情緒。Kardefelt-Winther 等(2014)提出的網絡成癮的“失補償”理論認為網絡成癮者是為了逃避現實生活中的問題或減輕自身的負性情緒而使用網絡,尋求心理補償,并進一步導致了更為嚴重的網絡成癮行為。此結論也得到了研究者的支持,申子姣等(2012)在關于父母心理控制、父母行為控制與青少年網絡成癮的關系的縱向研究中發現父母心理控制可以預測青少年一年后的網絡成癮癥狀。因此,高父母心理控制下的青少年可能會有更大的風險依賴網絡,產生成癮現象。
而前測網絡成癮無法預測后測的父母心理控制,不符合兒童效應模型,一些研究也印證了這一結果。如馬玲玲等(2021)發現隨遷兒童的內外化問題行為無法預測父母的行為控制。趙金霞(2012)發現兒童中期焦慮癥狀無法預測一年后的親子依戀。一方面,孩子的網絡成癮行為會促進父母對自身的教養方式的反思,當父母意識到青春期的孩子處于心理和生理變化的敏感時期,過于嚴苛的管理和控制不利于孩子成長,他們會謹慎使用心理控制這樣侵犯性的教養方式。另一方面,本研究僅進行了六個月的追蹤測查,這種關系模式可能并不穩定,會隨著被試的發展動態變化。比如Lin 等(2020)收集的三次調查數據表明,在第一個時間段網絡游戲成癮和父母心理控制的關系僅符合父母效應模型,在第二個時間段卻發現網絡游戲成癮和父母心理控制符合互惠效應模型。
基于研究發現,本研究從家庭和個體兩個方面對網絡成癮的干預提供一些合理化建議。一方面,父母需要認識自主支持的重要性,也需要意識到心理控制對網絡成癮者的危害,在日常的教育中增加鼓勵性的話語,減少對青少年使用心理控制策略;另一方面,針對青少年網絡成癮的家庭干預,也需要考慮青少年網絡成癮作為壓力源對于父母心理和行為的影響,幫助青少年在鼓勵和支持下學會正確使用網絡,引導父母采用合理的教養方式,從青少年和父母兩個方面共同干預。
5 結論
(1)前后測父母自主支持和青少年網絡成癮呈顯著負相關;(2)前后測父母心理控制和青少年網絡成癮呈顯著正相關;(3)父母自主支持和網絡成癮符合互惠效應模型,即前測父母自主支持可以負向預測后測網絡成癮,前測網絡成癮也可以負向預測后測父母自主支持;(4)父母心理控制和網絡成癮符合父母效應模型,即前測父母心理控制越高,后測網絡成癮程度越高,但前測網絡成癮不能顯著預測后測父母心理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