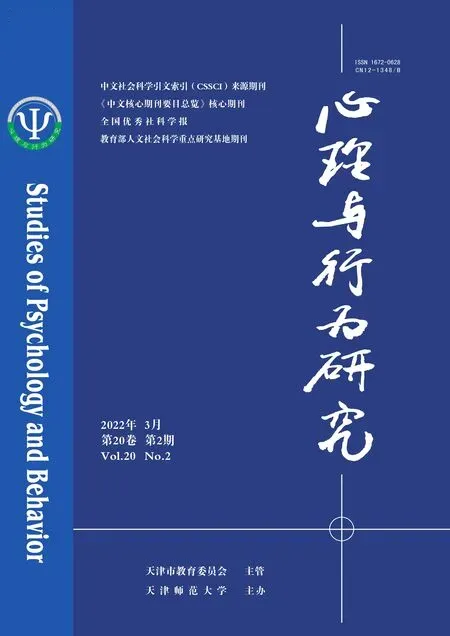社會比較對大學生公平感知的影響: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調節作用 *
徐曉惠 張耀華 徐 敏 張明浩
(魯東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問題青少年教育矯正管理研究院),煙臺 264011)
1 引言
在資源分配中,平等分配意味著對彼此的尊重(Engelmann & Tomasello, 2019)以及能夠關心他人的福利(Smetana & Ball, 2019)。人們會拒絕不平等分配,表現出不平等規避(inequality aversion)(Dawes et al., 2007)。然而,不同年齡個體對不平等的反應存在差異:4~6 歲的兒童只會拒絕對自己不利的不平等,即不利不平等規避(McAuliffe et al., 2017; Ulber et al., 2017);直到8 歲左右,兒童才開始拒絕對自己有利的不平等,即有利不平等規避(Blake & McAuliffe, 2011)。可以看出,8 歲是兒童對兩種不平等的反應出現差異的轉折年齡。這種發展轉變得益于兒童越來越能夠克服社會比較動機(social comparison)(劉文 等, 2017;Sheskin et al., 2014)。
社會比較是構成個體公平感知的主要心理機制(Baumard et al., 2013)。在公平研究中,社會比較是指相對于他人來說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劉文 等, 2017)。社會比較對個體公平感知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規避對自己不利的不平等,如4~9 歲兒童會拒絕同伴的收益多于自己的分配(McAuliffe et al., 2014);二是追求對自己有利的不平等。例如,Sheskin 等(2014)以5~10 歲兒童為研究對象,操控不平等規避的類型(優勢、劣勢)、不公平程度(高、低)以及是否付出代價(有代價、無代價),考察兒童的社會比較傾向,結果發現,當面對1∶1 和2∶3 兩個選項時,5~6 歲兒童傾向于選擇前者,即使付出一定的代價也要保證同伴的收益不多于自己。
然而,對擁有成熟公平概念的成人而言,已有研究大多關注社會比較對個體親社會行為的影響(聶婷婷, 石文典, 2020; 鄭曉瑩 等, 2015)、社會比較的方向對個體合作決策的影響(Gong &Sanfey, 2017)等,較少聚焦于公平感知這一維度。僅有一項研究探討社會比較對成人公平感知的影響,結果發現,成人會接受對自己不利的不平等,拒絕對自己有利的不平等(McAuliffe et al., 2014)。另外,相關研究缺少來自中國成人的數據。中國的傳統文化強調“中庸”,在資源分配中人們“不患寡而患不均”,力求平等。那么,社會比較會如何影響中國成人的公平感知,是否會得到與國外不同的研究結果?基于上述原因,本研究提出問題1:社會比較會如何影響成人的公平感知?
社會比較包含上行社會比較和下行社會比較兩個方向(韓曉燕, 遲毓凱, 2012)。研究發現,向上與向下的比較會以不同方式影響個體對分配結果的選擇,當個體處于劣勢地位,即進行向上比較時,個體更傾向于拒絕高度不平等的提議(Wu et al., 2011)。劉文等(2017)在研究中比較了向上與向下社會比較對6 歲兒童公平行為的影響。結果發現,在向上社會比較條件下,兒童主要是避免自己處于不利地位,而在向下社會比較條件下,兒童寧可付出一定的代價也會追求相對有利。另外,不公平程度和代價也是需要考慮的因素。不公平程度指的是個體與同伴收益的差值大小(Sheskin et al., 2014),代價指的是在不同分配結果之間進行選擇時,比較之下損失的資源(McAuliffe et al., 2015)。研究發現,不公平程度和代價均會影響兒童的公平感知:在高度不公平條件下,6 歲兒童的社會比較動機強烈,因此,即使是付出代價也要減少對方的收益,避免自己處于劣勢地位;在低度不公平條件下,兒童的社會比較動機較弱,因此,兒童傾向于選擇讓自己利益最大化的不公平選項(劉文 等, 2017)。
值得注意的是,社會比較對成人公平感知的影響與對兒童的影響并不一致。例如,McAuliffe等(2014)的研究發現,成人會接受對自己不利的不平等,拒絕對自己有利的不平等,而8 歲兒童則會拒絕兩種形式的不平等。結果產生差異的原因可能有兩點:一是在McAuliffe 等(2014)的研究中,成人面對的是真實出現的同伴,而在McAuliffe 等(2017)與 Ulber 等( 2017)的研究中,兒童面對的是匿名且未出現的同伴,可能成人更關注自己的名譽。研究發現,當面對名利博弈的困境時,人們大多會舍利取義(談晨皓 等, 2017),因為良好的名譽有利于個體獲得與他人合作的機會。然而,研究表明,5 歲兒童已經開始關注自身的名譽(Engelmann & Rapp, 2018),并能根據情境靈活使用不同的名譽管理策略(Rapp et al., 2019)。因此,如果兒童也面對真實出現的同伴,其行為決策應該與成人的表現無顯著差異。基于上述推論,對名譽的關注可能不是造成兒童和成人結果出現差異的原因。二是成人已經具有、但兒童尚未發展成熟的某種心理特征在其中起到了調節作用,其中比較重要的是主觀社會經濟地位。主觀社會經濟地位(subjective social status)是個體主觀上對自身社會經濟地位的認知(Adler et al.,2000)。進行這種推測有兩點原因:首先,成人能夠進行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評估,但是兒童還無法依據自身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經濟收入等因素與他人進行比較,從而得到一個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數據;其次,研究發現,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高低能夠調節個體的公平感知。例如,在獨裁者博弈中,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者分配給回應者的資源更多(Piff et al., 2010),類似的研究結果也見 Piff 和 Robinson(2017),以及 van Doesum 等(2017)的研究。然而,也有研究發現,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者的提議數額更高(Kornd?rfer et al.,2015; Kuang et al., 2020; Stamos et al., 2020)。例如,解曉娜和李小平(2018)使用獨裁者博弈任務,發現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者分享給同伴的資源更多。綜上所述,主觀社會經濟地位是制約個體公平感知的一個重要因素,其高低水平能夠調節個體在獨裁者博弈任務中的表現。由此,本研究提出問題2:不同主觀社會經濟地位條件下的社會比較如何影響成人的公平感知?
綜上,本研究以大學生為被試,探討社會比較對其公平感知的影響,并考察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在其中的調節作用。研究假設如下。
假設1:社會比較的方向會影響大學生的公平感知。具體而言,向上社會比較條件下,大學生會避免不利不平等;向下社會比較條件下,大學生會追求有利不平等。假設2:代價和不公平程度會影響大學生的公平感知。具體而言,有代價時,大學生傾向于追求利益最大化,無代價時,則傾向于追求有利不平等;不公平程度越高,大學生越愿意追求平等,不管這種不平等是否有利于自己。假設3: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能夠調節社會比較對大學生公平感知的影響。具體而言,相比于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大學生,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的有利不平等偏好更弱,公平感知更強。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隨機抽取三所高校的275 名本科生,經剔除無效問卷后,獲得2 6 5 份有效問卷。其中女生160 人,男生 105 人,平均年齡 19.16±0.67 歲,年齡范圍為17.37~22.28 歲。
2.2 研究工具
使用Adler 等(2000)設計的主觀社會經濟地位MacArthur 量表(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ES)來測量大學生的主觀社會經濟地位。
2.3 實驗設計
參考Sheskin 等(2014)的研究,實驗為2(社會比較:向上、向下)×2(不公平程度:低度、高度)×2(代價:無、有)×2(主觀社會經濟地位:低、高)的四因素混合實驗設計,其中社會比較、不公平程度及代價均為被試內變量,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為被試間變量。參考劉文等(2017)的研究,設計了8 種不同的分配方案,見表1。代價包含兩種水平:一種代價是“無”,不管選擇哪個選項,被試的收益不會改變;另一種代價是“有”,如果被試選擇平等選項,收益值可能減少,也可能增加,取決于社會比較的方向。不公平程度也包含兩種水平,“1”和“7”,即被試和同伴之間收益的差值。因變量是其分配行為得分。

表 1 不同社會比較方向下的分配方案
在每一種分配方案中,前邊的數字代表被試自己的收益,后邊的數字代表同伴的收益。因變量指標是被試的選擇得分。如果被試選擇讓對方的收益值不高于自己的收益值,那么得分為0 分,反之,得分為1 分。被試的得分越高,其追求有利不平等的動機越弱,公平感知越強。例如,在向上社會比較條件下(如2∶2 vs 2∶3),如果被試選擇2∶2 這種分配方案,自己沒有損失,只是損失了同伴的收益,這時被試得0 分;如果被試選擇2∶3 這種分配方案,自己和同伴都沒有損失,這時被試得1 分。在向下社會比較條件下(如1∶0 vs 2∶2),如果被試選擇1∶0 這種分配方案,自己和同伴的收益都受損,這時被試得0 分;被試如果選擇了2∶2 這種分配方案,自己和同伴都沒有損失,這時被試得1 分。該實驗目的是考察被試是否愿意付出一定的代價來追求相對有利,進而分析社會比較對大學生公平感知的影響(劉文 等,2017)。選擇這種計分方式而非直接比較每種條件下被試選擇平等方案的比例,原因如下:首先,該計分方法參考Sheskin 等(2014)和劉文等(2017)這兩項研究,為了將本研究結果與已有研究結果進行對比,沿用了與其一致的計分方法;其次,如果直接比較每種條件下被試選擇平等方案的比例,那么利己選項和利他選項都將被歸類為不平等選項,難以區分兩者的作用。
2.4 實驗程序
采用線上問卷的形式。實驗程序包含兩個階段。(1)獨裁者博弈。告訴被試他們將作為提議者和另一名不認識的同伴分配一些資源。指導語如下:“請你在自己和另一名不認識的同伴之間分配一些資源,下面每個題目都給出了兩種分配方案,請你在兩種分配方案中選擇一種,每種方案中前邊的數字代表你將獲得的收益,后邊的數字代表你的同伴將獲得的收益。請你思考后作出自己的選擇。”在實驗過程中對社會比較的方向及每種方案中選項的呈現順序進行平衡,即對于每一種分配方案被試都會進行兩次選擇。因此,在每一種實驗條件下,被試得分最低為0 分,最高為2 分。(2)主觀社會經濟地位測查。給被試呈現一張MacArthur 量表梯子階梯圖(見圖1),要求被試根據自身和家庭成員的受教育程度、職業地位和收入水平評估自己處在梯子的哪一層。

圖 1 MacArthur 量表梯子階梯圖
3 結果
對8 種實驗條件下大學生的分配行為得分進行卡方檢驗,均未發現顯著的性別差異(p>0.05)。因此,將每種條件下男生和女生的分配行為得分合并計算。
3.1 大學生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分布特點
參考高文珺(2018)對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分類,對大學生報告的主觀社會經濟地位進行統計分析。結果發現,處于中間社會地位認同(5、6 級)的人數最多,比例為53.31%,其次是中下社會經濟地位認同(3、4 級),人數比例為26.42%,然后是中上經濟地位認同(7、8 級),人數比例為12.45%,最后,低社會經濟地位認同(1、2 級)和高社會經濟地位認同(9、10 級)的人數比例均較低,分別為6.41%和1.51%。該結果與高文珺的調查結果相似。
根據上述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數據,將被試分成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組(認同數值6~10)和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組(認同數值1~5)。兩組中的人數分別為101 人(38.11%)和164 人(61.89%)。
3.2 社會比較、不公平程度和代價對大學生分配行為的影響
對被試在各個條件下分配行為得分進行統計,結果見表2。

表 2 不同條件下被試的分配行為得分(M±SD)
3.2.1 社會比較、不公平程度、代價及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對大學生分配行為的影響
以大學生的分配行為得分為因變量,進行2(社會比較:向上、向下)×2(不公平程度:低度、高度)×2(代價:無、有)×2(主觀社會經濟地位:低、高)的混合方差分析。結果發現,社會比較的主效應顯著,F(1, 263)=1613.83,p<0.001,η2p=0.86,當進行向下比較時,被試的得分更高;不公平程度的主效應顯著,F(1, 263)=6.46,p=0.012,η2p=0.02,當不公平程度較低時,被試的得分更高;代價的主效應顯著,F(1, 263)=7.77,p=0.006,η2p=0.03。當有代價時,被試的分配行為得分較高。
社會比較、不公平程度和代價三者之間交互作用顯著,F(1, 263)=4.25,p=0.04,η2p=0.02。進行簡單簡單效應分析,考察社會比較在不公平程度和代價各個水平上的差異。進行配對樣本t 檢驗發現,在不公平程度和代價的4 個水平上,社會比較的簡單簡單效應均顯著,被試進行向下社會比較時的得分均顯著高于向上社會比較時的得分。結果分別為:低度不公平無代價條件下(M向上社會比較=0.23, SD=0.53; M向下社會比較=1.77, SD=0.55),t(264)=29.95,p<0.001,Cohen’s d=2.85;低度不公平有代價條件下(M向上社會比較=0.28, SD=0.58; M向下社會比較=1.88, SD=0.38),t(264)=33.60,p<0.001,Cohen’s d=3.26;高度不公平無代價條件下(M向上社會比較=0.12, SD=0.39; M向下社會比較=1.88, SD=0.37),t(264)=43.85,p<0.001,Cohen’s d=4.63;高度不公平有代價條件下(M向上社會比較=0.15, SD=0.45; M向下社會比較=1.86, SD=0.42),t(264)=38.00,p<0.001,Cohen’s d=3.93。上述結果說明,當面對有利于自己和平等選項之間的抉擇時,被試傾向于選擇平等選項,而非追求相對有利。
同時,社會比較和不公平程度之間的交互作用顯著,F(1, 263)=20.57,p<0.001,η2p=0.07。為了能更為清晰地分析社會比較在不公平程度和有無代價條件下對分配行為的影響,進一步分析社會比較的不同水平上的簡單交互作用。結果表明,在向上社會比較條件下,不公平程度和代價之間的簡單交互作用不顯著。在向下社會比較條件下,不公平程度和代價之間的交互作用顯著,F(1, 264)=12.73,p<0.001,η2p=0.05。對不公平程度和代價的交互作用進行簡單效應分析,配對樣本t 檢驗發現,在低度不公平條件下,有無代價兩者之間差異顯著,t(264)=3.68,p<0.001,Cohen’s d=0.23,即有代價條件下的得分(M=1.88, SD=0.38)顯著高于無代價條件下的得分(M=1.77,SD=0.55),說明相比于獲得相對優勢,被試更想保證自身收益最大化。在高度不公平條件下,有無代價條件下被試的得分差異不顯著,被試在兩種條件下都傾向于選擇平等選項。可以看出,大學生主要關注自身收益,而不是自己和同伴之間的收益比較。在無代價條件下,高低不公平程度下的分配行為得分存在顯著差異,t(264)=3.68,p<0.001,Cohen’s d=0.23,即高度不公平條件下的分配行為得分(M=1.88, SD=0.37)顯著高于低度不公平條件下的分配行為得分(M=1.77, SD=0.55),也就是說,只有在低度不公平,雙方資源差距較小時,被試才愿意讓自己處于相對優勢。在有代價條件下,高度不公平程度下的分配行為得分差異不顯著,被試在兩種不公平條件下都傾向于選擇平等選項。可以看出,大學生具有強烈的平等性偏好,而非追求相對優勢。
3.2.2 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對大學生公平感知的影響
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主效應不顯著,F(1,263)=0.14,p>0.05。代價和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交互作用顯著,F(1, 263)=4.16,p=0.042,η2p=0.02。進行簡單效應分析,結果發現,代價在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個體中的效應顯著,F(1, 163)=14.46,p<0.001,η2p=0.08。無代價時被試的分配行為得分(M=3.97, SD=0.07)低于有代價時的分配行為得分(M=4.23, SD=0.07)。代價在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個體中的效應不顯著(M無代價=4.04, SD=1.10; M有代價=4.08, SD=1.08),F(1, 100)=0.25,p=0.619。具體結果見圖2。

圖 2 不同主觀社會經濟地位下代價對被試分配行為的影響
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與社會比較之間的交互作用邊緣顯著,F(1, 263)=3.08,p=0.080,η2p=0.01。進行簡單效應分析發現,在向下社會比較條件下,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M=7.51, SD=1.13)比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M=7.19, SD=1.81)分配行為得分更高,F(1, 263)=3.23,p=0.073,η2p=0.01。在向上社會比較條件下,高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的分配行為得分差異不顯著(M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0.68, SD=1.49; M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0.93, SD=1.81),F(1, 263)=1.47,p>0.05。具體結果見圖3。

圖 3 不同社會比較條件下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對被試分配行為的影響
4 討論
4.1 社會比較、不公平程度及代價對大學生公平感知的影響
社會比較無處不在,影響個體生活的方方面面。研究發現,社會比較會影響大學生的公平感知。向上的社會比較會使個體處于不利不平等的位置,向下的社會比較則會使個體處于有利不平等的位置。相比于向下社會比較,在向上社會比較條件下,大學生的得分更低,而且在不公平程度和代價的四個水平上均發現相同的結果。說明大學生具有強烈的不利不平等規避傾向,他們進行決策時的主要動機是為了避免相對不利。該結果與以往的研究結果一致,即無論兒童還是成人,都不喜歡自己處于劣勢地位(Paulus & Essler,2020; Sheehy-Skeffington & Thomsen, 2020),5~6 歲的幼兒甚至愿意付出一定的代價來阻止同伴的收益多于自己(Sheskin et al., 2014)。
代價和不公平程度也會影響大學生的公平感知。相比于無代價條件(如2∶1 vs 2∶2),在有代價條件下(如1∶0 vs 2∶2),大學生的得分更高,即更愿意選擇讓自身和同伴均獲益更大的平等選項,而非有利于自己的選項。不過,進一步的分析表明,代價的這種效應只在向下社會比較低度不公平條件下存在,即無代價時,被試大多追求相對有利,而有代價時,被試大多選擇平等選項,即不愿意承擔一定的成本來獲取相對優勢。該結果說明,大學生更加關注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非獲取相對優勢。造成這一結果可能有兩點原因:首先,當自己處于優勢位置成為他人妒忌的對象后,人們不僅會體驗到自信、愉快等積極情緒,也會產生焦慮、壓力等消極情緒(劉得格 等, 2018; Parrott, 2016),因此,被妒忌者為了緩解這種矛盾體驗更有可能和妒忌者分享資源(Yu & Duffy, 2016)。其次,中國的傳統文化講究均衡,人們普遍認同“木秀于林,風必摧之”,“槍打出頭鳥”等,因此,即使有機會獲得比同伴更多的收益,即不公平程度較高時,大學生也可能會傾向于選擇平等,從而維持一種相對和諧的人際關系(吳燕, 周曉林, 2012)。
4.2 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在社會比較影響大學生公平感知中的調節作用
社會認知視角(social cognitive perspective)的觀點認為,高社會經濟地位個體比較關注自我,認為人的行為與自身的相關性更大,傾向于做出有利于自身的行為;而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比較關注外部情境,需要依賴他人才能掌握生活資源,更有可能做出有利于他人的行為(Piff &Robinson, 2017)。因此,高社會經濟地位者比低社會經濟地位者具有更低的利他行為傾向(Kraus et al., 2012)。
研究發現,在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中,代價的效應顯著,即有代價時被試的得分顯著高于無代價時;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大學生都傾向于選擇平等選項,有無代價并未影響其分配行為。另外,在向下社會比較條件下,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的得分更高;在向上社會比較條件下,高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的得分差異不顯著。上述結果說明,相比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的大學生其有利不平等偏好較弱,他們不僅關注自身獲益是否最大化,同時也愿意讓同伴的獲益增加,體現出一定的利他性。這與國內的一項以兒童為研究對象的結果一致(Chen et al., 2013),同時也支持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更愿意進行利他性分享(Piff et al., 2010; van Doesum et al., 2017)這一觀點。然而,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在向下社會比較條件下愿意追求有利不平等,且未表現出更加慷慨的行為,這一結果支持社會認知視角,但也與以往的某些研究結論不一致。例如,鄭曉瑩等(2015)的研究發現,僅僅通過向下社會比較讓個體在心理上產生“達”的感覺,就能讓個體展示出更多的助人行為。同時,研究者認為,高社會經濟地位個體擁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和對自身更強的控制感,應該會比低社會經濟地位個體展示出更多的利他性分享行為(Whillans et al., 2017)。究其原因,可能是本研究中選擇平等選項需要被試付出的代價值“1”和“7”并不高,均沒有達到高社會經濟地位個體的心理閾限,不構成高成本。有研究表明,當親社會行為的成本增高時,高經濟地位個體比低經濟地位個體更容易表現出親社會行為(Kornd?rfer et al., 2015)。
4.3 存在的問題及研究展望
本研究存在以下問題。首先,本研究中的同伴是一個未出現的陌生人,這可能會導致被試的社會比較動機較弱。以往研究發現,相比于朋友,當面對陌生人時,個體知覺到的社會比較感較弱(Jones & Rachlin, 2006)。其次,雖然主觀社會經濟地位更能預測個體的社會行為,不過如果能再輔以客觀社會經濟地位的數據,例如收入、職業和受教育程度(楊沈龍 等, 2020),在解釋個體公平感知方面可能更具有說服力。
5 結論
(1)社會比較、不公平程度和代價均會影響大學生的公平感知,向上社會比較時,大學生會避免自身處于劣勢;向下社會比較時,他們不會追求有利不平等。不公平程度較高時,大學生的社會比較動機更強烈。大學生不愿意承擔一定的成本來獲取相對優勢,他們更加關注自身利益是否最大化。(2)主觀社會經濟地位能調節社會比較對大學生公平感知的影響:低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有利不平等偏好更弱,公平感知更強;高主觀社會經濟地位大學生愿意追求有利不平等,公平感知更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