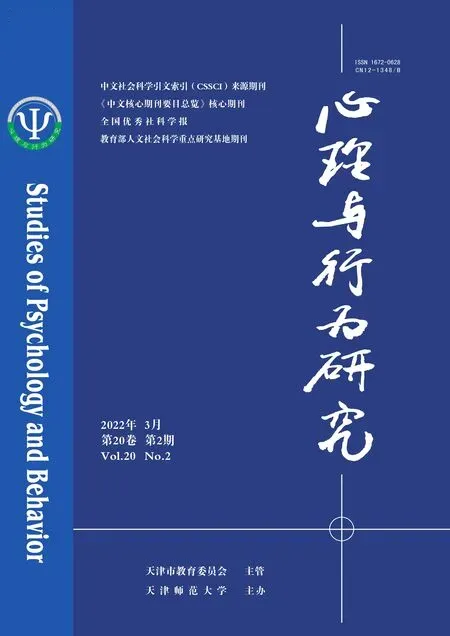人格對幼兒白謊行為的影響:“冷”“熱”執行功能的并行中介作用 *
孫云瑞 韓映虹 呂 勇 劉 芳
(1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天津師范大學心理與行為研究院,天津 300387) (2 天津師范大學心理學部,天津300387) (3 學生心理發展與學習天津市高校社會科學實驗室,天津 300387) (4 天津師范大學教育學部,天津 300387)
1 引言
白謊(white lie),即善意的謊言,指以避免給聽者帶來消極情緒或以他人利益為出發點而說的謊(Bok, 1978; Erat & Gneezy, 2012)。白謊的產生推動了兒童社會性的發展,對兒童白謊行為的研究,為研究者了解兒童如何與他人互動并形成積極的社會關系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已有研究表明,3 歲兒童已能掩飾自己的真實情緒并做出白謊行為,隨著年齡的增長其白謊行為迅速發展(Heyman et al., 2020)。在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不沖突的情境下,大部分兒童會為了他人的利益而做出白謊行為(張娜, 劉秀麗, 2014; Heyman et al.,2020)。在自我利益與他人利益沖突的情境下,即使白謊會損失兒童一部分自我利益,仍有一部分兒童選擇白謊行為(Nagar et al., 2020)。這些有白謊行為的兒童是否共同具有某種人格特質?這是本研究擬探討的問題。
1.1 人格與白謊的關系
已有研究表明,具有特質積極共情(trait positive empathy)(岳童 等, 2021)的個體更傾向于理解和感受他人心理狀態并主動與之產生情感共鳴,而做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呂勇, 孫云瑞,2022)。因此,特質積極共情被視為高利他性的人格特質(岳童 等, 2021)。兒童白謊行為的前提建立在其充分理解說真話會給聽者帶來消極情緒反應,而說謊話會給聽者帶來積極情緒反應的基礎上(Broomfield et al., 2002)。那么,兒童人格中的積極特質是否也能預測白謊行為?已有研究多集中于人格與親社會行為關系上,并發現大五人格中的親和性、宜人性及情緒穩定性等特質是預測個體幫助、捐贈、合作等親社會行為的重要指標(Kline et al., 2019; Smillie et al., 2019)。外傾性、神經質等人格因素也可用來預測其謊言發生的可能性(Sarzyńska et al., 2017)。然而,現有的研究常把白謊與黑謊(即為隱瞞錯誤或避免因自身的過失受到懲罰而說的謊)(Bok, 1978)等同起來,將說謊行為視為兒童問題行為之一,認為說謊與反社會人格特質密切相關(Shao & Lee, 2017)。因此,兒童的白謊行為是一種特殊的親社會行為,除上述與親社會或謊言有關的特質外,還有哪些人格特質可預測幼兒的白謊行為的發展仍屬未知。據此,本研究提出假設1:人格特質對兒童的白謊行為具有預測作用。
1.2 人格與“冷”“熱”執行功能的中介關系
執行功能(executive function, EF)是指個體在實施目的行為過程中以動態、靈活的方式協調多個認知子系統活動的復雜認知過程(Miyake et al.,2000),它有效地協調著個體說白謊時復雜的心理活動。因此,基于白謊行為發生的心理機制,本研究首先關注“冷”執行功能(Zelazo & Müller,2002)這一中介變量。“冷”執行功能與背外側前額皮層(dorso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相聯系,即無情感動機卷入的純認知。作為執行功能的一種,“冷”執行功能可預測謊言發生的頻率,并影響個體維持謊言的能力(Talwar et al., 2017)。白謊代表著相互矛盾的道德和社會規則,兒童要想成功地說謊,需要在頭腦中同時存儲真實和錯誤的信息,抑制住自己報告真實信息的反應趨向,并不斷地在真實信息與虛假信息之間靈活轉換(Williams et al., 2016)。因此,白謊行為的發生和維持與執行功能的三個子成分(抑制控制、工作記憶和認知靈活性)息息相關(Goldstein &Naglieri, 2014)。但以上的研究將執行功能視作以“冷”執行功能為單一的認知結構。人格是影響個體認知能力的重要因素(趙宇晗, 余林, 2014),而執行功能作為個體進行認知活動所必須運用的高級認知功能,受到人格的影響。已有研究發現人格與執行功能有一定相關性,如執行功能與外傾性、盡責性呈正相關,但與神經質呈負相關(Bell et al., 2020; Krieger et al., 2020)。且人格對執行功能具有一定預測作用,如神經質和責任性分別負向和正向預測執行功能中工作記憶子成分等(Dima et al., 2015)。但對于兩者關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特殊人群,如注意力缺陷障礙人群和老年人等,鮮見對健康人群,尤其是幼兒的研究。3~6 歲是兒童執行功能高速發展的關鍵時期(Zelazo & Müller, 2002),同時也是其人格形成的重要時期(楊麗珠 等, 2015),幼兒的哪些人格特質可預測其“冷”執行功能的發展仍屬未知。據此提出假設2:“冷”執行功能在人格對白謊行為的預測中起到中介作用。
與純認知、去情景化的任務誘發的“冷”執行功能相比,涉及到情感卷入和攝入動機誘發的“熱”執行功能(Zelazo & Müller, 2002)也是白謊發生的動力源泉。“熱”執行功能與眶額皮質(orbitofrontal cortex)相聯系,即受情緒動機激活的認知。兒童是否做出白謊行為不僅需要兒童對說謊后聽者的反應進行認知評估,還需要動機和情緒的共同參與。因此,本研究還關注了“熱”執行功能這一中介變量。一方面,若要發生白謊行為,個體需要理解他人的情緒情感,并試圖減輕他人的痛苦(呂勇, 孫云瑞, 2022; Erat & Gneezy,2012)。這一過程需要兒童有高度的情感卷入,這正與“熱”執行功能的特征高度相似;另一方面,白謊行為的發生也受到復雜的心理機制驅動,如親社會愿望、聲譽期待等(Berman & Silver,2022; Heyman et al., 2020),這些動機也與“熱”執行功能的攝入動機相關。“熱”執行功能并非完全剝離認知成分,因此“熱”執行功能并沒有清晰的成分劃分(李紅 等, 2004)。人格影響個體認知能力的同時也影響其情緒情感體驗(Krieger et al., 2020)。Umemoto 和 Holroyd(2016)的研究發現情緒穩定性特質高的個體在由情緒驅動的“熱”執行功能的任務轉換中表現更差。Dima 等(2015)發現高外傾性個體更容易注意到新的刺激和信息,認知轉換性更好。據此提出假設3:“熱”執行功能在人格對白謊行為的預測起到中介作用。
關于“冷”“熱”執行功能是否存在關聯的實證研究很少見。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兩者的區別,并認為兩者為執行功能的兩個方面(Miyake et al., 2000)。雖兩者在3~4 歲兒童身上表現出一定的不同步,但在兒童的整個學前期兩者是相輔相成、同步發展的,并無相互預測關系(李紅 等,2004)。一些研究指出,可將“冷”“熱”執行功能的關系轉化為心理理論與執行性功能的關系來研究,因為兩者都涉及是否理解和推測他人信念等更為復雜的心理過程(李紅 等, 2004; Russell et al., 1991)。但心理理論與執行功能之間到底誰為前提尚存在爭議,很多研究認為兩者是相互促進且同步發展的(Hughes, 1998; Sai et al., 2021)。Frye 等(1998)提出認知復雜及控制理論(cognitive complexity and control theory),認為心理理論和執行功能是一種平衡式并行發展的關系,且兩者之間有共同的心理成分。基于以上研究,本研究提出假設4:“冷”“熱”執行功能間相互獨立,二者在人格對白謊行為的預測關系中起并行中介作用。
綜上所述,本研究的目的是在分析人格特質對兒童白謊行為預測作用的差異性基礎上,探討“冷”“熱”執行功能在人格與白謊行為中的并行中介作用(假設模型見圖1),以揭示人格影響白謊行為的內部機制。

圖 1 假設模型圖
2 研究方法
2.1 被試
采用整群抽樣,抽取天津市三所幼兒園9 個班221 名3~6 歲幼兒作為測試對象。測試前與其主要監護人簽訂知情同意書。正式施測前篩除有語言障礙的幼兒2 名和色弱的幼兒1 名。最終選取218 名幼兒作為研究對象,平均月齡為53.83±1.09月;其中男孩103 名,女孩115 名。
2.2 研究工具
2.2.1 中國韋氏學齡前兒童智力測驗量表
采用林傳鼎和張厚粲(1986)修訂的中國韋氏學齡前幼兒智力測驗量表(WPPSI)中的詞匯測驗,獲得每名幼兒的言語能力分數。測試中要求幼兒對每個詞進行“是什么”的解釋,共22 題。根據幼兒解釋程度進行2 分、1 分及0 分三種評分,連續5 次錯誤則停止測試,總分范圍為0~44 分。
2.2.2 幼兒人格發展教師評定問卷
采用楊麗珠等(2015)編制的幼兒人格發展教師評定問卷,問卷包括:智能特征、外傾性、親社會性、認真自控、情緒穩定性五個維度,15 個特質,共60 題,采用Likert 5 點計分,由教師對幼兒日常行為是否符合描述情況打分,從“非常不符合”到“非常符合”分別計1~5。其中 13、17、22、32、40、42、51、55、58 題為反向計分題。在本研究中各維度的內部一致性信度分別為:0.93、0.90、0.93、0.93、0.81。 驗證性因素分析表明,問卷結構的擬合指數良好(χ2/df=3.14,CFI=0.88, TLI=0.88, RMSEA=0.05)。
2.3 測試任務
2.3.1 “冷” “熱”執行功能測試
本研究共包含5 項任務,其中任務1、2、3 測試兒童的“冷”執行功能,任務4、5 測試兒童的“熱”執行功能。每名兒童均需完成以下測試,任務的呈現順序隨機。
任務1:手部游戲任務(抑制控制子成分)。該任務出自Hughes(1998)的手部游戲(handgame)。任務中要求兒童出示與主試相反的手部動作(手掌、拳頭),如,主試出手掌,兒童就出拳頭。正式測試中主試先出什么手勢是隨機的,該任務共進行16 次正式測試,并記錄兒童正確出示相反的手部動作的次數。
任務2:動物游戲任務(工作記憶子成分)。該任務出自陸露等(2018)的工作記憶廣度任務。測試中首先呈現給幼兒一些動物圖片,每個動物旁邊都有一個數字與之相對應,動物與數字同時呈現。要求兒童在規定時間內注視并記憶動物與其對應的數字。呈現結束后,動物消失,只剩下相應的數字,要求兒童回憶剛才相應數字對應的動物是什么,根據其回答的正確性來計分。共隨機呈現15 次數字,兒童每正確回答出某個數字對應的動物,計1 分,滿分為15 分。
任務3:維度變化卡片分類任務(認知靈活性子成分)。該任務出自Frye 等(1995)的卡片分類任務(dimensional change card soring, DCCS),主試向兒童呈現不同顏色、形狀的圖案卡片。圖案為黃色的圓形、紅色的圓形、黃色的三角形和紅色的三角形。轉換前階段,要求兒童按照顏色對一組卡片進行分類;轉換后階段,要求兒童按形狀對另一組卡片進行分類。實驗轉換前后各進行16 次,其中8 次是按顏色分,8 次按形狀分,并按照ABBA 平衡順序。只記錄兒童在轉換后階段中的表現。如按形狀分類,對一組得1 分,否則得0 分。
任務4:找貼畫任務。該任務源于陳昱翀等(2017)的找貼畫任務。主試要求兒童在分別放有5 張貼紙的5 個不同顏色的盒子中找貼畫。兒童每找到一張貼畫,不論對錯,主試都會給兒童積極的反饋,并告知兒童若把所有的貼畫都找到,便會得到一個更大的獎勵。每次找到貼畫后的空盒主試都會再放入其他4個盒子中并打亂順序。任務總共進行15 個試次,主試記錄兒童犯錯的次數。得分通過公式“15-X”(X 為兒童找貼畫的次數)換算成0~10 分。
任務5:窗口任務。該任務源于Russell 等(1991)的窗口任務(windows task)。本測試中主試與兒童坐在測驗桌同側,助手坐在對側,要求兒童和助手進行比賽贏貼畫的游戲。首先主試向兒童呈現兩個“開有窗口的盒子”,該盒子里的內容只有兒童能看到,而助手看不到。隨后主試將一張貼畫投入其中一個盒子,并告知兒童:“助手不知道貼畫會放在哪個盒子里,請你向她指出貼畫所在位置,若你所指的盒子里有貼畫,則你贏;若你所指的盒子里是空的,則助手贏。贏者獲得一張貼畫。”主試與兒童進行兩次練習后,兒童完成8 次任務。然后將獎勵要求改為相反規則。記錄在獎勵目標發生改變后兒童贏得的貼畫數。
2.3.2 白謊行為測試
采用最后一輪游戲范式(final round of game paradigm)(Talwar et al., 2017)對幼兒進行個別施測。幼兒和主試A 進行棋盤游戲。棋盤上印有36 張卡通圖(共有6 種卡通圖,每種卡通圖在棋盤的不同位置上各重復出現6 次)。骰子的6 個面各印有一張與棋盤相對應的卡通圖。主試A 與幼兒共進行5 輪棋盤游戲,每輪游戲輪流擲骰子,看誰的棋子在棋盤上占領地最多,誰就獲勝并得到一枚代幣。前4 輪主試A 故意輸給幼兒。最后一輪游戲中,主試A 借故離開,并請主試B 代替其繼續與幼兒進行游戲。主試B 操控最后一輪游戲,仍讓幼兒贏。但游戲結束后主試B 與幼兒商量,希望幼兒能告訴主試A“是主試B 贏了最后一輪游戲”,這樣主試B 也能獲得一枚代幣。幼兒回應后,主試A 回到房間詢問幼兒“是誰贏了最后一輪游戲”。基于先前研究(Williams et al.,2016),為檢查幼兒是否真正理解白謊情境,并確保幼兒欺騙性陳述與其謊言保持一致,主試A 會追問幼兒三個問題“你一共贏了幾次?姐姐(哥哥)贏了幾次?誰應該得到最后一個幣?”當第一輪問題中幼兒對主試A 回答“主試B 贏得了最后的比賽”且對第二輪的3 個追問問題的回答與其謊言相一致,則編碼為白謊,計1 分;否則編碼為真話,計0 分。
2.4 施測過程
測試采用個別施測,所有任務均在幼兒園安靜的活動室內完成。由于被試年齡較小,對每名幼兒的測試分兩階段進行,兩個階段間隔一周。一個階段對其進行智力測驗量表(WPPSI)中的詞匯測試和白謊行為測試;另一階段對其進行執行功能的五個任務測試。為減少順序效應和疲勞效應對結果的影響,執行功能的五個任務的測試順序均隨機呈現,且每個任務間都安排幼兒休息。
2.5 數據處理與統計分析
使用SPSS26.0 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卡方檢驗、Pearson 相關分析;使用Mplus8.0 對數據進行WLSMV 估計,檢驗白謊行為與其他變量間的關聯性,并建立結構方程模型檢驗假設的中介效應。
3 結果
3.1 幼兒人格、“冷”“熱”執行功能與白謊行為的相關
將五個任務的得分分別轉化為正確率,進行標準化處理,并將前三個任務的總分的平均分作為“冷”執行功能的得分;后兩個任務的總分的平均分作為“熱”執行功能的得分。由于不同年齡幼兒說白謊的比例存在差異(χ2=29.64, p<0.001),幼兒的執行功能和白謊行為會受其語言的流暢性和速度的影響(Poland et al., 2016),因此,本研究將年齡和言語能力作為控制變量。由于白謊行為屬于二分變量,采用Mplus8.0 進行WLSMV 估計,了解幼兒的白謊行為與各變量的相關和偏相關關系。控制年齡和言語后,幼兒的人格特質中除認真自控與“熱”執行功能呈顯著負相關,與“冷”執行功能和白謊行為呈顯著正相關外,智能特征、外傾性、親社會性與其“冷”“熱”執行功能和白謊呈顯著正相關;幼兒的“冷”“熱”執行功能和白謊呈顯著正相關(見表1)。
3.2 “冷”“熱”執行功能的并行中介作用
使用Mplus8.0 檢驗中介效應。前人的研究表明更好的檢驗多重中介的方法是bootstrapping method(Cheung, 2007)。此外,因結果變量為類別變量,故采用WLSMV 估算法,這一方法是針對類別變量更為穩健的估計方法(方杰 等, 2017)。建立以人格各維度為自變量,白謊為因變量,“冷”執行功能(二階潛變量)和“熱”執行功能為并行中介變量,年齡和言語能力為控制變量的結構方程模型。結果發現測量全模型擬合較好:χ2/df=1.06,p=0.39,CFI=0.99,TLI=0.99,RMSEA=0.02,90% CI=[0.00, 0.06]。
對模型路徑進一步分析發現(見圖2),智能特征(β=0.24, p<0.01)和親社會性(β=0.43,p<0.01)可正向預測白謊行為。智能特征(β=0.35,p<0.05)和認真自控(β=0.15, p<0.05)可正向預測“冷”執行功能;“冷”執行功能正向預測白謊行為(β=0.37, p<0.05)。外傾性(β=0.19, p<0.05)和親社會性(β=0.18, p<0.05)可正向預測“熱”執行功能,認真自控可負向預測“熱”執行功能(β=-0.10, p<0.05),“熱”執行功能(β=0.29,p<0.01)可正向預測白謊行為。

圖 2 “冷”“熱”執行功能在人格特征與白謊行為間的中介作用
在上述分析的基礎上,采用偏差校正百分位Bootstrap 分析檢驗中介效應的顯著性。在原始數據(n=218)中,重復隨機取樣1000 次,計算中介效應的平均路徑值和路徑系數95%的置信區間,檢驗全模型中各中介路徑的顯著性。控制了年齡和言語能力,各路徑的效應值、95%置信區間上下限如表2 所示。

表 1 幼兒人格、“冷”“熱”執行功能與白謊行為的描述統計及相關、偏相關分析(n=218)
由表2 可知,“冷”執行功能在智能特征和白謊行為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0.13,95%置信區間為[0.03, 0.27],即智能特征可直接正向影響白謊行為,也可通過正向影響“冷”執行功能進而影響正向白謊行為;“熱”執行功能在親社會性和白謊行為間發揮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0.05,95%置信區間為[0.01,0.12],即親社會性可直接正向影響白謊行為,也可通過正向影響“熱”執行功能進而正向影響白謊行為;“熱”執行功能在外傾性和白謊行為間發揮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為0.06,95%置信區間為[0.00, 0.14],即外傾性通過正向影響“熱”執行功能進而正向影響白謊行為;“冷”“熱”執行功能在認真自控和白謊行為間發揮完全并行中介作用,中介效應值分別為0.06 和-0.03,95%置信區間分別為[0.01, 0.13]和[-0.07, -0.01],即認真自控可通過正向影響“冷”執行功能和通過負向影響“熱”執行功能進而影響白謊行為。以上各間接效應估計值的95% 的置信區間不包括0,即中介效應顯著。

表 2 模型中特定間接效應檢驗結果檢驗的 Bootstrap 分析
4 討論
4.1 智能特征和親社會性對幼兒白謊行為的直接預測
本研究發現智能特征對兒童的白謊行為具有正向預測作用。Zelazo(2015)的研究支持了本結論。智能特征高的幼兒往往表現出頭腦的反應靈敏、記憶力好,對環境的適應力強,這些特征促進了其白謊行為的發生和維持。親社會性是幼兒人格中的道德成分,與白謊的親社會性動機緊密相聯。親社會性人格特質對幼兒的白謊行為具有預測作用,這一結果得到Kline 等(2019)研究結果的支持。進入幼兒園后,幼兒開始出現合作、分享、同情等親社會行為,標志著其社會化水平的發展。其親社會性經歷了由他控向自控,由絕對的自我中心發展到他人中心,最后過渡到關系中心的過程(楊麗珠 等, 2015; Williams et al., 2016)。因此,幼兒人格中智能特征和親社會性的發展促進了其白謊行為的發展。
4.2 “冷”“熱”執行功能在人格特質與白謊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
本研究發現,“冷”執行功能在智能特征和白謊行為間起部分中介作用。高智能特征的兒童探索求知欲強,思維靈活性較強,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強(楊麗珠 等, 2015),其執行功能中工作記憶和抑制控制越好,發生白謊的可能性越大(Talwar et al., 2017; Williams et al., 2016)。本研究還發現,“熱”執行功能在外傾性與白謊間、親社會性與白謊間起顯著中介作用。Sarzyńska 等(2017)的研究支持了本研究結論,該研究發現社交能力和外傾性較高的人在社交互動中說謊更多。高外傾性和高親和性的幼兒在集體生活中表現出更多的熱情友善、喜歡與他人合作的特質(楊麗珠 等,2015)。這種特質與情感卷入度較高的“熱”執行功能息息相關(Poland et al., 2016)。白謊行為的發生除了認知基礎外,還需情緒和動機的誘發(Nagar et al., 2020)。
本研究還發現,兩種執行功能均在幼兒人格中的認真自控對白謊行為的影響中發揮中介作用,但認真自控增強“冷”執行功能、減弱“熱”執行功能。其原因在于:幼兒人格中的認真自控與大五人格中的責任性類似,主要包括自我調節能力、抑制不適宜反應、集中與轉移注意的能力(楊麗珠 等, 2015)。認真自控高的幼兒的行為控制能力較好,而這一能力促進了“冷”執行功能的發展,進而使得幼兒在白謊情境中更好地抑制住自己想要說出實情時的情緒反應(Sai et al., 2021; Talwar et al., 2017)。相反,認真自控性較弱的幼兒,面對理性的道德準則和感性的情感因素沖突的白謊情境時,其情感容易被卷入,表現出更多的沖動任性,延遲滿足能力較弱(Poland et al., 2016)。因此,自我控制能力越弱的幼兒,其“熱”執行功能越好,越容易產生白謊行為。
4.3 研究局限與未來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需要改善和進一步探討的問題。第一,3~6 歲是兒童的人格形成和發展的重要階段(楊麗珠 等, 2015),由于橫斷面研究的局限,本研究只將人格看作一個靜止的因素來探討其對幼兒執行功能和白謊行為的影響,根據認知-情感人格系統理論(cognitive-affective personality system)(Mischel & Shoda, 1995),兒童白謊行為發生后其獲得的社會評價反饋從一定層面上也可能反過來影響其人格的發展,未來的研究可考慮把個體置于動態的社會情境中來考察三者的關系。第二,本研究僅控制了幼兒的年齡和言語能力兩個變量,但幼兒白謊行為受諸多因素影響,如兒童自身的移情能力、心理理論,家庭及社會情境等因素。幼兒自身因素也對白謊行為起到調節變量的作用,未來的研究可以綜合探討中介和調節變量,分析二者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以期更全面地揭示人格對白謊行為的作用機制。
5 結論
(1)智能特征和親社會性可直接正向預測白謊行為;(2)“冷”執行功能可部分中介智能特征對白謊行為的間接預測關系;“熱”執行功能可部分中介親社會性對白謊行為的間接預測關系;外傾性對白謊行為的預測作用完全以“熱”執行功能為中介;認真自控對白謊行為的預測作用完全以“冷”和“熱”執行功能為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