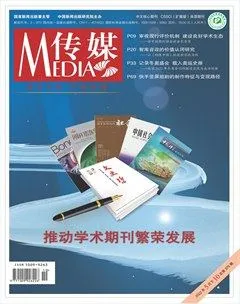研究口語傳播特性 提升用戶溝通能力
江傳鋒
隨著媒介形式的不斷變遷,信息傳播的方式持續發生著變化。社交媒體正以燎原之勢改變著傳統信息傳播的手段,逐漸形成基于用戶關系的信息生產模式。即用戶作為社交媒體中口語傳播的主體,他們不再是信息的被動接收者,而作為主動參與者能夠發起并參與信息傳播,并與其他用戶產生信息交互。社交媒體上的口語傳播正編織成以用戶為結點的開放式傳播網絡,形成新的社交形態。由王媛所著的《社交媒體時代口語傳播的交互性研究》一書,以新媒體時代背景為依托,以口語傳播為主要研究對象,通過六個章節展開詳細論述,通過梳理口語傳播的歷史進程,歸納當下社交媒體環境下口語傳播的形態特征,幫助讀者深入認識基于社交媒體構建起的新傳播業態,為社交媒體用戶提升溝通能力提供豐富的理論和實踐指導。
社交媒體中口語傳播交互性的五種實踐形態。在口語時代,信息的傳播與意見的交流渠道單一,一則通過公共演講的方式進行宣講,二則通過傳統的大眾傳播媒介,以公共表達的形式將信息傳達給大眾。隨著媒介的發展和變革,口語傳播也新衍生出不同以往的特點。不同于傳統口語傳播的單向性和權威性,交互性成為社交媒體最具代表性的特征。無論是以匯集各方資源,以數據和用戶為核心的“平臺型”媒體,還是以人際關系為紐帶的“社群型”媒體,抑或是以滿足人們日常生活需求為目的的“工具型”媒體,以及無需以獨立形式存在,依附于各類媒體形態中,只為用戶社交需求提供服務的“泛在型”媒體。這都意味著一個縱橫交錯、盤根錯節的社交媒體網絡生態正在形成,并不斷更新著人類社會的交往交流方式。但是,受限于各類社交媒體的功能性差異,口語表達和傳播形式往往存在差異性,此書作者將社交媒體中口語傳播的實踐形態歸納為以下5種:問答型、微課型、直播型、社交型、音頻型。
社交媒體的多元種類,口語傳播的多元形態為用戶口語溝通構建起不同的關系和互動機制。“問答型”交互主體常以普通話作為口語交際的基礎,用戶關系既包含一對一模式,也包含一對多模式,交互關系的產生往往是其中一方帶有明確的信息服務需求導向,試圖尋找解決方案,答主必須用清晰的邏輯、簡明扼要的語言對提問者的疑問進行層次分明的闡述,故而在口語表達樣態中多采用陳述語態,如知乎社區中問答的模式,就體現出了社交媒體中口語傳播的多元形態。“微課型”的信息交互以直播形式展開,具有及時互動的特征,人與人之間口語交互的場景從客觀存在、相對穩定的物理空間移植到虛擬化的網絡公共空間,傳播的信息帶有極強的專業性和知識性,呈現出內容垂直化和受眾圈層化的特征,如現在火爆的“CCTALK”,就屬于微課型的交互形態。口語傳播中“直播型”的實踐形態,顧名思義需依托帶有直播功能的社交媒體,可打破地域限制、實現跨區域的交流互動,支持視頻交流、語音交流、評論留言、圖文總結、回放存儲等多種功能,任何用戶皆可作為主體發起直播交互。就目前而言,很多社交媒體都帶有“直播型”特征,這也是社交媒體中最為顯著的特征之一。“社交型”更側重于用戶的人際關系和社交圈,用戶可利用多元化方式進行信息傳播,但信息交互也受限于用戶之間的強弱關系和互動機制,強關系社群用戶之間互動頻率更高、黏合性更強,因而用戶與社交媒體的黏性更高,如微信就屬于強關系聯結,而微博則屬于弱關系聯結,無論是哪一種聯結方式,都屬于社交型傳播形態。音頻型口語傳播實踐具有獨特的伴隨屬性,以音頻為內容主體,用戶無需動用視覺系統,所以在語音語調上追求較強的感染力,且個性鮮明、特征明顯,像喜馬拉雅聽書所打造的“廣場”、“圈子”,就是典型的音頻型口語傳播實踐。以上5種實踐形態中,直播型和社交型往往伴隨著視覺場景關系的轉換,問答型、微課型、音頻型則更傾向于語音的傳播。
依托于社交媒體的用戶交互行為往往伴隨著感官體驗、內心感覺、場景連接等多重維度,使用戶能在交互過程中獲得更加立體豐滿的體驗。用戶之間的口語交流在傳播形態和內容生產方式上更為開放、多元。除此之外,社交媒體的出現為人們創造了新的“現場”與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在場”,將人們從“現場與在場”的溝通模式、依托文字、符號、書信等媒介方式的互動,移植到虛擬的終端平臺,從物理空間和社會空間構成的現實世界帶入到全新的虛擬世界。
社交媒體中口語傳播交互性的內外因。口語傳播跨越了漫長的時期,在新媒體時代依托媒體環境的多樣化建立起新的溝通情境。原生口語文化語境下口語傳播的交互性是強調“在場性”溝通情境下的鏈接互動,依托紙質媒介下的口語傳播側重于對媒介載體的依賴,互聯網時代背景下口語傳播的交互性模糊了時間、空間的分界,實現溝通主體的“虛擬在場”,注重交互的及時性。圍繞口語傳播交互性嬗變的成因,本書作者分別從語境外因、話語內因兩個層面展開相關論述。
從外因角度,作者從“傳播語境、文本語境、語境還原”三個緯度展開探討,以美國傳播學者梅羅維茨在《消失的地域》一書中提出的“媒介即情境”理論作為邏輯起點。梅羅維茨的“媒介即情境”觀點融合了媒介技術學派倡導者麥克盧漢“媒介即訊息”的觀點和社會學家戈夫曼的“面對面互動”論。梅羅維茨認為新媒介的產生重塑了新的媒介環境,也帶來新的情境——信息系統,新情境的產生消解了傳統意義上客觀存在的場景,打破了物質場所、物質距離界限的信息傳播,調整和改變了人們的社會角色和社會行為。在“媒介即情境”的理論支撐下,口語傳播的價值更在于交互雙方價值觀念的碰撞,在于每個溝通主體都能參與集體思考與表達。在“媒介情境論”的基礎之上,作者首先將傳播語境視為交互性外因的進階節點,從口語傳播中用戶主體平權、場景交互、協作生產三個緯度審視社交媒體的傳播語境;其次,作者以文本語境作為交互外因的制約節點,探討了口語傳播的修辭情境、話語框架、修辭特征等問題;最后,作者將交互外因的歸結遠點落腳于語境還原論,認為語言是一個復雜、多層次的系統,要將其放到具體語境中,才能把握完整準確的意義。
從內因角度,作者將研究方向從語境轉換到話語層面,從符號資源、陳述語態、關系語法三個緯度進行闡釋。在符號資源層面,作者基于“社會符號學”理論,提出在社交媒體口語溝通實踐中,可從“話語”、“設計”、“生產”三個層次,為口語溝通的事件和文本提供多重符號情境下的信息交互,構建“多模態”的溝通模式。新媒體環境下的口語溝通帶來的及時互動性,需在單位時間內精準表意才更容易激起無數多元溝通主體的情感共鳴、點燃話題,口語傳播中的陳述語態最能簡練清晰表達觀點,傳遞重要信息。在語法因素層面,作者分析了口語溝通主體如何通過語言建構自我身份和社會關系,其中包括通過互動控制特征確保溝通主體的平穩關系;構建簡單有序的規則體系,即溝通主體輪流闡述;采用“問題-回答”、“回答-回答”等常見的信息交換結構;注重溝通中語言的情態和禮貌,輔助提升自我形象和社會形象。
社交媒體中口語傳播的互動效果探析。媒介發展最主要的作用之一是為了更好地傳播信息,更有效地促進用戶之間的交流,尤其在當前新媒體環境下,其口語傳播實踐已然加速了信息的傳播、意見的交換、輿論的表達。毋庸置疑的是,其中社交媒體的發展使社會全體成員都能參與信息的流動與交換,社交媒體中的口語傳播方式已然朝全方位、多維度的模式方向邁進。作為社交媒體口語傳播實踐中的核心群體,用戶長期占據中心位置,傾向于在社交媒體進行口語傳播實踐時,能將網絡中的社交關系進一步拓展演變為現實的社交關系。通過鏈接不同的社群板塊,不斷嫁接編織形成新的社會關系,從而實現身份轉型、價值升級,這對社交媒體用戶而言有著積極意義。
同時,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為用戶帶來便利,支持用戶逆向上傳,改變傳統媒體下口語傳播的流程,允許用戶個人進行信息內容的創作、生產、傳播,構建起一個具有黏性而穩定的用戶社區群,從而帶來巨大的流量。但社交媒體的快速發展、普遍的使用率,傳播主體“去中心化”、“去權威化”的傳播權利也導致其必然存在負面性影響。社交媒體過度的便捷性、快速性、及時性、實時性等媒介技術特性下產生的信息形態,往往是碎片、冗雜、過載的,信息洪水現象日益嚴重,信息供給明顯過剩。在“泛娛樂化”傾向蔓延和精英階層話語權缺失的時代背景下,社交媒體的口語傳播傾向短小、簡潔、直觀的表達形式,并不要求用戶進行深入、理智、系統的思考,往往只需在當下作出快速及時的互動反饋,傾向于感性的表達。在流量為王的時代,為吸引受眾眼球,放緩沉淀速度,在信息傳播中形成不少利用夸大歪曲事實、聳人聽聞的手段獲取關注、博取“噱頭”的跡象,不斷挑戰社會道德底線、違背社會主流價值觀,“泛低俗化”的風潮愈演愈烈,極其容易給價值觀尚未成型的青少年帶來潛移默化的不良影響。
毫無疑問,這種“全員參與”的新傳播業態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傳播秩序的流動、創造和融合。在網絡公共傳播空間中,用戶主體的“虛擬在場”性、集體無意識、群體情緒化等易引發“路西法效應”。通過自律與他律的形式全面提升用戶素養,維護網絡公共空間安全、有序、健康發展就顯得迫在眉睫。
隨著媒介技術的不斷更新,社交媒體的形態仍在持續發生變化,對社交媒體口語傳播的研究依然值得繼續關注和完善。縱觀全書脈絡,本書作者以口語傳播的交互性為基本問題、從現實形態、本質特征、外因邏輯、內因呈現、社會影響五個層面,通過理論論述結合具體案例展開論說。社交媒體下的口語傳播以“人”作為中心媒介,以信息系統作為情境,以關系作為互動基礎,在口語溝通中構建了人與社會的新型鏈接模式。全書緊緊圍繞著口語這一最基礎、最基本的傳播方式,不僅可以幫助讀者更加深入地了解口語傳播的歷史過程,也能夠為社交媒體用在口語傳播的實踐中提供科學的理論支持與實踐指導。同時,對口語傳播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推動意義。
作者單位 商丘廣播電視臺
【編輯:孫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