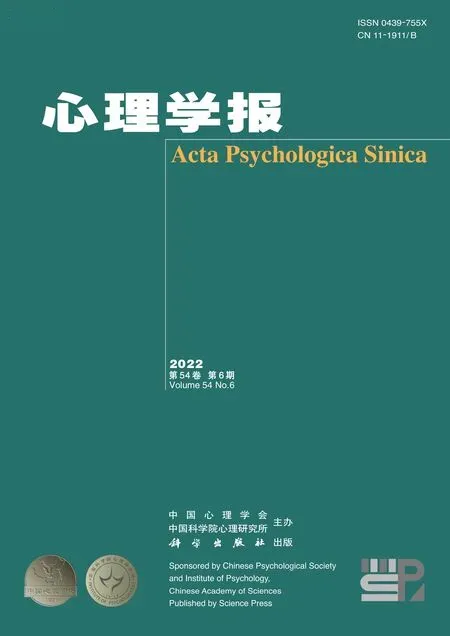聲譽關注與社會距離對傷害困境中道德決策的影響:來自行為與ERPs 的證據*
占友龍 肖嘯 譚千保 李琎 鐘毅平
(1 湖南科技大學教育學院心理學系,湘潭 411201) (2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長沙 410205)(3 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心理學系;4 認知與人類行為湖南省重點實驗室,長沙 410081)
1 引言
自然界充滿了社會困境,個體必須在自我和他人的利益最大化之間進行權衡(Rand &Nowak,2013)。道德決策(moral decision-making) 就是一種典型的涉及自我和他人之間得失權衡的社會決策,指當面臨多種可能且存在兩難沖突的行為途徑選擇時,個體在社會制度和規范的指導下根據自我價值導向做出最優選擇的過程(Rilling &Sanfey,2011)。它常涉及到一系列維護自我利益和阻止傷害他人之間的權衡,且決策者會伴隨強烈的負性情緒體驗和認知沖突(Greene &Haidt,2002;Pletti et al.,2015)。雖然經濟學家們大都認為人類在經濟決策中往往極度自私,但近期心理學家們卻發現人們在道德決策中表現出了一種“超級利他的(hyperaltruistic)”決策傾向,即以犧牲自我利益為代價來減少他人的痛苦(Crockett et al.,2014)。事實上,親社會行為在社會互動中確實出奇地普遍,即使個人會付出較大的代價,甚至是面臨各種風險(Fehr &Fischbacher,2003)。為什么人們會穩定地表現出親社會行為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人們內心具有一種以犧牲自己為代價來造福他人的動機,我們稱之為“利他主義(altruism)” (Wilson,1992)。然而,與直覺經驗相反的是,另一種解釋認為:人們以犧牲自己利益為代價去幫助他人的直接動機,可能在進化上是具有適應性的(Fehr &Fischbacher,2003),是個體為了滿足某種長遠的自我利益而有意或被迫產生的(Rand &Nowak,2013)。利他行為雖然通常會導致自己應得利益的損失,卻能在一定條件下獲得他人的贊賞,進而獲得好的聲譽,并通過聲譽的傳播在未來為自己獲得更多的收益(Hardy &van Vugt,2006;談晨皓 等,2017)。可見,如果人們做出了某種親社會的選擇,那么這個選擇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純粹的利他主義,多大程度上是出于精明的利己主義,這還需要進一步的實證研究來證實。因此,本研究旨在考察聲譽關注對不同社會距離下道德決策行為的影響,并采用事件相關電位技術(eventrelated potential,ERP)探討兩者如何交互影響道德決策中個體的行為與神經反應。
以往研究對親社會行為中的聲譽機制進行了大量研究(Lee et al.,2018),并認為提高聲譽是使親社會行為最終服務于自身利益的一種特別重要的方式(Fehr &Fischbacher,2003)。例如,不少研究試圖將聲譽關注對慷慨行為的直接影響與利他動機區分開來,他們要求被試在公開場合(vs.私下場合)表達參加慈善活動的意愿。結果發現,與私下情境相比,人們在公開場景下(如有朋友、募捐者、異性或內群體成員在場時)對慈善事業捐贈的會更多(Bereczkei et al.,2015;van Vugt &Iredale,2013);甚至呈現類似眼睛的線索刺激時,人們也會做出更多的利他行為(Mifune et al.,2010;鐘毅平 等,2019)。同時,風險決策的相關研究也發現,被試在匿名情境下會為了更多的金錢收益而做出更多利己的風險選擇,但這種利己的選擇在決策結果公布給搭檔時顯著減少了(Arfer et al.,2015;Bixter &Luhmann,2014)。此外,道德決策的相關研究發現,被試在他人在場時會表現出更多的道義性選擇和親社會行為,因為他們對個人聲譽表現出了更高水平的關注(Lee et al.,2018;傅鑫媛 等,2015;占友龍 等,2020)。競爭性利他主義(competitive altruism)較好地解釋了聲譽關注對人們利他行為的影響機制。該理論認為人們之所以表現出利他行為,是為了在他人面前塑造出可靠的利他形象(van Vugt et al.,2007),并通過聲譽的傳播而獲得更多的合作機會,它是一種主動通過投資聲譽來獲得收益的獲利策略(Barclay &Willer,2007)。例如,大量行為研究在不同類型的親社會行為中均發現了這種“利己的利他主義(egoistically biased altruism)”行為傾向,如犧牲當前收益以博取好的名聲,以便在隨后任務中或未來獲取更大收益(Chiang,2010;Sylwester &Roberts,2010;van Vugt &Iredale,2013);在提前獲知搭檔不能提供獲益機會時(Alpizar et al.,2008;Semmann&Milinski,2004),人們在當前任務中會主動減少自己的利他行為(van Baar et al.,2019)。這些研究表明,聲譽關注確實是人們表現親社會行為的一種重要動機,但是這種利己的親社會動機如何與純粹的利他動機相區分,目前還缺乏足夠的直接研究,尤其是其背后的認知神經機制。
然而,以往研究僅僅關注了聲譽對親社會行為的影響,卻較少關注其他社會情境因素對聲譽機制的調節,如決策者與接受者之間的社會距離(Wu et al.,2011)。利己的利他行為是通過對自己進行聲譽投資,進而在未來合作中為自己謀取更多利益,那么當利他對象的身份信息(如社會距離)提供是否具有合作價值的潛在信息時,決策者應當會利用這些信息來調節自己的利他行為,以避免不適宜的利他行為造成自身的不恰當損失。現有研究發現,人們的親社會行為受到決策者與決策對象之間社會距離的調節(Chen et al.,2009;Christensen &Gomila,2012;Sarlo et al.,2012)。例如,與陌生人相比,人們更愿意犧牲自我利益去幫助親人和朋友(Loke et al.,2011;Miller &Bersoff,1998),并在社會困境中表現出更多的共情(宋娟 等,2016)、信任與合作等親社會行為(Chen et al.,2017),也會更愿意損失自我利益來減少欺騙、電擊等傷害行為(Crockett et al.,2014;Zhan et al.,2020)。一些ERP 研究也發現,與陌生人相比,個體在涉及親人或朋友的道德決策中會消耗更少的時間來權衡得失,會體驗到更小的負性情緒沖突(誘發更小波幅的P2),并消耗更少的認知資源(誘發更小波幅的P3),最終做出更多的利他性選擇(Zhan et al.,2018,2020;占友龍 等,2020)。然而,與電擊他人而自己獲利的情境相比,被試在電擊自己而陌生他人獲利情境中的利他行為消失了(Volz et al.,2017)。該研究認為人際關系疏遠而導致的不確定性,會給決策者帶來強烈的情緒和認知沖突,促使其采用一種“利己的利他主義”策略來指導道德決策,而并非是依據一種純粹的“超級利他的”道德原則。這些研究表明社會距離調節了道德決策中自我與他人之間損益的權衡。
由于聲譽關注與社會距離同時存在于社會決策中,單獨考察它們對道德決策中自我與他人之間得失權衡的影響,勢必會妨礙我們對“超級利他主義”和“利己的利他主義”這兩種特殊的利他動機的深入認識。以往研究發現,當決策者的身份不確定時,人們寧愿選擇更小的收益水平,也要和社會距離較近的朋友完成信任博弈任務,而非社會距離較遠的陌生人(Campanha et al.,2011;Yu et al.,2015)。由此可知,聲譽關注與社會距離會對利他行為中自我與他人之間得失的權衡產生交互影響,聲譽機制可能在社會距離較遠的情境中更容易出現。然而,截止目前,關于聲譽關注與社會距離是如何交互影響道德決策的還不是很清楚,尤其是其背后的認知神經機制。
研究發現,利用高時間分辨率的ERP 技術可以很好地揭示個體在道德決策中權衡自我與他人得失的時間進程(Gui et al.,2016;Sarlo et al.,2012;Yoder &Decety,2014;Zhan et al.,2020)。之前研究在道德決策中主要關注3 個階段的ERP 成分:早期的道德直覺過程(如N1)、中期的情緒反應過程(如P2 或N2)和晚期的認知推理過程(如P3 或LPP)(Gui et al.,2016;Yoder &Decety,2014)。在早期的道德直覺階段,額中部腦區的N1 成分反映了個體對道德情境和選項中的相關信息(如道德行為的效價等)進行快速編碼和初級加工的過程(Gui et al.,2016;Yoder &Decety,2014)。在中期的情緒反應階段,前額部腦區的P2 和N2 成分反映了個體對兩難情境中沖突的探測和負性情緒體驗(Gui et al.,2016;Yoder &Decety,2014)。此外,研究發現該階段的道德決策還會在頂葉誘發一個明顯的P260 成分(Sarlo et al.,2012),且成分的大小與個體的厭惡情緒強度存在顯著相關(Sarlo et al.,2014)。在晚期的認知推理階段,頂葉位置的P3 或LPP 成分代表了緩慢但受控制的精細加工過程,如復雜社會情境下的道德評價和推理(Beste et al.,2012;Chen et al.,2009;Gui et al.,2016;Paynter et al.,2009)。因此,這些腦電成分分別從直覺過程、情緒過程和認知過程來反映道德決策中情緒與認知的作用。近年來,越來越多研究者采用ERPs 的優勢開始分別探索社會距離和聲譽關注對道德決策的影響。例如,有研究考察了社會距離對幫助困境下道德決策的影響(Zhan et al.,2018,2020),并發現涉及親密他人的兩難決策誘發了更小波幅的與認知沖突和負性情緒體驗有關的P2 成分,在晚期階段誘發了更小波幅的與認知資源投入有關的LPP 成分,并發現被試主觀報告的愉悅情緒體驗與P260 波幅呈顯著負相關,決策時間與LPP 波幅呈顯著正相關。然而,過往研究大多考察的是聲譽關注和社會距離單獨對道德決策過程的影響,鮮少有研究探討兩者如何交互影響道德決策中的行為和神經反應。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究當道德決策涉及自我利益與他人傷害的兩難權衡時,個體在聲譽關注與社會距離交互影響下是如何決策的。
此外,以往的研究更多關注了指定性道德范疇中道德決策的認知神經機制,即讓被試決定是否愿意損失自我收益來幫助他人(Campanha et al.,2011;Gross et al.,2020;Zhan et al.,2019;占友龍 等,2020)。然而,關于禁止性道德范疇的研究較少,即讓被試決定是否愿意為了增加自我收益來主動欺騙或傷害他人(Janoff-Bulman et al.,2009)。通常,不幫助正遭受痛苦的他人僅會被視作為一種冷漠的行為,而主動傷害他人來獲利卻是一種不可容忍且不道德的行為,兩類道德范疇下的道德行為可能反映了不同的心理機制(Noval &Stahl,2015)。因此,從行為結果來看,“幫助他人”與“不傷害他人(抑制)”是屬于道德的行為,而“傷害他人”或“不幫助他人(冷漠)”是屬于不道德的行為(Carnes &Janoff-Bulman,2012)。本研究擬采用一個涉及電擊傷害與金錢收益的兩難權衡任務(Crockett et al.,2014;Liu et al.,2020;Volz et al.,2017;Zhan et al.,2020;崔芳等,2020),來考察聲譽關注與社會距離如何調節道德決策中自我與他人得失的權衡,及其背后的神經機制。該任務的新穎之處在于,被試需要在一系列是否通過電擊他人來增加自己金錢收益的兩難權衡中進行選擇,這種結合了自我收益與傷害他人的兩難決策,更能真實地觀察到被試是否會在不同情境中表現出“超級利他主義(即犧牲自我收益而減少或不傷害他人)”或“利己的利他主義(即為了獲得收益而更多地選擇傷害與自己社會距離較遠的他人)”決策傾向。同時,該任務還能確保我們觀察到聲譽關注與社會距離如何動態調節道德決策中個體的神經反應,以揭示心理與生理水平上的內在關系。
綜上,本研究采用“電擊-獲利困境”任務和ERP 技術,考察聲譽關注與社會距離如何交互影響傷害困境下道德決策的行為和神經反應,并將驗證如下假設:(1)在匿名情境中,與社會距離疏遠他人(熟人和陌生人)相比,被試對社會距離較近他人(朋友)會表現出更多的助人選擇,表現出一種“利己的利他主義”決策傾向;(2)與朋友和陌生人相比,熟人關系的不確定性,會導致涉及熟人的兩難決策誘發更強的負性情緒體驗,并消耗更長的決策時間和誘發更強的神經反應(如更大的ERP 波幅);(3)然而,這些行為和ERP 指標上的差異在公開情境下會因為聲譽關注而顯著減弱或消失。
2 方法
2.1 被試
利用G*Power 3.1 對樣本量進行估計,保證中等效應量(=0.25),計算后發現至少需要24 名被試(Faul et al.,2007)。因此本次實驗共招募了30 名被試(男生14 人,女生16 人,年齡為18~26 歲,平均年齡為22.38 ± 1.52 歲)。所有被試均為右利手,無精神疾病或神經癥病史,視力正常或矯正后正常。所有被試之前并未參與過類似的電擊實驗,以減少被試的主觀經驗對實驗中電刺激強度的主觀知覺。而且,為了滿足任務要求,每個被試在實驗前被告知要分別帶一名同性別的朋友和熟人到實驗室,并與實驗室中的另一名陌生主試,共同完成一個“電擊-獲利困境”任務。在實驗開始前,所有被試均被明確告知:若認真完成實驗任務將會獲得一定金額的報酬,它由基礎被試費(30 元)和額外任務獎勵兩部分組成;額外任務獎勵為被試在實驗中真實通過電擊他人而贏得的金錢,并按照100 :1 的比例兌換后,與基礎被試費一起支付給被試。同時,朋友和熟人也被明確告知:在實驗過程中,你們將會坐在隔壁的另一個房間,并根據電擊決策指令而接受真實的疼痛電刺激,但該決策指令既可能是被試發出的,也可能是電腦程序隨機發出的。實驗結束后,你們將會分別獲得30 元作為實驗報酬。此外,實驗前所有被試均簽署知情同意書,并獲得了湖南師范大學科學研究倫理委員會批準同意。
2.2 刺激與程序
本實驗采用3 類目標他人的名字(即朋友、熟人、陌生人)作為社會距離的啟動刺激,且3 個同性別目標他人的名字字數是一樣多的,并要求被試評價名字刺激的熟悉度。其中,朋友是指“頻繁且穩定交往了3 年以上的同性好友”,熟人是指“點頭之交了3 年以上的同性同學或同齡人”,陌生人是指“實驗之前從來沒有見過的同性別陌生他人”。在本實驗中,朋友和熟人都是被試提前篩選后帶來實驗室的,而陌生人實際上為實驗室一位同性別的陌生實驗員充當,所有被試之前均沒有見過,也不認識。此外,采用自我中包含他人量表(Inclusion of Others in the Self,簡稱IOS)來評定目標他人與自我的親密程度,將得分在5~7 分的目標他人操作為社會距離親近的他人(如朋友),將得分在3~4 分的目標他人操作為社會距離中等的他人(如熟人),將得分在1~2 分的目標他人操作為社會距離疏遠的他人(如陌生人) (Aron et al.,1992;鐘毅平 等,2015)。在“電擊-獲利困境”任務中,通過呈現電擊對象(即朋友、熟人、陌生人)的名字來操作社會距離。
根據前人關于聲譽關注的操作方法(Arfer et al.,2015;Bixter &Luhmann,2014),本研究通過“被試所有的決策結果多大程度會傳遞給目標他人觀看”來操作。被試被告知:目標他人都坐在另一個房間中,里面有一臺跟實驗室電腦聯網的電腦,被試選擇電擊與否的結果會按照不同比例來實時在線公布給目標他人看到。在公開條件下,被試被告知:“您所有的決策結果都會通過電腦聯網呈現給目標他人”;在匿名條件下,被試被告知:“目標對象并不知道電擊決策是由誰做出的,有可能是決策者,也可能是電腦程序隨機做出的”。同時,被試完成兩個block 決策任務后,均會完成一個聲譽關注感知的9 點等級評定(1 代表一點也不會覺得個人聲譽會受到影響,9 代表個人聲譽將會受到極大影響)。
疼痛電刺激通過一個多通道疼痛電刺激儀來發射,采用電極線和電極片連接到3 個目標他人(朋友、熟人、陌生人)的左手手腕背部,通過控制電刺激儀的電壓值來調節疼痛電擊的強度。在簽訂知情同意書后,每個被試(即任務中的決策者)在實驗前都需要完成一個由Crockett 等(2014)研發編制的疼痛電擊閾限程序,它可以確保我們能獲得一個逐漸增強的疼痛電刺激矩陣。一方面,該程序的目的是通過最小誤差法來獲得每個被試根據自身疼痛感受而產生的具有20 個不同電壓強度(從弱到強)的疼痛電刺激矩陣。因此,3 個目標對象(朋友、熟人、陌生人)接受的電刺激強度都是由決策者(即被試自己)來確定的,均是同一套不同強度梯度的電刺激矩陣。這樣設計能有效避免產生其他額外變量的產生,因為單獨測量3 個目標他人的疼痛閾限,勢必會產生3 套不同強度梯度的電刺激矩陣,且彼此之間會存在顯著的個體差異,進而對被試的行為反應產生額外干擾。同時,本實驗還測量了3 個目標他人接受疼痛電刺激的最低和最高閾限值,避免發送的電擊強度超過了目標對象的閾限范圍,從而導致無疼痛感覺或超出承受范圍的情況出現。另一方面,該程序也是為了讓被試自己能夠清楚地體驗和感知到不同強度的電刺激作用于軀體的疼痛感受,為正式實驗中被試決策是否電擊目標他人提供參考點,幫助其根據自身的疼痛感知來推斷接受者可能的疼痛感受,進而在自我金錢收益與他人疼痛傷害之間誘發兩難沖突。
此外,滴定法被用于收集實際電擊強度與疼痛主觀感受強度之間的匹配關系。具體而言,疼痛電擊的最小閾限值為0.1 mA,被試被要求進行主觀疼痛感知的11 點等級評定(0 代表一點也不疼痛,10代表難以忍受的疼痛)。電壓值以3:1 的比例逐漸進行遞增,當疼痛主觀評分達到10 點時,該時的電壓值為最大閾限值。同時,每個被試還需要根據滴定法,給每個電擊強度匹配一個在心理上等值的金錢收益(即回答“接受多少mA 電擊來獲得多少元金錢收益是值得的?”)。該滴定程序每個被試都要重復3 次,以確保他們能清楚地感知到疼痛電擊強度與金錢收益數量之間的配對關系。因此,該程序針對每個被試都會獲得一個包含20 對的“疼痛電擊vs.金錢收益”矩陣。最終,30 名被試的平均疼痛電擊值的范圍為1.00 伏特~15.22 伏特,平均金錢收益值的范圍為0.10 元~3.50 元。該“疼痛電擊vs.金錢收益”矩陣會被用于正式實驗中的“電擊-獲利困境”任務,進而考察被試在權衡“增加自我收益”與“減少他人傷害”時的行為和神經反應。
采用改編的“電擊-獲利困境”任務(Crockett et al.,2014;Zhan et al.,2020),考察被試在面對不同目標對象時如何在“自我收益”與“他人傷害”之間進行權衡,即被試是否會為了增加自我收益而選擇對他人實施痛苦的電擊傷害(即利己的行為傾向),或者犧牲自我收益而選擇減少或不傷害他人(即利他的行為傾向)。被試將與另外3 個目標對象共同參與完成一個真實的疼痛電擊與金錢收益任務。被試在實驗中擔當決策者,3 個目標對象(朋友、熟人和陌生人)擔任被電擊者。在實驗過程中,為了提高實驗的生態效度和真實性,被試在腦電實驗室完成任務操作,3 個目標對象均坐在隔壁的另一個房間,通過電極線連接其左手手腕背部的電極片上,并根據電擊決策指令而接受真實的疼痛電擊。重要的是,被電擊者無法確認決策者的真實身份,他們被告知電擊指令既可能是被試發出的,也可能是電腦程序隨機發出的。由此,決策者會面臨一系列二選一的兩難抉擇:是讓目標對象接受疼痛電擊而自己獲得金錢收益,還是不選擇對他人實施疼痛電擊而自己沒有金錢收益。在每個試次中,被試都是決策者,接受電擊的對象是3 個目標人物中的任意一個,但金錢收益均歸被試所有。
在正式實驗中,首先呈現一個注視點200 ms;緊接著呈現情境指導語,若為公開場景,則指導語為“您接下來的決策結果會通過聯網傳送給目標對象獲知”;若為匿名場景,指導語為“您接下來的決策結果不會傳送給目標對象”;在呈現黑屏100 ms之后,呈現接受疼痛電擊的對象名字刺激500 ms;在呈現500~1000 ms 的隨機黑屏之后,呈現決策界面3000 ms,被試的任務是又快又準地按鍵反應,“F”鍵代表電擊,“J”鍵代表不電擊;按鍵選擇后呈現1000 ms 的黑屏;然后呈現電擊界面1000 ms,若被試選擇了電擊,則閃電標志成亮黃色,表明目標對象正在接受真實的疼痛電擊,若被試選擇不電擊,那么閃電標志是灰色的,則無疼痛電擊發送;然后呈現反饋界面,若當前試次為公開情境,則反饋結果為“您的決策結果正發送給對方”;若當前試次為匿名情境,則反饋界面為500 ms 的黑屏;緊接著呈現被試目前已經累加獲得的金錢數量;最后,對決策時的愉悅情緒體驗進行9 點等級評定(1 代表極其不愉悅,9 代表非常愉悅),按鍵反應后結束該試次。在實驗開始前,所有被試均被明確告知:每個試次都會按照被試的選擇來真實執行電擊或不電擊目標對象,整個實驗總共360 個試次,包括公開與匿名情境各1 個block,2 個block 之間休息一次,呈現順序在被試間進行平衡,完成整個實驗大概需要45 分鐘(見圖1)。

圖1 “電擊-獲利困境”任務中單個試次的實驗流程圖
2.3 數據記錄與分析
在線記錄是使用Neuroscan ERP 記錄與分析系統(Neuroscan Inc.,USA),按國際10-20 系統擴展的64 導電極帽記錄EEG。在線記錄時將參考電極安置于左側乳突位置,離線后轉為雙側乳突為參考電極,雙眼外側安置電極記錄水平眼電(HEOG),左眼上下安置電極記錄垂直眼電(VEOG)。濾波帶通為0.05~70 Hz,采樣頻率為500 Hz/導,頭皮阻抗< 5 kΩ。線下分析時采用EEGLAB 工具箱,將數據由單側乳突記錄轉化成雙側乳突,濾波參數為0.1~30 Hz。采用ICA (Independent component analysis)分析來剔除眨眼和動作偽跡(Delorme &Makeig,2004;Pl?chl et al.,2012)。同時,我們檢查了整個EEG 數據,并剔除了高噪音的試次,如較大的肌電、眨眼、心電偽跡。極端值的剔除標準為± 80 μV(Gui et al.,2016)。分段時間為目標刺激出現前的200 ms 到出現后的800 ms,并對-200 ms 到0 ms的數據進行基線矯正。在剔除偽跡之后,每個實驗條件下的平均試次數均保留了85%以上(每個條件下60 個試次),平均試次為56.17 ± 1.88 個;其中公開情境-朋友條件下58 個,公開情境-熟人條件下57 個,公開情境-陌生人條件下55 個,匿名情境-朋友條件下56 個,匿名情境-熟人條件下55 個,匿名情境-陌生人條件下56 個。
在ERP 數據上,結合全腦地形圖的視覺觀察(請見圖3B),以及前人的ERP 研究結果(Gui et al.,2016;Sarlo et al.,2012,2014;Yoder &Decety,2014;Zhan et al.,2020)與本實驗目的,我們主要選擇了以下15 個電極點來分析傷害情境下道德決策所誘發的ERP 成分:F3,Fz,F4,FC3,FCz,FC4,C3,Cz,C4,CP3,CPz,CP4,P3,Pz,P4。其中,N1 (80~160 ms)、P2 (160~260 ms)和N2 (260~360 ms)在前額部和額中部腦區被較為顯著地觀察到了,因此采用該兩個腦區的6 個電極點(F3,Fz,F4,FC3,FCz,FC4)的平均值作為其觀測值。其次,P260 (200~300 ms)和LPP(300~450 ms)在中部、頂中部和頂部腦區被較為顯著地觀察到,因此采用該3 個腦區的9 個電極點(C3,Cz,C4,CP3,CPz,CP4,P3,Pz,P4)的平均值作為其觀測值(請見圖3A)。各ERP 成分在各自時間窗口被測量與分析,并對這些ERP 成分的平均波幅進行了3 (社會距離) × 2 (決策情境)的重復測量方差分析,其平均數與標準差見表1。

表1 不同實驗條件下各ERP 成分的平均數與標準差(M ± SD μV)
此外,皮爾遜積差相關被用于考察道德決策過程中行為和神經反應的內在關聯,以有助于闡述各ERP 成分所反映的心理功能和意義。所有數據的統計和分析均采用了SPSS 20.0 (IBM Corp.,Armonk,NY,USA)軟件來完成,統計結果非球形時同樣采用Greenhouse-Geisser 法校正值,多重比較采用Bonferroni 法校正。
3 結果
3.1 操作檢驗結果


3.2 行為數據結果
(1)電擊比例

(2)決策時間

(3)愉悅情緒主觀評定得分


圖2 各實驗條件下的電擊比例、決策時間及愉悅情緒主觀評分(注:*p < 0.05,**p < 0.01,***p < 0.001,下同)
3.3 ERP 結果
(1) N1 成分


圖3 各實驗條件下被試完成道德決策時在Fz 與Pz 點誘發的腦波形圖以及差異波腦地形圖
(2) P2 成分

(3) N2 成分

(4) P260 成分

(5) LPP (300~450 ms)

3.4 其他分析結果
對匿名情境減去公開情境下各變量的差異值進行皮爾遜積差相關分析,結果發現:主觀愉悅度評分與P260 波幅在不同社會距離條件下存在顯著的負相關(朋友:=-0.39,=0.03;熟人:=-0.41,=0.03;陌生人:=-0.37,=0.03),表明決策誘發的P260 波幅越大,被試在道德決策中體驗到的主觀愉悅度更弱(請見圖 4A);而且,決策時間與LPP (300~450 ms)在各社會距離條件下存在顯著的正相關(朋友:=0.34,=0.04;熟人:=0.43,=0.03;陌生人:=0.37,=0.03),表明決策時誘發的LPP (300~450 ms)波幅越大,被試在道德決策中消耗了更多時間和認知資源來解決兩難沖突(請見圖4B)。此外,電擊比例與所有ERP 成分均不存在顯著的相關(=0.03~0.25,s > 0.15)。

圖4 三種社會距離情境平均后P260 波幅與愉悅度評分以及LPP 波幅與反應時之間的相關散點圖
4 討論
本研究采用ERP 技術探究了聲譽關注與社會距離對道德決策的影響及其時間加工進程的特點。結果發現,匿名情境下被試對不同社會距離他人的兩難電擊決策體現出了一種明顯的“人際差序性”,即與社會距離較遠的熟人和陌生人相比,被試更愿意放棄自我利益而減少對社會距離較近的朋友進行電擊傷害;而且,在決策時間和電生理指標上表現出了一種典型的“熟人效應”,即與朋友和陌生人相比,涉及熟人的兩難決策花費了更長時間,并誘發了更大波幅的與負性情緒反應有關的P260,以及與認知推理有關的LPP (300~450 ms)成分。然而,行為和ERP 指標上的這種“人際差序性”和“熟人效應”在公開情境下減弱或消失了。這些結果表明,匿名情境下個體在傷害困境中完成道德決策時可能采取了一種“利己的利他主義”決策傾向,且人際關系中熟人關系帶來的不確定性在道德決策中會誘發更強烈的情緒負荷和認知沖突,而公開情境誘發的聲譽關注在抑制自私傾向和消除人際關系的不確定性上可能起到了關鍵作用。該研究發現為揭示中國文化背景下人際關系與聲譽關注交互影響人際間道德決策的行為特點及其大腦加工時程特點,提供了一定的實證依據。
4.1 社會距離和聲譽關注共同調節了道德決策中個體的利他行為動機
與以往研究一致(Chen et al.,2017;Cheng et al.,2010),本研究發現被試在電擊-獲利困境任務中的利他性決策傾向表現出了一種穩定的“人際差序性”,即人際距離越近,個體更愿意放棄自我金錢收益來減少對親密他人的疼痛電擊傷害。以往研究認為,人際關系越親密或越近,人們越愿意對親密他人表現出親社會意愿和利他行為,如更多的共情、幫助、信任和合作等親社會行為(Chen et al.,2017;Cheng et al.,2010)。在道德決策中,以往研究同樣發現了這種人際距離的差異,即相比于熟人和陌生人,個體對朋友會做出更多有付出的兩難幫助決策(Zhan et al.,2018,2019;占友龍 等,2020)。在現實生活中,涉及傷害的決策通常是發生在消極情境中的,如威脅生命的沖突情境,因此減少朝向自我或親密他人的傷害將超越一切其他情況而占據優勢地位(Tomasello et al.,2012)。換句話說,當面臨真正的傷害時,人們首先思考的是如何先減少自我或親近他人的傷害,然后再考慮陌生他人。因此,在本研究中,當朋友、熟人和陌生人均面臨了被電擊的疼痛傷害時,個體會優先選擇損失自我金錢收益降低對朋友的電擊傷害,然后才考慮熟人和陌生人,因為個體可能無法容忍親密他人遭受傷害。此外,這種具有利己的利他決策傾向也符合親社會行為的親緣選擇理論,即人們選擇放棄自我利益來幫助親人和朋友,是為了更好地維系血緣關系,保護自我基因的延續,具有進化意義(Hamilton,1964;Tan et al.,2015)。由此可知,該研究結果證明了第二個假設:社會距離調節了傷害困境下道德決策的行為傾向,對朋友的電擊決策要顯著少于對熟人和陌生人的,表現出了一種明顯的“利己的利他主義”決策傾向。該研究發現與西方被試在人際間道德決策中表現出的“超級利他主義”傾向是有顯著區別的(Crockett et al.,2014;Volz et al.,2017),中國文化背景下人們普遍通過“關系自我”來指導人際間的社會互動行為(Ma &Han,2011;Zhu &Han,2008),因此在不同社會距離情境下的道德決策表現出了一種明顯的“人際差序性”。
然而,不同社會距離下個體的這種“利己的利他主義”決策傾向受到了決策情境的調節。具體而言,與匿名情境相比,個體在公開情境中的決策時間更快,做出的電擊傷害選擇更少,且利他性決策傾向上的“人際差序性”被削弱了。這一研究發現與以往的研究結果是一致的(Barclay &Willer,2007),當決策結果被公開時,個人會為了贏得更好的聲譽而表現出更多的利他行為。例如,大量行為研究發現,個體當前任務中的利他行為是為了贏得好的聲譽,進而在隨后的或未來的社會互動活動中為自己獲取更多利益(Chiang,2010;Sylwester &Roberts,2010;van Vugt &Iredale,2013)。然而,當個體提前獲悉自己無法在后續或未來的社會互動任務中獲取更多收益時,如在決策結果公開、游戲規則共享、搭檔更換等情境中,人們在當前任務中會顯著減少自己的利他行為,甚至不表現出明顯的利他傾向(van Baar et al.,2019;Semmann &Milinski,2004),且這種行為傾向在那些特別自私的或擅長社會交際的個體中更為明顯(Bereczkei et al.,2015)。因此,該結果部分證明了本研究的第一個和第三個假設,即決策結果的公開會導致個體關注自我形象或聲譽,進而促使其在道德決策中表現出更少的傷害行為,而匿名情境為被試提供了利己的可能性,因此被試表現出了更少的利他選擇,且對與自己關系越近的朋友做出了更少的疼痛電擊傷害。然而,這一研究發現并不能充分地證明被試在公開情境下的道德決策遵循了“超級利他主義”這一行為傾向。實際上,雖然被試在公開情境下對3 類目標他人的電擊傷害減少了,并且顯著低于匿名情境下的,但傷害比例仍然達到了50%,這說明被試可能是為了維護自身聲譽而減少了傷害行為,表現出的可能是一種減弱了的“利己的利他主義”行為傾向,而非一種純粹的“超級利他主義”。
4.2 熟人關系的不確定性調節了道德決策中的情緒和認知過程
更有趣的是,我們在反應時指標上還發現了一種明顯的“熟人效應”,即與朋友和陌生人相比,被試在涉及熟人的電擊-獲利兩難任務中花費了更長時間來思考和做決策。這一研究發現獲得了以往相關研究的支持,如早期有關人際關系的中國本土化研究表明,熟人處于人際關系的中間地帶,是情感成分和工具成分相混合的區域,如果情感性成分提高,則從熟人關系發展為親密關系,反之,如果情感性成分降低,則從熟人關系向陌生人關系轉變(黃光國,胡先縉,2005)。此外,國內一項有關人際情感偏向的外顯和內隱判斷研究也發現,人們對自我秉持一種積極的情感偏向,對陌生人則秉持一種消極的情感偏向,而對熟人的情感偏向是非常模糊且不確定的(袁曉勁,郭斯萍,2017)。可見,由于熟人處于人際關系的中間地帶,在人際互動中具有很強的不穩定性和模糊性,從而導致人們在社會互動中產生了不確定感,進而影響了道德決策的過程。
在ERP 指標上,我們同樣觀察到了這種“熟人效應”,即與朋友和陌生人相比,涉及熟人的道德決策誘發了更大波幅的ERP 成分(如N1、P2、P260和LPP)。在早期的直覺反應階段,相比于朋友和陌生人,涉及熟人的兩難決策在額葉誘發了更負的N1 波幅。N1 成分在道德決策過程中普遍被認為反映了一種快速而自動的道德直覺過程,代表了個體對道德情境中與決策有關信息的初級加工和注意偏向,如好壞、真假等道德效價信息,以及誘發情緒和認知沖突的突顯信息等(Gui et al.,2016;Scheele et al.,2014)。這表明熟人關系導致的人際不確定性在道德直覺階段就已經自動捕獲了更多注意,進而為后續的精細加工做好準備。在中期的情緒反應階段,這種“熟人效應”繼續在出現在前額葉的P2 和頂葉的P260 成分上,即涉及熟人的兩難決策還誘發了更大波幅的P2 和P260 成分。P2 被認為反映了道德決策中的沖突監控,更大波幅的P2表明道德困境誘發了更強的認知沖突(Chen et al.,2009)。隨著決策進程的推進,先前感知到的認知沖突開始誘發相應的情緒反應,并在頂葉誘發了P260 成分。以往ERP 研究認為P260 反映了道德決策過程中由道德刺激或兩難事件誘發的情緒反應過程,情境誘發的認知沖突越大,情緒反應則越強,P260 的波幅就越大(Gui et al.,2016;Sarlo et al.,2012;Yoder &Decety,2014)。在晚期的認知推理階段,這種熟人效應仍然體現在頂葉的LPP (300~450 ms)成分上。前人相關研究認為,LPP 被認為反映了道德決策中的認知推理和道德評價過程,其波幅大小反映了個體為解決道德困境而投入的注意資源和認知努力(Beste et al.,2012;Chen et al.,2009;Gui et al.,2016;Paynter et al.,2009)。在本研究中,與朋友和陌生人相比,涉及熟人的兩難決策在道德決策的大腦時間加工進程中均分別誘發了更大波幅的N1、P2、P260 和LPP (300~450 ms)成分。而且,被試報告的主觀愉悅體驗與P260 波幅成顯著的負相關,決策時間與LPP (300~450 ms)成分呈顯著的正相關,說明涉及熟人的決策確實誘發了更強的負性情緒反應,并消耗了更多注意資源和認知努力來解決該兩難沖突。ERP 指標上的這種“熟人效應”也獲得了以往相關研究的支持。例如,有研究采用ERP技術考察了社會距離對道德決策的影響,同樣發現涉及熟人的兩難幫助決策誘發了更大波幅的P260和LPP 成分(Zhan et al.,2018;占友龍 等,2020)。因此,這些研究結果表明,熟人關系的不確定性在道德決策的不同時間加工進程中,確實給決策者帶了更強烈的情緒和認知負荷,并消耗了更多的注意資源和認知努力來解決該道德沖突,以最終做出適應的道德決策。人際間道德決策在反應時和ERP指標上的“熟人效應”這一研究發現,拓展了以往關于人際距離影響利他性社會決策的認知與神經機制的研究發現,并進一步揭示了中國文化背景下人際間道德決策的中國特點。
4.3 聲譽關注削弱了道德決策中的傷害厭惡和認知沖突
本研究還發現涉及熟人的決策在ERP 指標上所誘發的“熟人效應”在公開情境下消失了。具體而言,決策情境與社會距離的交互作用在 P260 和LPP (300~450 ms)這兩個ERP 成分上均被顯著觀察到了,即與匿名情境相比,這兩個指標上所觀察到的“熟人效應”在公開情境下消失了。該研究結果表明聲譽關注可能削弱了兩難道德決策所誘發的傷害厭惡和認知沖突。這一研究結果同樣獲得了以往相關研究的支持。例如,一系列行為研究發現,在匿名情境或無他人在場時,決策者會為了獲得更多金錢收益而做出更多利己的風險選擇和更少的道義性判斷,而當決策結果公開或有他人在場時,決策者卻表現出了更多利他的決策意愿和行為(Arfer et al.,2015;Bixter &Luhmann,2014;傅鑫媛 等,2015;占友龍 等,2020)。此外,相關的ERP 研究也發現,在匿名情境(占友龍 等,2020)或私下情境(Zhan et al.,2020)中,與朋友和陌生人相比,熟人關系的不確定性在幫助困境下的道德決策中確實誘發了更大波幅的與厭惡情緒有關的P2 成分,以及與認知推理有關的LPP 成分。然而,當犧牲自我利益而幫助他人免受傷害這一決策行為能被受助者獲知的時候(與匿名情境相比),決策者會表現出更強的利他主義動機來維護自我聲譽或形象,且兩難決策誘發的在不同社會距離間的差異也消失了(占友龍 等,2020)。這表明個體在公開情境下增加的利他行為可能是源自于一種“利己的利他主義”,其目的是為了維護自我聲譽或形象的,而非真正的“超級利他主義”。在本研究中,當決策結果通過電腦聯網呈現給受助者時,個體會感知到較強的聲譽損失風險,進而促使其在不同社會距離情境下均表現出了更快和更多的利他性選擇。由此可知,決策結果公開所激發的聲譽關注,可能削弱了兩難傷害決策所誘發的厭惡情緒和認知沖突,進而減弱了不同社會距離情境間神經反應的差異。因此,聲譽關注可能通過削弱不確定性的人際關系所誘發的厭惡情緒和認知沖突而調節道德決策的行為反應。這一研究發現進一步在傷害困境下的道德決策過程中驗證了由于聲譽關注而引發的“利己的利他主義”行為傾向,并從大腦時間加工進程上提供了一定的生物學證據。
首先,本研究的結果豐富了道德決策的雙加工模型(the dual-process model)。該理論認為個體的道德認知中存在情緒和認知兩套系統,前者是一個平行的,自動化的加工過程,而后者是一個控制的,包含認知努力的過程,會占用較多的心理資源(Greene et al.,2001,2004)。研究者認為道德決策中情緒與認知的參與程度會受到情境因素的動態調節(Christensen &Gomila,2012;Zhan et al.,2018;占友龍 等,2020)。在本研究中,與親密的朋友和疏遠的陌生人相比,個體對人際關系不確定的熟人進行兩難傷害決策時,消耗了更長的時間,并體驗到了更強烈的負性情緒和認知沖突,表現出一種典型的“熟人效應”。這說明個體對朋友或陌生人進行兩難決策時可能有更多情緒/經驗系統的參與,而對熟人進行決策時可能需要更多認知系統的參與來權衡得失。因此,本研究的發現對道德決策的“雙加工理論”在不同社會距離情境下的作用條件進行了一定的補充和解釋。其次,本研究在中國文化背景下考察社會距離與聲譽關注交互影響傷害困境下道德決策的認知和神經機制,研究發現在一定程度上對以往相關研究有所拓展和推進。一方面,本研究在兩難電擊選擇上發現的“人際差異性”以及在反應時和ERP 指標上發現的“熟人效應”,這跟以往西方研究中發現的“超級利他主義”傾向是顯著不同的,表現出了一定的中國特色。另一方面,本研究還發現與匿名情境相比,被試在公開情境下對3類目標他人做出了更少的電擊傷害選擇,且不同社會距離情境下ERP 指標上的差異消失了。然而,電擊傷害比例仍然達到了50%以上,這表明公開決策結果所誘發的聲譽關注可能對個體的利己動機產生了一定的抑制作用,但對個體利他動機的激發可能是有限的,個體的決策傾向仍是一種減弱了的“利己的利他主義”。這一研究發現為進一步揭示道德決策中利己與利他動機的權衡機制提供了一定的行為與腦電證據。最后,本研究采用的“電擊-獲利困境”任務較好地誘發了一種“增加自我收益”與“減少他人傷害”的兩難沖突,并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改編而與ERP 技術相結合,有助于揭示傷害困境下道德決策中個體權衡利己與利他動機的大腦時間加工進程特點。ERP 指標上的研究發現對以往的行為研究結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推進與拓展,也為探討不同社會情境下道德決策的認知和神經機制提供了新的方法借鑒。
本研究仍存在不足之處,一方面實驗采用的“電擊強度-金錢收益”矩陣是根據主觀報告和滴定法收集得到的,其目的是通過被試自身的主觀疼痛感受來推測目標對象的疼痛感受,因此可能會存在較大的個體差異,如容易受到個體的疼痛敏感性和共情能力的影響。未來研究可以進一步探討高、低疼痛敏感性或共情能力個體在傷害困境下道德決策時的差異特點。另一方面,本研究從主觀愉悅度和決策速度兩個方面對行為和ERP 結果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解釋,然而卻忽視了傷害厭惡(Crockett et al.,2014;Volz et al.,2017)和自我形象關注(Zlatev et al.,2019)在其中可能起到的重要作用。因此,未來研究需要構建有關傷害厭惡或自我形象關注的行為模型來探究聲譽關注與社會距離對道德決策的影響,并進一步分析其與神經生理指標上的關聯性,從而提高其解釋力度。
5 結論
本研究采用ERP 技術從大腦加工的時間進程角度,考察了聲譽關注和社會距離對傷害困境下道德決策的交互影響。結果發現:在匿名情境下,與熟人和陌生人相比,個體更愿意犧牲自我收益來減少對朋友的疼痛電擊傷害,行為指標上表現出一種明顯的“利己的利他主義”傾向;且涉及熟人的道德決策耗時最長,誘發了更強的厭惡情緒(以P260 為指標)和認知沖突(以LPP 為指標),反應時和ERP指標上表現出一種明顯的“熟人效應”。然而,這種“利己的利他主義”決策傾向和“熟人效應”在公開情境下分別減弱和消失了。結果表明,決策結果公開激發了個體對個人聲譽的關注,進而有效削弱了利己傾向和人際關系的不確定性在道德決策中所誘發的厭惡情緒和認知沖突。本研究從行為和電生理層面揭示了聲譽關注對不同社會距離下傷害困境中道德決策的調節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