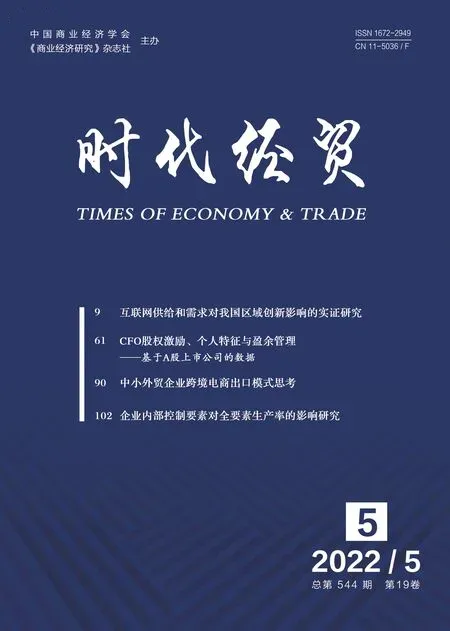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影響
陳前進 徐為賓
(暨南大學國際商學院 廣東珠海 519070)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全球經濟增長狀況持續(xù)低迷,國內外市場同樣出現(xiàn)了不同程度的需求不足問題,而有效解決需求不足是實現(xiàn)經濟再次增長的關鍵因素,因此各國政府積極出臺了各種產業(yè)政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經濟政策,導致全球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進一步加劇。我國作為貿易大國,出口貿易在貿易總量當中占據(jù)著重要地位,伴隨著中美貿易摩擦的開始,美國有意限制資本與技術密集型產品對我國的出口而在進口貿易上堅持保護主義,這一舉措使得我國的出口前景更加的撲朔迷離。基于此背景,“十四五”規(guī)劃明確提出要從產業(yè)政策轉向促進產業(yè)升級上來,只有脫虛向實發(fā)展,才能真正為經濟高質量發(fā)展打下堅實的基礎,在全球不確定性日益增強的環(huán)境下穩(wěn)定發(fā)展。出口技術復雜度則可以有效衡量產業(yè)結構優(yōu)化指標,因此探討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對我國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影響是實現(xiàn)經濟高質量發(fā)展的重要議題。那么,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是否影響一國出口技術復雜度?這種影響的機制又是怎樣?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對于一國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影響在不同條件下是否保持一致?本文嘗試探討上述問題。
文獻綜述與理論機制
(一)經濟政策不確定性
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是指當經濟政策變化時,人們無法預期判斷有關經濟領域事件發(fā)生的可能性,即發(fā)生的有關經濟事件與人們一般考慮的狀況不同,反映了經濟的運行狀態(tài)與經濟參與者的評估與預期不一致的程度。要想了解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影響,首先要對其進行有效衡量,現(xiàn)有文獻多是以構建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指數(shù)來進行測量(Baker、Bloom、Davis,2016;陳樂一、張喜艷,2018)。
本文將從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的效應進行文獻梳理,主要從國內及國外企業(yè)投融資行為及貿易角度切入。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會通過外部需求、流動性資金需求及長期資金需求對企業(yè)的投資行為產生影響(王義中、宋敏,2014;李鳳羽、楊墨竹,2015;駱飛,2019);鄭淑芳等(2020)從雙向國際直接投資的視角切入,分析了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對于全球價值鏈嵌入度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經濟政策不確定性降低了中國制造業(yè)在全球價值鏈的分工地位。還有部分學者認為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降低了企業(yè)融資的能力,同時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還有可能進一步增加了企業(yè)的現(xiàn)金持有(王朝陽等,2018;才國偉等,2018);貿易政策不確定性的加大對于我國高技術產品的出口有抑制作用(劉鈞霆等,2021;王明濤、謝建國,2019);潘家棟、韓沈超(2018)認為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會有效抑制我國出口貿易,并且這種影響主要是通過生產供給路徑實現(xiàn)的。
(二)出口技術復雜度
出口技術復雜度作為有效衡量出口貿易質量的重要指標,相關研究就顯得尤為重要。
從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測算方法上進行文獻梳理,目前關于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測量方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Hausmann、Hwang和Rodrik (2007) 提出的兩步法,第一步需要在產品層面計算出口技術復雜度,再通過產品層面的出口技術復雜度計算國家層面的出口技術復雜度;另一種方法是基于Hummels、Ishii和Yi (2001)的垂直專業(yè)化模型來測算,通過識別中間投入產品,再根據(jù)國際垂直專業(yè)化分工程度來測算出口技術復雜度。
從影響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因素進行文獻梳理,部分學者從技術升級的角度研究對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影響,出口規(guī)模的增加并不能有效提高出口技術含量,而企業(yè)技術升級對于提高出口技術含量有著重要的作用,這是現(xiàn)有學者普遍支持的觀點。劉志堅(2021)認為數(shù)字經濟發(fā)展可通過刺激技術出口行業(yè)加大研發(fā)創(chuàng)新投入,從而提升出口技術復雜度;基于貿易層面的研究,盛斌、毛其淋(2017)研究發(fā)現(xiàn),最終品與中間品的貿易自由化能夠顯著提高企業(yè)出口技術復雜度,這主要是由于通過競爭效應與種類效應所引起的;張鳳等(2018)提出出口持續(xù)期的延長有利于國內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提升;田暉等(2020)研究發(fā)現(xiàn)經濟政策不確定性對我國制造業(yè)出口具有顯著的抑制效應。也有部分學者從制造業(yè)服務化的視角來研究出口技術復雜度,制造業(yè)實現(xiàn)服務化有利于使企業(yè)從以制造為中心轉向以服務為中心、進而可提升服務業(yè)的技術創(chuàng)新能力、提升服務業(yè)的技術溢出效應和有助于服務業(yè)高端人力資本的積累,從而能夠提升服務業(yè)出口技術能力(王思語、鄭樂凱,2018;劉敏,2019);另外還有部分學者從制度質量的視角來研究出口技術復雜度,張雨、戴翔(2017)認為服務業(yè)部門利用國際投資對于服務業(yè)出口技術復雜度有著顯著提升的作用,制度質量作為調節(jié)變量也對此過程具有正向促進作用。
(三)理論機制
已有研究表明影響一國出口技術復雜度的關鍵在于一國的技術研發(fā)水平,本文認為經濟不確定性通過以下兩種渠道作用于出口技術復雜度:第一,國內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會給國內外投資商提供預警,他們會將資金投入到那些經濟政策波動較小的國家(單東方,2020),使得“學習效應”的作用下降,無法在國外廠商投資的過程中獲得技術溢出,同時國內廠商由于本國經濟政策的波動性過大,也會相應減少對國內的投資,甚至可能將資金投入到別國市場,從而降低了國內的研發(fā)資金,進而降低研發(fā)水平致使我國出口技術復雜度進一步下降;第二,由于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會對產品的出口產生負面影響(謝申祥、馮玉靜,2020;郎麗華等,2021),使得企業(yè)整體利潤空間降低,同時會增加企業(yè)生產的可變成本(張成思、劉貫春,2018),減少企業(yè)的固定投資與研發(fā)資金,進一步抑制出口技術復雜度。
模型設定與變量說明
(一)計量模型設定
本文主要考察我國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對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影響,在現(xiàn)有的研究基礎上構建的回歸模型如下:

其中,EXPY為t年出口國家j的技術復雜度;EPU為t年出口國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波動指數(shù);X為控制變量集,包括出口目的國基礎設施建設情況、人均GDP水平、人口總數(shù);ε為隨機誤差項;μ為國家的虛擬變量,由此來控制不能觀測的固定效應;δ為所在年份虛擬變量,用來控制當前年份的整體形勢。
(二)變量說明
1.解釋變量——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
本文在研究經濟政策不確定性時使用的數(shù)據(jù)來源于Baker、Bloom和Davis (2016)。Baker指數(shù)是通過統(tǒng)計《南華早報》每月刊發(fā)同我國經濟、政策及不確定性有關文章的報道數(shù)量,并以當月報道總數(shù)量進行標準化,以得到中國每月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指數(shù)。和大多數(shù)研究相同,基于該月度指數(shù)使用年度算術平均(EPU1)來表征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并用幾何平均指數(shù)(EPU2)來進行穩(wěn)健性檢驗(張成思、劉貫春,2018)。
算數(shù)平均值計算方法:

幾何平均值計算方法:

2.被解釋變量——出口技術復雜度
本文采用1995-2015年中國制造業(yè)的數(shù)據(jù)測算對其他國家的出口技術復雜度,具體行業(yè)分類方法借鑒Lall(2000)的方法,測算方法上采用Hausmann等(2007) 的方法。具體過程如下所示:
(1)測度每類出口產品的技術復雜度。即:

其中,PRODY代表產品k的技術復雜度,x代表國家i產品k的出口額,X=∑x代表國家i的出口總額,Y代表國家i的人均實際GDP。
(2)計算中國對某國的出口技術復雜度。即:

其中,EXPY表示中國對國家i的出口技術復雜度,xik代表中國對國家i產品k的出口額,X=∑x代表中國對國家i的出口總額。
3.控制變量
本文采用出口目的國人均GDP水平、出口目的國人口總數(shù)、出口目的國基礎設施情況作為其控制變量。其中,出口目的國人均GDP數(shù)值是將人均實際GDP數(shù)額取自然對數(shù),出口目的國人口總數(shù)也是將其取自然對數(shù),出口目的國基礎設施情況是將人均電力消費取自然對數(shù),以上數(shù)據(jù)來源均為世界發(fā)展指標(WDI)數(shù)據(jù)庫。
實證結果與分析
(一)描述性統(tǒng)計
從表1的描述性統(tǒng)計結果來看,各個指標存在一定的差異。出口技術復雜度最大值為19.1342,最小值為0,但這是由于數(shù)據(jù)缺失導致的,實際上出口技術復雜度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相差較小,說明我國對國外出口技術復雜度差別不明顯;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最大值為236.7176,最小值為35.5665,標準差為48.7215,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相差較大,說明樣各國之間的經濟政策不確定性程度存在較大差異;出口目的國國內基礎設施建設指數(shù)最大值為1.4867,最小值為-5.214,標準差為1.1993,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相差較大,說明樣各國之間的基礎設施建設能力存在較大差異;出口目的國人均GDP最大值為11.6854,最小值為4.5057,標準差為1.5863,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相差較大,說明樣各國之間的經濟規(guī)模差異較大;出口目的國人口總量最大值為20.9934,最小值為9.1929,標準差為2.0439,最大值和最小值之間相差較大,說明樣各國之間的消費市場規(guī)模存在較大差異。

表1 變量描述性統(tǒng)計
(二)基準回歸結果及分析
為保證上述回歸模型結果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本文在模型回歸之前考慮了以下幾個問題:首先,考慮到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并非嚴格外生的,從而可能導致內生性問題,且相關文獻對于內生性問題一般使用工具變量來解決,然而由于沒有嚴格外生又可以替代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的工具變量,因此本文在模型中加入固定效應項來降低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變量可能受到的內生性影響。其次,考慮到模型中所用數(shù)據(jù)隨時間變化,而傳統(tǒng)的固定效應模型只考慮到了個體效應,而沒有對不同時期、不同地區(qū)的殘差相關性進行考慮,可能導致估計結果存在較大偏誤,因此本文采用固定效應模型的同時加入國家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以此來消除傳統(tǒng)固定效應模型由于只考慮個體效應所導致的估計偏誤問題;另外,由于采用了國家固定效應、時間固定效應,因此本文剔除了貿易引力模型中常用的距離、共同語言等控制變量。最后,為克服面板數(shù)據(jù)可能存在的組間異方差問題,本文采用常用的數(shù)據(jù)處理(取對數(shù))和穩(wěn)健標準誤進行回歸。基準回歸結果如表2所示。

表2 基準回歸結果
表2中基準回歸第1列顯示的結果是單純考慮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這一關鍵變量而未納入其他變量所得,結果顯示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越大越不利于我國出口技術復雜度,逐次加入基礎設施建設、人均GDP及人口控制變量,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對出口復雜度的影響依然顯著為負,這也側面驗證了此結論的穩(wěn)健性,可知人均GDP越高則越有利于一國出口技術復雜度的提高,而人口越多及基礎設施建設越完善卻對出口復雜度的提升有減弱的作用,這可能是由于數(shù)據(jù)統(tǒng)計不足的問題所導致的。
(三)穩(wěn)健性分析
為了驗證結論的穩(wěn)定性,本文采用替換自變量、滯后一期及劃分樣本的方式來進行驗證,檢驗結果如表3所示,同時上文采用的逐步回歸也側面驗證了回歸結果的穩(wěn)健性。

表3 替換自變量回歸結果
由表3可知,在不添加控制變量之前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與出口技術復雜度是顯著為負的,在添加出口目的國基礎設施情況、出口目的國人均GDP及出口目的國人口總數(shù)控制變量之后,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與出口技術復雜度依然是顯著為負的,證明了此結論的穩(wěn)定性。
由于考慮到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效應可能存在滯后性,本文選擇將其進行滯后一期回歸,如表4所示。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提高依舊會降低我國出口技術復雜度,同時將原有樣本按照發(fā)達國家與發(fā)展中國家進行劃分(劃分標準來源于聯(lián)合國開發(fā)計劃署公布的人類發(fā)展報告),回歸結果依然顯著,上述兩項進一步證明了原有結論的穩(wěn)定性。

表4 自變量滯后一期及劃分樣本回歸結果
結論與建議
經過改革開放四十多年的發(fā)展,我國已成為全球的貿易大國,但還遠未達到貿易強國的標準,隨著世界經濟發(fā)展大環(huán)境的不確定進一步增強,這是我國進行貿易轉型的好時機,提高我國出口技術復雜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現(xiàn)實意義。因此,本文基于1995-2015年我國對169個國家出口數(shù)據(jù)考察了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對出口技術復雜度的影響,研究發(fā)現(xiàn)經濟政策的不確定性會顯著抑制出口技術復雜度,在各項穩(wěn)健性檢驗當中,回歸結果仍保持一致,證明了此項結論的穩(wěn)定性。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本文提出以下建議:第一,當前我國經濟發(fā)展中面臨著產業(yè)結構升級問題,事關能否保持長期高效的經濟增長,因此有關部門要積極推動科技體制改革,促進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值產業(yè)的發(fā)展;第二,有關部門在進行經濟政策調整時,應注意把握市場實際狀況及政策實施力度,不能盲目地脫離市場實施“一刀切”政策,有針對性地、合理地進行經濟政策的調整才能發(fā)揮其原本的經濟作用,積極滿足創(chuàng)新型企業(yè)的發(fā)展資金需求,拓展出口技術復雜度提升的空間與渠道;第三,貿易伙伴國之間應當增強友好互信的合作關系,積極主動溝通,避免因政策信息的偏差導致的貿易摩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