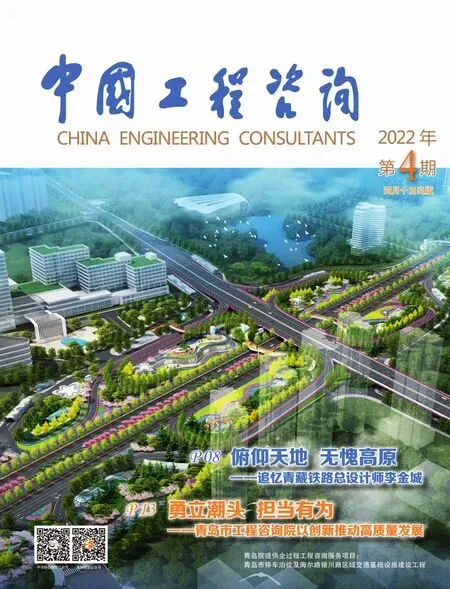基于產城人維度的國家級新區建設研究及對浙江省的啟示建議
文/童志怡 沈鋒 毛家怡
國家級新區是承擔國家重大發展和改革開放戰略任務的綜合功能區,在各地經濟發展中起著重要的風向標作用,全國已先后設立19個國家級新區。從發展歷程看,國家級新區建設起步早、類型多、經驗足,因此有必要總結分析國家級新區建設經驗,用以指導浙江省省級新區的總體布局和路徑安排。
一、國家級新區建設情況分析
(一)國家級新區的設立背景和管理模式
1.設立背景—承接國家戰略,注重東西平衡
從時間脈絡看,國家級新區的設立共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1990-2009年),國家批復設立上海浦東新區和天津濱海新區,推動沿海開放重心由南向北拓展;第二階段(2010-2013年),國家相繼批復設立重慶兩江、浙江舟山群島、甘肅蘭州和廣州南沙4個新區,推動區域經濟發展格局逐漸由“東部率先”向“四大板塊”(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和東部率先)的區域協調發展邁進;第三階段(2014年以后),先后批復設立西咸新區、貴安新區、西海岸新區等13個新區,形成對“四大板塊、三大支撐帶”( 三大支撐帶:“一帶一路”、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國家戰略的重點支撐[1]。
從空間分布看,19個國家級新區中,位于東部沿海經濟相對發達地區的有7個,其設立的主要目的在于“質”的層面,即探索經濟高質量發展路徑;其余12個位于經濟發展水平相對較低的東北、西部和中部地區(東北3個、西部6個,中部3個),其設立的目的主要是考慮東西部區域平衡發展,將國家級新區打造成新經濟增長極,帶動區域經濟快速增長[2]。
2.空間基底—獨立行政區+跨市整合+市內融合
國家級新區設立的空間區劃基底有四種方式,見表1[3]。

表1 國家級新區空間基底情況及主要特點
3.管理模式—地方政府與管委會交叉并行
國家級新區的日常管理有四種基本模式,見表2。

表2 國家級新區日常管理模式
(二)國家級新區建設發展情況評價
1.國家級新區發展路徑分類:以開發區類型為主
由于功能定位和管理模式的差異,國家級新區的發展路徑呈現以下三種類型:一是改革主導型(準經濟特區),以政策試驗為主,作為經濟體制改革的試驗田,為進一步擴大改革范圍積累經驗,充當改革先行地和標桿示范基地,主要包括浦東新區和濱海新區,其中濱海新區承擔一部分改革任務,但是在實際運行過程中仍然偏向發展主導;二是發展主導型(升級版開發區),整合土地等空間資源要素,以特色產業發展為導向,打造地區經濟增長新引擎,帶動當地及周邊區域經濟增長,包括2010-2016年間成立的16個國家級新區,為國家級新區的主體;三是區域平衡型(再造新城),承接過載大城市外溢的各項資源,在大城市周邊再造新城類型的新區,實現區域協調平衡發展,主要指雄安新區。
2.國家級新區發展階段評價:經濟貢獻明顯,產業轉型較難
根據第三產業占比、國家級新區與所在市GDP增速比兩個指標,對代表新區進行分析,見圖1、圖2。根據圖1和圖2,將國家級新區發展階段分為初創期、上升期、轉型期和成熟期四個階段,見表3。

表3 國家級新區發展階段評價

圖1 國家級新區第三產業占比變化趨勢

圖2 國家級新區與所在市GDP增速比變化趨勢
國家級新區與所在市GDP增速比處于1.2至1.4之間時,對所在市的經濟增長貢獻明顯。西海岸新區、湘江新區和南沙新區的GDP增速比呈“凸字形”下降趨勢,趨向于1.0,新區增長后勁不足;濱海新區、舟山群島新區的GDP增速比波動較大,第二產業主導明顯,制造業升級動能不足,高端服務業發展乏力,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難度較大;浦東新區GDP增速比波動較小,基本穩定在1.3左右,并且經過兩個十年的發展,第三產業占比從25%提升至77%,形成以金融、航運、貿易為主導的現代服務體系,新區進入成熟穩定發展階段。
3.國家級新區產城人融合程度評價
從產業、城市、人口三個維度,分別選取GDP、建成區面積和常住人口三個數據的增速作為評價指標,對浦東新區、濱海新區和舟山群島新區三個國家級新區的產城人融合程度進行評價,見圖3、圖4和圖5。

圖3 浦東新區GDP、常住人口、建成區面積增速情況

圖4 濱海新區GDP、常住人口、建成區面積增速情況

圖5 舟山群島新區GDP、常住人口、建成區面積增速情況
(1)浦東新區:產城人同步發展。經過30年的發展,浦東新區已進入穩定發展階段,經濟增長高速穩定,城區建設略先于人口發展,目前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均趨于飽和,亟待尋求新發展空間。
(2)天津濱海新區:產業主導,城人同步跟上。濱海新區經濟發展總體后勁不足,GDP增速下降明顯,缺少經濟新增長點,城市建成區面積和常住人口增速基本同步,滯后于產業發展,但均趨于飽和,城市建設放緩,人口吸引力下降。
(3)舟山群島新區:產業主導,城市擴展,人口滯后。舟山群島新區經濟增長強勁,GDP增速保持在10%左右,城市建設先于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但長期以來人口增長緩慢,“城等人”“產等人”現象較為嚴重。
二、對浙江省省級新區建設的四點啟示建議
(一)浙江省省級新區設立基本情況
2019年以來,浙江省圍繞大灣區建設先后設立杭州錢塘新區、寧波前灣新區、紹興濱海新區、湖州南太湖新區、金華金義新區和臺州灣新區6大省級新區,作為承接國家戰略機遇、輻射帶動省內區域發展和提升省域一體化水平的重要戰略抓手,基本情況見表4(2022年1月批準設立的溫州灣新區,由于設立時間短,暫未做統計分析)。

表4 浙江省六大省級新區情況一覽表
(二)對浙江省省級新區建設的四點建議
考慮到浙江省省級新區設立時間不長,發展水平參差不齊,建設模式各有特色,因此結合國家級新區建設情況,提出以下四點建議。
1.空間上,更加注重山海區域平衡
19個國家級新區中僅有7個位于東部沿海地區,其余12個位于中西部和東北地區,占近2/3,空間上考慮了東西平衡、山海兼顧,戰略上覆蓋了西部大開發、東北振興、中部崛起、“一帶一路”、粵港澳大灣區、長江經濟帶和京津冀協同等。
浙江省現有6個省級新區連同國家級舟山群島新區基本位于東部沿海地區,主要承擔了大灣區建設功能,因空間上的東西失衡,故建議更加注重山海區域平衡,聚焦大花園建設及大通道布局,在大花園地區增設省級新區,打造大花園地區新的經濟增長極,推動大花園與大灣區協同發展,助力山區26縣加快發展。同時省級新區的增設應當堅持功能集成、好中選優的原則,防止省級新區過多過濫。
2.功能上,更加突出改革創新味道
國家級新區中,上海浦東新區為改革主導型建設路徑,雄安新區為國家主導的戰略新城,其余17個國家級新區基本為發展主導型路徑,大致等同于開發區升級版,新區總體上“新”的味道不濃,浙江省省級新區情況亦與之相近。
浙江省省級新區建設因此需要更加突出改革探索功能,圍繞浙江省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將其中涉及的科技創新、數字化改革、分配制度改革、城鄉區域協調發展、公共服務、生態產品價值實現等重大改革任務分解落實到相應省級新區建設中去,每個省級新區至少承擔1項重大改革任務,發揮新區先行先試作用,探索部分行政審批和管理權限下放至新區。對于需要增設的省級新區,應當堅持發展與改革并重,在確定其發展定位的同時,明確其改革攻堅使命。
3.職能上,處理好新區與行政區的關系
國家級新區中,除上海浦東新區、舟山群島新區、廣州南沙新區、青島西海岸新區、大連金普新區5個新區是基于完整行政區組建外,其余14個均為跨區域整合組建而成,跨區域整合的新區在整合過程中跨區域利益沖突問題普遍存在,新區和原所屬行政區的經濟管理、社會管理職能的邊界劃分不清,導致管理成本較高、管理效能偏低。為破解上述問題,國家級新區做了大量有效探索,如南京江北新區按照管理職能遞減原則,將新區分為核心區、直管區、共建區和協調區四類,直管區(包含核心區)由江北新區管委會直接管轄,共建區由管委會和原行政區政府部門共同管轄,協調區由管委會和原行政區政府部門協調管轄。
浙江省現有省級新區中,除金華金義新區外,其余均由開發區整合地方街道組建而成,在整合過程中需要重點發揮產業鏈整體協調作用,通過產業融合帶動區域融合,同時需要兼顧被整合行政區的利益訴求,防止被整合區的邊緣化。目前,杭州錢塘新區已整體轉變為行政區—杭州市錢塘區,因此現有省級新區以及未來可能增設的省級新區,均需要同步考慮后續可能出現行政區劃調整問題,提前開展行政區劃調整的可行性研究。
4.路徑上,把握好產城人發展節奏
國家級新區建設總體上均呈現產業先導、城市擴張、人口增長的發展節奏,但產城人發展的融合程度不盡相同。上海浦東新區產城人基本同步發展,協調性較好;天津濱海新區產業主導,城人同步跟上,但后續經濟增長乏力,拖累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舟山群島新區產業和城市發展均較快,但人口增長滯后。
反觀浙江省省級新區建設,產業發展十分迅速,但城市建設和人口增長均相對滯后,市政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所需資金缺口較大,因此在發展中需要堅持“以產興城、以產引人、以城留人”的原則,通過機制創新,吸引外來高端人才加入,助推本地農村人口就業轉移。根據產業發展需要和常住人口增長趨勢,穩步推進城市化進程,重點防止城市過度擴展和房地產化,通過產業發展、稅源增加和投融資模式創新,擴大市政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建設資金來源。
三、結束語
相較于國家級新區,省級新區的設立時間和發展歷程較短,因此需要充分借鑒國家級新區的建設經驗,同時也可以推動省級新區與國家級新區的互動。一方面,設立國家級新區的條件不成熟但又急需在發展空間上尋求突破的,可以通過設立省級新區,先行開展省內探索;另一方面,對于成長迅速、示范效果好的省級新區,可以推動上升為國家級新區。通過國家級新區和省級新區的互動,將有助于加速國家戰略和地方發展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