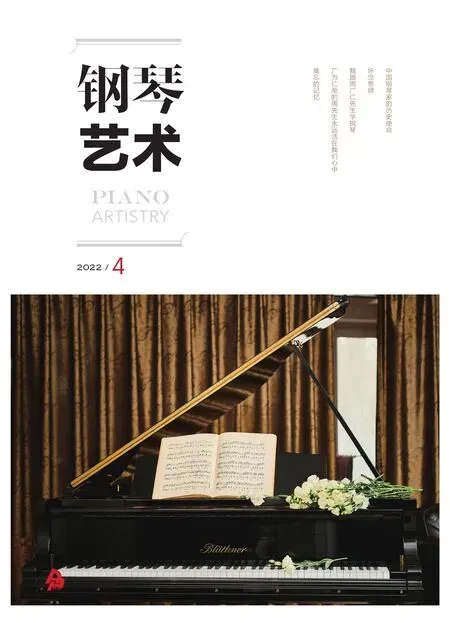懷念恩師
文/但昭義

2022年3月7日午后,突然得知恩師走了,止不住撕心裂肺、淚如泉涌……
從20世紀60年代到今天,那些往事又一幕幕涌現眼前。
我的老師是周廣仁
1961年的早春二月,北方還是乍暖還寒的天氣,距離川音選送我赴京進修學習的時間轉眼已過去近半年,但我還沒有真正找到鋼琴老師,心啊,何等焦急。臨行前,老院長常蘇民把他的想法交代給我的情景時時在我眼前浮現,他說:“眼下沒有別的辦法送你到中央進修鋼琴。學校沒有打擊樂,我跟李凌同志(時任中央樂團團長)已談妥,送你去中央樂團學習打擊樂,同時進修鋼琴。川音鋼琴教學底子薄,寄希望于你們學成回來。”語重心長的話語與現實的情景令我焦灼不安。
起先,樂團分配一位年輕指揮張孔凡先生教我。張老師能在音樂上給我指導和幫助,但從鋼琴專業的角度,他不能幫我解決彈奏上存在的許多毛病,如彈奏緊張、手指跑不動、彈奏概念不清,等等,又如何能繼續下去?在困難時期,學校能夠送我出來學習,不僅每月給我發生活補貼,在樂團無力提供練習用琴的情況下,還專門從四川運一臺鋼琴來北京供我專用。在那個年代真是不容易的事!我感到自己壓力很大,卻束手無策。京城人才濟濟,名師不少,而我人地兩生,尋師無門,萬般焦急。我找到中央廣播樂團的老同學舒承一,他替我求到他的同事,樂團鋼琴獨奏員周勤齡老師。可不知道是因為我水平太差,還是因為她工作太忙,沒上幾次課,她就打了退堂鼓。記得那是1962年3月25日,在她上完課后突然對我說,她不能再教我,讓我去中央音樂學院找周廣仁先生。我想,我這年齡、水平,去找中央音樂學院的大教授,中國著名的鋼琴家?有沒有搞錯?我天性怯弱,加之在鋼琴上的自卑,哪里敢想!我冒著膽兒請她幫忙介紹一下,卻被她一口拒絕了。從周勤齡老師家出來,我茫然不知所措。悶了幾天,想不出其他任何辦法,重任在身,不容猶豫,我逼著自己,鼓足勇氣去試一試。

我將來也要做這樣的老師
周老師在很短的時間里幫助我克服了彈奏上的一些毛病,她的課講得很細,不僅在要點上示范,而且常常整曲示范演奏,讓人折服。她每次講課要求明確、要點清楚,使我既知道要做什么,又知道該怎么做。所以,每節課都很有收獲,每節課都能有進步。當時,我做了好些筆記和課后感悟(以后有機會跟大家分享)。非但如此,做周老師學生的幸運不僅是在專業上的收獲,更為難能可貴的是深受她高尚品格的影響。
周老師每周日犧牲休息時間為我上課,并幾年如一日堅持拒收學費,即使我講明是由學校支付,她也堅決不收。許多事情當時很難去深層次地理解,恍然大悟時方知,她在默默踐行著“為四川做一點兒工作”的初衷。
20世紀60年代初的困難時期,樣樣都憑票供應。那時我戶口在四川,口糧只有27斤,比北京戶口要少7斤,確實吃不飽,但當時除了冰棒兒不要票其他全都要票,沒有任何別的辦法。周老師知道后就特別關照我,每節課后都留我吃飯,逢年過節一有機會就又讓我去她家吃飯。現在看,吃頓飯算不了什么,可在一切都定量供應的時期,讓我吃一口,周老師家里就要少吃一口。為我上課已經非常辛苦了,還要處處關懷備至,那種無私、那種潤人心扉的情懷,對于一個來自西部邊遠地區的普通學生而言,除了她善良崇高的品格,什么都難以解釋!
還有一件事使我特別難忘。困難時期,北京對外來人口管得特別嚴。有一段時間我亦受到“清理”,不能再住在中央樂團。那是我在北京學習時的第二次“危機”。如果找不到住處,我就得中斷學習回四川去。晚上,我看著幢幢樓房透出的燈光心里郁悶:這么大的北京難道就沒有我一個小人物的容身之地?幸而危難中偶遇一位從四川來的曾慶蓉同學,她動員勸說她的八叔把我留下了。她的八叔是化工八院的工程師,家住離樂團很近的化八院宿舍。他家人口多,夫妻倆和四個孩子,本無力幫助,只因是四川老鄉,又看我學習機會來之不易,就硬是把蜂窩煤爐灶移到過道,騰出廚房來讓我住。北京的冬天,門窗緊閉存在隱患。有一天我真的就煤氣中毒,險些發生意外。周老師了解我從不缺課也不遲到,但某個周日見我怎么不假未到?她放心不下,估計定有意外發生,遂動念要去找人!可當時她只知道我住化八院宿舍,并不確定住哪幢樓。而且那時她既不知八叔姓什么,也不知道八叔在化八院做什么,但第一直覺讓她感到此時必須要找到我,便硬是一幢一幢地在整個化八院宿舍挨家尋訪,找一個住在這宿舍院里彈鋼琴的學生。真不知道她遇到了多少“不知道”的回答,也不放棄,居然最后出現在八叔家門口了。當她突然出現在我面前時,我和八叔一家真是感動無比。誰都知道在那個通訊不發達的年代,在一個大宿舍區用這種挨幢詢問的方式找一個大家不認識的人有多難!這樣一位有聲望的中國著名鋼琴家、大名鼎鼎的鋼琴教授,如此牽掛愛護一個“編外”學生,真是格外令人欽佩。“教授尋生”這段故事就此在化八院被傳為佳話。
我開始到北京學習時,由于清楚地看到自己同北京高水平學生之間的差距,曾深為一種自卑心理所困擾。每每在音樂學院聽音樂會或考試,就會加深這種困惑。有一次附中學生考試,碰巧那天聽到當時附中兩名最突出的尖子生——石叔誠、謝達群彈琴。聽完他們的演奏,我的神經像被雷擊了似的,頓時產生了相當悲觀的想法:我覺得再繼續學鋼琴完全是沒有意義的事情。都二十多歲的本科生了,程度那么淺,彈得那么差,再怎么學、再怎么努力也彈不到人家附中孩子的水平,還搞這一行干什么?還談什么將來當老師!我的情緒驟然掉到谷底,這樣的情緒在回課時被周老師發現了。于是,她讓我坐下來跟她聊聊。我說,很想回四川不學了!她驚訝地問明原因后,沒有批評我,而是以自己的感受現身說法來啟發幫助我。她說:“我自己聽了好的演奏也有很多感受,我對自己看得很清楚,就說劉詩昆、殷承宗吧(他倆是中國20世紀五六十年代相繼在‘柴科夫斯基國際鋼琴比賽’中最年輕的獲獎鋼琴家),我這一輩子也達不到他們的水平,我知道我也不可能成為什么了不起的大演奏家了,但我還愿意學,因為我相信自己可以比過去更有進步,更有提高。”她接著說:“過去我們國家底子薄,現在也才解放十幾年。雖然現在看起來我們算比較優越的,其實也還是過渡時期的人。我想,再過三十年,中國的鋼琴演奏水平和教學水平將會比現在高很多,到那時候我也許更算不上什么,但每個人有自己的客觀歷史條件,只要在各自的崗位上盡心竭力,就算是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任務。你應該懂得,一定歷史條件下的人只能發揮一定的歷史作用,企及過高既不實際,也不科學,反而會傷害自己的積極性。”老師的話像一股清風一下子吹散了心中的迷霧,頓時云開霧散,陽光照亮了我的心。歷史條件、歷史任務、歷史作用……可以說自己也懂。但周先生如此有成就、有聲望的人,如此謙遜地看待自己,如此坦然地激勵學生,個中所彰顯的人格魅力,讓我不僅豁然開朗,還深刻受教。不僅消除了所有的困惑,而且感染我、推動我對事業燃起了永不放棄的執著追求。我會永遠追隨恩師的腳步活到老、學到老。那時的我深深體會到老師不僅在教我彈琴,更在教育我做人。我在當天的筆記中留下了這樣的話:“雖然在業務上我達不到老師的水平,但我將來也要做這樣的老師!”


“為四川做一點兒工作”
1976年“文革”結束后,四川的鋼琴教學開始啟動(當時四川音樂學院尚未恢復,四川省成立的“五七藝校”先招收了一個鋼琴班,我受聘在該班任教),周老師就不遠千里來到成都指導我們。她仍赤誠地抱著“為四川做一點兒工作”的初心。但她來四川時也曾遭受非議,有人說:“四川既然沒有教師,就不要再招生!”按照這種邏輯,落后地區就活該落后,永遠別去管它。周老師心里可不這么想,她的心里裝的是大國情懷。她認為單靠一兩個中心城市不會有真正的事業興旺。她常說她愿做“開發”的工作,愿做“雪中送炭”的工作。她想的不是從自己手上出幾個尖子學生,她希望播下更多的種子,讓他們能在中國更廣大的地區去開發啟蒙不斷提高。他們短時期可能沒有驚人之舉,然而他們在各地進行的工作,無疑將會給祖國鋼琴事業的發展帶來新的希望,發現更多的人才苗子。周老師不為名,不為利,堅持自己的信念,為發展中國的鋼琴教育事業腳踏實地地干,揀最需要的事情干,揀人家不愿干的事情干。在四川期間,她除了給鋼琴班的學生上課,還有求必應地給川音和在藝術院校工作的鋼琴老師上課,給在文藝團體工作的鋼琴演奏人員上課。她的日程排得滿滿的,辦講座、開教材示范演奏會、組織教師專題學術研究和專題學術演奏……言傳身教,影響了川音一代教師。除此之外,她還擠閑偷空、見縫插針地給我開“小灶”。她曾半開玩笑地對我說:“我可是沖著你來的!”這表明她一刻也沒有忘記她希望通過幫助我來實現“為四川做一點兒工作”那個最早的心愿。因此,她希望我比別人更努力一些,學得更多一些。這期間,她曾為我專門分析講解了巴赫的30首創意曲、莫扎特的全套奏鳴曲。每次都是一邊彈一邊講,讓我從整體上有一個印象,為我今后的獨立研究打基礎。她還想出一個辦法讓我接受最新信息,她來四川時帶著剛剛到手的一本英文版鋼琴論著。于是,她就一邊讀原版書,一邊口譯出來,讓我邊聽邊記,并同我討論體會,她還說,這也是她一次很好的學習機會。
按:口苦,是臨床上常見癥狀。常癥以口苦為主,無其他明顯不適。由于口苦是該患者的主要癥狀,無法辨證,而小柴胡湯主要可治療口苦之癥,所有通過小柴胡湯治療以后可以獲得良好的治療效果。
那時,她親自教了四川省“五七藝校”的六名學生,后來大家知道的郭峰就是其中之一。她給這批學生上課,都是公開對所有老師開放的。定期的演奏會和專業考試,也總帶著我一起,默默傳授給我一些經驗。孩子們有演奏會、考試都會緊張,她不是口頭上說幾句安慰的話,而是帶著學生一連幾天走臺鍛煉,走一次臺,點評一次,幾次下來,學生個個都變了樣,上臺不那么緊張了。她開心地對我說:“小但,這辦法靈吧!”
她離開成都回京前,組織了一次教師音樂會,參加的都是所謂“教師培訓班”里的學生。這次音樂會她特地安排了四位老師彈肖邦的四首敘事曲,她安排我彈第一首。音樂會前,也讓我們走了好幾次臺。正式演出那天,我這個“緊張派”還是有些控制不住,彈完下來我對自己非常不滿意。可周老師一直堅持說我彈得不錯,我就是不信。她開口說:“我們聽錄音,聽了你保證會改變看法。”果然,聽下來確實改變了。她告訴我,有時候主客觀感覺是不一樣的。教學生,要學會客觀評價,好就是好,表揚鼓勵再提高;差就是差,自以為是的要批評教育!她就是這樣,時時處處讓你能學到東西。
在四川半年,周老師特別辛勞,做了大量工作。她的講學為四川音樂學院鋼琴系的老師恢復了教學業務,為恢復高考招生后的教學工作做了準備,為四川鋼琴教學后來躍居全國前列作了重要的貢獻。
教學路上送一程
1978年2月,“文革”后的首批大學生入學,我有了第一個專業學生,也算正式開始了我的專業鋼琴教學生涯。從那時起,周老師更加佐助我的教學工作。
在我家的書櫥里至今還珍藏著一本《常用音樂術語詞典》,這本詞典是李其芳老師在中央“五七藝校”任教時選編的。那時“文革”剛剛結束,這類專業用書不是很少而是根本沒有,因此顯得特別珍貴。周老師希望我有這樣的詞典幫助學習和教學,但當時沒有復印機。于是她不惜犧牲寶貴時間,硬是一字一字親手為我抄了一本寄給我。我清楚地記得,那天我收到這份手抄詞典,捧著它眼淚就涌了出來。我知道,這不是一本薄薄的詞典,而是一份厚重的期望,是讓我永遠不敢退縮懈怠的鞭策!
為了幫助我熟悉更多的作品,在那個資料貧乏的年代,她不僅向我提供各種曲譜資料,還無私地為我提供錄音帶。她家后來添置的復印機便是她為了方便為學生們提供資料用的。尤為可貴的是,如果她得到一份新資料,她會把最新的東西立即傳給學生。有一次,我正在北京,潘一鳴老師打電話給周老師說他新得到一個魯賓斯坦演奏的肖邦夜曲唱片,彈得非常棒,讓周先生去拿來聽。周老師取回后立刻復錄了一套給我帶走,我說 :“你還沒有嘞!”她說:“嗨!你拿走吧,我這兒要,那還不容易?”她得到一套錄有霍洛維茲、魯賓斯坦、弗里德曼、諾瓦伊斯和1980年剛剛在“肖邦國際鋼琴比賽”中名噪一時的波格雷里奇等大鋼琴家演奏的肖邦瑪祖卡曲集,她認為通過聽不同鋼琴家演奏的瑪祖卡對我們學習掌握肖邦瑪祖卡的風格會大有幫助。于是,她又馬上復制了一套給我寄來,還專門用英文打字機給我打印了一份目錄。

有一年,我為陳薩準備國際鋼琴比賽,曾考慮彈巴伯的奏鳴曲,我沒樂譜,一個電話過去,老師就把她的原版曲譜給寄來了,我真不好意思。她說:“你先用,用完再給我不就得了。”我知道,在這一點上,周老師對所有的學生都一樣,她的資料從來都是無保留提供的。
在我從事鋼琴專業教學的頭幾年,周老師像對待剛剛放飛的小鳥一樣,一方面讓它獨立,一方面又扶持幫助它。她在北京,我在四川,怎么做呢?她想出了辦法,讓我利用假期去北京跟她上課,學新作品,掌握更多文獻和教材充實教學曲目。20世紀80年代初,我的工資收入還很低,承擔赴京的費用有一定困難,周老師又慷慨解囊資助我路費,而且在北京的吃、住、練、教全由她包下來。她為什么要這樣厚待我呢?那是因為她深深了解我這塊“料”的長短之處。先天不足基礎差,中等資質底子薄,但勤學、努力、善思。北京三年的學習加深了她對我的了解。我相信她認為當初答應教我沒選錯人!周老師了解我會擔當起她讓我明白了的“歷史責任”,也知道要我能真正發揮作用還得幫我。她就這樣成了我繼續教育的加油站。在教學的路上一程一程地帶我送我。我已記不清那些年我去過多少次北京,但我卻清楚地記得那時候學到的許多曲目在以后都發揮了重要作用:陳薩第一次在“中國國際鋼琴比賽”拿大獎,決賽和獲獎音樂會演奏的門德爾松《g小調第一鋼琴協奏曲》就是在那會兒學的。
進入20世紀90年代,我的學生漸漸成長起來,有的好苗子開始嶄露頭角。他們立即受到周老師的關注,只要有機會周老師就會給他們上課。她的想法很明確,通過指導他們,進一步幫助我提高。
1994年8月,我帶吳馳去德國參加“艾特林根國際鋼琴比賽”,途經北京,周老師百忙中抽空為吳馳上課;我們去德國以后,陳薩又專程赴京,為她參加首屆“中國國際鋼琴比賽”備賽;陳薩要去參加“利茲國際鋼琴比賽”,離京那天早上,周老師一定要聽她首輪比賽的重頭曲目貝多芬《降A大調鋼琴奏鳴曲》(Op.110),提出了幾條特別要注意的關鍵問題。
1996年9月,陳薩在“利茲國際鋼琴比賽”中獲得第四名,是一個具有歷史性意義的成果。周老師高興極了,她給我寫信說:“小但,祝賀你取得了教學上的巨大成功,它證明了你多年來大膽的想法和試驗是成功的,我真為你感到高興,真是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她還在信中對陳薩在比賽中的表現給予了熱情的贊揚,同時,用很長的篇幅提出了對陳薩下一步安排的建設性意見。她希望陳薩能成大器,“成為中國一流的女鋼琴家(阿格里奇式的人物)”。此時,她表揚我們,期望我們,但從來不提她怎么幫了我們。從周老師身上,你可以看到她心里裝的不是一兩件具體的事,她始終考慮著整個中國的鋼琴事業!
為深圳注一片深情
1995年,我從四川調到當時被國人稱為“文化沙漠”的深圳,那是我秉承恩師精神,更愿做鋼琴基礎教育的選擇。那時,不少來自全國的鋼琴教師奔往深圳,在深圳“文化立市”的指引下,推動深圳鋼琴起步發展。1996年,我所在的深圳藝術學校在市文化局的支持下,提出要舉辦一次全國性的青少年鋼琴比賽。我立即電告周先生,我們很默契地想到了一塊兒——舉辦以倡導鋼琴學生合作的“雙鋼琴·四手聯彈比賽”。1997年首屆“全國青少年雙鋼琴·四手聯彈比賽”在周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成功舉辦了。


2004年,深圳在“文化立市”的目標指引下,提出打造“鋼琴之城”的舉措。如何充實“鋼琴之城”的內涵,搭建一個立足深圳、面向國際的平臺,引進更多當代鋼琴藝術家匯聚深圳。我請她出山,與她共同商量,反復醞釀形成了舉辦“中國深圳國際鋼琴協奏曲比賽”的構想。周先生擔任過很多國際鋼琴比賽的評委,有豐富而寶貴的經驗。這對于第一次舉辦國際大賽的深圳來說,真是不可多得的資源。首先,她同意了擔任評委主席的邀請,之后我和她一起制定章程,確定比賽方式和比賽曲目,在邀請評委等方方面面依靠她來定板。她把第一屆聯系評委等許多煩瑣的具體工作全部擔在了自己肩上,還主動承擔了兩屆比賽評委大師課的翻譯工作。她就是這樣的品格、這樣的人!為了支持深圳鋼琴事業的發展傾注了一片深情!2006年10月,首屆“中國深圳國際鋼琴協奏曲比賽”一舉成功。在國際音樂界贏得極其良好的聲譽。比賽至今已成功舉辦了四屆,更于2015年正式加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旗下的國際音樂比賽世界聯盟。
周先生在深圳擔任評委期間曾接受媒體采訪,她說:“深圳的鋼琴事業是足以讓每個深圳人感到驕傲和自豪的。”而深圳人知道,這份驕傲和自豪,離不開周先生一直以來的深切關懷和鼎力支持。周先生是深圳“鋼琴之城”夢想騰飛的親歷者和見證者,我們將永遠銘記她對深圳文化建設和鋼琴事業的巨大貢獻和深情厚誼。
尾 聲
“其德也潤,其藝也馨,其言也智,其氣也雅,其色也溫,其建也巨,其澤也遠,其見也深”,這正是對我們深深敬仰的周先生的寫照。
周老師的一生并非一帆風順。她經歷了青年獲獎的榮光,又經歷了中年喪夫的哀傷;她經歷了鋼琴事業成就的輝煌,也經歷了人世間不可理喻的種種責難;她經歷了鋼琴家斷指的折磨,卻又迎來了重返舞臺的光芒。然而,她不驚不變的風貌依舊是她那中國鋼琴事業發展的大視野、大胸襟與大情懷。無論人生怎樣沉浮,她卻巋然不改“廣仁”之大家風范與人格本色。
我最后一次見周先生已是“新冠疫情”肆虐在這片土地上的時候。周先生的兒子寶寶和女兒小漣他們和我有著幾十年的友情,應允我們去家里看望。當時,周先生意識已不從人愿,但她聽到寶寶說小但叔叔來了時突地睜開了雙眼,露出久違的微笑,親切而輕聲地叫了聲“小但啊……”我含著淚水撲向她的床邊,拉著她的手,看著她親切的微笑。一旁的寶寶和小漣都不由自主地露出了驚喜的神情和叫聲。他們告訴我,媽媽精神好的時候,會指著一幅我跟她合影的畫像說:“那是小但……”
彌留之際,我沒能守護在她身旁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遺憾!所幸,恩師病中一直得到兒女睿智的管理和悉心照料。親人們給了她臨終前溫暖的陪伴,她走得非常安詳,這是她的福氣!也讓我們得到了莫大寬慰。
懷念恩師,令我憶起慶祝恩師88歲華誕音樂會的一番情景。
師兄弟姐妹們要我代表大家講話,接下來是我演奏《思戀》。當我從講話的位置慢慢移步走向鋼琴時,開始念誦自己心里填寫的歌詞:
我思念恩師的深情,
還有那春風化雨無私的教誨。
我思念恩師的深情,
還有那諄諄教導哺育我成長的場景。
啊,周老,
如果有一曲思戀的琴聲,
向您飄來,
那就是我,
那就是我……
情景中,我合著歌詞唱起最后一句歌聲,沙啞的嗓音載著滿滿的眷念準確地落在琴鍵的F音上與飄逸的思緒匯合,奏響了我的《思戀》,獻給最崇敬的恩師周廣仁先生。
我的一生從周先生那里得到的太多太多,而回報她的卻甚少甚少。她已安然離去,我則不敢松懈:繼承先生的大視野、大胸襟、大情懷,將先生為師為人的大家風范傳承下去,一代一代永不停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