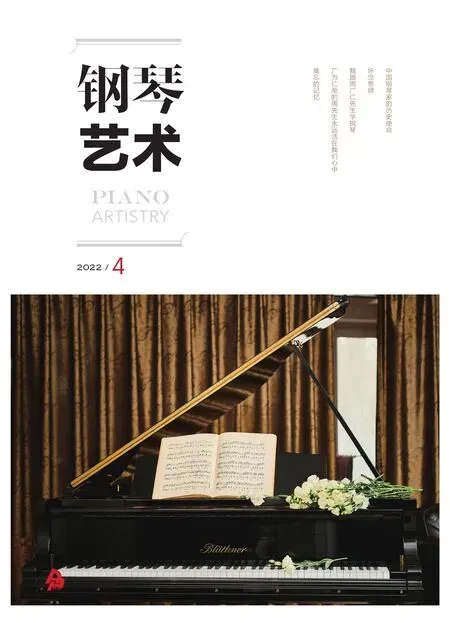周廣仁的生日
——追憶那年
文/劉元舉
得知周廣仁先生辭世的噩耗,悲傷著踱步陽臺。進入夜幕的窗外,那些亮著燈光的樓群,一時變得模糊起來……
從我第一次走進鋼琴界撰寫了中國第一部鋼琴書《中國鋼琴夢》至今,已有32年了。這期間,我在北京和深圳也多次跟周先生有過重逢,每一次都被她那溫煦寬厚和慈祥所打動。她很關心我為鋼琴界又寫了什么作品。
前幾年聽說她身體一直不佳,便為她擔心,但當她精神矍鑠地出現在“中國深圳國際鋼琴協奏曲比賽”上時,我們都為她的康復而欣慰著。
明天就是婦女節,可是她卻永遠地離開了這個世界。我找出了當年為她寫下的這篇文字,謹此緬懷。
我第二次走進中央音樂學院內的“紅眼樓”,找到二單元的樓門時,禁不住停下掃視一圈兒。這樓造型極其一般,像一個使用舊了的火柴匣,人們叫它“紅眼樓”,可見當初多少人渴望住進這里啊!我在想,當人們羨慕地瞅著這棟樓而眼紅時,除了嫉妒之外還會不會想點別的?
樓道是安靜的,我一層一層地往上邁步。不斷發現住在這里的人有個特點,鐵皮包裹的自家門上貼個標志,諸如“李宅”“林宅”之類。可我上到四樓瞅見了右側的那扇門時,門面上沒有留下任何標記。我擔心此番登門會不會像上一次那樣找不見我急切要采訪的人,所以按門鈴時手指有點發軟。上一次是一個多月前,我從上海采訪完趕到北京,不曾想我尋找的人卻剛剛離開北京去往上海了。有人對我說,你要寫中國的鋼琴,必須采訪周廣仁。不寫周廣仁,簡直是天大的遺憾。但愿這一次能采訪成功。
“周先生在家嗎?”我期待的門開了。我學著別人那樣稱呼周廣仁為周先生。
老太太是周先生家的保姆,她挺和善地說:“她還沒回來,你進來等著吧。”
進了客廳,發現沙發上已經坐著三個人。這是一家人。兒子在中央音樂學院附中鋼琴專業,是周廣仁教授的學生,他們夫妻是天津音樂學院的教師。男的教小提琴,女的教鋼琴。彼此介紹一下之后,我打開采訪本和他們聊起來。
男老師姓劉,很健談,先從他的兒子談起,兒子在幼兒園騎小三輪車時,他發現了兒子的肌肉素質好。兒子把三輪車蹬得飛快,超過別的小朋友—大截。他便想到讓兒子彈鋼琴。果然,兒子一上琴,手指的機能好,機敏、靈活,彈得特別快。他讓兒子每天下午4點上琴練到7點,吃飯時看電視,吃完飯做功課,每天這樣。本來是5歲開始學琴,因為地震沒堅持下來。8歲時正式學,學了兩年半,在天津舉行的“‘春芽獎’第一屆兒童鋼琴比賽”中奪取了第一名。同年在五十多名來自全國各地的考生競爭中,以第6名的成績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小。

談到普及性鋼琴教育時,劉老師說,學鋼琴的孩子不一定長大就干這一行。不干這一行,學了鋼琴也比一般不學琴的聰明。有個小孩小時學鋼琴,長大了沒考音樂學院,考取了天津南開大學研究生。他耳音特好,學琴練的,記憶力、敏感性都好,這為他學習英文奠定了基礎。他的英文很出眾,可以給美國留學生講課。學琴而不干專業,對以后干別的也深有影響。國外一些國家對小學生要求必須學一門樂器,樂器考不合格,文化課好也不發給畢業證。我們國家那么多孩子學鋼琴,完全是自發性的,特別感人。
劉老師談得很有道理,我正想就這個話題深談下去,來人打斷了。
是一對德國夫婦,領著一個挺漂亮的小女孩,大約五六歲吧,黃黃的羊毛卷頭發,藍晶晶的大眼睛,長睫毛向上翻翹著,很像一個布娃娃。他們帶來了一盒禮品,包裝挺藝術,還有一束鮮花。他們用洋味兒的漢語和我們打了招呼,然后把禮物相鮮花都放在桌子上,挺遺憾地告辭了。那小女孩大概感冒了,從進屋就一直咳嗽,他們走后,聽說這是德國駐中國大使館的,那個小女孩在周先生創辦的星海青少年鋼琴學校(以下簡稱“星海”)學彈鋼琴。
我瞅著德國人給周先生送的禮物和鮮花,不免有點蹊蹺。一問劉老師,才恍然大悟,今天是12月17日,是周廣仁教授61周歲生日。能在這個日子采訪周廣仁,的確是幸運的事。可惜自己此前不知道,否則,一定也為周先生準備一件祝賀禮物,哪怕是一張賀卡。
不斷地有人來電話,不斷地有人按門鈴。客廳的人越來越多,沙發都坐不下了。我對劉老師那—家三口的采訪只好告一段落。
保姆恐怕有70歲了,客人們都恭敬地稱她“姨媽”。她說周廣仁本來說3點40分回來的,可已經4點多了,還不回來。屋子里光線暗下來。我留神著墻壁。墻上有一幅油畫挺棒,是一個姑娘在彈鋼琴。這是青年時代的周廣仁,畫面質樸無華,人也質樸而真誠,全然找不到一絲的矯情。這大概就是周廣仁的特點吧?我暗自揣摩時,門鈴又被按響。我看到的是一個頭戴帽盔的人的背影,虎虎有生氣,動作極利索地在走廊一閃,就進了廚房,很像個年輕小伙子。我忽見屋里的客人騷動著站起身,議論說周先生回來了。
我是耳朵聽錯了還是眼睛看錯了呢?我緊盯著那個戴頭盔的人,待那頂摩托頭盔摘下來一甩頭發時,我怔住了,她的身材矯健,面孔紅潤溢著光彩,哪像一個61歲的老太太啊!
屋里人一派虔誠地站起身瞅著她。她朗聲笑著逐一和客人們打招呼。都是她的熟人,唯獨我是生人。我只顧盯著她瞅,忘記了準備好要說的話,待到她挨近我,也微微一怔時,我慌得亂了分寸。她似乎為了減少我的尷尬,隨即面帶笑容地向我伸出手。我自報家門,說明來意,她立刻直率地說:“今天過生日咱們一起玩玩兒,不談工作了。”
我也覺得這種場合不該占用她的時間,否則會掃了大家的興。
里屋里一直有人彈琴,此時大概聽說她回來了,琴聲停止,從屋里沖出來兩個男孩子,八九歲的樣子,穿著一樣款式一樣質地的藍衣服,精精神神地往周先生面前一站,遞上祝賀的卡片。
周老師高興地接過去時對客人介紹,這是“星海”的學生,他倆在練四手聯奏,準備登臺演出。
又一個小女孩送來了祝賀的卡片。周先生叫她丁丁。丁丁說,卡片是她自己動手做的,這使周先生更加高興。她看著卡片上用英文寫的祝詞,馬上挑出寫錯了的一個字母,那女孩羞得臉紅了低下頭。周教授笑了,屋里人也笑了,氣氛顯得更加活躍。
那邊又響起電話,周教授奔過去接。她的嗓音很高,情緒也高,不斷地發出朗朗笑聲。一個電話剛放下,又來一個,都是祝賀她61大壽的。
那兩個不肯安分的男孩子見人太多,打算溜走,被撂下電話的周教授喊住了,讓他們吃了生日蛋糕再走。結果,一盒生日蛋糕搬到茶幾上切開了。沒有點蠟燭,這稍稍有點兒遺憾,但我認為不會沒有蠟燭,或許周教授太忙了,嫌點蠟燭太慢,耽誤時間。從她進屋,就沒有坐下喘口勻乎氣兒。她的四川的學生趕來了,廣州的學生趕來了,學生的年齡相差很大,顯然不是一代人。但他們對周教授都有著同樣的真情。那個年輕的姑娘送給周教授的是件羊毛衫,當場就讓她試。周教授毫不含糊,以她特有的爽朗勁兒把羊毛衫穿上了。那是件桃紅色的羊毛衫,很時髦,也很藝術,穿在周教授的身上,使她本來就顯年輕的身段更年輕了。她笑著解嘲道:“瞧,一個老太婆穿這么漂亮的衣服還挺摩登!”人們都笑得歡心。
又是電話。她讓我們自己吃蛋糕。保姆,也就是“姨媽”,給我們每人一個盤子、一把鐵叉。鐵叉準備得太充分了,每人一把之后還剩下了一束。看得出,這里常常是聚會的場所。周教授的學生代替主人給我們在盤子里放蛋糕,我們吃著蛋糕,周教授在打電話,我們把蛋糕吃完了,她的電話還沒打完。61大壽的祝賀儀式就這樣開始了。很簡單,很隨便,也很舒服。在這樣的氛圍中,再靦腆的生人也不會有半點難為情的。周廣仁是名震中外的鋼琴家和教育家,她曾先后六次擔任在美國、智利、法國、挪威等國家舉行的世界性國際鋼琴比賽的評委。能在她的家中參加她的生日宴會的確是一件榮幸的事情。據劉老師說,去年周教授過60大壽時,那才隆重呢!她的學生們為了祝賀她的生日專門在學校的音樂廳開了一場音樂會。音樂廳座無虛席,參加演奏的同學們激情高亢地和周教授同時登臺,周教授給協奏。師生的情感在歡快熱烈的旋律中高揚彌散,強烈地感染了聽眾,人們熱烈地鼓掌。周教授很激動,就像當年登臺成功的演奏受到熱烈歡迎一樣。可以想象出,那是一個多么別開生面、多么有意義、多么鼓舞人感動人的生日啊!一年后的今天,雖然來的人不那么多,雖然沒有舉行那種規模的音樂會,但家長們、學生們、朋友們不也還是從全國各地趕來為她祝壽嗎?再看看她擺在書架上的那密密層層的賀卡,就可以感到有多少人在為她祝福,為她祝壽。她擁有的很多很多,她太受擁戴了,她一點兒都不寂寞。
出于職業的習慣,我在留心著她打電話。她操著一口流利的德語,我以為是和大使館來過的那對夫婦通話,可她放下電話時說,是德國朋友從柏林打來的,祝賀她的生日。
她撂下電話坐到桌前,催我們:“快吃呀!”我們都笑了。因為我們已經吃完了,只剩下放在她的盤子里的一塊蛋糕是留給她的。她端起剛咬了一口,電話又響了。她用英語對話,電話是從美國打來的。從跨進家門的那一刻起,她始終充滿熱情地迎來送往,電話沒完沒了,幾乎每隔5分鐘便來一個。她的情緒是那樣的飽滿,精力是那樣的充沛,面色紅潤,眼睛深邃明亮,頭發也是烏亮的且有光澤,就是說,你怎么看她,都覺得她不像是一位61歲的老人。
周廣仁對鋼琴事業的重大貢獻,不僅在鋼琴演奏和教學上,她還做了大量的組織和傳播工作。那么著名的教授,走進普通人的行列,進行最普通、最基礎、最煩瑣的教學工作。她在學校時,教那些專業學生很有經驗,她到社會上進行普及教育,也有一套經驗。這種經驗的獲取,與她辛勤的勞作是分不開的。她所創立的“星海”必將載入中國的鋼琴史冊。她不倦地為祖國鋼琴事業的發展而奔走呼號,短短幾年內,她幾乎走遍了全國的主要城市,天津、沈陽、昆明、成都、上海、福州、廣州、廈門……她到處講學,到處演奏,她是那么急不可待地去融化清冷、撞碎沉默,她要讓鋼琴去震蕩每一座城市、每一顆心靈。她像個虔誠的傳教士,像個苦行僧,每到一地,都盡心盡力。她所走過的地方,都留下了長久的余震,她是最好的鋼琴傳播者。她還應邀到美國講學。那是康薩斯城密蘇里大學埃德加·斯諾基金會的邀請,并且授予她客座教授的榮譽證書。她在美國期間,介紹中國音樂中國鋼琴,走了30多個城市,每到一地便引起轟動。她還在美國29所大學進行了演奏,除了演奏西方聽眾熟悉的莫扎特、貝多芬、舒曼、肖邦的作品外,更多的是演奏中國作曲家的鋼琴作品。如賀綠汀的《牧童短笛》、黎英海的《夕陽簫鼓》、王建中的《繡金匾》等。她是多么希望中國的音樂、中國的鋼琴走向世界啊!
有位美國人曾在一次家宴上率直地問她:“我真想了解了解,你們為什么那么頑固地要回去?你們不覺得美國好嗎?”
她沉思著說:“我很喜歡你們的國家,但我的祖國是中國。如果我的母親有病,難道我們能不護理嗎?何況那兒有我的工作,我的學生!”
愛國,對于周廣仁來說絕不是一種口號,更不是一種時髦,那是她幾十年不曾動搖的信念。年復一年,她是怎樣地含辛茹苦,怎樣的奉獻啊!她的手被鋼琴砸壞躺在病床上時,沒有沉浸在自己的悲傷中。她考慮的是如何為祖國的鋼琴事業發揮自己更大的作用。她從她們這一代鋼琴家的成長過程,想到了下一代。她認為希望還是在下一代,在未來。她認為中國的鋼琴教育,無論鋪開還是尖端,比以前抓得好這是事實,但普及教育太落后。日本等國在普及方面所做的工作要比我們強得多。中小學的音樂教育水平太低,不是所有的學校都有音樂教師,也不是所有的音樂教師都能教鋼琴。要想多出人才、早出人才,就必須搞好普及教育,要從兒童抓起,最好的辦法是創辦一所學校。
她把她的想法和有關人士說了,得到了支持和擁護。星海鋼琴廠的一位副廠長極有遠見,他認為他們廠子不光要搞生產,還應該對社會的鋼琴教育做貢獻,于是,他答應為周廣仁提供十臺鋼琴搞普及教育。鋼琴有了,這使周廣仁非常興奮,但校舍、場地、師資這一系列的困難都需要著手解決。她畢竟是知名人士,只要她一牽頭,什么事情都好辦了。她與北京二中接上了鉤。二中當時搞了個小型鋼琴班,準備搞一次鋼琴比賽,請周廣仁去指導。周廣仁風塵仆仆趕去,結識了二中音樂教師曾福梅。曾福梅雖然是個普通的中學教師,但她視野開闊,對培養鋼琴人才與周廣仁有著同樣的熱心和干勁。她們一見如故,志同道合,結成朋友。曾老師敬佩周廣仁,這么有名的教授一點架子不擺,和普通教師一樣對事業充滿熱情,充滿真誠。周廣仁也很佩服曾老師,曾老師比自己想得更早,干得更早,她已經先行一步,盡管還很匆忙,盡管水平還很有限,但精神十分可嘉。在曾福梅老師的介紹下,周廣仁接觸了一批中學教師,她認為這是北京最棒的教師。這些老師和曾老師一樣,在那么差的環境中,在那么不被重視的條件下,不圖名,不圖利,默默地腳踏實地地培養人才,這就是北京的希望。這使她相當感動。但這些教師的水平有限,又使她很焦慮。為此,她拿出一定的時間和精力,無條件地給這些教師們搞了些教學法,他們特別刻苦,特別專心,因而提高很快。
籌建一所鋼琴學校需要做大量有形和無形的工作。特別是首創階段,既無校舍,也無經費。作為主要創始人的周廣仁在這段時間操了多少心,上了多少火,跑了多少腿,磨了多少嘴,就可想而知了。得感謝當時二中的那位開明的校長張覺民,這是個非常有經驗的教育工作者。他一聽說要成立星海青少年鋼琴學校,馬上表示贊同,并且積極想辦法幫助解決校舍問題。利用二中的一個倉庫,分隔成八間屋子,從中央音樂學院借了十把琴凳,周廣仁一手挑選了十名精干的教師,登報發出招生廣告。按當時的條件,只能招收四十名,因為十臺琴,十名教師,每個星期天授課。每個老師只能上午教兩名,下午教兩名。當時條件比較艱苦,沒有教材,老師們自己動手編印,積極性空前高漲,簡直可以說熱火朝天。在周廣仁的帶領下,一到星期天,教師們齊刷刷涌來,中午飯自己帶,學校一分錢經費也沒有。這就是星海青少年鋼琴學校的初創情況,原先打算招收青少年,后來確定全部招收少年兒童。這所學校完全是業余的,由三方面聯合操辦:中央音樂學院、北京二中、星海鋼琴廠。周廣仁擔任校長。
正式建校是1983年9月。整整辦了六年,于1990年1月停辦。這六年間,周廣仁付出了許多辛苦,許多代價。大事小事,她都得過問,都得負責。初創時期還便于管理,可越辦越不容易。但是,“星海”畢竟創出了牌子,而且在全國產生了廣泛的巨大的影響。
綜觀星海青少年鋼琴學校,有如下幾個特點:
其一,不拘一格招收和培養人才。
“星海”本來是面向北京招生,但外地的學生也紛紛慕名前來。按照嚴格的考試,不分內外,只要夠條件,就吸收。這就打破了地域,構成了更大規模的競爭局面。另外在招生數量上也有別于專業學校。原定招生四十名,實際招收了七十名。多招三十名顯然增添了負擔和麻煩,也不同程度地為教師增加了壓力,但畢竟沒有把三十名人才拒之門外。這就比專業學校有著較大的伸縮性和靈活性,可以不拘一格地招收和培養人才。
其二,讓學生和家長都感到溫暖。
青島有名學生,考入“星海”時才9歲。家長豁出自己的職業,陪同孩子來京。沒有錢,學校幫著想辦法,沒有房子,學校幫著租借。還有從福建來的、湖南來的,遇到了生活上的麻煩,周廣仁親自幫助解決。有的學生和家長沒地方住,她就讓住在自己的家里。幾年來,她的家簡直成了客棧,至今還有學生住在她家。外地來的學生困難要比當地的多得多,有的堅持一年,實在堅持不下了,學校就給送回去。無論送回去還是迎進來,都是滿腔熱情,讓孩子和家長充分感到學校的溫暖。
其三,有專業學校的某種特點。
比較正規,比如考核,比如經常搞學習演奏會,比如出個車爾尼849中某一條比賽,在通過的學生中發獎學金。比如組織教師和學生演出搞募捐、支援非洲等社會活動。
其四,教師責任心和事業心比較強。
因為業余教學,教師的收費標準要高于正常工資,所以比較容易調動積極性。周廣仁的榜樣力量使教師們紛紛效仿。后來,教師發展到三十人,在校生二百多人,有點失控,教師的素質也開始下降,這是后話,也是“星海”停辦的一個原因。但幾年來,教師們做出了辛勤的努力,完成了各自的教學任務。特別是校長周廣仁,她對學生充滿了愛心,充滿了責任感。她常常為外地一些有才氣的孩子沒能遇上好老師而惋惜。她給予這些外地孩子更多的同情和愛護。她也盡自己的最大能量接受那些外地來的孩子。這些孩子大都比本地孩子刻苦,但這些孩子一般存在的毛病也較多。教兒童彈琴最難的就是入門,一開始教好了,以后就順了;一開始要亂了,就太誤人了。壯族女孩偉偉開頭兒沒開好,入門沒入好,就是亂。為了改正她的毛病,周廣仁費了好大的工夫。經過兩年的精心培養,偉偉考進了中央音樂學院附小。還有那個青島來的學生,也是經過“星海”的四年培養,考入中央音樂學院附小的。六年來,“星海”共培養學生三百多人,其中九十一人通過了初級班結業考試。在北京市舉行的兒童鋼琴比賽中有二十九人獲獎。其中獲一等獎的兩人、優秀獎兩人、二等獎七人、三等獎六人、鼓勵獎十一人。六年中,共有十人先后考入中央音樂學院和上海音樂學院附中、附小。“星海”的建立對于推動或者掀起中國的那場鋼琴熱潮起到了先鋒作用。可以說,他們為我國如何開展業余鋼琴教育開拓了路子,摸索了經驗,為我國的鋼琴事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是,這樣的學校畢竟是第一次創辦,問題是難免的。比如校舍,冬天無法解決取暖問題,學生和老師上課時都難以伸出手來,凍得直哆嗦,直淌鼻涕,比如教師和學生的管理,人員擴大,造成管理上的某種程度的混亂,有的教師不服從領導,有時愿來上課就來,不愿來就可以不告而辭。教學質量保證不了,家長、社會漸漸有了意見。“星海”的地位高,名氣大,與現實存在的問題反差越來越大。周廣仁是個無比認真的人,她的眼中容不得沙子,她說,要想糊弄,想搞“維持會”,她堅決不干。為了維護鋼琴的尊嚴,也是為了維護“星海”的聲譽,她草擬了一份“告全體師生書”,決定停辦星海青少年鋼琴學校,并預訂在1990年1月14日下午2點在中央音樂學院大禮堂舉行“建校六周年學生音樂會”,檢閱“星海”的成績并留作永久的紀念。
“星海”的使命完成了,但周廣仁的使命沒有完成。她總結了“星海”的經驗和教訓,又著手創辦了樂友鋼琴學校。鋼琴由樂友鋼琴廠提供。這所學校設在北京的海淀區,海淀實驗小學給提供一個很好的教學樓,可以上集體課。幾年來,周廣仁一直在做集體課的試驗,在“星海”時,就曾用兩臺鋼琴一起給四個孩子上課,孩子們很開心,互相比著,效果蠻好。她認為對兒童一個一個單獨授課,是一種極大的浪費。她總結“星海”的一條重要教訓是培養師資問題。“星海”的滑坡在于教師質量的下跌,以至于到后來,她無法把握教師的教學情況。她打算在“樂友”培養一批過硬的鋼琴教師。她要把她的學生拉去,把學生們培養成教幼兒鋼琴的老師,要告訴學生們怎樣教幼兒,怎樣規規矩矩、認認真真地去干。她準備創辦“樂友”后,本人不再教幼兒,專門培訓老師。上課時,她要坐在那兒聽,及時發現老師的問題,及時幫助解決,幫助提高。她認為抓老師才是抓住了根本。
周廣仁在向我談到未來“樂友”的設想和措施時,十分興奮。她甚至自豪地說“樂友”條件非常好,每次可以用小車接送上課的教師,這樣便可保證上課時間,保證教師的積極性。
周先生還談了她以后更大的設想。她說先在北京地區搞鋼琴基礎建設,而后到全國各地走走,去幫助各地搞建設。到了退休之后,她計劃走遍全國。她是真正把鋼琴當作畢生追求的事業來搞的,不是為了一個人,也不是為了一群人,而是為了一個國家。用夜以繼日、嘔心瀝血、含辛茹苦等詞匯形容她一點兒也不過分。去年,她到美國照顧女兒坐月子,是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休假,時間為一個月。她幫女兒料理家務,帶小外孫女去游泳池游泳,每天也挺忙活。可她仍然覺得閑得難受,閑得發慌,夜里竟然睡不著覺,怎么辦?她就閉著眼睛開始備課,有時備到天亮還是無法入眠。女兒心疼媽媽,希望媽媽多住些天,多享享福,可她哪知道媽媽是個不會享福的人啊!對她來說,最大的享福就是投入到自己喜歡的工作中,而且越忙她就越感到充實。等她離開美國,回到她的學生身邊,回到她所熟悉和熱愛的工作中,她再也不失眠了。
她工作起來常常不顧一切。1986年,由于過度疲勞,右耳突然聾了,經過治療,仍然不見效。耳朵對于她來說是多么重要!最麻煩的是她出席國際鋼琴比賽當評委時,必須保持良好的聽力。一個耳朵倒也可以幫她完成視聽,但她就怕圍在一個圓桌吃飯時,坐在她右邊的人跟她說話,這種時候,她的右耳是聽不見的,她必須掉過身來正面對著對方。她怕人家知道她耳聾,作為國際級的評委,耳朵聾了那多晦氣!貝多芬兩耳聾了,聽不見雷聲,卻能分辨清音樂,因為他有一顆屬于音樂的智慧的心靈,他可以用心靈去聽。周廣仁也有一顆音樂的心靈,她每次作評委工作,都完成得很出色。為祖國爭了光。
時間的確不早了,她生日的夜晚,幾乎被我的采訪占據了,她明明說今天生日好好玩玩,不談工作,可她還是談了,而且一談就談了許多。明天,她還要在全國鋼琴演奏比賽中擔任評委工作,因為這是“文革”后全國舉辦的第一次專業鋼琴演奏比賽,肯定有許多事情等著她。
似乎還有許多問題想跟她探討一下,關于中國鋼琴現狀、關于世界鋼琴現狀,乃至關于她本人情況。但我實在不忍心再打擾她了。我發覺就連燈光都不舍得去照亮她的臉,而是躲躲閃閃地在她的面頰投下明暗相襯的光斑,那暗的部位顯得抑郁、顯得蒼老了。她縮在沙發上,終于顯出了疲倦。在她的旁邊,是那個壯族小女孩。她已經蜷縮在沙發上睡著了,胖胖的臉蛋透出甜甜的紅潤,長長的額發披垂著,很像一只溫順可愛的小獅子。今天是周先生的生日,她過得是一個緊張而忙碌的生日。
你不妨想象一下,一個61歲的老太太戴著白色的頭盔,駕駛一輛藍白相間的日本雅馬哈摩托車,在潮水般的車輛中穿梭,有時頂風冒雨,有時頂著炎炎烈日,據說北京的交通法有規定,50歲以上的人不許騎摩托,即使有駕駛證的也只能延長五年,可她已經遠遠超出了這個限制。她是一個特殊的人物,是一個偉大的女性!交警已經熟悉了她,只要遠遠地看到她騎的那輛閃著藍白光色的雅瑪哈,就充滿敬意地向她行著注目禮。而她呢?每次到了交叉路口,都極守規矩,瞅準綠燈,才緩緩駛過。她的腰板總是挺得筆直,目光總是盯著前方,前方的路對她來說,總是寬闊的,總是灑滿陽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