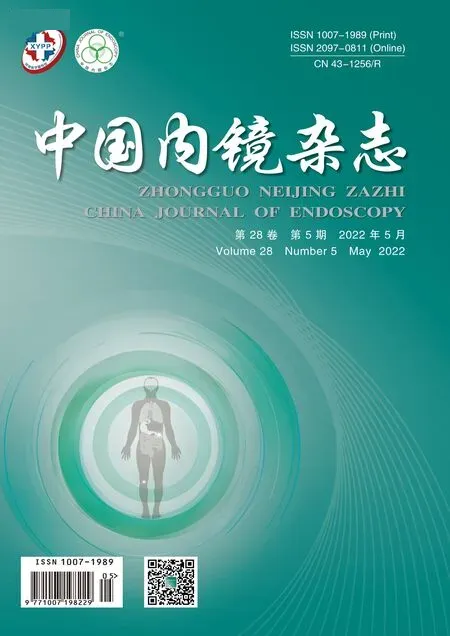內鏡輔助新西蘭兔咽喉反流病動物模型建立方法的改進與比較*
代麗麗,湯維,尤悅,吳宏林,彭光華,陳朝輝,周雪華,耿爽,林笑含
(杭州師范大學附屬醫院 耳鼻咽喉科,浙江 杭州 310015)
咽喉反流病(laryngopharyngeal reflux disease,LPRD)是耳鼻咽喉科的常見病,因咽喉部受胃內容物反流侵襲,臨床常表現為:咽干、咽痛、咽喉部異物感、咽喉部痰多、頻繁清嗓、聲音嘶啞、發聲疲勞、喉痙攣、慢性咳嗽、窒息感及吞咽困難等[1-2]。近10%的耳鼻喉科門診患者存在LPRD[3]。其中,近55%的聲嘶患者存在LPRD[4]。體外實驗是研究LPRD發生機制和探討療效的關鍵。因此,建立LPRD動物模型具有重要意義。目前,關于LPRD的動物模型以新西蘭兔為主,多以食管內支架為基礎建立模型,但各有優缺點。本研究在國內外相關研究的基礎上,經過改進,建立方便易行的LPRD動物模型,旨在為臨床提供參考。
1 材料與方法
1.1 實驗動物和分組
選取2021年1月-2021年5月采用球囊擴張食管下括約肌(lower esophageal sphincter,LES)及食管上括約肌(upper esophageal sphincter,UES)來制造的,生理狀態相似的健康普通級新西蘭兔LPRD模型32 只,以隨機數表法對其進行編號,并將實驗兔分為實驗A 組(n=11)、實驗B 組(n=11)和對照組(n=10)。實驗兔均為雄性,年齡5個月,體重2.5~3.0 kg。實驗A組采用球囊擴張UES和LES;實驗B組以食管內支架為基礎擴張UES,聯合球囊擴張LES[5-6];對照組在UES及LES處置入食管球囊,但不行食管球囊擴張。所有實驗兔在標準實驗室環境下適應性飼養3 d,再行建模操作。比較3 組實驗兔喉咽部喉鏡下反流體征評分量表(reflux finding score,RFS)的評分,監測3組實驗兔的喉咽部pH,并記錄組織病理學變化[5-6]。本研究經杭州師范大學動物倫理委員會批準,嚴格遵循實驗動物使用指南及福利原則。
1.2 材料
球囊擴張導管(南京微創,型號:BDC-10/55-7/18,直徑10.0 mm,長度55.0 mm),壓力泵(南京微創,長度1 800.0 mm),金屬支架(南京微創,型號:MTNDA-S-8/50-2.7/1800,直徑8.0 mm,長度5.0 cm),推送器[南京微創,內鏡逆行胰膽管造影術(endoscopic retrograde cholangiopancreatography,ERCP)置入器,直徑2.7 mm,長度1 800.0 mm,導絲:直徑0.89 mm(0.035 in)],咽喉反流監測使用Digitrapper?反流測試系統(Medtronic,美國),內鏡系統及鼻竇內鏡(歐亞,直徑4.0 mm,長度175.0 mm)。實驗兔購于余姚市泗門鎮建飛實驗兔養殖場[動物許可證號:SCXK(浙)2021-0004]。
1.3 建立新西蘭兔模型手術方法及術后處理
術前分別禁飲禁食8 h。實驗兔麻醉給予30 mg/kg 3%濃度的戊巴比妥鈉耳緣靜脈注射,麻醉后實驗兔仰臥于手術臺上,固定頭部及四肢,以直角開口器撐開兔嘴。
1.3.1 食管球囊擴張LES經鼻胃管置入球囊至胃內,鼻胃管及球囊插入食管內的長度(以門齒為基準)約35 cm。其中,新西蘭兔門齒距賁門的距離為22 cm,未擴張的球囊長度約6 cm,球囊前導絲約4 cm,鼻胃管內可見胃液反流。固定球囊,退出胃管約10 cm,然后將一定量的蒸餾水(約6 mL)注入球囊內以擴張球囊,向外拉球囊和鼻胃管,直至球囊的近端卡在胃賁門處無法向外拉。將球囊內蒸餾水抽干,固定鼻胃管,向外拉出球囊使其中點位于胃食管交界處。緩慢注入蒸餾水,使囊內壓力加至10 psi(1 psi=6.895 kPa),維持5 min,充分擴張LES,中間休息3 min再重復擴張球囊一次,共擴張2次。見圖1。

圖1 球囊擴張LESFig.1 Balloon dilation of LES
1.3.2 食管球囊擴張UES經鼻胃管將球囊置入食管內,鼻胃管及球囊插入食管內的長度(以門齒為基準)約20 cm(門齒到環咽肌的長度約10 cm),固定球囊,向外拉鼻胃管約10 cm,在內鏡直視下確定球囊位于環狀軟骨以下位置,向球囊內緩慢注入蒸餾水,使球囊內壓力增加至10 psi,維持5 min,使UES 充分擴張,中間間隔3 min,共重復2 次。見圖2。

圖2 球囊擴張UESFig.2 Balloon dilation of UES
1.3.3 食管上段置入金屬支架經鼻胃管將置入系統的導絲置入距離門齒約20 cm處的食管內。在內鏡直視下,通過置入系統,將金屬支架釋放在食管內,彈開后,呈空心圓柱狀的支架可提供支撐力支撐UES。在兩側臼齒中間的軟腭處,固定支架頂端的絲線,防止支架位置變動以及絲線被實驗兔咬斷。24 h后剪斷絲線并撤除。見圖3。

圖3 支架擴張UESFig.3 Stent dilation of UES
1.4 術后處理
手術中密切監測實驗兔呼吸及心跳狀況,如遇呼吸困難等情況,立即中止實驗。為預防術后感染,術后30 min內,對實驗兔肌肉注射40萬u青霉素鈉注射液。術后實驗兔給予含5%糖鹽水飼養,禁食24 h后,給予標準飼料飼養。
1.5 觀察指標
1.5.1 一般狀態術后定期觀察3組實驗兔的一般狀態,包括:體重、食欲和死亡情況等,比較3組實驗兔之間的差異。
1.5.2 新西蘭兔上消化道2 h pH 監測采用pH監測系統監測所有實驗兔術后第2 和4 周的24 h 上消化道pH值。①電極放置:采用鹽酸羥甲唑啉(5 mL∶1.25 mg)收縮實驗兔鼻黏膜血管,并用2%利多卡因膠漿行鼻黏膜表面麻醉,在pH 為4.0 和7.0 的緩沖液中校準電極,將電極從鼻腔經鼻咽部插入口咽部;在內鏡直視下,將電極插入至食道入口下方,此時,探頭與前鼻孔距離為11.0~12.0 cm;為防止電極移動,使用絲線縫合,電極固定于前鼻孔和鼻背部,在實驗兔背部安裝無線數據發射器,將電極線越過實驗兔頭頂與發射器連接,給實驗兔穿上特制的衣服,防止實驗設備脫落;記錄2 h 內的實驗兔喉咽部pH 值(圖4);②pH監測結果的獲取[7]:實驗結束后,使用儀器配套的分析軟件(AccuView pH-Z)對所得數據進行分析,當pH值達到直立位<5.5和臥位<5.0時,視為1次反流事件[5];記錄2 h內咽喉反流的次數、反流時間占比和最長反流時間。建模成功的標準為:直立位2 h內,反流事件>1次[8](圖5)。

圖4 pH監測示意圖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pH monitoring

圖5 pH監測系統Fig.5 pH monitoring system
1.5.3 喉鏡檢查和RFS分別于建模前3天和建模后4周,對實驗兔采用喉鏡檢查并拍照,參照RFS對圖像進行評分。評分系統包括:聲門下、聲帶及喉彌漫性水腫、紅斑或充血、肉芽腫、后聯合增生、喉內黏稠黏液附著和喉室消失等[9]。
1.5.4 病理檢查手術4 周后采用戊巴比妥鈉(100 mg/kg)過量麻醉并處死所有實驗兔,取UES 和聲帶等組織,采用10%甲醛溶液固定,石蠟切片后行HE染色,在光鏡下觀察組織病理學改變。
1.6 統計學方法
選用SPSS 22.0 軟件分析數據,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均數±標準差(±s)表示,組間比較采用方差分析,組內前后比較采用t檢驗;不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中位數(四分位數)[M(P25,P75)]表示,組間比較及組內前后比較均采用Kruskal-WallisH秩和檢驗;計數資料以率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LPRD建模結果
實驗A 組11 只實驗兔建模成功9 只,建模失敗1只,建模死亡1只,死于喉梗阻。實驗B組11只實驗兔建模成功8 只,建模失敗2 只,建模死亡1 只,死于肺部感染。對照組10只實驗兔建模成功0只,建模失敗10只,建模無死亡。實驗A組和實驗B組的建模成功率及死亡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2.2 喉鏡RFS評分結果
實驗A 組建模前3 天RFS 為(2.90±1.37)分,建模后4周為(8.60±2.32)分;實驗B組建模前3天RFS為(3.10±1.20)分,建模后4周為(8.40±1.84)分;對照組建模前3天RFS評分為(2.40±1.35)分,建模后4周為(2.60±1.17)分。實驗A組與實驗B組組內建模前后RFS 比較,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對照組建模前后無明顯差異。見圖6。

圖6 3組新西蘭兔術前及術后喉鏡圖像Fig.6 Preoperative and postoperative laryngoscopy images of three groups of New Zealand rabbits
2.3 咽喉部pH值監測結果
2.3.1 實驗A 組和實驗B 組建模前后建模成功的實驗A 組,建模前3 天、建模后2 和4 周的酸反流事件數(次)分別為0.00(0.00,0.00)、4.00(4.00,6.00)和4.00(2.75,5.00)次;建模成功的實驗A組,建模前3 天、建模后2 和4 周的酸反流時間百分率(%)分別為0.00(0.00,0.00)%、17.50(15.40,19.00)%和16.45(13.30,19.90)%;建模成功的實驗A 組,建模前3 天、建模后2 和4 周的最長反流時間(s) 分別為0.00 (0.00,0.00)、27.00 (18.00,33.00)和20.00(17.75,24.75)s。建模成功的實驗B 組,建模前3 天、建模后2 和4 周的酸反流事件數(次)分別為0.00(0.00,0.00)、4.00(2.75,5.00)和4.00(2.00,5.00)次;建模成功的實驗B 組,建模前3天、建模后2和4周的酸反流時間百分率(%)分別為 0.00 (0.00, 0.00)% 、 17.50 (12.93,19.15)%和26.50(20.40,28.25)%;建模成功的實驗B 組,建模前3 天、建模后2 和4 周的最長反流時間(s) 分別為0.00 (0.00,0.00)、25.50 (20.75,32.75)和23.00(15.50,27.00)s。實驗A 組和實驗B 組酸反流事件數(次)、酸反流時間百分率(%)及最長反流時間在建模前3 天、建模后2 和4 周組內比較,差異均有統計學意義(P<0.05)。
2.3.2 對照組建模前后對照組建模前3天、建模后2和4周的酸反流事件數(次)分別為0.00(0.00,0.00)、1.00(1.00,1.75)和1.00(0.25,1.75)次;建模前3 天、建模后2 和4 周的酸反流時間百分率(%) 分別為0.00 (0.00,0.00)%、0.20 (0.10,2.75)%和0.80(0.28,1.50)%;建模前3 天、建模后2 和4 周的最長反流時間(s)分別為0.00(0.00,0.00)、2.50 (2.00,4.75) 和4.50 (3.00,7.00) s。對照組酸反流事件數(次)、酸反流時間百分率(%)及最長反流時間在建模前3 天、建模后2 和4 周組內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
2.3.3 3 組實驗兔比較建模后2 和4 周,實驗A組和實驗B組酸反流事件數、最長反流時間和酸反流時間百分率較對照組均有提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實驗A 組和實驗B 組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P>0.05)。見附表。

附表 3組實驗兔建模后2和4周觀察指標比較 M(P25,P75)Attached table Comparison of observation indexes 2 and 4 week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model among the three groups of experimental rabbits M(P25,P75)
2.4 病理檢查結果
對照組喉咽部及食管上端黏膜未見明顯炎癥。實驗組食管及喉咽部黏膜均可見慢性炎癥,喉咽部黏膜可見大量淋巴細胞和漿細胞浸潤,伴腺體增生和間質水腫;食管黏膜表現為淋巴細胞浸潤,局部鱗狀上皮可見角化不全。見圖7。

圖7 3組病理特點Fig.7 Pathological features in three groups
3 討論
對于LPRD發生機制的研究及治療方法療效的探討,體外實驗必不可少。因此,建立LPRD 動物模型,尤其是如何簡便、安全地建立動物模型,是體外實驗的基礎,具有重要意義[10]。在實驗動物的選擇上,豬[11]和狗[12]因其咽喉黏膜上皮組織與人類最為相似,被認為是最佳的建模動物[13]。但存在建模周期長、購買價格貴、養育成本高和基因庫相對不完善等問題。這使得新西蘭兔[14-15]及大鼠[16-17]成為了應用最為廣泛的實驗動物。但是,鼠的咽喉黏膜與人非角化復層鱗狀上皮不同,其角化上皮能抵抗一定的反流物,而兔的咽喉黏膜與人體組織相近,且對反流抗性弱,更易建模,具有良好的經濟性。因此,兔成為建立LPRD動物模型的首選。目前,常見的建模方法基本都參照胃食管反流病動物模型的建模方式[18-19],包括:外源性和內源性。外源性方法是指:在實驗動物咽喉部涂抹一種或多種外源性物質,包括:胃酸、胃蛋白酶和膽鹽等,模仿人咽喉反流物,刺激咽喉部上皮組織,使其產生炎癥及潰瘍,最終引起LPRD[20]。這種方法操作簡單易行,對于實驗動物的刺激性小,成活率高,劣勢在于人咽喉反流物較為復雜,單一或者多種(胃酸、胃蛋白酶和膽鹽等)外源物質不能完全模擬人咽喉反流物及LPRD的發生過程。而內源性方法則是通過咽喉手術,人為改變實驗兔的胃腸道解剖結構,使反流屏障被破壞,從而達到加強動物自身胃腸內容物的反流效果,包括:賁門肌松弛術、賁門置管術、幽門縮窄術[21]、鼻飼管置管術[15]、LES 球囊擴張和UES 支架植入[5]等。內源性方法的優點在于:更加擬合LPRD的病理生理過程,可從發生機制上說明問題;缺點在于:手術及麻醉風險較大,對于術者要求高,動物成活率較外源性方法低。有研究[22-24]通過大鼠模型發現,減少大鼠睡眠時間和給予高脂飲食可誘發LPRD,該研究從病因學的角度對LPRD 動物模型進行探索,研究意義大,但建模時間過長,實驗中混雜因素過多。
LPRD 相關機制的研究極少。胡穎[25]在新西蘭兔模型的研究中發現,LPRD 的食道和喉上皮細胞間隙擴大,且在大鼠模型上發現claudin-3 表達水平明顯降低。FENG 等[11]用巴馬小型豬建立LPRD 模型,也證實了喉上皮細胞間隙擴大,并認為橋粒明顯減少。這兩項研究均可證明喉咽黏膜屏障被破壞。針對產生損傷的機制,有研究[26]基于新西蘭兔模型發現:白細胞介素-8 和血管內皮生長因子可能與咽喉反流和喉癌的發病機制有關,但LPRD的相關機制仍需進一步開展。
本實驗借鑒了LES 球囊擴張和UES 支架置入法,并予以改進。但原方法中UES金屬支架固定困難,易脫落到胃中,難以保證UES擴張效果,且支架難以取出,金屬支架多次使用后還會出現金屬絲變形,可能損傷血管導致大出血,也可能破壞食管組織導致穿孔。因此,本研究通過球囊擴張UES,對UES解剖結構造成破壞。但在實驗過程中發現:利用球囊對UES進行擴張易導致實驗兔窒息,需在喉鏡直視下操作,避免球囊導管擴張后堵塞聲門。另外,本研究還發現,在進行LES球囊擴張后,直接上拉球囊進行UES球囊擴張,易引起喉痙攣及誤吸,導致實驗兔在手術過程中死亡;而在LES 球囊擴張后先從食管退出球囊,再重新插入食管,進行UES球囊擴張,可有效避免誤吸及喉痙攣,降低死亡發生率。
本研究顯示,有效擴張新西蘭兔LES及UES可使實驗兔形成LPRD;建模后pH值監測結果顯示:實驗兔各項反流指標均明顯提高;組織病理學檢查顯示:實驗組新西蘭兔喉咽部及食道黏膜淋巴細胞廣泛浸潤,提示黏膜發生不同程度慢性炎癥。這表明:通過有效擴張實驗兔LES 及UES,可以建立LPRD 實驗兔模型。本研究有效地擴張了新西蘭兔LES及UES,且建模成功率高,符合LPRD病理生理過程,適用于體外研究,相較于LES球囊擴張聯合UES支架固定,操作相對簡便,術后死亡率更低。
綜上所述,本研究通過擴張LES和UES,成功建立了LPRD 兔模型,經pH 監測、RFS 評分及病理檢查,驗證了模型的有效性,與LES球囊擴張和UES支架固定法相比較,成功率和死亡率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本研究的建模方法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實驗過程中,實驗動物并發了較嚴重的胃食管反流。而臨床中的LPRD患者常不伴有胃食管反流,本模型也無法對此做出解釋[27]。目前,本研究團隊致力于一種新型LPRD 檢測試劑的開發,已在本模型上應用,并取得了較好的檢測效果,為進一步開展臨床試驗及深入的分子機制研究奠定了基礎,具有實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