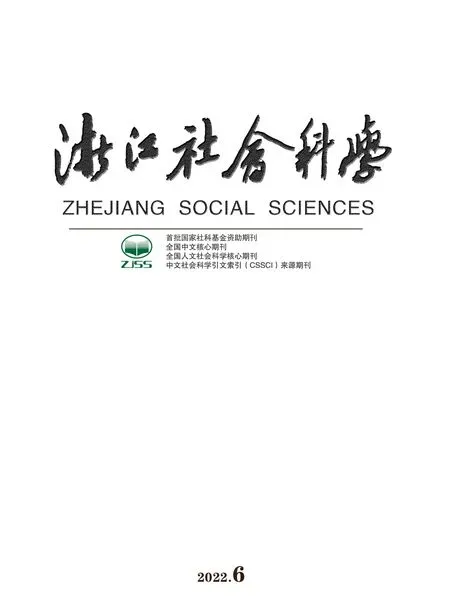經學史研究的三維向度芻議
□ 關長龍
內容提要 經學史是一個嵌套了三個層級概念的語詞,第一級為六經本體,第二級為研究六經本體的經學,第三級才是對經學做歷時研究的經學史本身。經學內容的三維向度決定了經學史展開的基本脈絡。此三維向度可稱為考據經學、格致經學和致用經學。其中考據經學是對六經本體特別是文本的解讀和研究,格致經學是對六經本體之問題意識的義理體知,致用經學是對六經本體的踐行與經世致用。三者的歷時展開則構成了經學史研究基本脈絡的三維向度。
當代經學史家林慶彰先生指出:“經學是我國特有的學問,并無現成的理論可取資,以致各本經學史的著作皆陳陳相因。”①如此,我們不妨追本溯源、顧名思義地追問一下“經學史”概念的內涵。從字面上理解,經學史無疑就是研究經學的歷史,而經學又是研究經的學問,可以說,經學史是一個嵌套了三個層級概念的語詞。
漢初陸賈《新語·道基》云:“后圣乃定五經,明六藝。”②這里的“后圣”當指孔子編定六經而言。③按“五經”是文獻角度的概念,④不包括“樂經”,因其無通常意義上的文本,而“六藝”則是致用角度的概念,故兼“樂藝”而論。泛指則經、藝可通,故亦有“六經”之名。漢時以“五經”配五常之道,又賦予了這組經書以宇宙論意義,使之成為軸心時代圣言封閉之前的“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⑤,后世不得隨意損益之。⑥
經目既定,則作為“研究經的學問”的經學之意也就容易理解了。可以說,嚴格意義上的經學只能是指對“五經”或“六藝”的研究與致用。近代學人馬一浮先生指出:
六藝者,即是《詩》《書》《禮》、樂、《易》《春秋》也,此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⑦
這一理解把“學科”時代的“六藝”研究重新與“六經”對接,即以“六藝”喻為織帛的“經”線,它始終不變,而在與時俱進的“緯線”編織中逐漸成帛,循至今日,此六藝固亦可以“該攝一切學術”乃至“西來學術”⑧。也就是說,經學是中國一切學術文化的學統格局,它也是符合這些學統格局的學術文化之總合。當然,這一理解以歷時的“見本而知末”論之則可,如以共時的“見末而觀本”則固不能通,故從現代學科視角而言,經學之目當亦有所限定,要之以文本考據求真、義理格致求善、致用踐行求美為目,庶幾略可明之。
如此,則經學史的研究內容就可以理解為對歷史時空中的經學之目作斷面掃描式的描寫、歸納和總結。下文即依此而對經學三目的形態稍作討論。
一、六經本體的解讀與考據經學
經學所賴以存在的前提和基礎就是“六經”之實,然而“六經”本體的形成卻不是先在的存有,也不是一蹴而就的產物。《朱子語類》卷85 云:
《儀禮》不是古人預作一書如此,初間只是以義起,漸漸相襲,行得好,只管巧,至于情文極細密周致處,圣人見此意思好,故錄以成書。
沈文倬先生更具體地推論說:
如果認識到有了事實才有可能對事實進行記錄,那么,上文所論證的由禮物、禮儀構成的各種禮典早已存在于殷和西周時代,而“禮書”則撰作于春秋之后,就沒有什么可以懷疑的了。⑨
與《儀禮》的成書情況相似,《周易》經文的形成也是“人更三圣,世歷三古”,至于解經之作的十翼之傳,其產生還要晚些。還有《尚書》據“上古”時期的典謨訓誥誓命等而抄傳,《詩經》 由采風而匯集,《春秋》因魯史而刪定,以及“樂者樂也”的“樂經”僅憑師徒口耳相傳實無文本。這些文獻的定型成“經”必有各自的時間節點,今所見的戰國秦漢文獻皆屬之于圣人孔子,后世從之,所謂“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⑩。此雖或有進一步考辨的空間,然其差失也應該不會很遠,況且這一認同也給研究六經的學問——經學設定了起點和一個理想的 “本體原型”,從而讓中國文化有了一個“家園”符號,其后所有的文化成長都是從這個“家園”中走出來的。
由于孔子僅是“刪定”六經,故在此之前既已存在的“六經”本體就只能稱為“前經學時代”的文獻,這也是現代多數經學史著作采用的意見。對于這些文獻,亦頗有時人對其中的一些內容有所解讀訓注,如《易》之“十翼”,《禮》之“喪服”“記”等及三代出土文獻之可與六經比證者,凡此雖未必徑能引為經學之論,然亦皆經學研究所不能回避的資源,其于“六經”本體的認知和理解并有助益。
至于“六經”底定之后,傳者既廣且經論亦夥。如《后漢書·徐防傳》即載云:“《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自子夏。”其后三傳、三禮(此指大小戴《記》和《周禮》)之書,諸子摘引之論,經師傳授之說,歷歷多矣。況秦火之后,又增殘損。?《漢書·藝文志》云: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故《春秋》分為五,《詩》分為四,《易》有數家之傳。戰國從衡,真偽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燔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
漢代大興文教,秦時博士與民間學人口誦筆錄,兼有地下文獻時出,五經文本不僅有傳家的訛奪衍乙之異,亦有今文、古文之別,此又增六經“本體原型”的推定之艱。馬宗霍先生即指出:
自六經燔于秦而復出于漢,以其傳之非一人,得之非一地,雖有勸學舉遺之詔,猶興書缺簡脫之嗟,既遠離于全經,自彌滋乎異說。是故從其文字言,則有古今之殊; 從其地域言,則有齊魯之異;從其受授言,則有師法家法之分;從其流布言,則有官學私學之別。?
這種情況隨著時間的展開和地下文獻的涌現,也不斷吸引著學人對六經“本體原型”的趨近期待與努力熱情。
與此“本體原型”追溯相伴的經學學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文本傳承中的載體先后、文字是非、經注體例以及相關文獻既多之后的檢索查證手段等等,研究此類問題的學問在傳統學術中被稱為“文獻學”;另一是文本異代之后的識讀理解方面的學問,此在傳統學術中被稱為“小學”。此外,作為“小學”的延伸內容,還有與六經本體相關的名物故事、典章制度等等,戴震《與是仲明論學書》云:
至若經之難明,尚有若干事。誦《堯典》數行,至“乃命羲和”,不知恒星七政所以運行,則掩卷不能卒業。誦《周南》《召南》,自《關雎》而往,不知古音,徒強以協韻,則齟齬失讀。誦古《禮經》,先《士冠禮》,不知古者宮室、衣服等制,則迷于其方,莫辨其用。不知古今地名沿革,則《禹貢》職方失其處所。不知少廣、旁要,則《考工》之器不能因文而推其制。不知鳥獸蟲魚草木之狀類名號,則比興之意乖。而字學、故訓、音聲未始相離,聲與音又經緯衡從宜辨。漢末孫叔然創立反語,厥后考經論韻悉用之。釋氏之徒,從而習其法,因竊為己有,謂來自西域,儒者數典不能記憶也。中土測天用句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線,其三角即句股,八線即綴術,然而三角之法窮,必以句股御之,用知句股者,法之盡備,名之至當也。管、呂言五聲十二律,宮位乎中,黃鐘之宮四寸五分,為起律之本,學者蔽于鐘律失傳之后,不追溯未失傳之先,宜乎說之多鑿也。凡經之難明,右若干事,儒者不宜忽置不講。?
要之,文獻學與小學成熟之后,從現代的學科視角而言,其內容已超出經學范圍,不過我們還是可以說,經學中的文獻學與小學成績,皆是指向對六經“本體原型”的趨近與理解,故這兩方面的經學旨趣可以說都是屬于求真的學問,我們稱之為考據經學。此成績多以傳箋注疏、專題考證以及辭書等形態呈現,這也是現代一般經學史研究的主要內容。
二、六經本體的體知與格致經學
六經是軸心時代先知們用以認知現實世界的智慧結晶,然而六經本體簡約且傳有闕誤,?考據經學于文本所無者只能持“蓋闕如也”的策略,然而這又難敷人們生活世界對六經“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的需求。黃侃先生即曾指出:
五經應分二類,《易》、《禮》、《春秋》 為一類,《詩》、《書》又為一類。《詩》、《書》用字及文法之構造,與他經不同,《易》、《禮》、《春秋》則字字有義。《詩》、《書》 以訓詁為先,《易》、《禮》、《春秋》以義理為要。《詩》、《書》之訓詁明,即知其義,《易》、《禮》、《春秋》之訓詁明,猶未能即知其義也。?
其實《詩》《書》亦有訓詁明而未能即知的義理內容。故后世學人除即文本以追溯其本體原型外,還采取了越文本而直面六經所認知的現實世界的治學思路,即準擬先圣智慧的思維方式和義理策略,以認知切己時空中的義理生態和生命體悟,來經緯和對接六經本體的義理類型,并寔正文本傳承的義理闕誤,這種經學內容可以稱為格致經學。它與前節所述的考據經學一起,共同推動了對理想的六經本體原型的建構。
《孟子·離婁下》載云:“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也就是說,同樣是對現實世界社會事件的記載,甚至同樣是對齊桓、晉文時代史事的記載,六經中的《春秋》經過了孔子的審定,就楷定了社會史認知的義理典范。《淮南子·泰族訓》謂圣人“法天”而制六藝,“六藝異科而皆同道”?。又《白虎通·五經》云:
經所以有五何?經,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經?。樂仁,《書》義,《禮》禮,《易》智,《詩》信也。人情有五性,懷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
這里把六藝與天道生化萬物的展開質素“五行”相擬配,其是非當否雖或有可議之處,然欲以宇宙論的視域而賦六經以全文化的科別或格局統攝意識卻是值得肯定的。下表所輯為戰國秦漢之際文獻所載六經的義理“格局”觀:
諸家所論六經的“格局” 類型大致是有共識的,姑以今語歸約轉述如下:
《易》述天道流行之理。《書》載事件文書之理。
《詩》通心性情志之理。《禮》言行為儀式之理。

春秋《郭店楚簡·物由望生》?易書詩禮樂《春秋》所以會古今之事也。《禮記·經解篇》 絜靜精微,《易》教也。《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 書》,□□□□〕者也。《詩》所以會古今之詩〔志〕也者。《禮》,交之行述也。樂,或生或教者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莊子·天下》 《易》以道陰陽 《書》以道事 《詩》以道志 《禮》以道行 樂以道和 《春秋》以道名分《荀子·儒效》 《書》 言是其事也。疏通知遠,《書》教也。溫柔敦厚,《詩》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淮南子·泰族訓》《詩》言是其志也。《禮》 言 是其行刺幾辨義者,《春秋》之靡也。《春秋繁露·玉杯》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春秋》 正是非,故長于治人。《史記·滑稽列傳》 《易》以神化 《書》以道事 《詩》以達意 《禮》以節人 樂以發和 《春秋》以道義。《易》 本天地,故長于數。《書》著功,故長于事。《詩》道志,故長于質。《禮》制節,故長于文。樂詠德,故長于風。《漢書·藝文志》蓋五常之道,相須而備,而《易》為之原。《書》 以廣聽,知之術也。《詩》 以正言,義之用也。《禮》 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樂以和神,仁之表也。《春秋》 以斷事,信之符也。
樂發感通和合之理。《春秋》辨社會人倫之理。
這種歸約擬類在傳統目錄學中也有學人討論。?近代馬一浮先生在《泰和會語·論西來學術亦統于六藝》中也有較為具體的擬配分疏:
因《易》明天道,凡研究自然界一切現象者皆屬之。《春秋》明人事,凡研究人類社會一切組織形態者皆屬之。……
文學、藝術統于《詩》、樂,政治、法律、經濟統于《書》《禮》,此最易知。宗教雖信仰不同,亦統于《禮》,所謂亡于禮者之禮也。
哲學思想派別雖殊,淺深小大亦皆各有所見。大抵本體論近于《易》,認識論近于樂,經驗論近于《禮》。唯心者樂之遺,唯物者《禮》之失。凡言宇宙觀者皆有《易》之意,言人生觀者皆有《春秋》之意,但彼皆各有封執而不能觀其會通。?
具體到個例而言,如《易》以明天道中關于本體形態的描述。朱熹、呂祖謙所編《近思錄》首設“道體”一目,輯引北宋五子共五十一條意見以闡釋其義。若以今智論之,則猶有可申者。按《周易·系辭上》云:“是故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兇,吉兇生大業。”這是對宇宙本體“基因態”的一個描述,即宇宙的終極初始態為太極與陰陽和合為一的存在形態,當陰長陽消或陰消陽長時,作為基因的“太極”成為陰陽消長變化背后的“生命力”,陰陽的消長輪回,就應該是“三”者一起行動。這是一個很神奇的模型,它從宇宙本體太極而來,包容了宇宙變化的一切可能。《老子》說“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應該也是這個道理。與太極本體形態一樣,在太極動而生化時,因為太極無形,故其動必以陰或陽的形態呈現,并與陰陽二氣形成“陰陽三合”的“基因態”組配,不可再行拆分。當此基因態組配再行兩兩組合時,就進入到了物質世界的質素態,此質素態的類型在《尚書·洪范》中即以五行明之。由本體——氣態——質素——萬物(包括人)的四分法,無論其正確與否,宇宙的終極形態以及如何生化萬物(包括人)的問題意識,仍然是今日宇宙學的成立原因和最后的落腳點,且以今論之,如果作推源追問,則萬物由量子組成,量子由能量轉化,能量與宇宙“奇點”的關系如何? 而量子以及量子組合的萬物與宇宙“奇點”的關系又是如何? 縱使我們還沒有科學的結論,但是卻不能因為沒有結論而阻止對這一問題的思考與假說。或者說,六經時代的先哲已對宇宙論有了系統而深入的思考了,生今之世的學人在無視今日宇宙論研究成果的情況下,卻要以“他者之心”臆度先哲“合外內之道”的思考,則不僅有違經學“通經致用”的本意,也很難獲證先圣后賢積智成識的本意。
又如對道德場域中“仁”的理解。陳來先生在《仁學本體論》中梳理了古今歷代關乎“仁”之概念的重要理解。如其總結義理重整時代的宋代仁學理解云:
自宋代以來,已經十分注重“仁體”的觀念,在他們的運用中,大體上說,心學是把仁體作為心性本體,而理學哲學家則把仁體作為宇宙的統一性實體。……在宋明理學的理解中,仁體是萬物存在生生、全體流行的渾然整體,故天地人物共在而不可分。仁體不離日用常行,即體現在生活和行為,無論是識仁還是體仁,人在生活中的踐行和修養就是要達到仁者的境界,回歸到與仁同體。?
現代學人論者亦多,然而如果橫不能把“仁”置于道德場域中觀察,縱不能因經而上推于天道而下求于身體,則不能得先圣立仁之本意。前者要求在道、德、仁、義、禮、智、信、性、命、情、理、欲、意、識等概念場域中分疏“仁”的位置和義理設定,后者要求在生命體知的本體流行以及個體與萬物生化互動中明確“仁”的工夫和義理設定。所以在今日看來,關于“仁”之概念的思考與闡釋還有進一步深入展開的空間。
最為復雜的則是關乎《禮》經的問題意識。因為它所直面的對境是人們生活世界的行為方式,無論一個個體是有意還是無意,他都需要活動。即使重要的典禮活動亦是如此,無論一個人了解還是不了解婚禮、喪禮,他的人生都要經歷這兩個環節,如果從群體的視角來看,可以確定的是,每天都有很多個體要舉行婚禮和喪禮。如果從學術體用的視角而言,則其他四經兼有“明體”工夫,而《禮》經則全為“致用”工夫,故《漢書·藝文志》說“《禮》以明體,明者著見,故無訓也”,即《禮》是道體致用流行而表現于行為認知的結晶,其所表現的行為亦名為禮,故不需用另外的詞來轉釋“禮”的語義。然《禮》經闕文多矣,而致用禮目的制作又多如漢初叔孫通綿蕞禮儀一樣投上所好,未必皆能盡“明體達用”的學術工夫,這也是許多“當代”踐禮制作如唐《開元禮》、宋《政和禮》等多受學人批評的原因所在。宋代朱子乃以個人之力推補《禮》經所未備,其《儀禮經傳通解》之作介于馬一浮先生所謂的宗經與述經之際,?也就是我們這里所說的經學“文本認知與解讀”和“格致展開與思考”之間的一種著作,至清儒徐乾學《讀禮通考》、秦蕙田《五禮通考》、黃以周《禮書通故》等著作,則已初具上推下求以考禮之全體大用的特色了。
至于《詩》經、《書》經、《春秋》經相關的義理思考和研究,也當系于此一經學目下。
劉師培在《經學教科書》中指出:
且后世尊崇六經亦自有故,蓋后儒治經學,咸隨世俗之好尚為轉移。西漢侈言災異,則說經者亦著災異之書;東漢崇尚讖緯,則說經者亦雜緯書之說。推之魏晉尚清談,則注經者雜引玄言; 宋明尚道學,則注經者空言義理。蓋治經之儒各隨一代之好尚,故歷代之君民咸便之,而六經之書遂炳若日星,為一國人民所共習矣。?
此論解經者隨“世俗之好尚為轉移” 所舉諸例,皆為義理格致的研究成績,并不是說在那些時代文本認知的考據經學成績就絕無僅有。考據經學與格致經學是兩種類型的成績,二者雖相互倚伏,但也各有其發展的脈絡條理,故應分別述之,才可謂平允該備。
要之,格致經學的主要成績當是指向求善的學問,其具體呈現多為關乎名物故實、典章制度的專門史研究和義理名相的哲學史、心理學史研究,以及情感技藝、人倫禮俗的文學史、科技史和社會史研究等等。大致說來,凡有意指向或對接六經本體的義理致思,皆可以歸于格致經學目下。
三、六經本體的踐行與致用經學
秦漢時六經多稱六藝,正為強調其致用的“術藝”功能,此在上節所輯諸家論六經義理格局中的類型已略可知。《漢書·儒林傳》以六藝為“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倫,致至治之成法”,清皮錫瑞在《經學歷史》中也具體揭示了這一現象:
(前漢)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
或謂今日已時易境遷,不可能再用《禹貢》治河、《洪范》察變了云云,這是一種不識變通的“原教旨主義”看法。六經既引織帛成匹之“經線”為喻,把中華文明比喻作一匹基于六經而仍在編織的帛面,則當知僅有經線是不可能成就帛匹的,而是要遵從六經所設之經軸筘齒來編經織緯,才能成就歷史時空中每一個當下文明的“帛匹”進境。當然,在編經織緯時如果發現經線有呲毛散敗,也要別加清理接續,以為時用。至于因時空之變而對此經線作損益改造,以適應織緯技術的提升和當下時空對帛品形態的需求,也都是情理中當有之義。唯經線的清理接續當有理致,不可遽加截斷而別為機杼,是謂文明斷裂,其結果將是《孟子·滕文公上》 辟許行農家學派所可能出現的情況:“如必自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
如果六經(六藝)可以“千變萬化,其道不窮”?,則其“道體流行”必然與時空變化有著完美的一致性,亦即中國學術傳統所謂的“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仁者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的生態境界。這與現代管理學中的“目標管理”似有可比性。《左傳·昭公五年》載魯昭公朝會晉平公,從郊勞到贈物皆無失禮,晉平公贊其知禮,而大夫女叔齊卻說:“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其民者也。今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利人之難,不知其私。公室四分,民食于他。思莫在公,不圖其終。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于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于禮,不亦遠乎? ”?即強調禮是一種“時中”的境界,它是當下生活世界整體的恰到好處。我們再引二文來看六經的“目標”思考: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薭靜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
圣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天。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皆適調,六藝異科而皆同道。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為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樂之失淫,《詩》之失愚,《書》之失拘,禮之失忮,《春秋》之失訾。六者,圣人兼用而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
可以說,六經文本既是圣賢刪定的“至道”總結,也是對“至道”流行生態的“鴻教”示例,從生活世界道體流行的“目標”來說,只要呈現出“溫柔敦厚”“溫惠柔良”的生活氣象,即是《詩》道流行的境界;只要呈現出“絜靜精微”“清明條達”的氣象,即是《易》道流行的境界;只要呈現出“恭儉莊敬”“恭儉尊讓”的氣象,即是《禮》道流行的境界,如此等等。具體而言,又有“一本萬殊”的時中之變,或者說是匹帛編織之“經線”展開的“穿梭打緯”之延伸。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云:
(《春秋》)猶今之《大清律》,必引舊案以為比例,然后辦案乃有把握。故不得不借當時之事,以明褒貶之義,即褒貶之義以為后來之法。如魯隱非真能讓國也,而《春秋》借魯隱之事,以明讓國之義;祭仲非真能知權也,而《春秋》借祭仲之事,以明知權之義;齊襄非真能復仇也,而《春秋》借齊襄之事,以明復仇之義;宋襄非真能仁義行師也,而《春秋》借宋襄之事,以明仁義行師之義。所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孔子之意蓋是如此。?
此舉《春秋》中讓國、知權、復仇、行師數例中的道體流行細目,以揭《春秋》“屬辭比事”“刺幾辯義”的境界組成內容。
又如《易》述天道流行之理,必知天道乃能實現生活世界的“絜靜精微”“清明條達”,故于生活世界遇有嫌疑困惑的選擇之際,就需要“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故《禮記·表記》載孔子語云:“昔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神明,無非卜筮之用。”?又《白虎通·蓍龜》云:“天子下至士,皆有蓍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人類學家李安宅先生亦云:“卜筮的應用,幾于個個禮節上都有地位。”?日本漢學家池田知久先生也指出:“如果經學是天人之學,那么作為其必然結果,就不可能從經學內部完全排除術數的思維,經學的思維就不得不與術數性或神秘性糾結在一起。”?《周易》作為一個“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數理模型,它雖然對某些嫌疑猶豫之事可以給出一些具有“心理咨詢”性的方向性指導,但在具體細事的占斷上不可能有很高的準確性,?故致一些關乎具體類型的推占數術出現和發展,如天文、地理(風水)、人文(相術)、物理(五行)、日書等等,乃至現代學科發展中的心理咨詢、經濟建模、宇宙假說、天氣預報、地震預測、疫情監測、大數據算法等等,舉凡能對影響人們生活世界之選擇指導和疑難解惑的“數術”手段,皆可謂《易》道的“經緯”延伸,這些指導和解惑如果能對人們的生活起到實際的效果,那么有“嫌疑”“困惑” 之人的生活世界就會重新恢復為天道流行的“絜靜精微”“清明條達”境界。
又如《禮》述天人和合之理,也必知天道流行的秩序才能實現生活世界的“恭儉莊敬”“恭儉尊讓”。故漢初有叔孫通綿蕞禮儀,唐有《開元禮》,宋明清及民國有《政和禮》《明集禮》《清通禮》《北泉議禮錄》等等,皆是各代因《禮》經而“穿梭打緯”所制作的當代禮,至若殊方異域之禮俗、家禮之作,其理并同,皆欲使種群個體能在生活世界中最恰到好處地安措手足,若能使當事主體生出“恭儉莊敬”“恭儉尊讓”氣象,即是《禮》道流行的境界。在討論這個經例時,我們有必要揭出《禮》經致用中的一個“呲毛散敗”之處,那就是“封建制”或者說“宗法制”,按封建制或宗法制在春秋時期逐漸解體,然秦漢以后的帝國制度為維系君權而重推宗法制,以致《禮》道不能順利流行,《公羊傳》在釋《春秋》經隱公三年“尹氏卒”和宣公十年“齊崔氏出奔衛”時皆指出二人為大夫而稱“氏”,是“譏世卿,世卿非禮也”,豈以“小巫”之大夫世卿可譏,而“大巫”之天子世襲就不當譏?杜正勝先生即指出:
春秋晚期以后封建崩解,社會基本單位逐漸轉變成為個體家庭,集權中央政府才有可能實現。……這些家庭就是史書所謂的“編戶齊民”。編戶齊民奠定秦漢以下兩千五百年政治和社會的基礎,直到今日依然未曾改變。?
然自秦至清,終整個帝國時代,上下學人多推重宗法制,即《朱子家禮》仍襲用宗子制,蓋亦智者千慮之失,此是《禮》經致用中所當清除者。
其余如《詩》經疏通情志,與今之文學關聯密切;《書》經通鑒故實,與今之政治學關聯密切;樂經和合天人,與今之藝術學關聯密切;《春秋》經世敦倫,與今之社會學關聯密切。其致用之道雖指向領域各別,然其展開路徑則與《易》《禮》二經略同。
要之,致用經學的主要成績當是指向求美的境界呈現,其具體內容則為關乎主體修齊治平的全部行為規則與表達。?如關乎個體及大眾生活行為的法律制度、禮儀規范、道德教育等的研究與制作。如果說考據經學為“我注六經”,那么格致經學就是“六經注我”,而致用經學則是“六經與我合一”,所謂“道不虛行只在人”。唯于致用經學而言,現代學科研究與六經價值體系對接的邊界如何認識和規范,還需要作更深入細致的探索。
余 論
由考據經學和格致經學共同發掘和修繕六經本體原型,并進而致用其義理于當下的生活世界,則六經“體用一如”“經緯錯落”的歷史層次即由此生成。對這些經學的歷史層次加以斷代總結和描述應該就是經學史的研究內容。
雖然自先秦以來即有對學術研究的歷史加以總結和研究的專論出現,如《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以及歷代史書的藝文志、經籍志和儒林傳等,但晚近最有影響的經學史斷代概括當為《四庫全書總目》經部總敘:
自漢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學凡六變。
其初專門授受,遞稟師承,非惟詁訓相傳,莫敢同異,即篇章字句,亦恪守所聞,其學篤實謹嚴,及其弊也拘。
王弼、王肅稍持異議,流風所扇,或信或疑,越孔、賈、啖、趙,以及北宋孫復、劉敞等,各自論說,不相統攝,及其弊也雜。
洛閩繼起,道學大昌,擺落漢唐,獨研義理,凡經師舊說,俱排斥以為不足信,其學務別是非,及其弊也悍(如王柏、吳澄攻駁經文,動輒刪改之類)。
學脈旁分,攀緣日眾,驅除異己,務定一尊,自宋末以逮明初,其學見異不遷,及其弊也黨(如《論語集注》誤引包咸夏瑚商璉之說,張存中《四書通證》即闕此一條以諱其誤。又如王柏刪《國風》三十二篇,許謙疑之,吳師道反以為非之類)。
主持太過,勢有所偏,才辨聰明,激而橫決,自明正德、嘉靖以后,其學各抒心得,及其弊也肆(如王守仁之末派皆以狂禪解經之類)。
空談臆斷,考證必疏,于是博雅之儒引古義以抵其隙,國初諸家,其學徵實不誣,及其弊也瑣(如一字音訓動辨數百言之類)。
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義明矣。蓋經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
這一斷代選擇和內容評議,多為清末以來的經學史研究所取資。要之斷代選擇是經學史研究的“緯線”,只要與其內容評議配合有據,即稱允當;但作為經學史研究之“經線”的內容評議選擇,卻舍棄經學本體認知而別取概念模糊的 “漢學”“宋學”來加以分疏,?無疑會造成很大的混亂。究其所以如此的原因,大致也是林慶彰先生所指出的“經學內容包含太廣,學者兼顧不易”?有關。但作為學術研究,似不宜因為“兼顧不易”就回避之,故本文關于經學三維向度的思考,即欲拋磚引玉,幸同道正之。
六經(或稱五經六藝)是中國文化在濫觴時代的第一次總結性結集,作為軸心時代文明的代表文獻,歷代關乎自然、社會、人生的研究與踐行都不能回避它的存在,“人類一直靠軸心時代所產生的思考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被它重新燃起火焰。”?每一代的經學都在“返本開新”中重燃起那個時代的學術火焰,經學史研究則是把這些火焰合理地排列起來,使之成為照亮我們當下的學術主體性和文化重建之路的有用資源。
注釋:
①林慶彰:《經學史研究的基本認識》,載《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2年版,第2 頁。此外,清末民初以來經學史著作的基本情況請參葉純芳《中國經學史大綱》第一章“中國經學通史教材的歷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12 頁。
②王利器:《新語校注》,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8頁。
③陳立:《白虎通疏證·五經》:“孔子所以定五經者何?以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凌遲,禮義廢壞,強陵弱,眾暴寡,天子不敢誅,方伯不敢伐,閔道德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中華書局1994年版,第444~445 頁。又《隋書·經籍志》:“(孔子)乃述《易》道而刪《詩》《書》,修《春秋》而正《雅》《頌》。壞禮崩樂,咸得其所。”中華書局1973年版,第904~905 頁。相關論述文獻載錄甚多,此不贅引。
④五經指《易》《書》《詩》《禮》《春秋》五種文獻。
⑤王利器:《文心雕龍校證·宗經第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11 頁。
⑥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流傳時代”云:“孔子所定謂之經,弟子所釋謂之傳,或謂之記,弟子展轉相授謂之說。惟《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藝乃孔子所手定,得稱為經,漢人以樂經亡,但立《詩》《書》《易》《禮》《春秋》五經博士。后增《論語》為六,又增《孝經》為七。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為九。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為十三經,皆不知經傳當分別,不得以傳記概稱為經也。”中華書局2004年版,第39 頁。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第一課“經學概述”:“三代之時只有六經。六經者,一曰《易經》,二曰《書經》,三曰《詩經》,四曰《禮經》,五曰樂經,六曰《春秋經》。……流俗相傳,習焉不察,以傳為經,以記為經,以群書為經,以釋經之書為經,此則不知正名之故也。”載《劉申叔遺書》,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074 頁。
⑦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第一冊(上),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8 頁。
⑧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第一冊(上),第10、17 頁。
⑨沈文倬:《略論禮典的實行和〈儀禮〉書本的撰作》,載《菿闇文存》,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8 頁。
⑩?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 經部總敘,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 頁。
?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的《禮》僅存17 篇,而“凡百篇”的《書》亦僅存29 篇,此其大者。
?班固:《漢書》,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701 頁。
?馬宗霍:《中國經學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5 頁。
?戴震:《戴震全書》第6 冊,黃山書社1995年版,第371 頁。
?孔穎達:《宋本周易注疏·系辭上》:“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中華書局2018年版,第426 頁。又楊伯峻《孟子譯注·盡心下》:“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中華書局1960年版,第325 頁。又陳寅恪《楊樹達〈論語疏證〉序》:“圣言簡奧,若不采意旨相同之語以參之,則為不解之謎矣。既廣搜群籍,以參證圣言,其言之矛盾疑滯者,若不考訂解釋,折衷一是,則圣人之言行,終不可明矣。”載陳美延編《陳寅恪集·金明館叢稿二編》,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年版,第262 頁。
?班固:《漢書·儒林傳》,第3589 頁。
?張暉編:《量守廬學記續編——黃侃的生平和學術》,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8 頁。
?楊伯峻:《孟子譯注》,第192 頁。
??何寧:《淮南子集釋》,中華書局1998年,第1392、1392~1394 頁。
?下列“五經”無《春秋》,當為東漢時期受讖緯“赤制”影響而尊《春秋》為五經之宗的反映,與西漢時期以《易》為六經之源的理解不同,唯此缺少學理依據,已脫離經學發展的正軌。參程蘇東《〈白虎通〉所見“五經”說考論》,載《史學月刊》2012年第12 期。
??陳立:《白虎通疏證》,第447、327 頁。
?李零:《郭店楚簡校讀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60 頁。
?章學誠:《校讎通義·內篇二》“補校 《漢書·藝文志》第十”:“充類求之,則后世之儀注當附禮經為部次,史記當附《春秋》為部次。縱使篇帙繁多,別出門類,亦當申明敘例,俾承學之士得考源流,庶幾無憾。”載《校讎通義》,古籍出版社1956年版,第16 頁。
?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第一冊(上),第18 頁。
?陳來:《仁學本體論》,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4年版,第200 頁。
?吳光主編:《馬一浮全集》第一冊(上)之《泰和會語·論六藝該攝一切學術》自注云:“宗經、釋經區分,本義學家判佛書名目,然此土與彼土著述大體實相通,此亦門庭施設,自然成此二例,非是強為差排,諸生勿疑為創見。孔子晚而系《易》,《十翼》之文,便開此二例,《象》《彖》《文言》《說卦》是釋經,《系傳》《序卦》《雜卦》是宗經。尋繹可見。”參見第13頁。
?劉師培:《經學教科書》第八課“尊崇六經之原因”,載《劉申叔遺書》,第2077 頁。
?皮錫瑞:《經學歷史》“三、經學昌明時代”,第56 頁。
?屈守元:《韓詩外傳箋疏》卷5,巴蜀書社1996年版,第471 頁。
?楊伯峻:《春秋左傳注》(修訂本),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401~1402 頁。
???孔穎達:《禮記正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1903、2040、2095 頁。
?皮錫瑞:《經學通論·春秋》,中華書局2017年版,第394~395 頁。
?李安宅:《〈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2 頁。
?池田知久:《術數學》,載溝口雄三、小島毅主編,孫歌等譯《中國的思維世界》,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 頁。
?這與天氣預報、地震預測的建模推測類似,只不過《周易》是對整個宇宙時空的建模而已,所以在具體事例的測算上它的誤差也必然更大些。
?杜正勝:《古代社會與國家》,(臺北)允晨文化實業服份有限公司1992年版,第780 頁。
?桑兵《經學與經學史的聯系及分別》指出:“經學時代的經學不僅是學問,更主要是倫理的規范,社會秩序的基礎,或者說意識形態的正統。從禮制到禮俗,形成廟堂、市井、鄉土各個社會層面相互連接的道德觀念、人倫關系和制度體系。”參見《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11 期。桑先生的“經學時代”是基于國家制度層面的界定(漢尊儒學至清末民初取消經科),與經學研究層面的理解不盡相同。
?桑兵指出:“漢宋、今古等等大都是用后來觀念說前事,如漢宋基本是清學范圍的事,尤其是晚清以后事,而江藩、方東樹筆下的漢宋,與章太炎所說相去甚遠。今人所講漢宋,顯然更合于章氏的意見。”參見《經學與經學史的聯系及分別》,《社會科學戰線》2019年第11 期。
?林慶彰:《經學史研究的基本認識》,載《中國經學史論文選集》,第2 頁。
?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華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 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