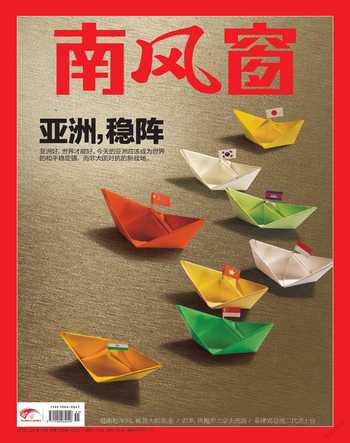胡宜安:“生死教學”二十年
朱秋雨

泰國的一部電影《死于明日》,是改編自真實的事件,其中有罹患心臟病的妻子,每天都在準備自己的離世,然而,丈夫卻意外先死于空難。
還有一位長壽的老人,妻兒都離世了,他在孤獨的人生中,度過了104歲的生日。
反復有獨白問主人公:“你怕死嗎?”“你知道死是怎樣的嗎?”“明知道要死,你會難過嗎?”
過去的22年,廣州大學的胡宜安教授,每天都在直面這些疑問。他是“生死學”這門學科的先行學者,2000年,他開設了《生死學》選修課,為國內的第一批研究人員。2009年,他再出版了國內唯一一本《生死學》教材。
我們的談話,就從這門課程開始。
有學者曾表示,“死亡是一種能力”。胡宜安認為,現代人正在喪失這種能力,而這種能力,是源于對待死亡的自然心態。
胡宜安說,在高校中,許多自殺的學生是“資優生”—資質優越的學生,更容易感受到生命的虛無。而缺乏對生命教育的一課,讓很多生命如同地基建在沙灘的大廈一般。
因此,在每學期開設的、面向全校招90人的通識課里,他的論題,始終圍繞著死亡是什么、瀕死體驗、疾病、自殺、安樂死、臨終關懷等。他試圖通過這些,讓人掙脫死亡恐懼,最大程度地敬畏生命。
20年間,情況逐漸變化。胡宜安的《生死學》在近年成了網紅課程,在清華的網課平臺上,獲得了十幾萬人訂閱,其中很多是社會人士。95后、00后學生,越來越直面死亡議題。
以下是他的講述:
上生死課的首要目的,是消除死亡的神秘性。
人對死亡的無知一大表現是逃避死亡。記得多年前課上有一個學生,她給我寫了一份至今仍讓我印象深刻的課后總結,記錄的對象是她逝去的、非常愛她的爺爺。
這個作業里有很多細節:爺爺生前以她為豪。女孩從小山村考上市重點高中時,她爺爺親自將她送到村口,囑咐說要考上大學。但就在高中一個中秋節篝火晚會的那天,她收到爺爺逝世的消息。
她后面的行為看起來有些壓抑:整整高中兩年,她屏蔽了親人離世的消息,沒問過爺爺葬在哪里,生前是否留下遺言。這樣的“屏蔽”舉動可能有毀滅性后果,壓抑的情緒也許會通過另一種極端方式爆發出來。
考上了大學以后,她選了我的通識課。我在課上強調的是,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不要只把死亡看作是很糟糕的事情。藏傳佛教有一個故事說,一個婦人兩歲的兒子夭折了,因此跑去求釋迦牟尼復活愛兒。佛說,你跑到拉薩城找一個沒死過人的家庭,要一顆芥菜籽,我就讓你兒子復活。
婦人敲了好幾戶的門,找不到這樣的家庭,慢慢理解了世上不存在這樣的芥菜籽。
我還會在課上介紹死亡的具體方式:疾病、衰老、災難、意外死亡等等,不同的“死法”意味著與死亡共處方式的不同。
瀕死體驗也是我講課的一部分。科學家的研究結論是:瀕死感受與具體境遇相關聯,發生意外者感受到特別強烈的狂喜,心跳停止的人,經常看到已經去世的親人和朋友,心臟病發作者較可能有經過隧道的感覺。
我講述這些是希望將死亡祛魅化。這個學生在學期作業里說,上完這門課后有勇氣且能站在爺爺的墓前,和他說話。
這也是生死學的一個功用—給活著的個體松綁。
生死課需要有實踐性環節,因為死亡發生在具體的情境。有一節課叫“生命的最后一個車站”,我讓學生給生命設限,想象自己死亡的方式,寫一份遺囑和墓志銘。這份作業會安排他們自愿當堂宣讀,課堂上經常有淚流滿面的時刻。
令人欣慰的是,他們對死亡的認識至少豐富了起來,不再只有恐懼或悲傷的情緒。有學生寫,“我從不覺得死亡是在剝奪生命,生命不是我們真正擁有的,我們從別處借了生命,總歸是要還的”;有人安慰在世的家人,“人間的你們再抬頭仰望星空,其實也在與我重見”。
我的童年是在湖南農村長大的。
人生第一次對死亡的認知,來源于很小的時候跟人出殯。這一幕一直像夢魘般銘記心中:下葬時將棺木往土坑里一放,再往上面圈土的時候,無名的恐懼感就燃起來了—人就躺在那里,萬世萬代永遠在那里了。
這樣的恐懼感一直延續到我長大、而立、衰老,教書時偶爾一激靈似的擊中我。所以生死學真是一個終身學習的課題。我也會告訴學生,擁有死亡恐懼與焦慮不意味著糟糕,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對死亡的感知,是人類才擁有的情感。
但這引出另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為什么我們都如此努力了,仍無法解除對死亡的恐懼?
城市生活和現代性是我歸因的一個主要角度。過去總說,中國的文化回避死亡,這是不對的。文化分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作為話語體系、國家主導層面,我們是回避死亡的。追溯源頭,可以到孔夫子與弟子的對話上。孔子在回答季路“如何侍奉鬼神”時說:“未知生,焉知死?”—生的問題還沒搞清楚,怎么能知道死呢?
但在民間層面上,受農業文明滋養的國人從不忌諱談論死亡。家庭里長輩過了60歲生日,就暗示自己的孩子,幫我準備一下。家里的孩子會找上好的木料,找木匠打成棺木,刷油漆,放在閑置的屋子里。老人家茶余飯后在田間地頭一轉,有時候就走到放自己棺材的老屋,忍不住往里面看幾眼。
這是很寧靜很美的畫面。
又比如節假日祭鬼拜神,我們老家以前吃飯的時候,會專門擺幾副碗筷,倒上酒,長輩念叨幾句:家里主事的有誰,“你們吃好喝好,拜托了”。送葬的時候,四五歲的小孩也在一旁見證死亡,比如騎棺,小孩子坐在棺材上。
傳統農村生活方式,生跟死非常和諧。但現代生活就從生產方式、生產力把死亡從生活掰開了。農村人以前一直是近距離地觀察、處理死亡。而現代人的死亡是把人押到醫院的臨終病房,尸體放在太平間。生病的人送醫院,家里的其他人該上班上班,得掙錢,得活命。
大家把疾病、死亡交由專業人員去處理,我們遠離了、也不了解病人的痛苦,生與死完全變成兩個世界。
再者,現代的大眾文化崇尚消費主義,傳遞的氛圍是健康的、青春的、活力的、美麗的。美容品、化妝品、保健用品的廣告,即便有老頭老太婆出現,也沒有一絲衰老的跡象,而是充滿生命活力。
衰老、死亡,所有這些非常負面的形象,在現代城市生活里像被掃進垃圾堆一樣,留下來的幻想是,人可以永遠青春靚麗、活力朝氣。
我很難說出自己如何克服了死亡焦慮。生死學的研究認為,越接近死亡,越能帶來真正的覺醒和生命觀的改觀,以致最后接受死亡,直面自己的死亡。
我人生有過一次危險的時刻。15年前的“五一”節后,我騎自行車去修電腦的途中,被一輛貨車撞倒,導致右肩鎖骨韌帶撕裂,鎖骨一端已挑起,右腦后開裂—所幸腦子未獲損傷。這樣的經歷讓我體驗到人生的無常,更能明白擁有生死智慧的重要性。
但直到現在,在現代話語體系上,生死學仍是禁忌。2000年我上報生死學的課程時,學院很快同意了。我過后才清楚,這樣的允許有多稀有。
很多教授告訴我,學校領導一聽到“生死教育”有關的字眼就皺眉反對。有的學者只能將它放在思政課下面,作為一個章節講。
2009年,我出版了《現代生死學導論》,作為國內第一本生死學教科書。那一年第一次有媒體采訪,我還接到電視臺的邀請上節目,但出場后才知道,另一個嘉賓是教爬樹的體育老師。我當時就明白,媒體只將生死學當噱頭,一個獵奇玩意兒。
沒等節目結束,我就走了。
我的教育有一個重要部分:祛魅化死亡后,我要告訴大家敬畏生命。
2019年起,廣州某區的殯儀館業務量減小,我就跟館長打了招呼,每學期帶學生參觀一次。學生首先參觀的是家屬與死者簡易的吊唁、告別儀式。這是生者與死者的對話,話語凝結著一個堅韌的結—念祖懷親,是各地喪葬習俗的重要一部分。
接著到火化車間參觀,了解一下不同價格的火化機器裝備,是如何讓人從有形到無形,最后灰飛煙滅的。
最后一部分是冷藏室。很多沒結案的刑事案件或者因故未及時處理的遺體,會被放進里面的抽屜,標著編號。殯儀館會按照標準,到操作間給這些遺體化妝。當人被裝進抽屜,變成真正意義上的物品以后,給人帶來的震撼無與倫比。
這些體驗勝過千言萬語。
我以前還會放一部日本的電影,是我在電腦城淘回來的,叫《生之樹》,講的是女人從懷孕、生產到孩童時期再到青年整個人生的過程。有一個女孩曾經跑過來和我說:“老師,我能不能拷這個電影回去,給我男朋友看?”
我感到欣慰。生死學回歸到最后,是處理人間親密關系和家庭倫理的切口。
很多哲學愛好者也喜歡選我的課,但十八九歲的孩子,對形而上學的內容思考得不夠。前幾天有學生問我,人死后的世界是否如同基督徒所說會上天堂,還是像佛教承諾的六道輪回?
我很難直接告訴他,無論哲學還是宗教,首要目的是消除個體的死亡焦慮和因為必死的結果造成的虛無。它們實際上都在為人生意義提供解釋,給人安身立命的歸屬,讓你別擔心別焦慮,回過頭來關照當下。
千禧年的前十年,我與80后的學生都在探討上述宏觀的、系統性的哲學理論。這群人在改革開放的時代出生,擁有獨屬于那個年代的集體意識,將生死與社會發展、國家命運聯系緊密。討論到最后,我們的課程主題會變成: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為社會做貢獻?
但這套方法面對95后、00后不奏效。我發現,新一代人更個性化,關心個體的命運與當下。我因此調整了課程設置,將一個個理論具化為情境,例如:如何面對親人的逝去?如果生命只剩下最后一公里了,如何選擇離去的方式?上呼吸機、搶救還是安寧療法、安樂死?給病人最好的告別是什么?
理解了生死以后,我其實不是一個樂觀的人。但我現在可以說,人生的座右銘是:時時可死,步步求生。
如果哪一天逝去了,我希望與一棵樹葬在一起,變成郁郁蔥蔥林子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