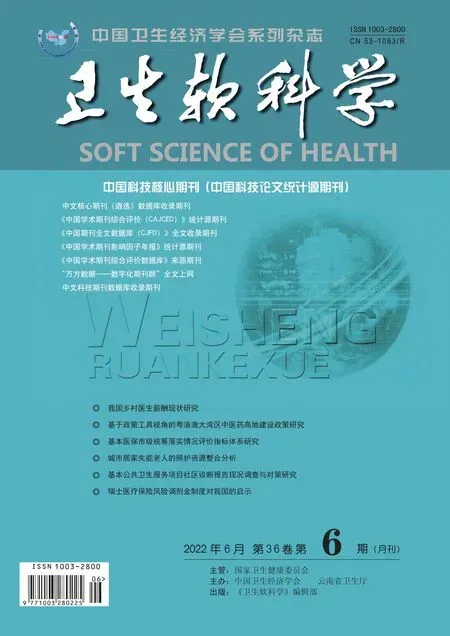我國兒科醫療資源配置與服務供給現狀及對策研究
史文欣,王曉東,劉 志,景麗偉,殷 璐
(1.淮安市第二人民醫院,江蘇 淮安 223002;2.青島大學附屬心血管病醫院,山東 青島 266071;3.國家衛生健康委衛生發展研究中心,北京 100044;4.首都醫科大學護理學院,北京 100054;5.南京醫科大學泰州臨床醫學院/泰州市人民醫院,江蘇 泰州 225300)
我國黨和政府一貫高度重視兒童醫療衛生服務,在兒科醫療服務體系、服務能力、隊伍建設等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政策及制度安排[1,2]。為緩解我國兒童醫療衛生服務資源短缺問題,2016年,國家衛計委、國家發改委等六部門聯合印發了《關于加強兒童醫療衛生服務改革與發展的意見》(國衛醫發〔2016〕21號)(以下簡稱《意見》),從總體要求和主要目標、加強兒科醫務人員培養和隊伍建設、完善兒童醫療衛生服務體系、推進兒童醫療衛生服務領域改革、防治結合提高服務質量等方面進行了明確。近年來,我國兒童健康核心指標持續改善,兒童衛生事業發展迅速[3]。在看到成績的同時,我國兒童醫療資源短缺、分布不均等問題依舊存在,且隨著2013年“單獨二孩”政策,2016年“全面兩孩”政策[4],2021年“三孩”等生育政策的實施和累積效應釋放,將使日益增長的兒童就醫需求與我國兒科資源短缺的矛盾更加突出。本文旨在全面了解2010-2020年我國醫療衛生機構的兒科資源配置和醫療服務能力發展和現狀,剖析我國兒科醫療資源發展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對策建議,從而為推動“十四五”期間我國兒童衛生健康事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決策參考[5]。
1 資料與方法
1.1 資料來源
數據來源于2011-2012年《中國衛生統計年鑒》、2013-2017年《中國衛生和計劃生育統計年鑒》、2018-2021年《中國衛生健康統計年鑒》中關于兒科資源配置與服務供給相關面板統計數據結果。
1.2 研究內容及方法
研究對象為兒科醫療資源配置和兒科醫療服務供給,選取的反映兒科醫療資源配置情況的指標主要包括:兒科執業(助理)醫師和兒科床位等。反映兒科醫療服務供給的指標包括:門急診人次、出院人數等。對相關指標進行縱向和橫向比較分析,縱向上采用動態數列分析2010-2020年各指標化情況;橫向上分析不同類型機構、不同專科、不同地域間的差異。采用絕對數、平均數、構成比、增長率、發展速度、年均增長速度等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我國兒科醫療資源配置情況
2.1.1 兒科執業(助理)醫師資源配置情況
2020年,我國兒科執業(助理)醫師總數達到16.34萬人,較2010年、2015年分別增長了4.76萬人和4.49萬人。從發展速度來看,2011年兒科醫師數有較大下滑,隨后呈逐年增加趨勢;從增長速度來看,2016年(7.69%)和2019年(9.86%)增長幅度最為明顯。2011年較2010年減少了1.97萬人;2014年和2020年兒科醫師數遞增均小于0.5(萬人/年),遞增速度分別為3.51%和3.12%;其余年份的兒科醫師數遞增均大于0.5(萬人/年),各年度遞增速度在5.05%~9.86%。10年間,全國醫療衛生機構兒科醫師數年平均發展速度為103.50%,年平均增長速度為3.50%。其中,“十三五”期間的平均增長速度為6.64%,遠高于“十二五”期間的0.46%。2020年底,我國每千名兒童執業(助理)醫師數達到0.64人,較2019年減少了0.03人。除此之外,2010-2019年每千名兒童擁有兒科醫師數呈逐年上升趨勢,2019年每千名兒童擁有兒科醫師數最多(0.67人)。10年間,每千名兒童擁有兒科醫師數年平均發展速度為102.14%,年平均增長速度為2.14%。其中,“十三五”期間的平均增長速度為4.24%,遠高于“十二五”期間的0.08%,見表1。

表1 全國醫療衛生機構2010-2020年兒科醫師數動態變化
2.1.2 兒科床位資源配置情況
2020年,我國醫療衛生機構兒科床位數為551,600張,較2010年、2015年分別增長了237,587張、87,002張;較2019年減少了8096張(1.45%)。從發展速度來看,除2020年以外,全國衛生機構2010-2019年的床位數每年均有增加,但發展不平衡。從增長速度來看,2011-2013年的增長幅度最為明顯,分別為8.76%、11.80%和8.49%。2016年和2019年床位數遞增均小于2.0(萬張/年),遞增速度分別為4.02%和3.40%;其余年份的床位數遞增均大于2.0(萬張/年),各年度遞增速度在4.72%~11.80%之間。2010-2019年,全國醫療衛生兒科機構床位數年平均發展速度為106.63%,年平均增長速度為6.63%。其中,2015-2019年的平均增長速度為4.77%,低于“十二五”期間兒科床位年均增長率(8.15%)。2010-2019年每千名兒童擁有兒科床位數呈逐年上升趨勢,2019年增長到頂峰的2.38張。2020年底,我國每千名兒童擁有兒科床位數回落到2.17張。
從兒科床位在基層和醫院間分布來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兒科床位數呈先增后降趨勢,2017年達到最多的101,133張,隨后又逐步下降到2020年的94,683張;占全部兒科床位數的比例由2010年的25.51%逐年下降到2020年的17.17%。醫院擁有的兒科床位數除2020年下降以外,其余各年份逐年增加,醫院兒科床位數占兒科床位比例始終維持在60%以上,到2019年增長至64.22%。2020年降為63.89%。
從醫院內的兒科床位數地域分布來看,東部地區各醫院擁有的兒科床位總數明顯多于中部或西部,但從近年來的趨勢來看,東部兒科床位總數占比呈逐年下降趨勢,中部和西部占比逐年提高,到2020年東、中、西部兒科床位數占比分別為38.51%、31.27%和30.22%,見表2。

表2 全國醫療衛生機構2010-2020年兒科床位數動態變化
2.2 我國兒科服務供給發展情況
2.2.1 兒科門診服務供給情況
2020年,我國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兒科門急診人次數發生大幅下滑,降為36,718.2萬人次,僅稍高于2010和2011年。其余年份,整體呈增長趨勢,2019年達到54,258.1萬人次,較2015年增長了6752.9萬人次(增長了14.22%)。2015-2019年兒科門急診人次數年均增長率為3.38%,低于“十二五”期間的7.54%。
從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和醫院間提供的門急診服務來看,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兒科門急診服務供給占比從2010年的23.88%逐年下降到2019年的17.74%,2020年又增長到20.48%;醫院提供的兒科門急診服務人次構成則從53.78%上升到2019年的61.41%,2020年降為56.26%。醫院和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提供的兒科門急診服務的絕對數量差距呈擴大趨勢。
從醫院提供的兒科門急診人次地域分布來看,東部地區一直占據一半以上,中部和西部各占1/4左右,東部服務量占比逐年下降趨勢,中部和西部占比則逐年提高,到2020年東、中、西部分別為48.62%、24.48%和26.90%,見表3。

表3 醫療衛生機構兒科門急診人次及構成 單位:萬人次
2.2.2 兒科住院服務供給情況
2020年,我國各類醫療衛生機構兒科出院人數同樣發生大幅下滑,降為1690.5萬人,僅稍高于2010年和2011年。其余年份,整體呈增長趨勢,2019年,我國兒科出院人數為2443.1萬人,較2015年增加了382.1萬人,增長了18.54%。2015-2019年兒科出院人數年均增長率為4.34%,低于“十二五”期間的6.95%。兒科出院人數占比,從2015年的9.84%下降到2019年的9.22%,兒科住院服務供給占比低于其他住院專科。
從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和醫院間提供的住院服務來看,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兒科住院服務供給占比從2010年的21.01%逐年下降到2019年的11.92%,2020年又增長到13.36%,接近2017年的水平;醫院的兒科出院人次數構成從2010年64.96%上升到2019年的71.25%,2020年降為68.02%,接近2013年水平。醫院和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提供的兒科門急診服務的絕對數量差距呈擴大趨勢。
從醫院提供的兒科出院人數地域分布來看,東部地區占比較大,從2010年的42.62%降到2020年的35.41%;中部維持在31%上下波動,2020年為30.98%;西部地區占比有較大提升,從2010年的26.85%上升到2020年的33.61%,占比首次超過中部。總體來看,東、中、西部醫院內兒科出院人數趨于日漸均衡,見表4。

表4 各醫療衛生機構兒科出院人數及構成 單位:萬人
2.3 我國兒科醫師工作負荷變動情況
2020年,我國兒科醫師人均每日擔負診療人次為8.95人次,降到2010年以來的最低值。我國兒科醫師的工作負荷壓力整體上呈先增后降趨勢。醫師人均每日擔負診療人次從2010年的11.36人,逐年增長到2014年的16.41人,隨后呈波動下降趨勢,到2019年下降到13.64人。兒科醫師人均每年擔負出院人次呈現同樣變化趨勢,2014年到達最高的183.61人,2019年逐漸降到154.14人,2020年降到最低為103.46人。總體來看,“十三五”期間兒科醫師的工作負荷要小于“十二五”期間。
2010-2020年,各年度兒科醫師的工作負荷均遠大于全體醫師、內科、外科、婦產科。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各科醫師的診療工作負荷都大幅下降。為此選擇2019年的數據做橫向比較。2019年,兒科醫師人均每日擔負診療人次分別是全體醫師、內科、外科、婦產科的2.19倍、2.20倍、3.34倍和2.11倍。兒科醫師人均每年擔負出院人次分別是其他科的2.25倍、1.71倍、1.61倍和1.87倍,見表5。

表5 主要分科醫師工作負荷變化情況
3 討論
3.1 我國兒科醫療資源量質、布局有待進一步加快發展和補足
3.1.1 兒科醫師總量增速較快,但與實際需求仍存較大缺口
我國兒科醫師數近10年來呈逐年增長趨勢,且“十三五”期間增長速度遠大于“十二五”期間。“十二五”期間我國兒科醫師數量增速不大的主要原因可能有兩方面[6]:一是兒科醫師的工作壓力大、風險大、待遇低、執業環境不佳、兒科糾紛多等導致兒科崗位吸引力弱和流失性大;二是1998年,教育部取消了兒科學專業,只能通過研究生教育以及專科醫師培訓項目,造成培養機制缺失[7],即便后來恢復兒科專業,鑒于兒科培養的周期較長,形成了兒科人才供應較長的真空期[8],整個“十二五”期間僅增加了不足2700名兒科醫師。針對兒科醫師短缺,“十三五”期間,我國政府高度重視兒科醫師隊伍建設,2016年印發了《意見》,并采取了加大兒科本科、研究生教育,加強兒科專業住院醫師規范化培訓,大力開展兒科專業繼續醫學教育,不斷完善學生資助政策體系,推進農村訂單定向醫學生免費培養,提高兒科醫師的薪酬待遇,將兒科醫師占比納入三級公立醫院績效考核等一系列措施,對于推動我國兒科隊伍發展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整體來看,2010-2020年,我國兒科醫師數增長幅度為41.11%、年平均增長速度為3.50%,均遠超0~14歲兒童的增長幅度(14.16%)和平均增長速度(1.33%)。但鑒于兒科醫師的底數不足,導致兒科醫師目前的總量仍存在較大缺口。2020年,我國兒科執業(助理)醫師占各科執業(助理)醫師總數的4.1%,遠低于0~14歲兒童占總人口的18.0%。2020年底,我國每千名兒童兒科執業(助理)醫師數為0.64名,未能夠實現《意見》提出的0.69名的目標,兒科醫師缺口近1.3萬。按國際上每千名兒童擁有1名兒科醫師的配置標準[9],我國兒科醫師的缺口近10萬。隨著我國生育政策的放寬和深化落實,兒童出生率和占比也會相應提高,這將對本來就緊缺的兒科醫師數量帶來更為嚴峻的挑戰。
3.1.2 兒科床位總量有一定幅度增長,但總量不足與區域分布不均的問題仍然存在
2010-2020年,我國兒科床位數的增長速度同樣高于兒童的增長速度。但“十三五”期間增長速度均要明顯低于“十二五”期間。“十三五”期間的床位增長絕對數量為87,002張、增長幅度為18.73%、年均增長速度為5.80%;而“十二五”期間分別為150,585張、4.05%和8.15%。此外,“十三五”期間,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機構的兒科床位數在數量和占比上都有所萎縮,醫院的兒科床位數則是穩步增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城鄉之間的兒科資源差距在擴大。從東、中、西部醫院兒科床位數分布來看,中、西部與東部的差距正在逐步減小。
我國在2017年每千名兒童兒科床位數已達到2.24張,提前實現了《意見》提出的2020年達到2.2張的目標。但我國兒科床位資源總量與實際需求仍存在不小的差距。2020年,我國醫療衛生機構兒科床位數僅占總床位數的6.06%,與兒童人口占比來看,嚴重不協調;同時,也小于醫療衛生機構兒科出院人數占總出院人數的比例(7.36%),均提示我國兒科床位資源相對短缺。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我國兒科床位數未延續以往逐年增加的趨勢,發生大幅下降,減少了8千余張床位。在我國兒科床位總數嚴重不足的情況下,亟需對造成下滑的原因進行深入剖析。同時,基層兒科床位數的持續萎縮,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基層兒科資源并沒有得到很好的發展,不利于形成兒科診療下沉和分級診療目的的實現。此外,東部地區的醫院內兒科床位數依然占比較大,區域間的兒科資源配置公平性有待進一步改善。
3.2 我國兒科醫療服務供給韌性和結構有待進一步優化
整體來看,我國兒童醫療服務供給呈逐年增長趨勢,兒童醫療服務需求得到較好的釋放。受新冠疫情的影響,2020年兒科門急診和住院服務發生大幅度下滑。通過2015-2019年的平均增長速度來分別推算,正常狀態下,2020年兒科門急診服務和出院人次數分別為56,092.0萬人次、2549.1萬人次,即可能由于新冠疫情造成服務損失量分別為1373.8萬人次和858.6萬人次。以上提示:一是兒科醫療服務需求整體上是呈逐年上漲的,但兒科醫療服務體系在疫情狀態下具有一定的脆弱性,部分兒科停診、限流等導致一部分兒科醫療需求沒有被滿足;二是此前的兒科醫療服務需求可能存在一定的過度醫療情況,部分非必須診療服務行為受疫情影響被壓縮。
從不同層級醫療機構的服務供給來看,我國主要是以醫院提供的兒科服務為主。這與國際上多數發達國家兒科擁有層次清晰的分級診療程序,大多數兒科患兒的診療服務在基層解決存在一定的不同。我國兒科門急診服務和住院服務的絕對數量在醫院和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之間的差距呈逐漸擴大趨勢。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承擔的兒科門急診服務量的絕對數量有所增長,但在整個兒科門急診服務供給的占比在逐年下降;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兒科住院服務供給絕對數量和占比均在下降。究其原因,可能與基層兒科服務能力較低,兒童家長對其信任度較低等造成。以上分析表明,我國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兒科服務供給在萎縮,我國兒科分級診療體系尚未有效建立,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的服務能力建設也在弱化。可能存在幾方面原因:一是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對于兒科專業人才的吸引力不足,基層兒科人才十分缺乏;二是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著力推動全科醫師制度的,對兒科專業不夠重視,部分兒科診療服務由全科醫師提供,造成兒科診療量分流;三是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實施基本藥物目錄,造成兒科用藥范圍狹窄、限制了兒科服務的提供,導致基層醫療衛生服務機構兒科服務能力逐步降低。提示基層的兒科診療服務發展速度慢于醫院兒科的發展,基層兒科服務能力有待進一步提升。
從東、中、西部的兒科服務供給來看,整體上東部提供的服務量最大,中、西部近年來的服務占比在緩慢上升。兒科門急診服務東部占據半壁江山,兒科住院服務東部也是一家獨大。服務供給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資源配置不均衡、服務能力存在差異等問題,需進一步優化資源配置和加強能力建設,促進東、中、西部均衡發展。
3.3 我國兒科醫師的超負荷工作有待進一步緩解
“十三五”期間,我國兒科醫師的工作壓力整體呈現減輕趨勢,到2019年已減輕至“十二五”初期水平,這與兒科醫師數量的增長有著密切關系。盡管從時間跨度來看,兒科醫師承擔的門急診和住院服務人次都在大幅下降,但仍遠遠超出同期的全體醫師、內科、外科、婦產科等。即使在2020年的疫情狀態下,兒科醫師的工作負荷也比大部分醫師的壓力要高。同時,兒童專科醫院醫師的工作負擔在各類醫院中最重。以2019年的兒童醫院為例,醫師日均擔負診療人次為13.6人次,在各類醫院中位列第二位,僅次于專科醫院中麻風病醫院的13.7人次,遠超綜合醫院;兒童醫院的病床使用率為94.12%,同樣在各類醫院中位列第二位,僅次于專科醫院中腫瘤醫院的106.07%。以上均反映出,我國兒科醫師的工作負荷仍十分巨大。而造成兒科醫師工作負荷過大的主要原因為兒科資源總量與兒科醫療需求之間存在較大缺口。
隨著“三孩”生育等政策的實施和累積效應釋放,兒科醫師的工作負荷可能會發生反彈。值得大家注意的是,兒科醫師長期的高負荷運轉,將不利于兒科醫療服務體系的高質量發展。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一是超負荷運轉不僅會增加兒科醫務人員的工作壓力,增大兒科醫患糾紛的風險;二是影響兒科醫務人員工作的積極性,導致兒科專業技術人員的流失[10];三是影響兒科實習醫師帶教和住院醫師的規范化培養[11]。從長遠來看,可能會降低學生報考兒科專業的熱情和從事兒科工作的積極性。進一步加劇兒科醫療服務資源的不足。
4 建議
4.1 加大兒科資源投入與優化資源布局需協同并進
應進一步開展專題調查研究,明確我國兒科資源的配置情況以及需求缺口,結合我國兒童人口數量發展趨勢和健康需求變化,科學測算未來兒科資源配置總量,加大相關兒科資源的投入[12]。各地區結合實際需求,提高兒科資源配置在地域間、省域內、城鄉間的公平性。通過醫療集團、兒科專科聯盟建設等,建立促進分工協作的長效激勵機制,推動高水平醫療資源向基層延伸。
4.2 加強基層兒科服務能力和服務水平建設
遴選和研究開發一批適宜基層使用的兒科常見病多發病診療適宜技術,并在基層進行推廣和規范應用[13]。進一步加強基層醫務人員兒科專項培訓,提高兒童常見病、多發病防治以及危急重患兒的識別、轉診和救治能力,將大部分兒科診療留在基層,提升患兒家屬對基層的信任度。通過提高基層醫療衛生機構報銷比例等醫保手段,合理引導兒科分級診療,分散就醫壓力。
4.3 加快兒科人才隊伍建設
提前布局兒科人才發展計劃,科學設定醫師規模、人才結構和人員配置等目標,將減輕兒科醫師工作負荷納入規劃的重點任務之一。改進兒科醫學人才教育機制[14],推動兒科學科的發展,在學科建設、學生招錄、兒科科研等方面予以一定的政策支持和傾斜;鼓勵高水平的醫學院校擴大兒科醫學碩士、博士研究生的招生規模,探索在有條件的醫學院校設置本科兒科學、中醫兒科學專業,加大兒科人才供給。注重醫務人員內部的能力提升和人才培養,通過擴大規培、轉崗培訓、繼續教育等方式,有針對性地提高在崗兒科醫務人員的業務能力。
4.4 完善兒科醫師績效考核與薪酬制度
加快兒科醫師薪酬制度改革[15],探索建立以服務數量、質量和滿意度等為主要指標的績效考核機制,適當提高兒科醫生的待遇;在一定程度上給予兒科醫師職稱晉升、職務提拔的政策傾斜,進一步提升兒科崗位吸引力和隊伍穩定性。
4.5 借助新興技術手段提升兒科資源利用效率
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背景下,“互聯網+醫療”在兒科醫療服務提供中已經發揮出了很顯著的效果。可充分借助互聯網+、遠程醫療等新興技術手段,提高兒科資源的整合性、可及性、高效性,進而緩解資源總量不足和配置不均等問題[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