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述故事,就是闡釋生存
俞耕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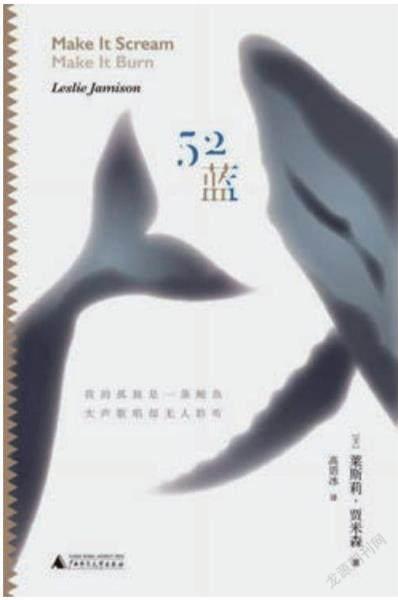
“我們講故事,解釋自己為何孤獨,或是被什么糾纏不清,而這些不復存在的故事可以像我們現今正在經歷的一切一樣,完整地定義我們。”作家萊斯莉·賈米森這樣寫道。她將講述作為理解自我的方法,而故事大多對應“過去的”與“他人的”。其非虛構文集,如《十一種心碎》《在威士忌和墨水的洋流》都在講述各色人物的心靈故事。《52藍》也延續這種散文紀實,圍繞著渴望、孤獨以及由之而來的沉迷。
“52藍”其實是一只能發出52赫茲的藍鯨,它完全超出同類的正常發聲頻率。這使它成為太平洋上獨自徜徉的高音吟唱者。獨特帶來的代價——孤獨,它意味著喪失情感聯結和認同慰藉。鯨魚的發聲除了辨識方向,尋找食物外,還有交流與擇偶的需求。“他們從未發現他身邊有任何同伴這一事實。他似乎永遠形單影只。這條鯨魚高聲呼喊著,卻似乎沒有任何呼喊對象——至少可以說,似乎沒有得到任何回應。”
作家用一個“男性的他”指代52藍,別有深意,這比附到當代人類精神困境之上。讓人想到巴別塔隱喻,永遠無法訴求于理解、回應與共情。即使一位男士結婚又如何?依舊無法避免個體孤獨,情感的同頻共振大多只是理想。某種角度看,我們或許和52藍一樣,都是僅有的孤種,自說自話。這個故事的另一半是48歲患病的未婚女性,病情使她從獨立變為孤立。莉奧諾拉感到被世界切除了,和藍鯨一樣無法訴諸他人的語言。
搜尋這條鯨魚也成了一種精神感召,越來越多的人群,都對52藍的遭遇,感同身受。其中蘊藏著心碎痛苦,希望失落和感傷猜想。跨物種的移情比附,恰好說明人類有共通的心靈掙扎:如戀情結束后的寂寞,丈夫與妻子的零交流……“大自然一直都將自己作為人類投影的屏幕。浪漫主義稱其為擬人謬化……我們將自己的恐懼和渴望投射到一切非我上——每一只野獸,每一座山。正因如此,我們似乎與它們親近了。這種行為同時結合了卑微、渴望和斷言一切。”
在愛默生看來,這就是自然的心靈,它對應一種人類邏輯和自我凝視的賦予。就像美國廣泛流傳的“都市傳說”,總是靠添油加醋的描述與移置,變成想象性的流傳與再闡釋。換言之,我們看到的并非52藍的蹤跡,而是自己的心跡,只不過借用自然界的物種來譬喻。這從深層說明,聆聽與發聲只是一廂情愿。我想作家強調了這個故事的“生育學象征”,其本質是單性不育,或是自我受孕。自然界的事實本身沒有價值,“且是不育的,就像單性”,“言下之意是人類的投射實際上令卵子受精”。這就和52藍無法擇偶的處境一樣。莉奧諾拉與藍鯨的情感聯結,在于悖謬的合一:喪失交流造成的獨立性。
這個故事本質在講我們賴以生存的隱喻。“隱喻永遠在連接兩個迥然不同的點;它意味著不存在孤立于他人的疾苦,不存在單獨存在的困境。孤單尋求隱喻,為的不僅僅是得到定義。”換言之,隱喻本身作為孤單的慰藉,象征性地解決了失語痛苦,渴望他人回應的需求。它意味著理解即闡釋,闡釋即生存。這正是文學治愈的功能。書中另一個轉世故事,就印證了自我與他人的互換,重生與共有。它同樣也尋求自我解釋的安慰:“把我的窘境看作是許多人所共有的。”轉世,保護了情感聯結的需求,它是綿延不滅,可以轉換的信念。從而,“我們給自己講故事,是為了活下去”,或是為了再活一遍。
此書以蔬菜名稱解讀為切入點,詳解二百七十余種中國蔬菜,并配以精美手繪科普圖。全書分為“綜述”和“各論”,“綜述”概述我國蔬菜名稱構成、命名緣由及構詞手段等,“各論”則分門別類地對各種蔬菜的所屬類別、起源地域、引入時間、栽培歷史、供應現狀、名稱由來、命名因素、營養成分、食用方法等內容進行詳細的考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