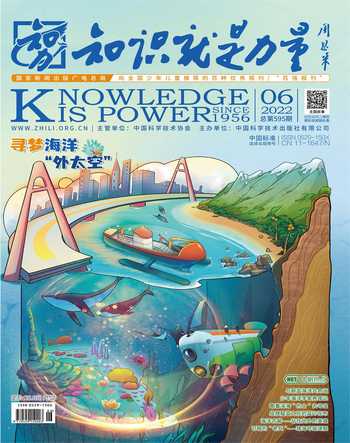生命奇跡中蘊含的危機
劉健

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烽火還在全球蔓延,各國頂尖的物理學家都在為釋放出被禁錮在原子內部的巨大能量而傾盡全力,奧地利物理學家埃爾溫·薛定諤卻因“一只貓”而聞名于世。
薛定諤在這一年出版了一本用物理學來解釋生命現象的書——《生命是什么》。書中,通過熱力學和力學理論來解釋生命的本質,引入非周期性晶體、負熵、遺傳密碼、躍遷式突變等概念,來說明有機體物質結構、生命的維持和延續、遺傳和變異等現象。最終,薛定諤指出,生命的特征在于“密碼本”,這個“密碼本”不但可以指導細胞組織的遺傳,還能讓有機體擺脫熱力學第二定律。
當戰爭的硝煙散去,薛定諤的這些思想指引眾多新銳科學家們走進了一座名為“分子生物學”的嶄新科學大廈。而攀登這座大廈的階梯就是薛定諤所說的“密碼本”。
1953年,美國分子生物學家沃森和英國生物學家克里克用一篇簡短的論文,描述了脫氧核糖核酸(DNA)的雙螺旋結構,人類就此翻開這本生命之書。

早在1896年,英國作家赫伯特·喬治·威爾斯出版了長篇科幻小說《莫羅博士島》。小說中,莫羅博士是一位醉心于研究生物進化的科學怪人。他在大洋深處的小島上定居,用各種外科手術將野獸轉變為“獸人”,還通過聲帶手術讓它們獲得使用語言的能力。但是,這些“獸人”身上的野性仍然無法從根本去除。于是,莫羅博士制定了“走路時不準手腳齊用”“不許吃肉吃魚”,以及“破壞法律的人是逃不掉懲罰的”等規則,來約束“獸人”
的行為,并親手處決那些違反規則的“獸人”。但最終,在追捕一只美洲豹“獸人”的過程中,莫羅博士與“獸人”雙雙斃命,島上靠莫羅博士維持的“秩序”迅速崩塌,其他“獸人”重新退回原始的生活方式。威爾斯通過小說中離奇的情節,展現了對科學發展與社會變革的雙重隱喻,引發了人們對于科技倫理的深入思考。
在小說《莫羅博士島》發表百年之際,1996年,美國好萊塢將其改編為電影《攔截人魔島》。影片在高度還原小說原著的同時,加入了最新的基因科學設定。馬龍·白蘭度飾演的莫羅博士試圖用經過精確編輯的完美基因去替代導致“惡”的獸性基因,從而制造出完美的“獸人”。但這種嘗試最終仍然以悲劇告終。
莫羅博士無法通過基因改造創造完美的“人”,而對基因的篩選和評價也可能讓我們的社會面目全非。1997年上映的科幻電影《變種異煞》就講述了這樣一個在“基因決定論”的社會背景下掙扎求生的小人物的故事。影片中,人類在胚胎階段就要經過基因診斷和修正,只有通過這種基因工程篩選和加工出生的人才是正常人,否則被視為“病人”。電影的主人公文森特·費曼就是所謂的“病人”。但文森特夢想成為一名宇航員,他用因事故導致癱瘓的正常人杰羅姆·莫諾的血樣和尿樣騙過了基因檢測,在經歷了各種磨難后,“病人”文森特終于以一名宇航員的身份飛上浩瀚的太空。
影片中所反映的基因歧視,也正是當代科技倫理學研究的前沿課題。從科學的角度來說,分子生物學發展到今天,不過是幾十年而已,與自然歷史數十億年的生物進化相比,不過是滄海一粟。基因對人類生理、心理與社會發展的研究,依然處在初級階段。更何況對于生命整體這樣一個復雜系統來說,我們的認識更是非常有限。因此,謹慎地使用基因技術,嚴謹地求證生命存在之理才是人類應該有的科學態度。

本期刊登的兩篇作品分別是中國科幻作家王晉康的《生命之歌》和潘蓁源同學的《鯨落萬物生》。其中,《生命之歌》是王晉康的代表作,也是中國當代科幻的經典作品,可以說是中國古籍《列子·湯問》中記載的《偃師造人》故事的當代版本,體現了作者對于科技發展與生命本質的哲學思考。而《鯨落萬物生》則是以現實生態環境中的“鯨落”現象為原型,構思出了“地球生物圈神經元網絡”這一前沿的科幻構想,文筆悠揚,頗為耐讀。
人類本質上是一種既平凡又獨特的生物,說人類平凡是因為我們與現今存活于世間的萬千生靈一樣,都是幾十億年地球生物演化的產物。而說我們獨特是因為在已知的萬千生靈中,我們是唯一嘗試理解我們所生存的這個宇宙,同時也在孜孜不倦地探索我們自身生命本源的物種。這種探索精神與理性,使人類在一次又一次的危機中浴火重生。因而,只有當我們真正意識到那份生命的“密碼本”中不僅有名譽與財富,同時也潛藏著各種意料之外的陷阱時,我們才能在不斷深入破解密碼的過程中保持應有的敬畏和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