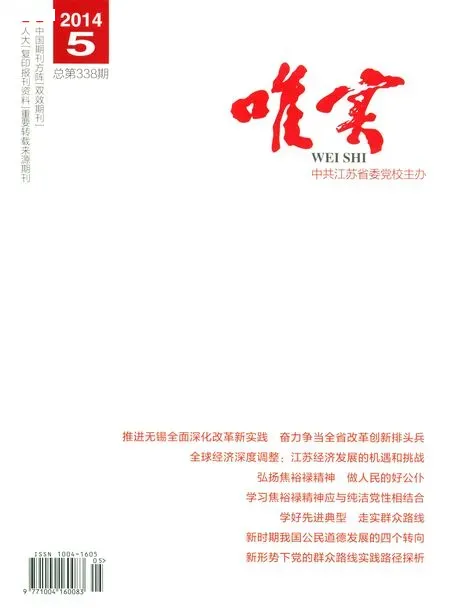江蘇人口變化對潛在經濟增長的影響
戚晶晶 周莉雅



經濟增長長期看供給,潛在經濟增長率由供給要素的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所決定。供給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和資本。人口是重要的供給要素,自2012年以來,江蘇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比重持續下降。若發生趨勢性變化,將影響江蘇經濟未來走勢,導致江蘇潛在經濟增長率進一步降低,進而引起實際經濟增長率下降。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七人普”)和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以下簡稱“六人普”)數據,江蘇人口增量608.8萬人,位居全國第三,與沿海發達省份相比,江蘇人口形勢面臨兩大挑戰:一是人口吸引力相對較弱。與浙粵相比,江蘇人口增量和增速存在較大差距。二是人口結構老化。江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浙江和廣東不減反增。江蘇應通過優化環境,吸引外來人口,以在短期內增加人口規模、改善人口結構,并通過深度開發人力資本,有效減緩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下降速度。
一、“七人普”數據顯示:
江蘇人口要素面臨新的挑戰
江蘇人口吸引力相對較弱。從省級人口增長看,2020年江蘇常住人口8474.8萬人,與“六人普”相比,常住人口增加608.8萬人,年均增長0.75%;同期浙江人口增加1014.1萬人,年均增長1.72%,高于江蘇0.97個百分點;廣東人口增加2170.9萬人,年均增長1.91%,高于江蘇1.16個百分點(見表1)。江蘇全省人口增量不及深圳一市人口增量(713.7萬人)。從主要城市人口增長看,分別選取三省人口增量排前五的城市,并按人口增量由大到小排序:蘇州(228.2萬人)位列第5,與前三名的深圳(713.7萬人)、廣州(597.6萬人)、杭州(323.3萬人)存在差距,甚至不及佛山(230.5萬人);南京(131.0萬人)位列第10,落后于東莞(224.6萬人)、寧波(180.1萬人)、金華(169.0萬人)和惠州(144.6萬人);無錫(109.0萬人)、常州(68.6萬人)、徐州(50.3萬人)各居第11、13和15位(見圖1)。同在長三角地區,江蘇城市對人口集聚效應弱于浙江。一方面,人口正增長城市數量少于浙江。10年間,江蘇10個地市人口實現正增長,3個地市人口負增長,鹽城、淮安和泰州的常住人口分別減少55.1萬人、24.4萬人、10.6萬人;同期浙江11個地市全部實現人口正增長。另一方面,核心城市人口增量小于浙江。江蘇和浙江各有3個地市人口增量超百萬,杭州以增加323.3萬人領先,蘇州以增加228.2萬人緊隨其后;南京增加131.0萬人,無錫增加109.0萬人,與寧波(180.1萬人)存在差距,甚至不及金華(169.0萬人)。作為浙江的核心城市,杭州和寧波吸引外來人口規模在“十三五”期間突飛猛進,杭州2019年人口增量高達55.4萬人,超越深圳位居全國第一,同年寧波人口增量達到34.0萬人(見圖2)。
江蘇人口年齡結構老化。從年齡人口看,10年間,江蘇勞動年齡人口減少250.0萬人,浙江、廣東卻呈增長態勢,勞動年齡人口分別增加413.6萬人、1014.9萬人。10年來,浙江和廣東的人口變動量以勞動年齡人口為主,而江蘇人口變動量以老年人口為主,老年人口增加593.1萬人。2020年江蘇勞動年齡人口5334.9萬人,比重63.0%;浙江勞動年齡人口雖比江蘇少953.3萬人,但比重高出4.9個百分點;廣東比江蘇多3334.8萬人,且比重高出5.9個百分點(見表2)。從老齡化水平看,2020年江蘇人口老齡化水平21.8%,在31個省市區中排第6。浙江人口老齡化水平18.7%,在全國排第18。廣東未來的發展優勢凸顯,是“人口吸引力最強”與“中國最年輕”的東部大省。2020年廣東人口老齡化水平僅12.4%,低于全國6.4個百分點,在全國排第28,僅高于青海、新疆和西藏。從人口撫養比看,2020年江蘇傳統人口紅利衰減,進入人口負擔期,人口撫養比高達58.9%,分別高于浙江和廣東11.5個、13.5個百分點,浙粵仍處于人口紅利期。10年間,江蘇人口撫養比上升18.0個百分點,浙江(上升10.2%)和廣東(上升9.1%)的增長速度更慢。由于人口撫養比由0—14歲少兒人口、60歲以上老年人口兩部分構成,前者是對未來生產力的投資,后者主要是消費人口,故需分析人口撫養比結構。江蘇老年撫養比在2017年首次超過少兒撫養比,2020年分別為34.7%和24.2%,廣東則以少兒撫養比為主,未來仍將成為“人口紅利最大贏家”(見圖3)。
二、人口形勢將帶來潛在經濟增長率
進一步下降風險
人口要素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作用路徑。經濟增長短期看“需求”,長期看“供給”。一個經濟體長期的經濟增長潛力取決于潛在經濟增長率。潛在經濟增長率是指,經濟增長所需的所有供給要素被充分利用的條件下,一個國家或地區能夠實現的經濟增長速度。根據生產函數法,潛在經濟增長率由供給要素的增長率和全要素生產率(TFP)所決定,供給要素主要包括勞動力和資本。如果供給要素發生了趨勢性變化,將直接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率,進而在長期使實際經濟增長率受到影響。人口要素主要通過三個路徑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率:第一,潛在就業。一方面,勞動年齡人口規模減小將導致潛在就業量減少,當其他因素不變時,將引起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另一方面,勞動參與率和自然失業率是人口年齡結構的函數,勞動參與率和自然失業率的變化會引起潛在就業的變化,最終影響潛在經濟增長率。第二,資本存量。人口撫養比的上升將引起儲蓄率下降,資本形成率降低,進而導致資本存量下降。第三,人力資本。勞動年齡人口素質是影響人力資本的關鍵變量。
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帶來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風險。在國家層面,由于人口要素面臨趨勢性變化,在其他變量未發生顯著變化的情況下,中國未來的潛在經濟增長會繼續下降,調整人口生育政策能使潛在經濟增長率的遞減程度有所減緩。在省級層面,依靠外來人口流入,提升本省勞動年齡人口供給,從而增加人口規模并改善人口結構。浙江、廣東通過外來人口流入,顯著改善人口要素,在其他變量未發生顯著變化的前提下,實現潛在經濟增長率上升,從而減緩了GDP增速過快下降勢頭。江蘇對外來人口吸引不足,10年間勞動年齡人口增量為負值,導致潛在經濟增長率下降,GDP增速下降幅度相對更大。根據“七人普”和“六人普”數據,2020年江蘇勞動年齡人口比2010年減少250.0萬人,若其他因素不變,根據測算,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下降導致2020年潛在經濟增長率較2010年下降0.6個百分點。改善江蘇吸引外來勞動年齡人口狀況:一方面,若10年間江蘇勞動年齡人口以浙江的增量水平增長,則需從省外多吸引663.6萬勞動年齡人口,全省老齡化水平將下降至20.3%(下降1.5個百分點),人口撫養比將下降至52.3%(下降6.6個百分點);由此,在其他供給要素不變的條件下,江蘇潛在經濟增長率可以較2010年提升1.0個百分點。另一方面,若10年間江蘇勞動年齡人口以浙江的增速水平增長,則需從省外多吸引832.2萬勞動年齡人口,全省老齡化水平將下降至19.9%(下降1.9個百分點),人口撫養比將下降至50.9%(下降8.0個百分點);由此,在其他供給要素不變的條件下,江蘇潛在增長率可以較2010年提升1.4個百分點。對“十四五”期間,江蘇全省勞動年齡人口變動對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影響初步測算。方案一:如果未來五年勞動年齡人口維持2010—2020年間的年均下降速度,規模將減少120.8萬人,2025年將降至5214.1萬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預計2025年潛在經濟增長率較2020年下降0.3個百分點。方案二:如果未來五年勞動年齡人口規模維持不變,2025年為5334.9萬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預計潛在經濟增長率保持不變。方案三:如果未來五年補齊2010—2020年間的勞動年齡人口減少量,即規模增加250萬人,2025年將升至5584.9萬人;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條件下,預計2025年潛在經濟增長率較2020年上升0.6個百分點。BE1A7AD5-28DF-4BAE-8F77-B9897E061276
三、應對人口變化對江蘇潛在經濟增長率的對策
江蘇對省際人口的集聚能力,包括“引得來”與“留得下”兩方面。從“引得來”分析,產業結構、就業機會、收入水平、城市能級等是影響省際人口流入目的地選擇的重要因素。從“留得下”分析,除了經濟因素之外,居住條件、公共服務、戶籍可獲得性等是影響流動人口居留本地的重要因素。江蘇可以創造更好的環境以吸引更多的省際人口“流入”并且“留下”,發揮人口要素對經濟增長的支撐作用。
推動更充分更高質量就業。以產業轉型升級創造優質就業機會,找準數字經濟、互聯網經濟與江蘇實體經濟的結合點,推動生產性服務業向專業化和價值鏈高端延伸,推動生活性服務業向高品質和多樣化升級,拓展行業邊界以催生新就業崗位。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完善促進創業帶動就業、多渠道靈活就業的保障制度。健全統一規范的人力資源市場體系,營造公平的就業環境。
實現高質量公共服務均衡供給。關注新市民和農業轉移人口,更高水平推動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聚焦人民群眾急難愁盼的民生問題,圍繞公共服務供需結構性矛盾突出領域,促進教育、醫療、托育、養老等領域提供價格可負擔、質量有保障的普惠性非基本公共服務,并順應消費升級和產業升級趨勢,做大做優健康、養老、文化、旅游和家政等生活性服務業。推進居住證制度覆蓋全部未落戶城鎮常住人口,不斷擴大居住證的基本公共服務“含金量”。
提高人民收入水平。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全要素生產率,支持企業通過提質增效拓展從業人員增收空間。優化分配格局,合理提高勞動報酬及其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完善創新要素參與分配機制,保障知識、技術、數據、管理等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拓寬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探索通過土地、資本等要素使用權、收益權增加居民要素收入。
降低人民居住成本。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完善住房市場體系和住房保障體系。南京、蘇州可探索閑置的工業、商服用地轉化為住宅用地,增加建設用地供應,適度放松容積率管治,在有限的土地上提供更多的住房。土地供應向租賃住房建設傾斜,擴大保障性住房供給,加快完善長租房政策,探索租購同權。落實租房補貼、住房補貼等政策。
建設人口友好型城市。南京、蘇州優化差別化積分落戶制度,放寬落戶限制,加快長期穩定居住和就業人群的落戶進程。探索在城市群之間建立社保繳納年限和居住年限累計互認。進一步提升中心城市功能品質,增強區域集聚輻射能力、人口承載能力。推動各地建設人口友好型城市,創建最佳就業創業環境、最優宜居生活環境。注重多渠道多方式宣傳,增強城市知名度,發揮中心城市的品牌效應。
(作者系江蘇省戰略與發展研究中心社會發展研究所高級經濟師)
責任編輯:戴群英BE1A7AD5-28DF-4BAE-8F77-B9897E0612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