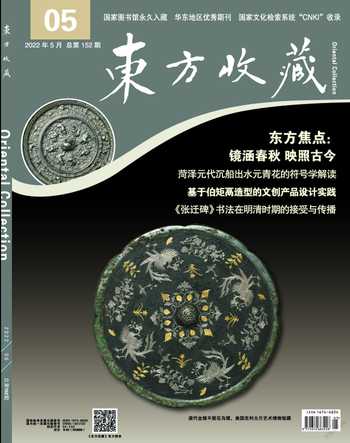略論金文月份合文與西周置閏問題
摘要:通過考證寓鼎以及盠駒尊的銘文可以判定,? ?的準確釋義應為“三月”,因此西周銅器“十又? ?”? ?應釋為“十又三月”。 所以,西周時期存在“年終置閏法”。由于周歷仍是觀象歷,月建擺動較大,缺少實行“年中置閏法”的條件,可以確定,西周時期不存在年中置閏的現象。
關鍵詞:置閏法;合文;金文
將數字與“月”字合寫用以表示月份,是西周銅器銘文的常見現象。前人對月份合文“? ? ? ?”的釋讀形成了兩種觀點:一種是“二月”,另一種是“三月”。但是由于含此銘文的銅器缺少確切紀年,又因銘文內容缺少傳世文獻印證,以及現有西周歷譜主觀性較大,因此合文的釋義問題仍有進一步論證的空間。筆者總結前人對夏商周三代歷法以及銘文的研究,以對此問題作進一步的探討,并且通過對上述兩個問題的研究,討論西周時期的置閏法。
一、? ? 應釋讀為“三月”
“? ? ?”的釋讀問題源于對寓鼎(《集成》02718,西周早期)的考釋,現將寓鼎銘文釋文如下:
隹(唯)十又? ? ? 丁丑,寓獻佩于王姤(后),易(賜)寓曼? ? ?(絲),對揚王姤(后)休,用乍(作)父壬寶? ? ? (尊)鼎。
此銅器銘文記載了作器者寓將玉佩獻給王后,王后賞賜他素絲的事情。釋文的爭議在于“? ? ”的釋讀。陳夢家與謝乃和將此合文釋為“二月”;唐蘭則在《西周青銅器銘文分代史征》一書中,將此合文釋為“三月”,并將此器斷于康王世。
筆者認為,唐蘭的“三月說”是正確的,原因如下:
其一,除“? ? ?”外,金文中有另一月份合文,寫作“? ? ?”,見于鑄叔皮父簋(《集成》04127,春秋早期)與另一寓鼎(《集成》02756,西周早期)。若該合文被釋為“二月”而非“一月”,則“? ? ?”的釋義應為“三月”。研究證明,將“? ? ?”釋為“二月”是準確的。
從西周到戰國晚期,中原諸侯國與楚國都稱一月為“正月”,銘文中的“一月”皆表示“一個月”,尚未發現例外。所以,“一月”的釋義并不準確。
《逸周書·世俘》記載了武王“有國”之年的干支日,起于一月丙午,終于四月乙未。一月到四月最少間隔60日,但是丙午到乙未僅間隔50日,可見,一月丙午當更正為“二月丙午”。若將此篇中的“二月”釋為“三月”,則可以與《周書·武成》中“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的記載相合。所以,“二月”之合文應為? ? ? 。
其二,凡有“? ? ”與“? ? ”出現的銅器,表示“月”的部分上部都較為平直,與表示數字的橫大致平行。由此可以判斷,“三”字當借用了“月”字一筆,“借筆”現象在古文字中并不鮮見,茲不贅述。[1]
其三,西周時期刻有“十又三月”(無合文)的銅器共有8件,其中西周早期3件、西周中期3件、西周晚期2件。可見,整個西周時期存在有年終加上一個月的置閏法,即年終置閏法,閏月寫作“十又三月”。
所以,若某一銅器的作器時間為“十又三月”,其中的“三月”也有可能寫作合文的形式,代表銅器為盠駒尊(《集成》06011,西周中期),其銘文記載:
隹(唯)王十又三月,辰才(在)甲申,王初執駒于? ? ?,王乎(呼)師豦召(詔)盠,王親旨(詣)盠,駒易(賜)兩,拜? ? ?首曰:王弗望(忘)氒(厥)舊宗小子,? ? 皇盠身。盠曰:王倗(不)下(叚)不其則邁(萬)年保我邁(萬)宗。盠曰:余其敢對揚天子之休,余用乍(作)朕文考大中(仲)寶(尊)彝。盠曰:其邁(萬)年世子孫孫永寶之。
盠駒尊的干支日為甲申,在日期上與其有關聯的是中方鼎(《集成》02785,西周早期),銘文記載:
隹(唯)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在)寒? ?(次),王令大史兄(貺)? ? 土。王曰:“中,? ? ?(茲)? ? ?人入史(事),易(賜)于珷王乍(作)臣,今兄(貺)? ? 女(汝)? ? 土,乍(作)乃采。”中對王休令,? ? 父乙? ? (尊),隹(唯)臣尚中臣。
唐蘭認為,十三月并非每年都有,甲申與庚寅只相差一天,所以兩器所載之事,很可能就發生在同一年的十三月。[2] 李學勤認為,中方鼎之“中”,就是靜方鼎(《集成》NA1795,西周早期)銘文中的“師中”。[3] 靜方鼎記載之事與昭王伐楚有關,中方鼎亦然,所以盠駒尊也應與昭王伐楚有關。
在所載地點上,與盠駒尊有關的是遣卣(《集成》05402,西周早期),同樣是與昭王伐楚有關的銅器,其銘文記載:
隹(唯)十又三月辛卯,王才(在)? ? ,易(賜)? ? 采,曰:? ? ,易(賜)貝五朋。? ? ?對王休,用乍(作)姞寶彝。
盠駒尊與遣卣都提到了“? ? ?”,此為地名。唐蘭指出:此地與宗周相近,是昭王伐楚時的常住地點。[4] 所以,盠駒尊與遣卣之做器時間相距不遠,很可能在同一年之內。如此,此兩器與中方鼎應是同年所做。甲申、庚寅、辛卯日跨度只有8天,可以排在一個月之內。[5]
昭王第一次伐楚是其在位十六年之事,根據《夏商周年表》,該年為公元前980年,次年即有十三月。[6] 甲申至辛卯日為該月的第十六至二十四日。由此可知,盠駒尊之“十又? ? ?”應釋為“十又三月”。[7]
綜上所述,“? ? ”應釋為“三月”,但仍有一些問題無法解決,從而無法將“? ? ?”的釋義完全確定。如下:
其一,除寓鼎與盠駒尊外,筆者搜集到帶有此合文的銅器共9個。這些銅器四要素不全,缺少具體王年,甚至有一部分缺少干支日,只能根據其紋飾和字體大致斷代。其銘文所載之事,尚未發現與其對應的傳世文獻,也缺乏時間上具有連續性的其他銅器的佐證。所以,無法確定這些銅器銘文的具體王年。
其二,中國歷史有確切紀年開始于共和元年,在此之前的年歷主觀推測成分較多,以致學界對西周時期的排譜尚無定論。所以,現有西周歷譜的準確性尚存爭議。
總之,“? ? ”的釋讀依然有待商榷,但是根據目前確定的研究成果來看,將“? ? ”釋為“三月”是較為合理的。
二、夏商周三代皆實行“年終置閏法”
根據前文所述可以斷定,西周時期存在“年終置閏法”,但“年中置閏”的存在尚有爭議。
周歷結合了夏歷與殷歷,研究周歷的相關問題,需以夏歷與殷歷為先決條件。
夏歷記載于《夏小正》與《尚書·堯典》之中,張聞玉認為,《夏小正》成書早于《尚書·堯典》,可以作為研究夏歷的史料。 [8] 潘鼐考證《夏小正》所記的星象,認為《夏小正》記載的星象是夏時期的。[9] 所以,夏歷的研究需要將上述兩個史料結合。
陳久金指出,《夏小正》是十月太陽歷,月長較大,且隨著月份增加,月間隔也越來越大。[10] 《夏小正》中對節氣的判斷有兩種途徑:一是觀物象,即觀察不同時間的生物活動;二則是觀星象。《夏小正》記載了鳥、房等星宿在不同季節與月份的變化,也記載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上”、六月“初昏斗柄正在上”。這表明在殷商之前,人們就已經觀測到了北斗七星斗柄指向與其他星象的變化規律。
《尚書·堯典》的記載指出了夏歷的兩個特征:夏時人們已經觀察到了春分到冬至日的白晝時長變化;夏歷排譜有四個關鍵節點,鳥、火、虛、昴四星在天空正南方,分別對應了仲春、仲夏、仲秋和仲冬。如果到了季節仲月,對應的星宿沒有出現在天空正南,就表示月份出現了偏差,應在此時設置閏月進行調整,即“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由于四星的偏移時間并不固定,所以,夏歷的置閏也不固定,有可能在年中某月,也可能在年終。但是夏歷還處于歷法的奠基階段,實行“年中置閏法”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夏歷應以“年終置閏”為主。
與夏歷不同,《左傳》昭公十七年(前525)載:“火出,于夏為三月,于商為四月,于周為五月。”[11] 此記載被認為是對殷歷的直接記錄。但是,《左傳》成書于春秋晚期到戰國中期,距離殷商年代久遠,其記載的殷歷實為宋人的歷法,與殷歷雖有聯系,但仍有差別。
通過對甲骨卜辭的考證,大部分學者都認為殷商時期出現了年中置閏的現象,但此種現象是否成定制,是學者討論的焦點。對此,學界產生了兩種觀點:殷歷在一定時期內同時采用“年中置閏法”與“年終置閏法”;殷歷置閏于年終,年中置閏是偶然現象或未發生過。
第一種觀點得到了董作賓、馮時等學者的支持。
董作賓在《殷歷譜》中指出,祖甲繼位之年,一月改稱正月,置閏在當閏之月,不再用“十三月”之名。[12] 董氏之觀點不被認可,因為在武丁之后的卜辭中仍有“十三月”出現。但這并不意味著董氏關于年中置閏的觀點是錯誤的。
陳夢家認同董氏關于年中置閏的觀點,他在《殷虛卜辭綜述》一書中指出:《珠》199條卜辭(《合集》11 545)是商代出現年中置閏的證據,在這些卜辭之中,癸亥、癸酉等日期不滿足無閏月情況下3至5月干支日的排列。由此可知,在當年的3至5月之間必然出現了一個閏月。[13]
馮時與張聞玉都認為,武丁時期出現了最原始的“無中氣置閏法”,殷歷用平朔平氣,一年12個月均可置閏。[14]? 馮時進一步認為,《甲骨文合集》10976證明了武丁時期可能出現了閏八月,而這一時期出現的閏十二月,有可能只是改變了位置的年中閏月,目的就是固定二分二至的所在月份。[15]
常玉芝進一步證明,在殷歷之中,出現過閏四月、閏六月與閏十月。[16] 至此,商代出現了年中置閏成為學界共識。陳遵媯在《中國天文學史》一書中進一步指出,祖甲至乙辛時期實行年中置閏,但祖甲時期的卜辭還有“十三月”存在,說明“年終置閏法”并未廢除,兩者經歷過一段時間的共存。[17] 所以,殷歷應同時采用過“年中置閏法”與“年終置閏法”。
但是,以鄭慧生、朱鳳瀚為代表的學者,對此提出了異議。
鄭慧生認為,傳統的“殷正建丑”的觀點是錯誤的,殷正應建未,以麥子成熟月為歲首。如果過了十二月麥子未熟,就補上一個月,卜辭寫作“十三月”,此即“年終置閏法”。與此同時,有了麥子成熟度這一物象,采用年中置閏法就容易了。九月,麥子應起身拔節,如果麥子未出現此情況,就應在九月置閏。所以,殷歷也應出現了年中置閏。
鄭氏不否認年中置閏,但他也認為,由于麥子的成熟度不易觀察,年中置閏并不常用,殷歷仍以年終置閏為主。[18]
朱鳳瀚認為,殷正建午,以大火星(心宿二)在黃昏時處于天空正南的月份為歲首。殷商時期的置閏就是為了讓該現象固定在出現于夏歷五月,因此置閏于夏歷四月,即年終是最好的方案。[19] 所以,殷歷應實行“年終置閏”。
更有學者認為,年中置閏可能未出現。張培瑜認為,殷歷部分大月月長可能大于30日,可見殷歷并不是嚴謹的陰陽歷;殷歷并不是推步歷法,不可能精準計算出朔望月日期,更不可能產生二十四節氣,即使殷商時人產生了年中置閏的想法,也不可實現。[20]
綜合以上觀點,筆者認為:殷歷出現過年中置閏。但是,由于實行年中置閏的條件尚不成熟,所以年終置閏才是殷歷最常用的置閏法。
周歷的月份排列遵從夏歷,但以子月(冬至月)為歲首(建子)。《詩·豳風·七月》記載:“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一之日為周歷正月一日。根據《七月》的敘述,夏歷七月,大火星(心宿二)開始向西偏移,天氣入秋;九月開始制作冬裝。周正建子,夏正建寅。[21] 所以,周的正月應為夏的十一月。
但是,對于《七月》中日期的解釋卻有爭議之處,爭議在于,《詩經注析》等的注釋中,“一之日”等日期使用周歷,“七月流火”等月份又使用夏歷,一首詩中為何會使用兩種歷法?只有兩種可能:周正建子是訛誤,或者周歷的月建經歷過變動。
張培瑜在《逨鼎的王世與西周晚期歷法月相紀日》一文中指出,若以“周正建子”作為依據,四十二年逨鼎(乙)(《集成》NA0745,西周晚期)等銅器與吳虎鼎的四要素無法排在同一歷譜中,若將其著作《中國先秦史歷表》中的月份整體后移一個月,上述問題即可解決。[22]所以周正應建丑。
若周正建丑,在“共和行政”不單獨紀年,且并入宣王紀年的情況之下,吳虎鼎的歷日與虢季子白盤(《集成》10173,西周晚期)等器的銘文歷日,又無法排在同一歷譜當中。[23] 由于“共和行政”是否單獨紀年存在爭議以及其他原因,周歷月建問題長期未能解決。
常玉芝認為,殷商到西周時期,皆以朏日為月首。[24] 王勝利進一步認為,周人應以觀察到新月的后一日作為月首,體現在金文中就是“既望”“既生霸”等紀日法的使用。可見,周歷也是觀象歷,而非推步歷。張培瑜也提出過類似觀點。那么在月建上,也應在觀察到“日短至”之后的月份作為月首。所以,周正應建丑。[25]
陳美東認為,研究西周歷法可從春秋時期的魯歷回溯。王韜認為,魯歷以僖公五年(前655)為界,前建丑后建子。但是陳氏的研究表明,僖公五年前也出現過建丑,之后也出現過建子,甚至有些年份建寅。《左傳》記載,魯歷出現過失閏或多閏的情況,因此導致月建不規律。由此可以推斷,周歷也可能出現過此種現象。在置閏方面,作為與周人習俗最相近的諸侯國,魯歷置閏就是置于年終。[26]
所以,周歷建子應為主要月建,但是也存在類似于魯歷的月建擺動,置閏也應置于年終。
綜上所述,筆者的結論如下:
1.“? ? ?”的釋義為“三月”,“十又? ? ?”為“十又三月”。
2.周歷雖有推步色彩,但仍為觀象歷。由于此階段天文觀測不夠精確,出現過數次“失閏”或“多閏”,導致月建擺動較大,不具備實行“年中置閏法”的條件,所以周歷應實行“年終置閏法”。
參考文獻:
[1]祝振雷.從鑄叔皮父簋銘校正古書中對“一月”的誤識[J].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0,29(01):79-82.
[2]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J].考古學報,1962(01):15-48.
[3]李學勤.靜方鼎考釋[C]. //第三屆國際中國古文字學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97.
[4]唐蘭.西周銅器斷代中的“康宮”問題[J].考古學報,1962(01):15-48.
[5]何景成.盠駒尊與昭王南征——兼論相關銅器的年代[J].東南文化,2008(04):51-55.
[6]夏商周斷代工程專家組.夏商周斷代工程1996-2000年階段成果報告:簡版[M].北京: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00 :88.
[7]張培瑜.中國先秦史歷表[M].山東:齊魯書社,1987 :45.
[8]張聞玉.《夏小正》之天文觀[J].貴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3(04):62-68.
[9]潘鼐.中國恒星觀測史[M].上海:學林出版社,2009:7-9.
[10]陳久金.論《夏小正》是十月太陽歷[J].自然科學史研究,1982(04):305-319.
[11]楊伯峻.春秋左傳注[M].北京:中華書局,2016:1544.
[12]董作賓.《殷歷譜》下編卷5:閏譜[M].中國臺北: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2:3.
[13]陳夢家.殷虛卜辭綜述[M].北京:中華書局,1988:217-223.
[14]張聞玉.古代歷法的置閏[J].學術研究,1985(06):117-122.
[15]馮時.殷歷武丁期閏法初考[J].中國歷史文物,2004(02):25-31+63.
[16]常玉芝.殷商歷法研究[M].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307-318.
[17]陳遵媯.中國天文學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36-137.
[18]鄭慧生.年中置閏:先秦歷法史上的重要改革[J].史學月刊,2009(11):25-30.
[19]朱鳳瀚.試論殷虛卜辭中的“春”與“秋”[C]. //仰止集:王玉哲先生紀念文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170-187.。
[20]張培瑜,盧央,徐振韜.試論殷代歷法的月與月相的關系[J].南京大學學報(哲學·人文科學·社會科學),1984(01):65-72.
[21]程俊英,蔣見元.詩經注析[M].北京:中華書局,1991:437-438.
[22]張培瑜.逨鼎的王世與西周晚期歷法月相紀日[J].中國歷史文物,2003(03):6-15+97.。
[23]張培瑜,周曉陸.吳虎鼎銘紀時討論[J].考古與文物,1998(03):72.
[24]常玉芝.殷歷月首研究[J].傳統文化與現代化,1997(05):26-38.
[25]王勝利.西周歷法的觀象歷屬性[J].殷都學刊,2004(04):33-35.
[26]陳美東.魯國歷譜及春秋、西周歷法[J].自然科學史研究,2000(02):124-142.
作者簡介:
蔡立錚,1996年生,男,漢族。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先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