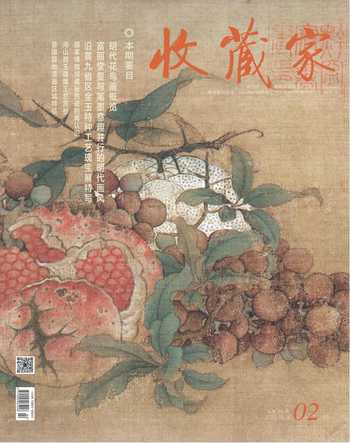帝后禮佛圖拓片考
張萌

















帝后禮佛圖浮雕位于河南洛陽龍門石窟賓陽中洞,鑿刻于北魏宣武帝時期,意圖紀念其父孝文帝和其母文昭皇后。20世紀30年代中期,這組浮雕被當時做洋莊生意的商賈盜鑿,兩面浮雕分別販售給美國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堪薩斯城納爾遜·阿金斯藝術博物館,致使我國重要文物外流。在浮雕被盜鑿之前,多位域外漢學專家曾造訪踏查浮雕,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記錄。本文考證的拓片,也出于浮雕遭毀前的傳拓,較為完整地存印并再現了浮雕全貌。
一、《帝后禮佛圖》拓片及原浮雕現狀
樊曉曼藏《皇帝禮佛圖》拓片(圖1)寬384、高221厘米,《皇后禮佛圖》拓片(圖2)寬358.5、高212厘米。目前藏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皇帝禮佛圖浮雕(圖3)寬390、高210厘米①,藏于堪薩斯城納爾遜·阿金斯藝術博物館的皇后禮佛圖浮雕(圖4)寬280、高200厘米。根據劉景龍的考證,東壁第三段(帝后禮佛圖浮雕)的高度為190厘米②。
通過拓片的尺寸、照片和浮雕的現狀照片,以及中域外漢學家們在龍門石窟考察時拍攝的照片,可以明確的是樊曉曼所藏皇后禮佛圖拓片要比目前納爾遜·阿金斯藝術博物館的浮雕內容更全面,后者缺少了賓陽中洞東南角南面墻上的浮雕,只保留了東面墻上的浮雕內容。而樊藏拓片包含了南面墻上的儀仗人物。
二、原始出處和當下來源
皇帝禮佛圖和皇后禮佛圖浮雕位于河南省洛陽市龍門石窟賓陽中洞,沿洞窟入口兩側墻面鑿刻,均位于墻面主題敘事的第三層。兩塊浮雕鑿刻于北魏時期,賓陽中洞為北魏宣武帝為紀念其父孝文帝和其母文昭皇后所開鑿,正處于龍門石窟藝術活動最活躍(495~537)的一段時期。龍門石窟的雕塑從整體來看,以唐代的數量居多,但是最重要的洞窟都是北魏時期開鑿的,比如古陽洞、蓮花洞、賓陽洞(圖5)。賓陽洞作為淺溪寺的主要洞窟,洞內最早的題記年份是公元595年,造像的主要風格特征屬于北魏,但是后人有所修補。
20世紀初,法國學者沙畹、日本學者關野貞、常盤大定和瑞典學者喜仁龍先后造訪并考察龍門石窟,留下了珍貴的影像資料和考古文字資料(圖6~圖8)。令人扼腕的是,1934至1935年位于賓陽中洞(賓陽三窟主窟)東墻上的帝后禮佛圖浮雕被全部盜鑿③。因此20世紀初期域外學者留下的賓陽中洞考古資料成為其遭毀前原貌的見證史料,尤其是沙畹和關野貞留下的影像和圖片。而樊曉曼藏《帝后禮佛圖》拓片,源于民國時期的一次傳拓活動,因此也具備了展示浮雕原始面貌的意義。故其時間下限應為1934年,即浮雕慘遭盜毀之前。
雖然沙畹拍攝的禮佛圖影像頗具史料價值,但是他在《華北考古記·石窟卷》中對賓陽中洞做出的推斷出現了失誤。原文中他對這組禮佛圖中的人物形象描述十分詳盡,沙畹當時也認為這兩組禮佛行列代表的是供養人,但是他根據洞口的《伊闕佛龕碑》碑文,將禮佛圖中的人物誤認為是魏王泰及其兩位王妃,并認為浮雕是7世紀王室服裝的實物圖像。依碑文所述,賓陽中洞佛龕是魏王泰為其已故母親文德皇后所建。然而沙畹忽略掉的是《魏書·釋老十》對賓陽中洞的建造原因早有記述:
景明初,世宗詔大長秋卿白整,準代京靈巖寺石窟,于洛南伊闕山為高祖、文昭皇太后營石窟二所。初建之始,窟頂去地三百一十尺。至正始二年中始出斬山二十三丈。至大長秋卿王質,謂斬山太高,費功難就,奏求下移就平,去地一百尺,南北一百四十只(尺)。永平中,中尹劉騰奏為世宗復造石窟一,凡為三所。從景明元年至正光四年六月已前用,功八十萬二千三百六十六。④
李泰命岑文本和褚遂良撰寫碑文時,是將之前的碑文磨平重刻,造成了后人的誤會。據大村西崖推斷③,這一謬誤肇始于歐陽修《集古錄》?,此后《河南通志》和《洛陽縣志》也都襲用了歐陽修的說法。
通過沙畹的影像(圖9~圖12),還能獲取一個有效信息,即樊曉曼藏兩幅拓片均為拼接制成,因為原窟中《皇帝禮佛圖》和《皇后禮佛圖》的浮雕均位于空間轉角處。上文中的線稿圖和拓片都沒能反映浮雕在石窟中的空間效果,只是在圖像意義上呈現出禮佛行列的敘事完整性。
1906至1935年間,日本建筑史學者關野貞多次來華考察,其中1906和1918年?兩次行程曾途徑河南省,故他在龍門石窟拍攝的賓陽洞浮雕照片(圖13、圖14)極有可能是在這兩次行程中踏查所得。1920至1928年間日本佛教史學者常盤大定先后五次來華考察文化古跡,此后他與關野貞合著《中國佛教史跡》《中國文化史跡》等書,均對龍門石窟有所涉及。二人的成果為1936年的另外兩位考古學家長廣敏雄和水野清一對龍門石窟的考察奠定了研究基礎,他們在1941年首版的《龍門石窟の研究》一書中汲取了關野貞的部分研究成果⑧,尤其是《帝后禮佛圖》的圖像文獻。因為長廣和水野去考察時,賓陽洞的禮佛圖像已被盜鑿而面目全非。
大村西崖在書寫《中國雕塑史》(1915)時,雖然未親自踏足中國,但從多位日本學者手中獲得了諸多踏查采訪的一手資料,尤其是影像與拓片。他在該書導言中提到了同窗早崎天真給他帶回龍門窟龕各處殘存遺品照片,其后冢本靖、伊東忠太和關野貞三博士也拍了很多考察照片回來。書中論及北魏時期龍門賓陽洞的供養人圖像時,也佐以影像圖片。唯一可以明確的是這兩張影像應該攝于1915年以前,如果拍攝者是關野貞,那么應該是他1906年那次考察時拍攝的照片。若非,則拍攝者有可能是早崎天真。
學者劉景龍《賓陽洞》一書中以大量圖片資料再現了賓陽洞東壁被盜鑿后的面貌(圖15)。據圖可知,《帝后禮佛圖》段損毀程度最甚,除卻第四層的十神像,上層浮雕均有不同程度的損毀。在短短幾十年的時間里,浮雕造像經歷了此前數個世紀不曾有過的浩劫。相對于吞噬一切的時間,人禍對文化遺產的侵蝕更為駭人。在1934年盜鑿后未運出境的殘片于1953年被青島海關通過故宮博物院交回龍門石窟保管所,共計7箱,包括身段殘片和面部殘片等。
關于龍門石窟被盜毀的情況,常盤大定在書中的記敘可為之做出腳注:
這里擁有無限的土偶和石佛資源,想要遍訪尋獵是多少天也不夠用的。洛陽滯留期間每天都出城入城,佛像之類昨天沒有的,今天有可能新到,即使每天去也沒有盡頭。這件事從另一個側面看,也可以說是中國各地的古跡每一年每一年,不,應該說是每一天每一天都在遭到破壞。非常遺憾的是,在現在這種情況下,無論何人也都是沒有辦法的。但愿至少我們能把其中有代表性的東西帶回我國加以保存,并能夠建起有關設施以便進行系統研究。⑨
三、關于《帝后禮佛圖》拓片的存世情況
因為流傳有緒,且經歷過幾次機構的征詢和收購活動,所以樊曉曼藏《帝后禮佛圖》拓片的真偽基本是可以確知的。
樊曉曼是前中央美術學院雕塑系教授王丙召(圖16、17)和妻子樊曼琳之子,《帝后禮佛圖》拓片實為王丙召夫妻二人珍藏。據樊曼琳口述,王丙召早年熱愛美術,考察各地著名石窟遺址,逐漸在雕塑上找到了自己的表達方式。曾以30多塊大洋購得《帝后禮佛圖》拓片兩幅。就在王丙召收入拓片后不久,得知原存拓片處失火,其余多套被燒毀,痛心不已。王丙召早年曾請榮寶齋的裝裱師傅對兩幅拓片進行裝裱,為表達謝意,便將個人收藏的十幾幅名家畫作及手稿贈予裝裱師傅,這其中包括世交好友李可染、葉淺予等作品。
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兩幅《帝后禮佛圖》拓片在人民英雄紀念碑《金田起義》浮雕的創作中起到了一定的參考作用。“文革”時期王丙召遭到抄家,包括兩幅《帝后禮佛圖》拓片等個人收藏均被學校抄走。
20世紀80年代初期,樊曉曼去吉林藝專索要王丙召被抄舊物時,從關志芬老師處得知拓片情況。據她回憶:當時發現兩幅《帝后禮佛圖》拓片就堆放在美術系庫房的地上,當時學校里的人展開拓片一看,只見一片墨跡,而且尺寸又大,還沒有觀賞價值,又沒有人懂得金石拓片,這才得以保存下來,由關志芬存放在學校資料室。因為她當時負責管理美術系的資料,然而庫房的保存條件有限,所以學校委派專人攜兩幅拓片前往北京,轉交給樊曉曼。此后拓片即由樊曉曼保存。
1986年,因家中存放條件有限,拓片出現破損,意在更好地保護修復拓片,經徐仁龍引薦臺灣某基金會,在燈市口一賓館內三方進行商議,后對方提出想以8萬美元購買這套拓片,并裁切后運往中國臺灣。樊曉曼、徐仁龍出于對拓片的珍視,未允。最后終止了修復拓片的商議。1989年,洛陽龍門石窟博物館館長宮大中從范曾處知悉拓片在樊曉曼這里,欲向其借展(在中國美術館展出),樊曉曼應允,但遇特殊情況作罷。
20世紀90年代初,經過戴澤的女婿馬宜國引薦,由拓曉堂就如何修復、保護拓片給出過具體建議,并進一步討論。1999年,經過馬宜國協助,對拓片進行了測量與拍照并刻錄光盤后轉交給史樹青。史老晚年曾感嘆“有生之年未見實物,生之憾矣。”
高峰在其博士論文中提到“北京博物館”也存有一套《帝后禮佛圖》拓片。而北京并沒有一座博物館叫作“北京博物館”,細究或許這里的北京只是一個方位定語,實則應為北京的某一家博物館藏品。筆者在故宮博物院藏品總目中檢索到一件題名為《民國拓禮佛圖》的藏品,編號“新00201944”,從題名表述中的傳拓時間和內容來看,與《帝后禮佛圖》拓片的情況高度一致,疑為當時所出多套之一。
此外,《皇帝禮佛圖》拓片的圖像也收錄在由普愛倫(Alan Priest)撰寫并于1944年出版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中國雕塑(Chinese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一書中,說明美國大都會美術館東亞部主任普愛倫是見過這幅拓片的,或者至少是通過某種渠道獲得了拓片的影像。
值得注意的是,沙畹在對《帝后禮佛圖》浮雕進行描述時,分別做了兩個腳注,提到沃馳曾在巴黎的賽努奇博物館展出兩幅拓片,而這兩幅拓片信息可在1913年出版的佛教藝術展《目錄冊》第683、684期中找到。如果沙畹的信息準確,那么至少在1913年以前,《帝后禮佛圖》的拓片就已經存在了。至于這兩幅拓片和樊曉曼手中的拓片是否為同一次傳拓活動所出,目前還難有定論。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拓片的制作時間下限可向前推至1913年。
常盤大定《中國佛教史跡》記錄了他1921年來華踏查的行程日志,其中11月2日的記錄為:“晴。得居住洛陽的森長鶴鳴氏同行至龍門,宿。因欲得賓陽、老君?二洞拓本而行。”?之后11月10日的記錄為:“晴。拓本完成。”說明常盤大定在1921年11月初,歷時近一周的時間找人完成了龍門石窟賓陽洞、老君洞的拓片,且這批拓片中是有造像拓片的。他在書中一篇名為《寶陽、老君兩洞拓片》的文章里對此次傳拓原委做了詳細交代,可惜本書的翻譯誤把文章題名“賓陽”譯為“寶陽”,犯了一個低級而嚴重的錯誤。通過分析文章內容和書前的行程日志,不難得出此篇即為賓陽、老君兩洞拓片相關記錄。據常盤大定說,在這次傳拓前,他所請的老拓翁雖然已從業40年,但是只拓過銘文,沒有拓印造像的經驗,于是他親自示范如何拓印,并囑咐其接續關系一定要明確。他在文章開篇寫道“龍門寶(賓)陽洞的全部拓片就不用說了,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也還沒有人做過。”據此,基本可以得出如下結論:首先,在1921年的傳拓活動前,就已經有日本學者做過賓陽洞的拓片,此次傳拓只為補全之前的遺漏。其次,這次傳拓很有可能是針對賓陽洞中某些造像的一次拓印工作。再次,因為存在接續關系,很有可能存在相對較大面幅的拓片制作。最后,有理由推斷日本學者在1922年前即完成了對賓陽洞造像和銘文的傳拓工作,并將這些拓片帶回日本進行研究。
綜上所述,《帝后禮佛圖》的存世拓片曾在法國、日本、美國出現過,中國的私人藏家和故宮博物院目前也分別保有,只是這些拓片是否均為一次傳拓活動所出,目前難下定論。
四、拓片價值
1.歷史價值
首先,皇帝和皇后以供養人的身份出現在石窟寺的浮雕上是北魏時期政教融合的體現。其次,石窟在1934年被盜鑿的遭遇客觀上使拓片本身的歷史價值得到提升,是保留浮雕原貌的存世珍本。并且,拓片比目前保存在美國的浮雕內容更加完整,在某些部分比修復的浮雕更能體現原始形態。
2.藝術價值
首先,與同壁其他三類主題浮雕(自上而下依次為《維摩變》《薩垂納太子本生》《十神像》)相比,《帝后禮佛圖》拓片在內容上更具世俗化意義,同時又顯示出北魏莊重典雅的皇家風范。其次,《帝后禮佛圖》富有敘事色彩的群像構圖,自此在東方美術創作中被視為一種帶有典范意義的藝術模型。比如之后的《孝子石棺圖》上也有類似的儀仗群像場面。再次,借由皇室供養人形象,褒衣博帶藝術風格呈現出浮雕造像的漢化特征。所以,拓片也客觀記錄了“群像構圖”和“漢化特征”在雕塑史上的地位。
3.文獻價值
帝后禮佛圖原窟雖然遭毀,但是浮雕仍保存在博物館中,所以拓片仍能作為復原的依據和參考。
本文在行文過程中配合考古報告圖片,借以證史。在不能實現實地踏查的情況下,考古報告中的圖像和影像資料即成為研究者的一手資料。可靠的圖像資料中所包含的有效信息遠比文字文獻更為直觀,更具說服力。由于對石窟寺的保護失守、盜匪猖獗,遭毀前留存下來的圖像文獻成為昔日風貌僅存的視覺證據。重新拼接復原的《帝后禮佛圖》浮雕早已流失其藝術風采,取而代之的是碎片般的記憶控訴,更妄論其在東壁整體浮雕中所承載的文化意義。
《皇后禮佛圖》原始照片出現在華辰2012年春季拍賣會上,拍品號990,銀鹽紙基,估價20000~30000元人民幣,最終流拍。或許當時國內并沒有藏家意識到這幅照片背后隱藏的歷史價值,可就在將近一個世紀以前,域外學者對這組浮雕的關注已遠超國人,甚至美國博物館的垂涎直接導致了原窟浮雕的盜毀及外流。不得不說王丙召對拓片的收藏意識于其時是超前的,雖然之后幾經輾轉劫難,終歸在20世紀80年代由樊曉曼繼而保存。通過對石窟寺浮雕和拓片的考證與追索,其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歷史、藝術價值也不言自明。
注釋
① Denise Party Leidy, Donna Strahan.Wisdom embodied: Chinese buddhist and Daoist sculpture in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M].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2010:62~65.
②劉景龍《賓陽洞:龍門石窟第104、140、159窟》,文物出版社,2010。
③大都會美術館東亞部主任普愛倫和岳彬記于1934年簽訂了盜鑿協定,兩塊浮雕于1934~1935年間被做洋莊生意的岳彬帶領一眾工匠盜鑿,將殘片自行修復拼接后運往美國紐約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和堪薩斯城納爾遜·阿金斯藝術博物館。
④魏收《魏書》卷110,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⑤大村西崖《中國雕塑史》,中國畫報出版社,2020。
⑥“唐岑文本三龕記貞觀十五年:右三龕記,唐兼中書侍郎岑文本撰,起居郎褚遂良書,字畫尤音偉。在河南龍門山山夾伊水東西可愛俗謂其東曰香山,其西曰龍門,龍門山壁間鑿石為佛像大小數百,多后魏及唐時所造,惟此三龕像最大,乃魏王泰為長孫皇后造也。”歐陽修《集古録》,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⑦關野貞《中國古代建筑與藝術》,中國畫報出版社,2017。
⑧在《龍門石窟の研究》的前言中,長廣敏雄提到他最初知道摩崖石佛是通過已故學生關野博士。筆者認為應是關野貞,因為本書中的第15幅插圖為《賓陽洞浮雕行列圖攝影》,右下標明攝影者為關野博士,此圖與關野貞拍攝的皇后禮佛圖局部如出一轍。
⑨?~?常盤大定《中國佛教史跡》,中國畫報出版社,2017。
⑩王丙召(1913~1987),山東益都人。擅長雕塑。曾任中央美術學院、吉林藝術學院副教授。
?關志芬是王丙召的美術系同事樸孝懷的夫人。?中央美術學院老師,王丙召同事、友人。
?高峰《雕塑家王丙召研究》,中央美術學院,2015。
?老君洞即古陽洞。
(責任編輯:尹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