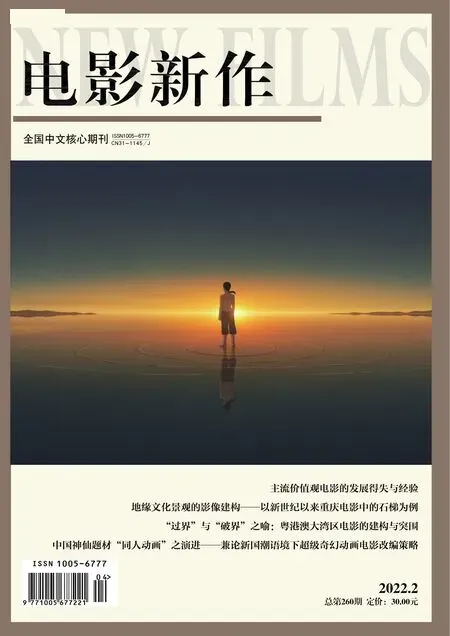流動于傳統、現代與革命之間:上海城市銀幕空間呈現的色彩譜系與未來面向
鄭 煬 鄧 然
晚清上海開埠后,五口通商的客觀地區環境迅速生成杳雜繽紛的城市景觀,洋場與海派的交相輝映,本土與世界的相互融合極為深刻地影響了上海的城市消費與工商發展,促使上海地區在城市功能與地位的轉型過程中,逐漸煥新為摩登的國際化大都市。直至抗戰結束,有“東方好萊塢”之譽的上海,一直是國內電影生產與電影消費的主要場所,甚至在亞洲范圍內亦屬首屈一指。因此,銀幕中的上海城市形象書寫成為中國電影最具辨識度和最具影響力的地域形象之一,并在各個時代承載和反映了不同創作內涵或主題。總之,上海的銀幕形象表征嵌入在中國電影發生發展的文脈之中。
上海城市空間中的娛樂、政治與市民生活共同指向了一種雙重形態的城市模式。上海娛樂空間由南向北跨越了洋涇浜,落戶于公共租界區,共同構成上海城市中的娛樂“現代性”。有反映紳商雅士、店員學生趣味的園林、游藝場,以及匯集三教九流、引車賣漿之徒的茶園、戲園,還兼具城市中搖曳著燈光的舞廳、電影院等摩登都市的空間。在城市居住環境方面,法租界內隸屬上流社會的花園洋房、中產階級或市民階層居住的新舊式里弄,以及“三灣一弄”內底層貧苦民眾棲身的棚戶區,成為早期上海影像居住經驗的原始摹本。人口結構的高度異質、空間結構的差異化與“一市三治”的政治格局,使得電影與上海互為敘事表里,從而在影像內空間生產實踐中突顯了上海銀幕形象在時代橫向上的多元性特征。其次,自開埠以來,上海城市區劃幾經調整,治權數度轉移。解放后的城市改造浪潮中,上海以曹楊新村為代表的工人新村建設運動,在改造資本主義大都會的舊上海的同時,努力生產著一種代表社會主義的新空間。改革開放后的新一輪城市建設又營造出別樣的現代化城市空間。因之,上海城市空間在不同歷史時期的數度擴張與轉變,決定了上海的銀幕形象在縱向上具有多樣性特征。所以,上海的銀幕空間生產在這一意義上,就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被改造客體,而且還包含了各種空間形象之間共時態的相互并行、接納或者排斥的關系。
即使如此,若以歷時性視角對上海銀幕形象進行考察,仍能夠提煉出這一形象系統的主要表征方式,亦即上海城市形象的時代主流。當然,這不意味著將上海的銀幕形象簡單化或庸俗化。因為,在任何社會或任何生產方式下的空間表象,都會顯著體現出統治群體以知識話語或意識形態介入空間構造的因素。所以,這個主流形象與中國電影在不同時代的不同主題表征基本同步。旁證是,當我們將視野放大到域外,可以發現中國香港、臺灣電影和西方電影在對上海進行呈現時,它們常能夠將紛繁復雜的上海形象類型化、程式化,形成特征更加顯著但略顯板滯的上海城市銀幕景觀。接下來,本文試圖通過對中國電影史上的典型上海銀幕形象進行考察,意在闡明各種形象內外的文化意涵及其生成的文化機制,并指向一種兼蓄包容意義的“紅色”上海銀幕形象建構的未來可能。抗戰時期上海一批以“隱退”選擇為主的文人的社會歷史心態。該著以“灰色”來修飾精英階層模糊的政治立場,以及他們在面對外在與內在雙重壓力下的處世態度。無意間,

圖1.電影《勞工之愛情》海報
一、“灰色”:現代性與進步話語的并立
傅葆石的《灰色上海》曾聚焦這一時期的上海被涂上了“灰色”基調,似乎和人們對“舊上海”洋場中的五光十色印象大相徑庭。
正如任何一種銀幕空間實踐本身并不會將抽象領域的意義顯露在表層一樣,“舊上海”時期的影片當然不會把自身建構成“舊上海”,因為這一話語表征生產于具有歷時性的銀幕空間之中,它無法對自身以“獵奇”與“回顧”的視角來審視。以現存最早的中國電影《勞工之愛情》為例,片中所展示的上海市民生活和娛樂空間即處于平視視角。雖然影片缺少對城市全景式的展現,但在這個“洋涇浜”(Pidgin)風情顯著的狹小弄堂空間里,長衫與西式禮帽、本行與外行、一樓的生活空間與二樓的娛樂場所等對比,顯示出本土與世界、傳統與現代之間較強的文化張力。
這個張力的社會背景是近代上海人口的迅猛增加,上海開埠時僅有50余萬人,及至1915年,這一數字翻了4倍。同時,租界向華人開放后,租界內華人人口亦增長迅速。伴隨著人口和文化、習俗遷徙的運動所帶來的顯在結果就是,作為都市的上海無處不在地體現著上述那兩組張力,即便是身處弄堂中的市民也無法免于受其影響。在不朽名作《神女》中,阮玲玉所飾演的妓女身份,本來可以使鏡頭穿梭于那些充滿“現代性”的場所時更為便利,但導演吳永剛卻讓攝像機角度忽然下沉,聚焦在人們來來往往的皮鞋之上。這個低視角的運用雖可以被解釋為藝術創作上的考量,但是我們無法忽略攝影機對這種混雜空間進行“分層”表述的意識。或許是為了保持影像風格的同一性,女人的生活空間不停地穿梭在一個又一個古典而傳統的弄堂之中。此時,浮夸、繁華的上海都市景觀,僅僅在想要強占女人的流氓腦海中,與她的“媚態”通過二次曝光疊印在一起。
這種類似的例子可以一直列舉下去,但倘若那樣,似乎會使人們誤以為銀幕上的上海“現代性”一直包裹或隱藏在傳統空間的外殼之下。但是,先將這一范式闡明,有利于我們在第二部分的論述。事實上,更多的早期影片選擇將上海都市的現代性景觀顯露于外,并且沒有單純將景觀當作一個具象的客體,而是試圖像居伊·德波所說的那樣以景觀為紐帶來重構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無論是保守的還是進步的電影人,都曾嘗試利用這一關系通過銀幕來重塑現實,體現了他們以作品展示表現空間(Representational Spaces)的自覺性。同樣由阮玲玉主演的《野草閑花》,導演就將當時蜚聲滬上的“新世界”游藝場擺在了最突出的位置:歌女在這個富麗堂皇的地方與富家公子一見鐘情,也同樣在這里被利欲熏心的雇主強迫登臺表演,但最終卻得以與富家公子重修舊好。我們暫且無意分析語言上“新世界”的雙關意味,只是意圖指出:“新世界”作為當時上海現代性特質最顯著的場所,這一空間表象(Representation of Space)吞噬了一切意欲顛覆其象征的資本主義現代性秩序。故而,身世凄慘的歌女在這一空間的作用力下,帥氣的富家少爺才得以匍匐在地乞求原諒,獻上他的“真情”。
對于進步電影而言,在20世紀30年代的左翼電影運動中,創作者則更傾向將上海的都市性作為批判的對象,而不會像《野草閑花》那樣顯得保守。這時,銀幕上的空間實踐就更加不會被誤認為是一種簡單的造型技巧,他們的強烈目的在于質疑、瓦解或者顛覆依靠統治集團通過空間表象所構建的意識形態。對于當時的左翼電影人而言,電影是與國民黨的落后意識形態進行斗爭的工具,他們需要用電影來揭露國民黨的腐敗官僚統治,宣傳反帝反封建的中國近代歷史主題。例如,著名左翼影片《馬路天使》的開篇,一幢高聳入云的大廈顯示出都市環境點綴的“天堂”以及深藏于地表之下的“上海地下層”之間的對立關系。而且,生活在“地下層”的人們若是想要通過近代機械工業的產物“電梯”攀上大樓,來與掌權者進行協商或者達成某種和解,就注定了他們最終將要面臨分別或者死亡的命運。
當然,并不是所有進步電影都會將這種空間批判立場以如此尖銳的方式展現出來,還有一些進步影片在指涉上海城市空間現代性時,會采取更詩意與充滿暗喻的方式。因為空間實踐中的主導權力對異己權力的排斥和消滅常常掩蓋在合理的外衣之下,這就決定了進步電影的斗爭方式可能會選擇更委婉和迂回的策略。“電通”公司的《都市風光》就將上海城市空間當成了這樣的一個“想象的能指”,成為寄寓斗爭意識的表現性場域。這部影片中的“鄉下人”透過“西洋鏡”看到了令人炫目、流光溢彩的上海城市景觀,地標性建筑在一組快速剪輯的蒙太奇中分外顯眼,閃爍的霓虹燈看板在汽車車窗視角的運動鏡頭中不安地跳動,寓示著即將進入這座城市生活的他們同樣將在這里遭遇傳統與現代之間的二元對立所帶來的撕裂與掙扎。影片的結構本身就是富有寓言性質的,這些人在上海遭遇略顯悲劇的戲謔命運之后又回到了他們最初看“西洋鏡”的那個火車月臺,跳起了歡快的舞步——這里用影像類比了中國那句用來形容人生的古老諺語——上海城市空間的繁華絢爛與致幻誘惑不過是一場“鏡花水月”。
二、“紅色之外”:都市現代性的放逐與沖突
如果說解放前上海都市的現代性或多或少還暗含一些“先進文化”意義的話,那么新中國成立之后這種意義上的現代性則在影片中被明顯地遮蔽了。或者,創作者們以俯仰秩序顛倒的方式將其放置在正統話語的對立面來進行批判。這一轉換,必然會對銀幕中上海城市空間的建構方式產生深刻影響。一般而言,史學家常將1949年當作中國電影發展涇渭分明的分水嶺,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從銀幕中上海都市現代性的隱褪與漸顯層面來看,新中國的人民電影一定程度上也繼承了將“現代性”隱藏或包裹在傳統空間外殼之下的方法論,或者將傳統空間置換為這一時期處于絕對主流地位的革命話語。換句話說,此前“傳統性(落后)/都市性(先進)”的二元對立已演化為“都市性(落后)/革命性(先進)”的圖解。從這一意義上延伸,則可發現都市空間與“非道德”之間的等式,已然被都市空間與“非革命”的等式所代替。“由于種種歷史原因,上海文化本身的內在矛盾未被尊重和認識。相反,發展現代化大城市的內在要求往往被指責為‘資本主義’傾向而受到抑制。”自然而然,上海依靠殖民經驗建立起來的都市文化,很快被放逐在紅色的人民電影光譜之外。

圖2.電影《女理發師》劇照
但是,這并不意味著上海銀幕形象意義的消退。相反,這一范式的建立恰恰指向了此種銀幕空間發生了類似哈貝馬斯所說的從公共空間向公共領域(Public Sphere)過渡的轉換。當然,我們無須苛守理論家在建構公共領域這一概念時所堅持的資本主義社會前提,而是在結構上認定在這個銀幕空間中發生的價值傳導,已然變成了溝通國家與社會之間的公共空間紐帶。更重要的是,電影所生產的社會公共輿論所不斷論證的正是政治系統的合法性。上海都市空間中的“現代性”,亦是在這一過程中被推向了革命正統觀念的對立面。以電影為中介,國家與社會之間緩沖地帶被彌補,因此無論這一地帶所發生的行動是試探、協商還是沖突,它都不會對國家或者社會產生真正意義上的威脅或破壞。這樣一來,銀幕中的上海都市“現代性”即使處于被批判或邊緣的位置,也不會對客觀空間中的上海產生實質的影響。毋寧說,這種被批判或遭到邊緣的上海都市“現代性”成為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實現價值傳輸與溝通的有利條件。這正是《關連長》中的整座上海城市都處于等待南下的解放軍來拯救的境地,被火災包圍的幼兒們必須被說著山東方言的關連長所救出的原因,也是上海電影創作者此時對自身文化境地的體認。
然而,在這個空間客體傾向被象征性使用的語境中,如果上海都市的“現代性”遭到流放,那么又是何者來填補它所留下的位置?城市景觀又將如何在銀幕中呈現?革命性在國家意志的干預下是否會立刻替代“現代性”占據顯要位置?可以看出,一些影片采取了利用表現傳統和新興空間來掩蓋、遮蔽“現代性”的方法,這與上文所提及的《勞工之愛情》十分類似,而不同的則是二者的政治、文化出發點以及對待傳統與現代之間文化張力的態度。嚴恭導演的《滿意不滿意》中認為當服務員就是“伺候人”的主人公最終受到教育,得以把“為人民服務”牢記心頭,這一處理方式即是將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歷史語境置換為社會主義行業平等的現實狀態,而提示歷史語境存在的意象恰恰是“松鼠桂魚”“陽春面”等傳統上海美食。消費主義在這里不可思議地成了連接傳統與“現代性”之間的中間節點,甚至使二者從對立側歸向了同側。相似的還有《女理發師》,被稱作“剃頭匠”的理發行業在片中得到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正名”。影片展現了已然歷經社會主義城市改造的新上海,外灘建筑群在片中只剩下了一尊用來隱喻“夫權”的雕像,這意味著曾經是上海都市“現代性”最佳表征的地標性景觀的意義已被重新嫁接。值得注意的是,女理發師一家仍維持著最原始的作息方式——利用公雞打鳴報曉來提示時間——這或許恰是空間現代性遭到意義重新嫁接之后發生的矛盾。
從某種意義上而言,傳統性確實可以跨越“現代性”進入革命語境之中,因為《女理發師》的批判目標可能既非“現代性”也非“非革命”,而是殘余在人們腦海之中的封建思想——韓非飾演的丈夫宣稱他寧愿“梳辮子”也不剃頭。從而,傳統與連接“現代性”的消費主義都在這里被劃歸同一陣營。處于革命性對立面的要素增加了,這便使它們之間更容易顯現出沖突的特質,那么前述的那種遮遮掩掩的方法就未必行之有效。例如,《不夜城》批判的是資本家剝削工人剩余價值和非法牟利、《霓虹燈下的哨兵》中解放軍戰士們必須抵抗資產階級“香風毒氣”的誘惑,《年青的一代》將布爾喬亞式的生活情調與人格和道德品質掛鉤。不必說,這些上海都市的“現代性”批判都十分尖銳。尤其是上海電影制片廠的《年青的一代》所體現的自我反思意識,與當時歷史環境中盛行的“自我批評”之風不無關聯。這種對都市“現代性”的反身性批判,若參照前文所述的《關連長》,則可以發現十七年間上海電影人在都市空間體認上的功能性轉調。
三、“熒光色”:從知覺經驗到“舞臺裝置”
年湮日遠所帶來的歷史景深,使人們越來越難以透過模糊的濾鏡去尋找歷史景觀內部的意義。中國近代史中的上海,由于其城市形成過程的復雜性,使它成為電影用以制造“夢境”、制造“無意義”景觀的絕佳空間。一時間,“舊上海”成了一個充滿誘惑力的場所,馬路、酒吧、電車、霓虹燈、游藝場、旗袍、黑色風衣等演化為表征上海城市的符號。
但是,結合這一時期的創作者的身份背景來看——大多來自香港地區和臺灣地區,似乎這種對上海的表達又不成為問題。因為這些形象和符號系統,不過是他們自身曾經在場的想象性投射。同時,若是我們同意作品的意義只有通過作品本身才是可明確闡述的,那么關于20世紀70年代至21世紀初期前后中國大陸、香港地區、臺灣地區的電影創作中的上海銀幕形象建構,就不能完全被看做是“程式化”“刻板化”的機械復制。正是由于這種理論上的糾纏,使我們更愿意用“熒光色”而非某種特定的顏色來概括這個階段的上海銀幕形象。
所以說,我們僅能承認這時銀幕中的上海呈現出了某種“架空”特質,但這種特質只不過是我們審視過去的回溯視角所帶來的。尤其是當我們在重讀20世紀70年代前后港臺電影作品之時,不應忽略這些創作者青年時期的上海經歷。張徹的《馬永貞》開創了“上海灘”戲碼的先河,貢獻了他的“暴力美學”代表作。片中的外白渡橋、沙遜大廈、十六鋪碼頭和充滿民國風情的戲園為馬永貞這一悲劇的英雄人物染上了一層“血色浪漫”,突出了影片的風格化和故事的傳奇性。早年曾有上海經歷的張徹此時不知不覺間完成了以香港影像塑造上海空間的“地緣漂移”,把上海的銀幕形象引介至香港電影之中。對于張徹來說,這或許是一次略帶個人懷舊性質的影像實踐,但更關鍵的成因則是20世紀40年代末期香港與上海之間的電影資本和人才轉移,不僅使香港在“六七十年代徹底替代上海成為新‘東方好萊塢’”,也令香港地區影人的創作經驗中都潛藏了一種“上海記憶”。他們關于上海經驗的知覺是直接且統一的,因此反映在影像內容與空間上的形式就具有一致性。若借用梅洛-龐蒂的理論框架來看,這一系列以上海“租界-孤島-淪陷區”為背景的影片,以及影片中對上海城市空間的再塑造,實際上就是通過這些南下影人動蕩漂泊經驗中“我者”與“他者”軀體之間的內在關系而生成的。從這一意義上來說,這些看似刻板的空間意象就并非是“無意義”的,因為它們與這些影人所經驗的肉體知覺相聯。這種知覺經驗(Sentient Experience),之后也在關錦鵬的《阮玲玉》、侯孝賢的《海上花》中得到了傳遞。
然而,此后借助更廣泛的大眾傳媒電視的力量,香港TVB出品的電視劇《上海灘》將這樣的經驗進一步強化。它引起的“萬人空巷”的收視狂潮伴隨著人們的快感、愉悅與神往,結果將“舊上海”的標志性城市空間景觀作為一種程式化的美學意象固定了下來。受此影響的影片不勝枚舉,即使是張藝謀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和陳凱歌的《風月》亦未能“免俗”——中西合璧風格的上海城市空間已然變成了黑幫角逐和火拼的舞臺。可見,在以制造“夢境”與順應觀眾的審美習慣來追逐商業效益的電影娛樂工業之中,從文本和意象之中抽離意義并非難事。另一部以馬永貞為主角的影片《惡戰》光是從片名就大概能推測其主要內容了,而且影片在片頭處還用字幕宣稱“1930年的上海,這里只有一個道理,弱肉強食”,“鐵掌門”“斧頭幫”等江湖幫會在上海灘不可一世。《羅曼蒂克消亡史》中的上海都市也僅僅是展現“羅曼蒂克”氣質的布爾喬亞式生活的容器。這種上海城市空間建構的范式雖然已淪為一種簡單的“舞臺裝置”,卻頗受觀眾歡迎,并在近二十年的諜戰、黑幫、抗戰、商戰等多種類型或題材的影片中屢見不鮮,或已成為流傳度最廣、最深入人心的上海銀幕形象。
不過對于曾經到過或者如今生活在上海的人們來說,這種“上海灘”式的上海城市銀幕景觀無異于虛妄的“異空間”。他們即使向往布爾喬亞式的生活情調,也不可能無時不刻在擔心遭受幫派分子的襲擾。另一方面,在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浪潮下,都市現代性的復蘇對人的“異化”又是一個常常潛藏在銀幕內部的題旨。《股瘋》中沉迷于炒股賺錢而險些導致家破人亡的女性經歷就極具批判力量。影片中熙熙攘攘的大世界天橋、東亞飯店、人民廣場、肇嘉浜路展現出現代都市不同尋常的誘惑力。從香港地區來上海的“表弟”則是一名投資商人。上海似乎又重新變回了“冒險家的樂園”。雖然有人因炒股大發其財,但是我們仍能夠看見片中有許多人居住在上海城市中心周圍那些從屬性的、被分割開來的空間,人與人的差異又因財富的重新分配被強調出來。對于那些身處不同層次居所之中的人們,重置他們之間人際關系的恰是那個位于抽象空間之中的“看不見的手”——股票。這一被資本邏輯支配的壓抑性空間,解構了那些本來美好的社會關系。這也正是《姨媽的后現代生活》中那位拜倒在“現代性”的石榴裙下的姨媽最終選擇以“后現代”的方式逃離上海的緣由。
四、“灰色”與“熒光色”之后:紅色上海銀幕形象建構的未來
毋庸置疑,若是以顏色為符號對近代中國進行修辭,那么最為顯眼的必然是紅色。當代中國的顏色符號指向了極具民族性與革命性的紅色。在中國的“紅色地圖”中,上海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搖籃、左翼文化運動的重鎮,龐大的城市體量和五方雜居的城市布局形成了紅色政權得以發生發展的客觀環境。多數以上海為背景的左翼電影運動曾經幾乎確立了一種上海銀幕形象的紅色修辭系統,但卻因國民黨的排擠與抗戰全面爆發中斷了這一進程。
因之,頗為遺憾的是,在中國電影目前的上海銀幕形象譜系之中,卻無法有效地將“紅色”系統單獨提取。最為直觀的原因,就是“灰色”“熒光色”的銀幕形象譜系占據了歷史進程中的大部分篇幅。具有鮮明上海特征的城市文化要素,即便在主旋律電影中也是“灰色”或者“熒光色”的。且看,電影《開天辟地》中,上海都市的特征要么被壓縮為外白渡橋、電車、輪船等驚鴻乍現的文化地標,要么遮蔽于大量的室內場景與夜景中——革命事件發生在燈紅酒綠的、現代的北京“新世界”,卻每每隱于上海這座國際大都市的黑夜里,分別指涉傳統與現代的京滬雙城之間形成了一種有趣的文化張力。另外,《紅色戀人》中的上海都市地標亦成為特定時期奇特愛情發生的背景板,“紅色”成了“戀人”的定語而非前提,革命敘事在洋場的景片下欲說還休。《秋之白華》中,象征上海都市文化的電影院卻同樣轉瞬而過,傳統戲園取代了電影院這一更受知識青年喜愛、更為普及的公共娛樂場所,成為楊之華與沈劍龍久別重逢后的約會場所。另外,西餐廳這一現代性場所成為襯托主角愛情的背景板,通過聚焦于菜品和主人公的鏡頭,讓我們意識到即便是在紅色氣質鮮明的主旋律電影中,上海城市的形象仍要依靠“吃西餐”這種具有“摩登”意味的行為來強調。
可見,在涉及上海的革命敘事中,上海的都市空間呈現與敘事母題的表現之間產生了割裂,原因在于歷史上“摩登”的“灰色”與“熒光色”凝成了上海城市銀幕形象系統的“刻板印象”(Stereotype)。從最新發布的《上海紅色文化地圖(2021版)》來看或許可見端倪——上海的革命舊址、遺址和紀念設施等紅色文化遺跡多處于舊時“租界”區域之中。原法租界內分布著中共一大會址、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機關舊址、中國共產黨發起組成立地等見證中國共產黨誕生的重要革命遺跡,原公共租界內同樣分布有中共二大、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中共中央軍委機關舊址等諸多革命遺跡。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現代性的城市空間支撐了中共領導的革命活動。

圖3.電影《1921》劇照
但是我們應該認清,“現代性”與“革命性”修辭系統之間之所以存在齟齬,并非是現代性與革命性本身不能相容。事實上,革命話語中所蘊含的思想啟蒙意識正是催生現代性的原料之一。由于“現代性”與“革命性”的修辭慣性所導致的“刻板印象”,使得它們逐漸演化為兩個互斥意識形態體系的形象標簽,從而使兩者顯得格格不入。例如,“現代性”修辭系統中的意象一般呈現為小轎車、摩天高樓、百貨商場、小洋樓、舞會與電影院等;“革命性”修辭系統中的意象一般慣用煙囪、農田、炮火、紅旗及煤油燈等。應當明確的是,這個修辭系統僅是純語意的情節結構,因此這些對立意象所指向的實際是創作形式問題,即試圖讓觀眾以自動感知的方式取代審美感知,來形成一種具有延續性的認識慣習。也就是說,“現代性”與“革命性”的修辭僅僅只是手段,并且應當將它們從對應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
將各種修辭系統從上海城市銀幕形象的刻板印象中解放出來的關鍵在于體現革命性的“紅色文化”的包容性。它不僅限于對“革命性”或革命歷史的重新闡釋,而且包含在中國長期革命、改革與建設過程中形成的理想、信念、道德、價值,以及對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它的外延既包含近代以來的革命基因,又指向中國民族偉大復興的精神凝聚。作為承載歷史和現實之重要紐帶,其作用與價值正逐漸得到體現。從上海的左翼電影傳統這一文脈來看,歷來以上海銀幕形象色彩的數度流動反映的是主流社會語境的變遷,即便是欲說還休、或隱或顯的革命敘事,也確證了其對主流價值觀念具有高度敏感性。故此可以推斷,當紅色文化的當代價值得到強調,那么如今革命敘事對上海城市銀幕形象的再現,就會將變得更富有生命力。
我們應當這樣理解,“紅色文化”是上海城市文化精神的靈魂,但其襯托和突出的是上海城市“海納百川”聚合多元文化的氣魄,充盈著吳越風情的江南文化與兼容并蓄的海派文化本來就是上海紅色文化的重要注解。“紅色文化”的突顯不意味著對其它文化的揚棄。在這種開放、包容又創新的城市品格下,都市“現代性”在這一城市空間中不會與“紅色文化”相頡頏,本土性與世界性在其中得到協商,或可產生新的融合效應。
從這一層面上看,近期的主旋律獻禮影片《1921》就可以看作是一次以“紅色文化”來重構上海城市銀幕形象的有益探索。其中重要的是,“游藝場”“十里洋場”等“舊上海”意象在與紅色文化對接時,生成了一種別具風格的“紅色”上海銀幕空間形象。影片中,“天韻樓”上國際代表與中共代表商量建黨事宜,“大世界”中的蘇俄、中國與日本的三股共產黨勢力交織在一起,“十六鋪”前的地標建筑最初即是通過毛澤東的主觀視角呈現出來,這使上海的典型意象集群在紅色語境下完成了銀幕重建。后來,在毛澤東奔跑途中,作為背景的繁華租界與其切身經歷的斗爭回憶場景相交織時,中國近代的屈辱歷史就與上海城市景觀在內涵上產生了有力的“文本間性”。換句話說,當銀幕中的上海作為容器、紅色文化作為其敘述的母題時,各種上海典型空間形態均在同一個框架下得以共存。
從這一探索中可以看出,“紅色”上海銀幕形象的建構可以被看作一種對異化的銀幕形象進行超克的總體文化革新策略,而且是從脫離作為工具的“色彩”支配下的文化合理性的出發點來進行的。上述影像實踐初步說明,在當今“紅色文化”的內涵外延已得到拓展的時代環境下,建構能夠包容文化光譜中的其他色彩的“紅色”上海銀幕形象,成為上海城市銀幕形象的“主色調”并非虛妄之言。因此,我們期待一種未來的“紅色”上海銀幕形象,它既基于“紅色文化”內涵的全新拓展,又能將彰顯主流價值觀念的敘事寓于上海都市空間之內,并且那些典型的“熒光色”都市意象反而成為支撐這種敘事的底盤,從而形成更具開放性與包容性的上海城市影像的文化光譜。一言以蔽之,在“紅色”上海銀幕形象中,上海都市可以被展現為革命性、現代性和傳統性相互指涉、復合交融的文化形象。
結語
19世紀末,作家韓邦慶以他的言情小說《海上花列傳》(侯孝賢在1998年將其改編成了電影)塑造了一個近代轉型時期風花雪月、風情萬種的上海形象。第一回中,韓邦慶假托的作者“花也憐儂”初時站在一片“浩森蒼茫、無邊無際”的花海之中,因見美景而喜,又因感懷花兒沉淪于海而悲,導致他搖搖欲墜、跌進花海之中,方知花海乃是一夢。醒時,站在上海地面華洋交界的陸家石橋的他嘆道:“竟做了一場大夢!”這座隔開舊租界與華界的石橋,雖說象征著上海城市現代性與傳統性一分為二的界碑,然而“花也憐儂”的這個夢境,又似乎喻指了傳統與上海都市之間漫長而豐富的“城鄉文化連續帶”。韓邦慶像是在提示我們,無論是要理解上海傳統社群或是現代都市,都應將目光聚焦在這座意義駁雜、象征性豐富的“石橋”上來考察。因為橋梁的意義在于連接與延續。因此,對于聚焦上海銀幕形象的研究而言,就應避免將銀幕中的都市性與傳統性、革命性與現代性對立起來,而是要在二元對立的理論框架之外“橋接”城市形象內外的意義與邏輯。這說明,林林總總的上海銀幕形象生產,與現當代中國轉型發展的文化機制密切相關,也使這個形象系統具備了解決“城市主義”道德困境的功能,并且在內涵上提供了使銀幕中的上海呈現從由自然意志主導的“封閉色彩譜系”走向由理性意志主導的“開放文化策略”的通道。
同時,還應將“石橋”這一“連續帶”的空間意義轉化為時間,以歷時性的視角進行闡釋,避免使對銀幕空間意義的探索陷入僵局,并停滯于對各種空間意象清單式的整理之中。而且上海城市銀幕形象作為考察對象,則更容易將這些空間意象單純當作足以寄情的審美意象。因此,本文并無意于羅列一個上海城市銀幕形象的清單,而是試圖將這種銀幕的空間形象放置于中國電影發展的脈絡當中,并從最具有概括性的“色彩譜系”中進行提煉,以圖求得上海城市銀幕形象的“理想類型”,并將這一形象系統的未來寄托于具有兼蓄包容特質的“紅色文化”。
【注釋】
1羅崗.空間的生產與空間的轉移——上海工人新村與社會主義城市經驗[J].華東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7(06):91-96.
2[法]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第二版)[M].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24.
3[美]傅葆石.灰色上海,1937-1945中國文人的隱退、反抗與合作[M].張霖譯,劉輝校.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5.
4鄒依仁.舊上海人口變遷的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3-5,90.
5[法]居伊·德波.景觀社會[M].張新木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17:4.
6李天綱.人文上海:市民的空間[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4:217.
7[法]莫里斯·梅洛-龐蒂.意義與無意義[M].張穎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7.
8[美]傅葆石.雙城故事:中國早期電影的文化政治[M].劉輝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215.
9上海市測繪院.上海紅色文化地圖(2021版)[M].北京:中華地圖學社,2021.
10熊月之.中共“一大”為什么選在上海法租界舉行——一個城市社會史的考察[J].學術月刊,2011,43(03):115-124.
11周宿峰.紅色文化基本問題研究[D].吉林大學,20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