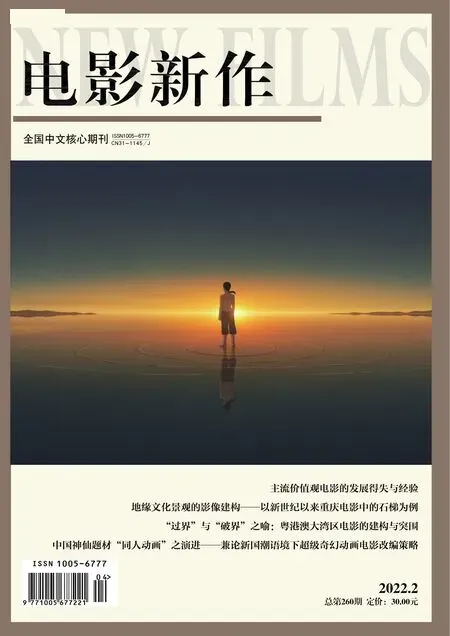民族·詩意·現代性:中國影像的文化反思
——評周安華新作《從地平線回望——中國影視的綽約瞬間》
張黎歆
在以科學理性為指導的當今社會,人看似以“造物主”的形象統治了世界,實際上,人也難逃淪為科學理性“仆人”的桎梏,成為其研究的對象和被觀察的客體。這種異化的“人”與“科學理性”的關系,無不折射出在“機械復制時代”作為主體的人對現代性反思的不足。在這樣的時代大背景下,周安華在《從地平線回望——中國影視的綽約瞬間》(南京大學出版社2020年版)一書中秉承人本精神,以民族性守望、詩意性觀照與現代性反思為思考標尺,敏銳且精準的把握了中國影視的發展脈搏,獨到的學術視角和高峰文化站位就文本展開了深度分析,開拓了中國影視研究的新視野與新高度,奏響了民族影視繼往開來的新篇章。
一、中國影像的民族性表述
無論是從近代中國求是圖存這一歷史底蘊出發,還是從亞洲多民族國家拒絕“東方主義”同質化的研究意義入手,民族性一直以來都是構成國家形象舉足輕重的重要部分。民族性的基礎是根植于歷史、文字和語言等方面的文化認同,而在多民族文學的范疇下,各個民族都在“表述”與“被表述”的過程中探求民族主體性的表達。電影是映射民族認同的三棱鏡,它們各自的民族性也在這樣的過程中得以呈現。《從地平線的回望——中國影視的綽約瞬間》緊緊地貼靠中國乃至亞洲地區深厚的歷史脈搏,將開闊的學術視野置于廣袤的民族文化語境的前景,從民族風俗里幻化電影具象的面孔,在影像重構的時代癥候中塑造立體的主體認同,于能動主體的現代性中傳遞民族電影的風骨與救贖。
作為民國電影研究的重要學者,周安華在“鏡頭春秋:電影與現代中國地緣文化”一章中,將目光聚焦早期中國電影的影像價值與民族化表述的議題。“相比于近代、民國那些早期電影階段,當代電影表現出更為活躍、更為凸顯的時代風貌與人文時尚的指證。”“文化精英意識”成為這一時期推動中國影像邁向高雅藝術的內在動力。金陵大學肇始的早期中國教育電影運動,使電影藝術大踏步走進大學神圣殿堂,肩負起“書寫生命理想,實現社會抱負”的民族復興使命。電影作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文化與思想表述的媒介,金陵大學的電影運動開啟了新興藝術與富國強民政治和文化抱負相結合的重要方式。作者觀照當下指出,中國民族電影的發展應具有超越時間、生命長度的思想,呼應啟迪民族認同的歷史使命。在全面考證中國二十世紀電影文化的生成機制和發展內涵后,作者提出了民族電影文學的價值復位:首先是電影跨文化、跨地域的意識;其次,在方法論上的突破之余,更重要的是路徑嫁接和視界復合。中國現代電影是中華民族的民族氣質與底蘊的外顯,也是中華傳統文化哲思的濃縮,考察一個時代的題旨、一個民族的悲歡離合。作為這一時期“與電影聯姻”最為親密的戲劇家曹禺,其作品將經典的文化內核鑲嵌進時代風貌中,且又跳脫出時間的禁錮,“使其十分自然地成為電影藝術改編最理想、最具價值也最富人氣的母本。”中國現當代文學與中國電影的發展是民族文化考究的雙文本,是過去與現代并置共生的基底,是對中國民族電影由平面進入立體反思的新路徑。
“文化危機在各種危機中乃最深刻之危機,因為文化是一個民族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是一個民族自我確立的本質特征。”同作為獨立于西方霸權話語外的國家和地區,“從中國到亞洲:區域電影現代風骨與姿態”一章關注到 “作為躍動的板塊電影,亞洲新電影其實不僅僅是地域影像的概念,它也是一種文化身份、一套表達方式、一種精神語匯。”新世紀亞洲電影多極影像的多元化表達,使得各民族所創造的影像具有鮮明的民族性。亞洲影像自身所賦有的跨文化和跨地域的雙重屬性,使其更具社會文化史和電影史的思考價值。“亞洲性”正孕育在亞洲電影的文化母體之中,它跨越了風俗、傳統與宗教,形成亞洲新電影自成一派的表意渠道和別具風格的類型趣味,進而令亞洲電影的‘內在根性’展露無疑。民族性和歷史息息相關,包含著強烈的文化歸屬感。“多極影像的確立和保持,摧毀的是霸權化、同質化,呼喚的是差異化、多樣化。”民族性的獨特價值在于其被賦予了時代變遷的屬性后,仍能保持異質性與獨立性。
亞洲電影的異軍突起,開啟了后“第三電影”(Third Cinema)的新時代,影像東方打破了既有殖民主義話語色彩的刻板印象,它們的出現為世界影壇帶來了新鮮的新東方主義美學。作者注意到,“在亞洲影像中則融匯著世俗化的儒教、佛教和道教觀念……隱含其中的東方價值,隱含其中的人倫情致和道德底氣,反映出亞洲電影對本土文化的高度自信,也使影片的人性主題獲得了與之極其匹配的廣大敘事空間和生活舞臺。”亞洲的民族電影在世界影壇上取得的成就,不是一味地追求極致的“東方主義美學”,而是表現出“兼濟天下”的“亞洲性”,關注底層、詢喚正義、堅守良知。

圖1.圖書《從地平線回望——中國影視的綽約瞬間》封面
二、作者意識的詩意性觀照
“詩意棲居”是海德格爾提出的“天、地、人、神”交織一體的維護人類生存家園的哲思,旨在以詩意,即藝術的形式回歸自然本質。 “詩意”是通過藝術的表達方式追求真理,揭示事物的本質。電影藝術亦如是。周安華的詩意胸懷其實質是對電影的反思,是對現代技術的批判。他認為,“一些研究者對流動態電影鏡像的迷失,說到底是一種觀念的迷失。”換言之,這些研究者僅將電影看作為一種傳遞哲學思考的媒介,是一種“超越藝術領域的表現方法”,一套“思考和揭示種群文化的工具”,而不是詩意的藝術。這一想法是需要警惕的,工具是藝術實現的手段,詩意才通往是藝術實現的目的。
“電影詩學:本體、嫁接與互文”以詩意為思辨,進而探尋事物存在的本質。作為第七大藝術的電影藝術,在誕生之初也經歷了“他者化”的陣痛。比較視野在電影研究學界是一個容易被忽略的方法,其無論是橫向的藝術門類的比較,還是關于縱向的藝術風格的更迭,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面對這樣“互為觀看”的尷尬境地,使得對電影本體的探索和明晰就顯得尤為迫切和重要。伴隨著與“他者”藝術的博弈,電影作為一門藝術的屬性被凸顯出來,這是對先前“電影作為媒介”誤判再思考的證明。 “重構的電影藝術理論,要以‘電影的藝術’為魂,觸及電影藝術本性、藝術方法、藝術邏輯等完整藝術理論架構。”電影大師作為電影理論的催生者與電影實踐的先行者,是鮮活的電影史,也是銀幕精神和藝術的標桿,觀照著電影藝術的蓬勃發展。文學作品中所蘊含的敘事母題,不論是小說的銀幕化再造還是電影與戲劇的凝結,都應在求同存異的思想指導下,回歸電影本體的精神、美學的原鄉。對于電影這類特殊的藝術來說,文化、哲學和邏輯都是從真實而感性的鏡像世界浮現而來,但電影研究要避免進入一個“曲高和寡”的誤區,即“面對同一個對象,于今的電影觀眾和研究者猶如山野里走岔了的兩個獵人,南轅北轍卻又不辨東西”。這要求我們要更立體、多維度地認識電影藝術的優長,探詢其成為大眾文化藝術的潛在性。
電影作為商品的屬性,在決定其藝術電影的生發外,又迅速衍生出具有票房導向的商業電影。細分之下,類型電影在商業性、藝術性和政治性等多重屬性的作用下,中國電影作品對現實社會的描摹和歷史底色的洞察,培養了一批眼界寬廣又各具特色的電影導演, 周安華的“類型、觀念和思潮:新國產電影縱橫”章節就此進行了深度剖析。“惟當我們能夠棲居時,我們才能筑造。”新中國的成立,為中華民族的飛速發展提供了安居樂業的保障和底氣。“人民性”是貫穿中國電影始終的創作宗旨,即使于改革開放后商業電影在尋求價值實現中,完滿地將人民性與傳奇性付諸鮮明生動的影像并有機融合,以營造夢想人生和視覺奇觀作為主體追求。當中國電影人開始重新認識市場價值時,對電影的理解變得更加豐富。電影美學與電影產業,亦如同大眾審美需求與大眾消費心理的先天契合性。受眾對商業電影的精神訴求,一方面體現為人們對真善美的真誠向往,另一方面體現為人們潛意識中對本我滿足的探索。電影藝術在精神和物質兩個層面源源不斷地提供謳歌生命的詩篇,令人們直接見證了社會轉型的文化三原色。 “中景現實主義”強調的觀眾與電影之間的疏離感,實際上“這些電影都以‘實誠’的態度直面生活,以即興手法捕捉常態社會情境,構成‘創傷敘事’和‘殘酷文藝’的特點”。在尋求價值實現中,它以營造夢想人生和視覺奇觀作為主體追求,讓人物有棲居之所,讓人性回歸人物本身,讓詩意蕩滌人性回響。
三、媒介政治現代性重寫
科技的進步為媒介融合提供了可能性,也對媒介政治的現代性重寫提出了挑戰。現代性是西方學者為了指稱和反思自身發展邏輯而創造的一個概念,它在誕生之初就隱含著“空間”與“時間”的雙重指向,這與媒介的“時空”二重性不謀而合。“現代性在總體性上反思現代社會生產、交往、生存和思維方式及其蘊含的思想觀念,進而為尋求一條發展的再生之路而提出的一個核心概念。”重寫現代性提供了另外一種理解現代性、具有解構主義和建構主義雙重特征的視角——“以‘重寫’為準則解構‘現代性’的基本特征,并在‘重寫’方法論指導下重塑‘現代性’的基本特征。”《從地平線回望——中國影視的綽約瞬間》對媒介政治大理路和大取向鞭辟入里的剖析,是在現代性事業展開之前的一種清醒意識、反思精神與開放姿態。
“電影的現代性”應被稱為一個包括形式上的現代審美特征與內涵上的現代意識的雙重概念,而后者才是理解“現代電影”的關鍵。它們都努力告別一種宏大敘事,拒絕一種意識形態的質詢。在“當代中國銀幕政治的整合觀照”一章中,中國電影在建國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不論是“老三戰”的血火記憶,還是謝晉電影的情感化表述,實質上都是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身份的確認和歸屬感的再表達,以及對政治敏感性和社會責任感在特殊歷史時期的反思。周安華提出中國銀幕政治的“歷史質感既扎根于民族文化的沃土,也飽含不同文明之間的碰撞,構成了與特定政治、文化深刻的互文關系。也形成了對社會大眾的廣泛精神和美學感召”。通過對“第五代導演”“第六代導演”乃至“新生代導演”作品的梳理和歸納,“個人-集體”與“家庭-國家”的這兩組相互作用,互為依賴的關系的闡述,是對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電影意識形態化的時代反思。這一時期的電影以期獲得主體的認同感,進一步完成公民身份的自我確認,同時也在社會主流意識形態的注視下,實現了電影傳播的高效賦能,成為新中國一種罕見的“公民教育文本”。文藝片的成熟,將個人書寫的歷史隱喻和被詮釋的都市人性拼貼、雜糅進更為私密的個體記憶當中,在本土堅守與跨文化博弈的過程中,富有時間哲思的新的時代話語的生成,標志著對既往銀幕政治權威性的消解與再建構。中國“現象電影”,基于后現代文化雜糅、拼貼的特點,轉化為與時代、與當代審美文化緊密相連的時間邏輯,并借此成為電影現代性的一個重要緯度。
作者前瞻性的學術思考還體現在“媒介融合:大理路與大取向”一章中,率先提出“電視媒介語言是一種復合性的、兼容性的視聽媒介語言,影響人們的觀念、情感和態度,實現電視自身的意義傳遞和價值載荷”。相較于資源傾斜度較高的中央媒體,區域性媒體的良性發展應遵守“高位運行原則”,即“高起點的貼近性、分眾化的親和性和定制化的服務性”。作者的思考并未局限于此,作為集電視藝術之大成的電視劇藝術,本書的后兩章以“電視劇藝術:奏響大時代樂章和世俗的美學”為發問,“叩響了對現代性圍困下‘人’的赫然在場這一哲學命題的大門”。視是真正的現代藝術,來自現代,映射現代,而現代性是內嵌于電視的密碼。在流動的時間長河中,立體而開放地審視電視的現代性,憑依民族電影的主體身份,確認不同的熒幕實踐其現代性追求的價值,是學術界應當堅守的方向。現代科技對于人的異化,使藝術成為心靈救贖的解藥。電視劇應本著人本主義精神,“創作者要在主流意識形態和大眾日常生活之間找到一種‘相關性’,盡量消除主流意識形態和傳統精英美學與大眾日常生活之間的距離”。它建構著民族精神,體現著民族道德情感的核心價值,并以其豐富的美學意味與歷史風貌,展示包括中華民族在內的人類共有的博大胸懷和歷史責任。電視劇藝術現代性的重寫,從來都不是對現實膚淺的刻畫和造夢工廠的升華,而是在貼近生活真實紋理的基礎上,譜寫出一首平民英雄的信仰組歌。它建構著民族精神,體現著民族道德情感的核心價值。
《從地平線回望——中國影視的綽約瞬間》是作者多年來保持高學術活躍度的同時,對所深耕的影視領域持續性哲學思考的集合。全書以詩意的語言串聯起電影美學、電影理論、媒介融合、文化研究、意識形態批評等多領域、跨文化的論題,及淺入深的論述結構、鞭辟入里的學術分析,在給人以思想啟發之余,又有如沐春風的豁然開朗之感。值此中國電影票倉傲視全球之際,本書的出現如清泉般沁人心脾又恰逢其時。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書”為鏡,可以知得失,綽約的瞬間,亦是影像的永恒。
【注釋】
1周安華.從地平線回望——中國影視的綽約瞬間[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22:29.
2同1,38.
3羅藝軍.中國電影與中國文化[M].北京: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1995:2.
4同1,86.
5同1,90.
6同1,88.
7同1,8.
8同1,6.
9同1,5.
10同1,79.
11韓慶祥.現代性的本質、矛盾及其時空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16(2):9.
12王依娜.后現代敘事的建構:“重寫現代性”及其方法論意涵[J].社會科學論壇,2022(1):191.
13同1,41.
14同1,113.
15同1,119.
16同1,143.
17同1,1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