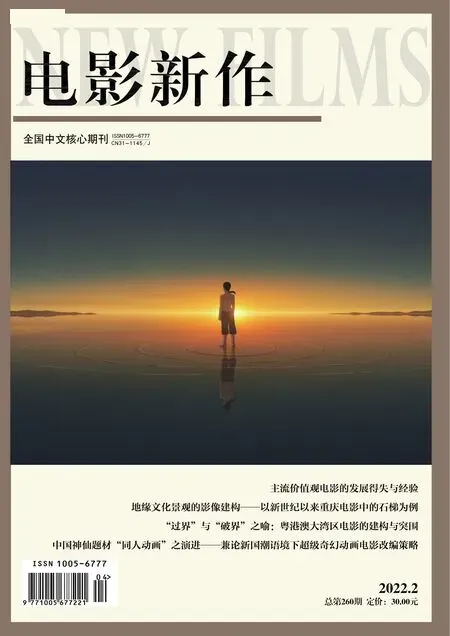“游改電影”的跨媒融合與空間重塑
原文泰 汝中雨
游戲與電影,在表現形式和娛樂功能上存在一定的相似度,某種程度上可謂異質同構的媒介形態,二者的發展也常伴隨著對彼此媒介特質的借鑒與融合,進而衍生出諸多新的藝術形式或游戲形態。基于人類視聽感知的特點,電子游戲為玩家們營造了一個白日夢式的世界,其交互性特征可以將游戲者拉入虛擬情境,并通過一系列情節敘事與獎懲機制實現對玩家情感體驗的控制。當下,電子游戲吸取來自電影的創作經驗,在游戲體驗上進一步向著沉浸感和電影感進化,電影業則嘗試具備雙重媒介機制的交互式電影與引擎電影等跨媒介融合產物,或將擁有強大市場影響力的游戲IP改編成“游改電影”。“游改電影”擁有著更為明確的電影身份,并且在影像層面表現出直觀的媒介互融性以及多層次的融合深度,這使“游改電影”成為討論影游融合的未來實踐中極具代表性的文本。
一、游戲與電影的跨媒融合
“游改電影”并非近些年新興的亞類型片種,1993年上映的電影《超級馬里奧兄弟》改編自任天堂游戲《超級馬里奧》,雖然人氣與口碑慘遭滑鐵盧,但此類IP改編卻被整個行業看到了商業先機。此后,一系列“游改電影”紛紛脫穎而出,產生了諸如《寂靜嶺》與《古墓麗影》系列、《生化危機》系列以及《憤怒的小鳥》等獲得不俗票房成績的商業影片。建基于游戲IP自身強大影響力而來的“游改電影”,其訴求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利用IP的強大影響力和既有的故事體系、世界觀等進行改造,并獲得游戲玩家與電影消費者等多個粉絲群體的認可,進而追求更好的票房回報。為了使得原始玩家能夠響應電影的號召,“游改電影”需要將游戲原作中的視覺元素與游戲機制進行一定程度的移植、改造與再造,創作出能夠引發玩家共鳴且符合電影美學的電影作品。
隨著游戲IP的不斷開發,“游改電影”在創作中也逐漸積累了一定的類型與美學經驗。但總體來說,該類型改編依舊處于探索發展階段,且愈來愈多新型游戲形式的出現也為“游改電影”的創作提出了機遇和挑戰。同時,很多“游改電影”陷入了既被游戲玩家指責原作精髓盡失,也被電影觀眾批評敘事過于受限于游戲的窘境。因此,游改電影以游戲為基礎的二次創作過程并不簡單。創作者需要關注的不僅是從游戲到電影的敘事策略的轉換,還要從二者的媒介機制出發,挖掘出各自不同的美學表意體系,不只關注視聽表征同時還需涉及感官機理層面進行思考,而在這一過程中,圍繞不同媒介形態進行空間重建是關鍵的思路。

圖1.電影《古墓麗影:源起之戰》(Tomb Raider,2018)劇照
在電子游戲的美學體系中,視覺畫面占據了主體位置,其主要由游戲美工部門負責,范圍包括游戲的場景設計、角色的形象設計以及操作界面中的技能效果等涉及視覺表現的建構與制作。電影畫面的視覺組成也大同小異,不過其生產媒介變成了經由導演策劃的攝影機。在電影對游戲進行畫面轉譯的過程中,游戲的場景設計是電影空間的主要參考,但由于兩者媒介機制的不同,電影在空間的視覺生成、質感塑造以及意義表達上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而媒介屬性則是觀察與理解游改影像轉譯策略中的重要支點。
相較于電影而言,電子游戲的空間具備著更強的完整性與可重復性。從影像生成的角度,計算機語言的數字符碼是電子游戲的根本基因,游戲影像的虛構性與交互性共同構建了玩家沉浸式的幻覺機制,呈現出特殊的空間性質。從本質透視,電子游戲的空間是一種素材數據庫的組成,無論是較為簡單的像素塊游戲,還是如今在技術上大大提升了空間細節與畫面質感的大型RPG游戲,電子游戲影像的視覺成像無論表現出多么惟妙惟肖的畫面效果,其實質仍然為定性的數字編程。“視頻游戲本身建立在0和1的計算機二進制符碼之上,游戲空間也是由程序和數據庫文件共同構建完成。”這也就說明,游戲影像同程序之間存在著核心的對應關系,只要計算機語言呈現為確定的排列,游戲中任何人性化的呈現都在被劃定的可知范圍內,這意味著電子游戲的空間具備一種可預知的固定性。當游戲空間進行復雜的素材組成時,玩家可以在個人操作與游戲意愿的雙重作用下實現對空間可能性的觀摩。這不僅僅得益于游戲影像的定性生成,還有賴于在數字化影像生成過程中攝影機的“消逝”,使得游戲空間形成了一種閉環,整個空間樣態在數字程序中建立出自身的完整性。同時游戲機制也在攝影機的消逝中響應著玩家對于空間的完整感受,體現為游戲程序向玩家提供了一個可手動控制的全方位視野。以RPG游戲來說,玩家可以通過控制搖桿來實現對當前場景的視覺環繞,并且這種觀察不受制于如電影攝影機所造就的影像流動與綿延,玩家可以憑借個人操作對游戲內畫面進行幾乎任何視角的停頓與凝視。此外,游戲空間的完整性還在于游戲在關卡內向玩家提供了較為整體且固定的空間體驗。例如,在平面化視覺游戲中,玩家可以將當前關卡的空間景象盡收眼底。而互動性較強的RPG游戲則在對應的關卡中給予玩家一個章節式的時空,玩家可以進行自由的穿梭,只要有操作意愿,就能夠對整個空間進行較為全面且可重復的瀏覽。
而傳統電影則有賴于現實空間進行生產,無論是光學膠卷還是數碼攝像,電影的視覺空間都源自鏡頭對物質現實的信息攝錄。因此,在攝影機記錄影像的時刻,電影空間就已成為被攝制器具占據、被景框切割的存在,成為現實元素與藝術形式的合成中介。愛因漢姆·魯道夫對電影空間言之為:“他不僅客觀地表現世界的面目,也主觀的表現世界。”“他能把現實中互無關聯的事情與物體之間建立象征的橋梁。他干預自然的結構,使具體的物體和空間成為顫動的、分散的幻影。”居斯塔夫·福樓拜則巧妙地指出了電影空間的特質,認為電影空間如同一個濃縮的宇宙空間,在電影鏡頭的觀察下展現出多重表意功能,并在運動的綿延中傳遞出超越性的情感。“誠如德勒茲所言,宇宙作為普世性變幻、波動、廻蕩的宇宙影像;生命以(身體)間隙和(思維)黑屏在宇宙中確立‘不確定性中心’;那么電影攝影機感知作為機器意識則既非此亦非彼,它在兩種方向和意義上開拓了非中心、解框架的模態,而又與作為‘不確定性中心’的生命影像相連接,因而在宇宙與生命之外開辟了存在的第三面向。”探討游戲與電影鮮明的空間差異,可以更好地思考“游改電影”對游戲的空間改造。
如今,電影與游戲在生產、觀影與傳播上也都發生了巨大變化,無論是電影觀眾還是游戲玩家,接收影像的方式都有了更多選擇,如電腦、手機、平板等多媒體形態都可以作為觀者面對影像時的終端平臺。游戲玩家出于對游戲運行要求與玩樂體驗的考量可能相對謹慎地切換交互平臺,而電影觀眾則可以在流媒體平臺更為快捷與方便的進行觀看,傳統觀影的空間與機制也就此分化。“按曼諾維奇的說法,電腦屏幕是一種‘交互屏幕’(interactive screen)。數碼視屏的交互特質讓影像從與觀眾的站立狀態中平躺了下來,以一種臥姿的方式呈現在人的眼下。影像松弛了下來,觀眾也松弛了下來,影像與觀眾的關系也從緊繃的線性邏輯中松弛了下來,觀眾以一種類似閱讀小說的方式與平躺的影像進行互動,移動、觸摸、選擇、刪除、傳遞、評論等等,在生理和心理上與影像達成了高度私密的親密關系。數碼視屏消除了影像與觀眾之間的物理距離、等級關系和線性結構,回到了觀眾的手中、懷里、膝上。”游戲的制作團隊在生產游戲的過程中便會考量到游戲所要運行的主流媒介平臺——電腦、手機或者電視等,因此在游戲設置中會進行視覺界面的兼容,并且會依照運行平臺設計最佳的視聽構建體系。當“游改電影”對游戲進行視覺改編后,玩家在觀看影片時也會形成不同的感官觸動。
對于游戲觀眾來說,他們在觀看電影時往往會帶入自身的游戲經驗,因此對電影的欣賞也會有一套更為復合的感知體系。克里斯蒂安·麥茨在揭示觀影是一種類似白日夢般的幻覺體驗時,談到了人體如何通過電影接近對真實世界的感知,以及電影又是如何在真實與虛擬中呈現了模擬的空間。“那些被電影的黑暗的子宮殘酷地拋到門廳的明亮、刺眼的光照中退場的觀眾有時有一種剛醒過來的人所具有的那種迷惑的表情(愉快的和不愉快的)。離開電影院有點兒像起床。”根據克里斯蒂安·麥茨針對擬白日夢的闡述,看電影意味著觀眾同電影產生交融并幻生出知覺移情的情感狀態,從而沉浸在半夢的感知里。“游改電影”則對這一觀影機制進行了再度鏈接,觀眾不僅僅將自身帶入銀幕內的虛構空間,并且在自身、電影和游戲之間形成相互糾纏的觀影狀態,最終達成流動和重疊的觀影體驗。這一方面來源于對游戲影像的視覺心理慣性,另一方面也與游戲數碼視屏同觀眾的距離關系和線性結構的獨特變化相互影響。當跨媒介改編發生時,作為媒介中的主體——觀眾,就不得不遭受心理經驗與心理認同上的多重沖擊,并對游戲媒介中業已形成的主體印象進行思考,最終在新的媒介空間中完成自我的重構。正如克里斯汀·達理沿襲德勒茲影像本質的思路所提出的,“在‘電影3’中,電影不再以一種統一的、不變的藝術形式存在,而是參與到跨媒介互動的世界中,是一種用者的電影(cinema of user)。達里的觀點與羅德威克的看法相互呼應。羅德威克在談到數字影像的特點時說,‘觀眾不再被動地屈從于影像中那不可逆轉的時間流中,而是在看與讀之間變化 :一邊沉浸于觀看一邊熱衷于操控,兩者處于一種相互交疊的狀態’。”
二、“游改電影”的空間再造
如前所述,正是由于游戲與電影在媒介形態上的顯著差異,讓“游改電影”在空間呈現與觀眾的情感體驗上呈現出特別之處,它既要對游戲中單薄的視覺指意進行媒介改造與審美填充,又要顧及游戲玩家和電影觀眾等不同群體的觀影期待。從空間的視知覺轉換上來講,這一跨媒介過程可以概括為三方面,分別是空間完整性的解構、放大以及視覺影像的綿延化。
首先是電影對游戲敘事空間網絡的解構。以游戲《魔獸世界》來說,原作擁有宏大的世界觀及復雜的敘事背景,建構出眾多具有不同設定意義的游戲場景,如地獄火半島、黑暗之門、鐵爐堡等地景式的關鍵空間,在玩家長期的游戲經歷中逐漸轉化為具備情感特質的視覺符號。因此,對游戲空間重新建構的過程,便是“游改電影”如何讓電影空間成為感召游戲玩家情感的有力工具的過程。這就要求“游改電影”能夠將復雜的游戲線索、視覺空間進行準確解構,并重新合成能夠勾連玩家游戲記憶并顧及電影受眾的敘事模式。在《魔獸》電影版中可以看到,一些具有關鍵敘事意義以及玩家記憶的場景被保留下來,如暴風城、卡拉贊、黑色沼澤等游戲中的關卡式場景。影片將游戲世界觀中12個族群之間,部落與聯盟的沖突精化為獸人部落與人類聯盟之間的沖突,體現出“兩個世界,一個家園”的核心主題。在經過策略性的刪節之后,故事從人類和獸人兩種身份陣營進行雙線敘事,又盡可能集合了游戲中的關鍵角色參與劇情,盡量滿足各個玩家的共鳴感。關鍵場景黑暗之門是兩條敘事線索的重要交匯點,古爾丹在使用邪能將家園生態嚴重破壞后,獸人不得不試圖通過黑暗之門進入艾澤拉斯開辟新領地。然而,黑暗之門的開啟需要有艾澤拉斯的邀請方能進入。由此,艾澤拉斯出現的叛徒自然成了一個敘事懸念,兩條敘事線索也在此交匯。影片將這一場景在游戲原畫的基礎上進行了一定程度的視覺改良,紫紅色天空下的黑暗之門變成了黑褐色的巖石大門佇立在烏云之下,烘托出蕭瑟陰冷、充滿危機的心理感受,成為電影中視覺震驚體驗和敘事高潮的重要空間。
其次是電影對游戲空間特征的還原與放大。受制于數字技術的電子顯像,游戲畫面在動態呈現畫面時對視覺精度的要求遠遠低于電影,這一方面使電影在還原游戲空間形態時擁有提升質感的空間,但同時也對電影的空間建構提出了要求。從“游改電影”對游戲精神的傳承來看,電影所呈現的空間風格應該同游戲原作形成融洽的承襲關系。但電影的敘事顯然異于游戲,從敘事視點到故事內容等層面,都需要增添新的劇情和框架,這也就不可避免會衍生出與游戲不同的敘事空間。而融洽的空間關系對于“游改電影”至關重要,電影創作者解決這一問題的路徑,主要集中在將游戲的原有空間特征放大表現,在視覺比例、畫面色彩以及文化特征等方面對新的敘事空間進行建構。無論是電影《寂靜嶺》追求游戲元素的現實還原,還是影片《生化危機》試圖建構新的風格化敘事空間,其空間本身都不再是游戲原作中大量二維平面的組合。尤其當空間進入敘事后,它不僅成為具有視覺表征意味的符號,而且還附攜著文本的多重表意功能。例如,電影《寂靜嶺》中通過實景搭建還原游戲里的寂靜嶺小鎮,在建筑風格上參考了游戲原作進行仿真建造,如教堂、醫院等。在內部空間,電影利用美術置景將游戲中的怪物以及空間形象進行銀幕細化,譬如在《寂靜嶺》游戲中怪物的視覺表現較為風格化,更多通過外形的鮮明特征如三角形頭,斷肢血跡等元素進行驚悚表現。而電影版則邀請了專業的身體表演者穿上特制衣物進行扮演,觀眾不僅能夠在銀幕上識別原作中的恐怖形象,且經由電腦技術后期調節的身體比例等元素也加強了恐怖感。再如,影片《古墓麗影:源起之戰》上映之后,有許多玩家類觀眾指出該片在墓穴等空間場景的設計上不僅出現了細節疏漏,而且在整體風格和敘事邏輯上都與游戲呈現的具有較大差距。譬如,原作中的廟宇、皇宮等大小不一的各式建筑均充滿著神秘又厚重的古典神話風格。而在電影中卑彌呼之墓雖然在視覺上更加精細化了,但原作中的空間氣質卻沒有被沿襲。此外,墓穴中的塔樓呈現出的粗糙質感,以及原作中充滿挑戰的機關謎題被轉化為粗暴簡單的空間裝置等均引起了眾多玩家類觀眾的詬病。
除了影像本身,觀賞空間的環境差異也影響了“游改電影”時空改造的策略。玩家的游戲環境往往相對明亮,為了適應這一特點,游戲制作者在色彩表現上更傾向于設計出高對比度、飽和度的畫面效果,這能夠讓玩家更易聚焦且更能激發游戲的欲望。但對于電影來講,過于飽和的色彩呈現在黑暗的觀影環境中常會顯得突兀(除非這是創作者獨特的個人風格),從而影響作品的電影質感以及觀眾的沉浸式體驗。所以在“游改電影”的畫面設計中,創作者需要在游戲原作的視覺風格上加以改造,結合敘事意涵及情感氛圍來進行恰當的藝術表現。在電影《魔獸》中,原本為紫紅色基調的地獄火半島被呈現為灰青色,而游戲中以亮藍色為主的鐵爐堡在電影中則是偏冷色調的黑白色。雖然相較于游戲原作的畫面有了鮮明差別,但是在影院的觀影過程中這樣的轉變反而照顧了觀眾的審美經驗,并與電影中的時空塑造成為一種整體式的空間體驗。顯然,“游改電影”對于游戲空間的放大是一個危險的契機,它一邊要求創作者應注重空間質感與空間細節的完善,同時也需要增加審美表現與文化內涵,畢竟“游改電影”的創作并非單純是游戲的電影化,而應遵從電影創作的邏輯且進行更好的藝術表達。

圖2.電影《魔獸》(Warcraft,2016)劇照
最后則是“游改電影”對于游戲空間的體驗改造。時間是電影藝術的重要維度,電影表現為時空中的連續運動影像,觀眾在銀幕前欣賞著創作者精心策劃的影像序列以獲得生動的情感體驗。而游戲影像則主要通過玩家的交互行為進行演繹,互動作為游戲的核心機制使得游戲空間也必須服從這一規則進行建立。如果將游戲空間比喻為立體的沙盤,“游改電影”在對游戲原作嘗試進行還原的過程,則是在立體沙盤中尋找“影像切片”的過程。為了使電影空間能夠更好地勾起觀眾的內心情感,不僅需要在畫面視覺上進行刺激,同時也需要對運動的影像本身進行情感施力。所以,創作者需要提取沙盤中最具情動價值的“影像切片”來進行鏡頭組織,以生成擁有獨特電影感知的時間影像。例如,影片《寂靜嶺》將游戲中的寂靜嶺小鎮進行物質復原后,在空間的影像表現方式上移植了一部分游戲原作中的鏡頭段落——車禍時充滿迷霧的公路等場景畫面,制造出了與原作內核相呼應的影像神秘感。顯然,攝影機可以通過多種方式對游戲中的空間進行復原,但對具有情動價值的影像切片的提取則可以最終組織為具有情感召喚力的運動影像,這種組織方式并非不動的切片與外接的時間形成的電影錯覺,而是如德勒茲所言的“心智質料”,“這種心智質料由運動、思維方式(前語言影像)和視點(前意義符號)構成,其實際作用在于構成完整的‘心理機制’,即構建某種語言的可陳述性”。
三、蒙太奇與長鏡頭的感官交互
伴隨著技術升級,電子游戲產生出更多的游戲類型,并在游戲效果、操作性以及故事性上有了長足的發展。尤其在視覺表現與交互性上,電子游戲體現出對電影藝術形式的參考與借鑒,其中以大型RPG游戲為代表,這也是大多數“游改電影”的重點開發類型。在游戲與電影相互借鑒的過程中,蒙太奇與長鏡頭兩種基本的鏡頭方式是兩者作為影像媒介共通的表現形式。

圖3.電影《古墓麗影2》(Tomb Raider 2,2022)劇照
在RPG游戲中,影像主要由玩家操作的運動游戲界面與某些游戲節點中程序設定的規定影像所組成,而無論哪種形式,游戲都在利用蒙太奇或是長鏡頭的方式進行著視覺組織。當電子游戲以影像的方式進行呈現時,也就昭示著這個可視的畫面存在著一個虛擬的攝影機,代表了玩家以虛擬空間內的視角,持續地跟隨游戲角色進行探索。同時,玩家的交互性操作則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攝影機”在游戲場景空間內的場面調度。用電影的形式去理解,這一互動場景就如一個可操作的長鏡頭,既靈活又單薄,既機械又自由地貫穿在游戲時空內。“游戲并不具有電影在時間上和空間上所具有的靈活性。這一明顯的缺失,對于玩家來說,正是獲得游戲空間在場感和控制環路需要付出的代價。”電子游戲中長鏡頭的特點在于它同人物和空間的關系較為樸素,系統往往會限定玩家或者由玩家手動調節一種舒適的被攝距離用于觀察與執行游戲操作,在玩家適應這種被攝距離后畫面將會相對固定地保持鏡頭與人物、空間的位置。其次,游戲過程中玩家角色始終處于視覺中心,鏡頭能夠以游戲操作對象為中心進行全方位的視野轉動。在游戲《寂靜嶺》中,玩家可以通過旋轉角色位置對空間進行整體觀察。相較于電影,游戲鏡頭的調度權掌握在玩家手里,能夠讓玩家更主動、更有策略地觀察與捕捉空間信息,然而由于位置關系的鎖定與玩家操作路線的局限性,長鏡頭無法在空間內實現個體更自由地游移,也無法通過景深對空間進行多義呈現。因此,在游戲的規定性的限制之下,長鏡頭多利用場面調度來渲染游戲空間的氛圍,增強玩家的情緒體驗或者交代人物與時空內的多重人物關系等,如游戲《古墓麗影:崛起》中勞拉·克勞馥同船長等人在屋子里的對話場景,長鏡頭的調度不僅幫助玩家迅速認識到新版本的游戲環境,同時還掌握了游戲內的主要人物性格以及人物關系。
“游改電影”則利用長鏡頭對空間表達進行了更為完整的視覺修繕,同時結合游戲的視覺特點做出更符合電影美學的意涵表達。在游戲《寂靜嶺》中,主人公在表里世界的不同空間內穿越進行線索搜集與游戲任務,這些進程的生成需要依賴鏡頭跟隨玩家所進行的主動操作來實現,這也決定了長鏡頭的表現形態。而電影《寂靜嶺》則通過長鏡頭對觀眾以及主人公實現了主動牽引,攝影機利用景深以及構圖等方式將一些游戲中存在的關鍵信息隱藏于電影畫面中。譬如,母親羅斯深入寂靜嶺后在各個地點之間穿梭尋覓,游戲中這些地點的位置需要玩家通過打開地圖或者解鎖一些機關來進行線索收集。而電影則將地點名稱以及敘事伏筆隱藏在前景或者景深處,通過鏡頭的推拉來對人物進行指引,以此提醒觀眾注意到一些重要的空間信息。這些方式既保留了游戲玩家的互動性,也實現了長鏡頭藝術化的電影表現,從而在游戲視角的主觀性與電影視角的客觀性中實現轉換。在長鏡頭對空間進行調度與呈現的過程中,“游改電影”的創作者將有意設置的空間氛圍元素流入觀眾視線內。例如,彌漫的濃霧,現實世界的大雨,飄落的雪花,忽明忽暗的燈光和銹跡斑斑的鐵絲網等,這些畫面元素在鏡頭的游移中悄然影響著觀眾的視覺注意,打破了游戲時強目的性的搜索,更側重于意境的營造和情感的烘托,不僅將空間在視覺上完整化,也將觀眾的感受綿延化了。因此,電影的空間變成了德勒茲所言的情動的集合,是“把知覺(perception)、情感(affection)和定見(opinion)的三重組織打散,代之以一座用感知物(percept)、感受(affect)和感覺(sensation)的聚塊構成的代行語言職能的紀念碑”。
此外,蒙太奇的思維也被游戲制作者應用在視覺表現或游戲機制中,典型體現在游戲給予玩家的一些規定性影像。例如,《古墓麗影:崛起》等游戲,在玩家進入非戰斗狀態的敘事節點時會暫時失去操作,游戲會呈現劇情段落,讓玩家沉浸于游戲角色并享受影像敘事中的情感表達,而且影像段落往往也承擔著游戲敘事的關鍵信息,需要玩家密切注意。由于交互性的短暫消失,創作者會在這樣的劇情段落使用電影化的表現手法,并借助蒙太奇等視聽手段對玩家的注意力進行持續吸引。蒙太奇的使用,一方面可以切換視角,讓玩家從游戲狀態時的單一視角脫離出來,并在聲畫關系中與角色實現情感互融。另一方面,蒙太奇可以在短時間內快速交代新的人物信息與游戲線索,讓玩家掌握游戲任務與相關信息,從而提升游戲效率。在玩家重新進入游戲狀態后,蒙太奇則體現為連續的游戲影像和玩家實施操作觸發特定畫面效果的剪輯方式。例如,游戲《寂靜嶺》中,玩家可以在搜索空間內的信息時進行相應操作以實現鏡頭的拉近與分切等。整體來說,蒙太奇在游戲中對時空的操控能力和藝術表現力還存在一定的局限。
“電影的奧妙在于它是一種蒙太奇的拼貼剪輯,從格里菲斯和愛森斯坦等采用蒙太奇技術以來,電影就擺脫了單純的復制既定對象的生產流程,而是轉向了另一種生產,即潛能的生產。”而在將游戲影像化的過程中,“游改電影”則更巧妙地利用蒙太奇將復原與改造后的空間細化,以強烈的奇觀性與指向性特征試圖抓住觀眾的注意力,展示出影像空間的潛能。《生化危機》系列電影為了表現游戲設定中末日世界的殘酷與危機四伏,不僅設計了大量驚悚可怕的異形形象,還構建了較為宏大且充滿奇觀性的末世空間。尤其在《生化危機6》中,創作團隊打造了各式奇異的空間形態,包括坍塌的摩天大樓,充滿異形的荒野,科技公司的地下裝置等奇觀景象。在人物于不同空間內斗爭的段落,電影以快速的蒙太奇進行呈現,在細碎而凌厲的畫面交替中,空間也被解構為不同的圖形碎片,以直接的視覺圖樣進入觀眾的視知覺,塑造了景觀的視覺震撼與敘事節奏,這與蒙太奇在游戲中所體現的功能有本質的不同,是屬于電影影像的根本力量。
作為具備強大娛樂功能的兩種媒介,電影與游戲通過即時視聽的方式將觀者帶入造夢體驗,但是兩者之間卻存在機制上的根本差異。這種區別在于,電影是觀眾透過銀幕望向“窗外”,如安德烈·巴贊將電影的畫面比喻為一扇窗。人們透過窗子去觀看現實,電影的完整性事實上“只能是幻覺的完整性,是建立在對本身是片段和割裂的視覺空間的想象性建構基礎上的完整”。而“游戲的經過則是一扇門,跨過這扇門,我們直接進入了另一個世界,在這個虛擬視象的世界里,視覺空間與真實空間中的體驗一樣,是綿延而流動的。游戲世界的空間完整是建立在玩家的主動參與之上的完整,無需想象的驗證,只要他想看,想去,他就能看到,能到達”。因此,在兩者空間視覺機制的差異中,長鏡頭與蒙太奇的生產與使用發生了變化,而“游改電影”作為兩種媒介的融合產物卻將它們相對有機地結合到了一起。梅洛·龐蒂在《知覺現象學》中對“深度”的空間及體驗進行了哲學性的闡述:“深度不可能來自物體,也不可能被意識規定在物體中;深度顯示物體和我之間和我得以處在物體前面的某種不可分離的關系,而寬度乍看起來就能被當做有感知能力的主體不包含在其中的物體之間的一種關系。”“深度不能被理解為一個先驗的主體的思維,而是被理解為一個置身于世界的主體的可能性。”對于“游改電影”而言,當目睹影像的人從玩家向觀眾進行身份轉變時,電影若試圖讓觀眾進入游戲與觀影的雙重沉浸體驗,則需要將所參照的“現實空間”成為“現實”與“游戲”融合與壓縮后的雙重空間,當蒙太奇與長鏡頭以參照又區別于游戲影像的方式進行電影表現時,從某種意義而言,便是在機制上將這兩種空間在對玩家觀眾“視覺判斷距離”和“參照物圖像式還原”的兩方面進行了合并,最終形成了梅洛·龐蒂所提出的“深度空間”的形成。
結語
游戲如今已被喻為“第九藝術”,在媒介多變與互融的當下展露出強大的兼容性,類型風格進行著快速繁殖,表現出了精彩的美學觀念。例如,《菲斯》式的像素風游戲,《紀念碑谷》式的低多邊形風格,《破碎維度的記憶》式的實驗風格,它們以精妙的游戲構思和另類的視覺風格在游戲市場收獲著眾多粉絲的青睞,也迸發出越來越大的商業價值。當下“游改電影”的開發多集中于一些熱門的大型電腦游戲,對其改編往往也缺乏媒介屬性的深度思考。很多“游改電影”上映后票房口碑不佳,而一些精良的獨立游戲也未被納入電影改編的視野。然而,電影與游戲的結合不僅僅是單純的IP開發,更應該是對兩種不同媒介的邊界性與本體屬性的探討。在深度的融合創作中,電影創作者既要關注商業與藝術的平衡,更應將媒介機制的融合納入藝術創作的深層考量之中。長鏡頭與蒙太奇這類電影常用的創作技法,如今已在游戲中被大量使用。在從游戲向電影的改造過程中,創作者需要圍繞長鏡頭與蒙太奇所展開的空間表達進行跨媒介的思考,并兼顧觀眾多層體驗的生成及其伴隨的影像機制,從而在游戲與電影中的跨界中尋找到媒介融合點,最終使得“游改電影”形成純熟類型機制與創作模式,真正成為新的媒介方式。
【注釋】
1孫燁娟.重構影像世界——跨媒介視域下從游戲IP改編到游戲化電影[D].北京:中國電影藝術研究中心,2020:46.
2[德]魯道夫·愛因漢姆.電影作為藝術[M].楊躍等譯.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1:112.
3孫澄.時間的景深:德勒茲電影理論研究[D].上海:上海大學,2014:3.
4張斌.從“觀看”到“游戲”——新媒體語境下電影的形態重構[J].當代電影,2015(11):170.
5[法]克里斯蒂安·麥茨.想象的能指[M].王志敏譯.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06:98.
6同4.
7應雄.德勒茲《電影1》中的“運動影像”[J].電影藝術,2009(4):113.
8張波.德勒茲《時間——影像》中的核心概念解讀[J].電影文學,2009(3):112-113.
9道格拉斯·布朗、譚雅·克里茲溫斯卡、范倍.電影-游戲與游戲-電影:走向一種跨媒介的美學[J].電影藝術,2011(03):100.
10[法]德勒茲等著.什么是哲學[M].張組建譯.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7:456.
11藍江.文本、影像與虛體——走向數字時代的游戲化生存[J].電影藝術,2021(05):13.
12李然.視覺文化視野中的視頻游戲研究[D].上海:華東師范大學,2013:67.
13同12.
14[法]莫里斯·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M].姜志輝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326.
15同14,3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