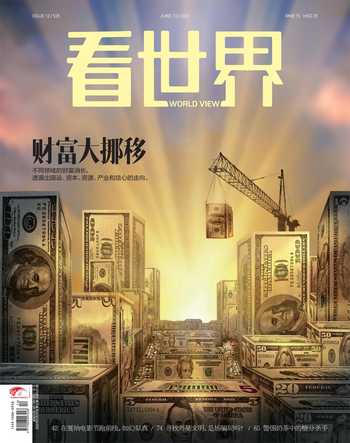逛名人墓園,是什么樣的體驗
陳科宇

維也納中央公墓,樹林小徑
這之后,我開始了一趟橫跨歐美的名人墓園之旅。
剛在瓦爾哈拉小鎮車站下車,天空下起毛毛細雨,把拜祭的氛圍烘托得很到位。細雨紛紛、霧氣氤氳、陰冷潮濕,不就適合拜祭嗎?真是“天空作美”。
從車站到墓園,我循著谷歌地圖一路上山。路上偶爾有車輛,不見行人。我心里估摸著,誰也不會挑新年首日來拜祭逝者吧?
走進始于19世紀的肯西可墓園(Kensico Cemetery),霧氣漸濃,讓人看不清前行的上山路。從墓園遙望對面山上的住宅,有肉眼可見的霧氣在深冬的枯樹與小屋間飄動。
這邊墓園里,陵墓風格各異,有的建造成希臘羅馬式的迷你宮殿,有的呈簡約刻字墓碑,或有十字架及雕塑神像伴守。
墓碑的分布如星羅棋盤,在濃霧間若影若現。此時景象跟經典恐怖電影《寂靜嶺》的封面相差無幾。
然而,我撐著傘行進在迷霧茫茫的墓碑之間,不但沒有恐懼,反而內心平靜,心生敬仰與敬畏。偶爾手機信號走弱導致導航偏差、迷失方向后,我也耐心等著信號穩定,再循著小徑走去。
深冬時節的紐約州肯西可墓園,人跡罕至。這種地方在東方人的觀念里肯定是“忌諱”,是“陰氣重”“生人勿近”的。因為怕受到責備,我至今都不敢告訴深度迷信的母親,我曾在細雨紛紛的新年,獨自前往紐約郊外的墓園,祭祀我最喜歡的作曲家。
其實,在市政公園還沒出現之前,歐洲人逛墓園可是很平常的事。

俄國音樂家拉赫瑪尼諾夫的墓地
在紐約郊區尋找拉赫瑪尼諾夫之墓,只是我的“墓園之旅”第一站。之后,我又跨越重洋抵達大西洋的另一端——歐洲。
在市政公園還沒出現之前,歐洲人逛墓園可是很平常的事。
晚春初夏的維也納中央公墓(Wiener Zentralfriedhof),是另一番景象。雖然天空陰霾,但用“人氣興旺”來形容維也納中央公墓并不為過。
拉赫馬尼諾夫僥幸在俄國暴力革命前逃到美國定居,卻獨自葬在紐約郊外的異鄉。在這方面,維也納的音樂家們就幸運得多,過世后還能在中央公墓“彼此為鄰”。
19世紀后半葉,奧匈帝國首都維也納的工業化發展,帶來城市人口的激增,而當時公共墓園已經不足以容納逝者的數量。因此,在1863年市政決定設立新的大型墓園,將城郊的一大塊土地劃為墓園用地。
然而,公墓的位置遠離城市中心,飽受批評,人們也不愿意將逝者葬在這么遠的地方。市政府因此絞盡腦汁,想方設法提高公墓的吸引力。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設立所謂“榮譽墓地”,將過世的名人墓地遷到中央公墓安葬或設立紀念碑,一方面吸引更多居民將家里的逝者安葬至此,與名人們為鄰做伴;另一方面吸引游客到訪,將中央公墓發展成為旅游景點。
維也納中央公墓中,至今有超過1000座“榮譽墓地”。這里安葬的名人,都為維也納乃至奧地利家喻戶曉,在音樂、詩歌、經濟、建筑、繪畫、演藝、政治乃至體育領域作出過巨大貢獻。比如,自1945年起設立的奧地利的聯邦總統墓地,就是新規劃的公墓區域。
在“音樂之都”維也納,中央公墓里的音樂家墓區自然不能少。作為榮譽墓地,今天在墓園里“彼此為鄰”的音樂家們的墓碑,也是從別處遷來的。貝多芬與舒伯特的墓于1888年遷至此地。不僅如此,勃拉姆斯、薩列里、施特勞斯家族以及勛伯格,也并非從一開始就安葬在中央公墓。

維也納中央公墓,莫扎特的“墓碑”位于音樂家墓區入口處的中央,左右兩側分別是貝多芬和舒伯特的墓碑
莫扎特的“墓碑”最為顯眼,位于音樂家墓區入口處的中央,但莫扎特卻是葬在離市區更近的圣馬克斯公墓。在莫扎特過世之后,甚至都沒有人能確定他埋葬的具體位置。直到1855年,有人將墓碑豎立在可能埋葬他的區域,然后墓碑被轉移至中央公墓的音樂家墓區。
“榮譽墓碑”的設立,至少達到了吸引游客的目的。來自世界各地、參觀維也納中央公墓的游人絡繹不絕。門口有多家鮮花店,供參觀人群購買后,為音樂家們以及奧地利的其他“榮譽人士”獻花祭奠。
維也納市政通過“榮譽墓碑”的宣傳手法提高公墓名氣,并非首創。
位于巴黎東部第20區的拉雪茲神父公墓(Père Lachaise Cemetery)始于1804年,比維也納中央公墓歷史更悠久。
在公墓出現之前,所有的安葬事宜都經過教會。逝者主要葬在市內的教堂里或毗鄰的教堂墓地。富裕階層主要葬在教堂里,而大部分民眾葬在教堂墓地。
法國巴黎及其他城市的人口,在18世紀初達到新高。隨著過世的人越來越多,教堂墓地越來越擁擠。遺體腐朽變質的味道以及衛生環境堪憂,構成嚴重的健康風險。去教堂參加禮拜儀式的民眾,感到極為不適。
1765年,經過多年研究與討論,巴黎市議會宣布禁止逝者遺體在市內教堂安葬,要求將遺體安葬在市區之外。
同時,在法國啟蒙運動的影響下,安葬除了宗教層面的意義外,更融入了世俗的紀念與緬懷性質。人們對于“生死”的觀念也發生了轉變,不再強調肉身遺體的腐壞,而是紀念、緬懷、思考逝者一生的成就。
在法國大革命之后,隨著越來越多的紀念碑豎立在公園與花園,普通民眾接受了這些有關遺體與安葬的新觀念。而1804年創建的拉雪茲神父公墓,實現了人們對“安息之地”的向往,也成為城市花園式墓園發展的重要節點。
作為法蘭西帝國皇帝的拿破侖宣布:“每位公民,無論種族或信仰,均有權得到安葬。”巴黎市政府不得不在郊區開辟新的墓地。
拉雪茲神父公墓啟用之初,由于地處偏遠,很少有人安葬于此。巴黎市政府組織了大型儀式活動,將寓言詩人讓·德·拉封丹與劇作家莫里哀的遺體移葬于此。于是,公墓名聲大噪。
為了與名人葬在一起,人們爭先恐后將逝去的家人安葬于此。在不到30年里,拉雪茲神父公墓的墓穴數量從最初的13座增加至3.3萬座。如今拉雪茲公墓安葬有100萬人,還不包括壁葬的數量。

如今拉雪茲公墓安葬有100萬人,還不包括壁葬的數量。
同時,現有的園林景觀,也為園內植物的種植生長提供了空間。公墓最初只受富人階層的青睞,后來園區的墓碑越來越多。隨著巴黎市區的擴大,現在的公墓就位于巴黎市區,公墓周圍的城市環境與公墓的寧靜氛圍相得益彰。
相比紐約蕭瑟的深冬、維也納陰霾的春末,巴黎的初夏陽光明媚。
我穿梭在拉雪茲神父公墓分割不同區域的小徑上,探尋著波蘭音樂家肖邦的墓位。
墓碑由低矮的鐵柵欄圍著,上面矗立著俯身撫琴的女性雕像,憂郁的神情似乎跟肖邦的作品很貼合;墓身刻著肖邦側像浮雕,樹枝在微風的吹拂下,在墓碑上留下搖曳的樹影。
墓前擺放著尚在綻放的花束,前來瞻仰駐足的游人一波又一波。在這樣寧靜安詳的氛圍里,“墓園”的含義似乎更突出的是供人休閑散步的“園地”,人們對 “墓園”與“死亡”也不再聞之色變。
歐洲公墓的發展,也對美國產生了深遠影響。研究美國公墓文化的美國學者凱斯·埃格納,曾在采訪中說道:
“1830年之后,越來越多的公墓設計有蜿蜒崎嶇的路徑以及秀麗如畫的景色,其理念就是讓人們在走進公墓大門之后,將世俗的商業化世界拋到腦后,進入冥想的空間、能夠與靈魂進行對話……要知道,在美國大城市,公墓誕生的時代還沒有休閑公園、博物館或植物園。公墓的出現,讓人們擁有了大片的休閑空間,可以沉浸其中,欣賞精美雕塑與園林藝術。”
我的公墓之旅,從2022年的第一天,一直延續到初夏。從紐約郊區到歐陸大都會巴黎,我對生死大事有了新的看法和體驗。
責任編輯何任遠 hr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