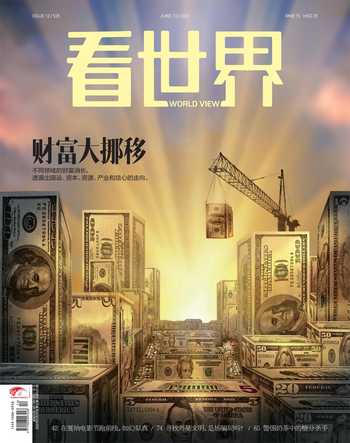韓國電影躍進史:永遠關注底層
憐青

電影《掮客》劇照
在剛結束的戛納電影節(jié)上,韓國電影人收獲頗豐。樸贊郁以《分手的決心》斬獲最佳導演獎,成為韓國第二位獲此殊榮的導演;演員方面,宋康昊憑借在《掮客》中的優(yōu)異表現(xiàn),拿下了最佳男主角,成為歐洲三大電影節(jié)中的首位韓國影帝。
這一消息讓韓國人振奮。5月29日,韓國總統(tǒng)尹錫悅發(fā)布賀電,稱樸、宋兩人的獲獎是對“因疫情而氣餒的國民莫大的安慰”。
千禧年以來,韓國電影以極為生猛的姿態(tài)步入世界影壇:2002年,韓國電影教父林權澤以《醉畫仙》首獲戛納最佳導演獎,為韓國電影走向國際開了個好頭;同年9月,李滄東的《綠洲》拿下威尼斯電影節(jié)最佳導演獎;2003年,《老男孩》與《殺人回憶》兩部被后人譽為“神作”的電影橫空出世,樸贊郁與奉俊昊這兩位日后韓國影壇的代表人物初露鋒芒。

2022年,樸贊郁憑借《分手的決心》獲得戛納電影節(jié)最佳導演獎

2020年,奉俊昊憑借《寄生蟲》獲得第92屆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導演獎
2004年,韓國電影同時揚威歐洲三大電影節(jié)。2006年,《漢江怪物》殺入好萊塢。此后的韓國電影一直驚喜不斷,包括2020年奉俊昊的《寄生蟲》狂攬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4個獎項,還成為后者歷史上首部獲得最佳影片的外語片。
韓國電影的起步并不算早,但其發(fā)展速度令人咋舌。除了上述影人外,在威尼斯兩度得獎的金基德,屢獲歐洲三大電影節(jié)提名的洪尚秀,戛納影后全度妍,柏林影后金敏喜,這些名字宣告著,韓國電影正值群星閃耀的時刻。
與韓國電影蓬勃發(fā)展并存的,是其國內(nèi)大量的陳年積弊。政治動蕩、經(jīng)濟危機沖擊、財閥權力過大、社會階級固化……這些都為韓國影人提供了無數(shù)可供創(chuàng)作的土壤。
在這樣的大環(huán)境下,韓國電影人走出了一條從學習類型片套路,到堅持底層視角、揭露殘酷社會矛盾的電影道路。樸贊郁與宋康昊在戛納的出彩,不僅歸功于其個人天賦異稟,更是韓國民族精神與冰冷現(xiàn)實碰撞的慘烈成果。
韓國電影經(jīng)歷了從模仿到創(chuàng)新的全過程。
熱播韓劇《請回答1988》里,出現(xiàn)了大量的港臺元素。韓國家庭的電視熒幕上,曾熱播《英雄本色》《倩女幽魂》《警察故事》等經(jīng)典香港電影,周潤發(fā)、張曼玉的海報被張貼在韓國孩子的房間—這也是上世紀80年代韓國電影環(huán)境的縮影。
1984年和1986年,韓國接連修訂《電影法》,降低了電影行業(yè)的準入門檻。韓國電影不再被少數(shù)電影制作公司壟斷,進口電影的大門也被敞開。國外佳作的涌入,提升了韓國觀眾的審美,強烈的文化沖擊也讓一部分韓國電影人逐漸覺醒,立志要拍出屬于韓國的好電影。
斬獲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的奉俊昊,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成長的。出生于1969年的他,認為自己是“好萊塢兒童”,科波拉、馬丁·斯科塞斯、昆汀等好萊塢大師的電影,填滿了他的青年時期。在頒獎現(xiàn)場,奉俊昊還不忘向自己的偶像馬丁·斯科塞斯致敬。
金鱗豈是池中物,一遇風云便化龍。韓國在1997年開始實行的“文化立國”戰(zhàn)略,給了奉俊昊這樣的電影人足夠的發(fā)揮空間。電影分級、減稅與扶持多管齊下,大量資本瘋狂進入電影業(yè)。
在韓國電影崛起路上打響頭炮的,是姜帝圭和他的《生死諜變》。這部1999年上映的電影,創(chuàng)下了當時韓國電影的票房紀錄:單片超600萬的觀影人次,占到了當年韓國觀影總人次的三成左右,讓風靡全球的《泰坦尼克號》在韓國市場“撞上冰山”。
韓國電影人更擅長刻畫小人物飄蓬般的命運。
從電影技法而言,《生死諜變》幾乎是照搬了好萊塢的敘事套路。男主最愛的女人是潛伏特工的設定,在當時都不算新鮮,但片中槍戰(zhàn)、打斗、愛情等商業(yè)要素應有盡有,還加入了讓韓國人激動不已的南北對抗元素。
這種好萊塢類型+韓國元素的設定,后來被奉俊昊發(fā)揚光大。2003年《殺人回憶》套用的,依然是好萊塢經(jīng)典的懸疑片套路。但奉俊昊通過灰暗陰冷的鏡頭語言,以一場未結的兇殺案,還原了1980年代經(jīng)濟下行階段韓國的社會百態(tài)。鏡頭里那幾乎伸手不見五指的鄉(xiāng)村黑夜,也是對1980年代為防敵襲,城市、工礦區(qū)、交通線的燈光都要熄滅的真實再現(xiàn)。
后來大熱的《漢江怪物》同樣如此,在怪獸外殼下,是借著老中青三代韓國人的遭遇,對韓國政府進行批判。

電影《寄生蟲》劇照

《殺人回憶》

《熔爐》

《孝子洞理發(fā)師》

《薄荷糖》
“想用現(xiàn)實生活作為元素,拍攝一部比類型電影還有趣、更加娛樂化的電影”,奉俊昊的設想,在韓國成熟的電影工業(yè)體系下得以施展。他切換各類型片游刃有余,進而在類型片中,表達自己的思考。
拿下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獎的《寄生蟲》,就是這種思考的結果。混合了恐怖、驚悚與黑色幽默的《寄生蟲》,很難被歸入單一類型,但內(nèi)核依然是對韓國社會嚴重貧富分化的無情嘲弄。
古代朝鮮半島地瘠民貧,為了生存,也就孕育出了“事大主義”的思想,即在外交中臣服于更強大的政權。
這種事大主義的思想,同樣影響著如今的韓國電影創(chuàng)作—因為“事大”,韓國人總不自覺會把自己放在弱者的視角。也是因為如此,韓國電影人更擅長刻畫小人物飄蓬般的命運,更習慣于從底層視角見證歷史的變遷。
此次加冕戛納影帝的宋康昊,尤其擅長演繹這樣的小人物命運。
以被譽為“韓國版《阿甘正傳》”的《孝子洞理發(fā)師》為例,宋康昊扮演的宋漢默是一名再平凡不過的理發(fā)師。導演借助宋漢默的生活,不動聲色地將歷史與諷刺植入其中。
面對已經(jīng)懷孕5個月卻不想要孩子的女友,文化水平不高的宋漢默,活用剛知道的“四舍五入”一詞,稱5個月的孩子已經(jīng)是完整生命應該留下來,一舉勸服了女友。
“漢江奇跡”背后的悲劇性一面,讓韓國電影人有著足夠的發(fā)揮空間。
事實上,四舍五入是當時韓國總統(tǒng)李承晚的“發(fā)明”。根據(jù)規(guī)定,李承晚需要2/3的票數(shù)也就是135.2票,方能繼續(xù)當選,但只得到135票的他卻以“四舍五入”為由,宣稱自己已經(jīng)取得足夠票數(shù)。
因為宋漢默的家離韓國總統(tǒng)府青瓦臺不遠,他也在機緣巧合下,被引薦為總統(tǒng)的理發(fā)師。但這樣的身份沒能讓他收獲名利,反而生出伴君如伴虎之感。數(shù)年后,宋漢默的兒子被當成是間諜同伙逮捕入獄,在拷打下雙腿殘疾。面對如此噩耗,宋漢默無能為力,只能舉起剪刀朝著青瓦臺的方向,當街剪下自己的頭發(fā),邊剪邊高喊“我是總統(tǒng)的理發(fā)師!”
最為諷刺的是,這是宋漢默在全片中唯一的“反抗”與宣泄—但即便是這種極其微弱的宣泄也并不持久,隨著一輛汽車鳴笛駛過,宋的崩潰戛然而止。作為個人,他在更強大的力量面前,只能讓道。
無獨有偶,與宋康昊、崔岷植并稱“韓國演技派男演員三駕馬車”的薛景求,同樣扮演了大量被歷史左右的小人物。
不少投資韓國電影的財閥,本身就是電影中被批判的對象。

電影《漢江怪物》劇照
李滄東執(zhí)導的電影《薄荷糖》采用了倒敘的手法,開片不久就是薛景求扮演的永浩走向鐵軌,迎著火車試圖自殺。隨著時間往回走,觀眾看到了永浩在過去1979—1999年里的悲慘人生。學生、士兵、警察、富豪、無業(yè)者,隨著一樁樁歷史事件展開,永浩的身份一次次轉變,他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財富,也在韓國的金融危機里蕩然無存。
1999年,一無所有的他被朋友的歌聲牽動起內(nèi)心深處的記憶,殺人的愧疚感最終壓倒了他。當時代車輪碾壓而至時,永浩的命運,就像那顆被長官踩碎的薄荷糖般,碎了一地卻無人關心。
畸形發(fā)展的創(chuàng)作土壤
韓國電影對底層的關注,與其特殊的國情密不可分。首爾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慶燮認為,韓國的發(fā)展是一種“壓縮型現(xiàn)代性”,即韓國社會在半個世紀里,有意圖地、壓縮式地完成了西方社會兩三百年間經(jīng)歷的工業(yè)化和經(jīng)濟增長,同時也提前經(jīng)歷了西方社會中出現(xiàn)的各種風險社會癥候群。
國家不幸詩家幸。“漢江奇跡”背后的悲劇性一面,讓韓國電影人有著足夠的發(fā)揮空間,而“壓縮”給韓國民眾造成了深刻危機感,也讓他們更愿意為社會類題材的電影買單。
以在戛納首映的《掮客》為例,這部作品盡管由日本導演(是枝裕和)執(zhí)導,但講述的依然是一個韓國故事。片中展示的“嬰兒暫存箱”與盜嬰送養(yǎng),折射的就是韓國灰暗的嬰兒買賣產(chǎn)業(yè)。
早在2012年,韓國電影《芭比》就講述了一個美國家庭試圖通過“跨國領養(yǎng)”的制度漏洞達成器官買賣的黑暗故事。而根據(jù)美聯(lián)社的調(diào)查,韓國有福利機構從1970年代開始,陸續(xù)將孩子賣往美國等海外地區(qū)。
單單圍繞兒童保護的相關話題,韓國電影便佳作頻出。2011年9月,電影《熔爐》上映,這部改編自真實事件的電影,講述了新到任的學校教師揭開聾啞學校校長與部分員工性侵、虐待學生的惡行,但惡人最終卻被輕判的故事。
電影上映37天后,韓國國會以207票通過、1票棄權,壓倒性通過了《性侵害防止修正案》,加長了對性侵幼童及殘障女子的追訴期并加重了相關刑罰。這個修正案也被韓國民眾稱為“熔爐法”。
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韓國的壓縮式發(fā)展給了本國電影人足夠的“舞臺”,但這種畸形發(fā)展孕育出的批判,大多只能流于情緒與表達—在光影的世界里,韓國電影人可以對各類社會現(xiàn)象任意抨擊,但真正能推動社會改變的案例卻屈指可數(shù);“熔爐法”的確感人,但毋寧說是偶發(fā)的奇跡。
不少投資韓國電影的財閥,本身就是電影中被批判的對象,但依然止不住他們對電影的投資。畢竟對于這樣的群體而言,民眾足夠喜歡現(xiàn)實題材意味著票房大賣,能賺得盆滿缽滿,那么承受點不指名道姓的嘲諷,又算得了什么呢?而這或許就是韓國社會中,最違和的現(xiàn)象。
責任編輯吳陽煜 wyy@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