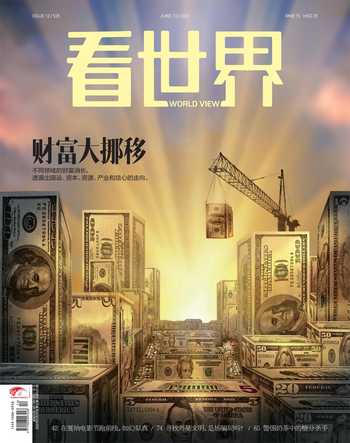電子游牧族,去生活的地方工作
菲力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游客在邦迪海灘享受夏日時(shí)光
“等賺夠了錢就去環(huán)游世界。”抱有這種幻想的絕大多數(shù)人,直至退休也沒能把錢賺夠,并最終應(yīng)了那句歌詞—“世界那么大,我只去過東南亞”。
1997年,日本半導(dǎo)體學(xué)者牧本次雄和英國《電子周刊》作者戴維·曼納斯首次提出了“數(shù)字游牧/電子游牧”的概念。彼時(shí),電子郵件正在顛覆傳統(tǒng)書信,諾基亞還統(tǒng)治著手機(jī)世界,一切正處于互聯(lián)網(wǎng)時(shí)代的前夜。但之后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全球部署5G基建,馬斯克高調(diào)宣布星鏈計(jì)劃。
如果再問“要工作還是要生活?”這一代人的回答將是:小孩子才做選擇,成年人都要。
利用電信設(shè)備和互聯(lián)網(wǎng)從事遠(yuǎn)程工作,就可以去任何想生活的地方。
“早上在米蘭大教堂旁的文藝區(qū)找間咖啡廳寫文章,搭配可頌和卡布奇諾,下午拿著意式冰淇淋漫步在米蘭大教堂,又或在前往威尼斯面具節(jié)的火車上,趕在截稿日前交出最后一篇稿。”這樣的描述,可謂是電子游牧族理想中的一天。
電子游牧族不同于一般的環(huán)球旅行者,旅途中至少要做到收支平衡方可持續(xù)。這就導(dǎo)致了目前電子游牧工作地和生活地的分化特征:電子游牧族大多來自人力成本較高的歐美發(fā)達(dá)地區(qū),并在當(dāng)?shù)胤e累了一定的客戶資源后,遷徙到物價(jià)較低的地區(qū)生活。
比如,美國的生活成本高達(dá)3000美元/月,而在泰國,可能不到1000美元就能過上同等體面的生活。剩下的2000美元對于年輕人來說,意味著旅行、學(xué)習(xí)的開銷,也意味著一定程度上能夠負(fù)擔(dān)起探索人生新可能性時(shí)伴生的失敗與風(fēng)險(xiǎn)。
2017年,愛沙尼亞的新電子居民人數(shù)已經(jīng)超越出生人口。
另一方面,電子游牧族也不同于遠(yuǎn)距離工作者,所以你還需要手持一本好用的護(hù)照。若是持一本非洲護(hù)照,會(huì)比一本德國護(hù)照少100多個(gè)免簽國,光是填表申請就能將你的浪漫消磨殆盡。
除此之外,“筆電在手、工作不愁”者在勇闖天涯時(shí),還需要考量當(dāng)?shù)氐木W(wǎng)速、安全指數(shù)、醫(yī)療和包容性,甚至夜生活、教育等各種非常實(shí)際的狀況。
德國柏林一家專為電子游牧族提供目的地推薦的公司Nestpick統(tǒng)計(jì):澳大利亞墨爾本高居全球電子游牧族宜居排行榜第一,顯示除了互聯(lián)網(wǎng)基建過硬,陽光、沙灘和海岸仍是人類本能的向往;阿聯(lián)酋和迪拜則因?yàn)槊舛惛呔拥诙?/p>
總之,對于電子游牧族來說,既要享受自然,也不能舍棄現(xiàn)代文明的物質(zhì)福利,但若為自由故,兩者—皆不可拋!
當(dāng)電子游牧族增加,并展現(xiàn)出巨大消費(fèi)力和生產(chǎn)力后,一系列為之服務(wù)的小眾產(chǎn)業(yè)也隨之誕生。一些人對此的寄望不只是重塑旅游業(yè),而是逆轉(zhuǎn)國運(yùn)甚至整個(gè)未來世界。
比如愛沙尼亞,這個(gè)人口僅有130萬且老齡化嚴(yán)重的波羅的海三小國之一,有意吸引這類來自全球的高收入人群(彼時(shí)“電子游牧”的概念尚未誕生)。
2014年,愛沙尼亞正式?jīng)Q定成為無國界國家,推出“電子居民計(jì)劃”。任何人都可以以電子方式簽署文件,申請?jiān)趷凵衬醽嗊h(yuǎn)程創(chuàng)辦公司,獲得專業(yè)銀行服務(wù)并使用國際線上支付系統(tǒng),以及取得電子居民身份證。整個(gè)過程要價(jià)100歐元,最快20分鐘搞定。
今天,愛沙尼亞已經(jīng)是全球數(shù)字化程度最高的國家之一,入學(xué)、買房、醫(yī)療電子處方、文件簽署等,90%以上的公家服務(wù)都可以直接在手機(jī)上辦理。換言之,除了結(jié)婚、離婚、土地買賣需要親自到場之外,其他一切皆可透過網(wǎng)絡(luò)憑借“數(shù)字身份證”搞定。2017年,愛沙尼亞的新電子居民人數(shù)已經(jīng)超越出生人口。
2019年,電子居民計(jì)劃為愛沙尼亞經(jīng)濟(jì)貢獻(xiàn)1400萬歐元,并催生出一萬多家企業(yè),包括上千家新創(chuàng)企業(yè)和四家獨(dú)角獸企業(yè),例如全球通訊軟體Skype、線上付款服務(wù)業(yè)者TransferWise、叫車服務(wù)業(yè)者Taxify等。
如果說“電子居民計(jì)劃”促進(jìn)全球高級人才為愛沙尼亞工作,那么2020年6月愛沙尼亞首創(chuàng)專為“電子游牧族”設(shè)計(jì)的“電子游牧簽證”,就是邀請全球的高收入電子游牧族來愛沙尼亞生活。

愛沙尼亞塔林市的高樓大廈

巴厘島,游客在街頭咖啡廳
不過,申請人需要證明近半年來每個(gè)月都有3500歐元以上的收入,這個(gè)數(shù)字是愛沙尼亞國民平均收入的兩倍。獲得資格者即可到當(dāng)?shù)鼐幼∫荒辏@一政策間接帶動(dòng)了當(dāng)?shù)芈糜螛I(yè)。巴巴多斯、百慕大及迪拜也緊隨其后,先后提供電子游牧族簽證。
這個(gè)市場究竟有多大呢?2019年美國有730萬電子游牧族,到2020年,這一族群成長至1090萬人。新冠暴發(fā)之前,這些人大多數(shù)是自由職業(yè)者,新冠疫情更是成了催化劑。預(yù)計(jì)到2035年,全球范圍內(nèi)將有10億電子游牧族。
新世界仿佛已向人們敞開大門,年輕人摩拳擦掌躍入其中,但我們的社會(huì)真的準(zhǔn)備好了嗎?
對于電子游牧族來說,第一個(gè)事實(shí)是,生活不會(huì)因?yàn)檫w徙而變得更容易,困難永遠(yuǎn)存在,只是不同。比如,你以為“游牧”的意思是邊玩邊工作不用打卡,但事實(shí)可能是大多數(shù)公司愿意采納遠(yuǎn)程合作的前提是適當(dāng)降薪。
預(yù)計(jì)到2035年,全球范圍內(nèi)將有10億電子游牧族。
于是為了維持收支,你可能需要打兩份工,每天16小時(shí)坐在佛羅倫薩街角的咖啡館里工作。再比如,如果你沒有超強(qiáng)的融入能力,行走在陌生的土地上,同時(shí)也意味著與社區(qū)組織脫軌,成為一座游離的孤島。
第二個(gè)事實(shí),就像巴厘島民眾面對大量電子游牧族而發(fā)出的憤怒之聲:“巴厘島被外界視為天堂,但對我們來說,這里是家。”對于當(dāng)?shù)孛癖妬碚f,相比經(jīng)濟(jì)效益更直觀的感受是,這些外來的西方富裕人口賺著高薪、享受著當(dāng)?shù)氐淖匀画h(huán)境,卻對在地文化既不感興趣也不尊重,他們只關(guān)心互聯(lián)網(wǎng)上的事。
他們不是觀光客,他們享有權(quán)利;他們也不是市民,不承擔(dān)義務(wù),那他們是誰?更可氣的是,“裝修時(shí)髦的咖啡館取代了當(dāng)?shù)丶彝ソ?jīng)營的小咖啡店,原來本地人鄰里之間或跟朋友聚會(huì)社交的場所也沒了”。
這些具體的抱怨證明,電子游牧族給社區(qū)帶來多大的機(jī)遇,也就帶來了多大的挑戰(zhàn)。一味地想象自由,就像一味地勾勒巴厘島的藍(lán)天白云一樣,都是虛幻的。
但正如前愛沙尼亞官員所說的,“電子居民”向世界證明的是這個(gè)國家的彈性。不論國家還是個(gè)體,被動(dòng)或主動(dòng),永遠(yuǎn)都需要學(xué)會(huì)從四分五裂的現(xiàn)實(shí)中尋找新的意義感和歸屬感,而“電子游牧”只是未來世界給這一代人提出的考題之一。
特約編輯姜雯 jw@nfcmag.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