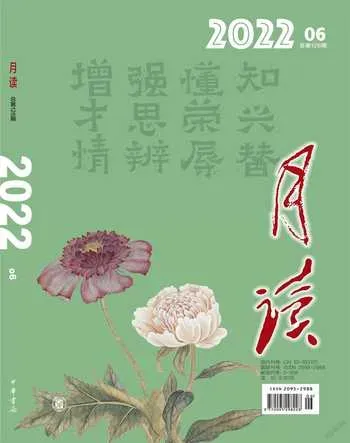金農與鄭燮:清代書法領域的“怪”才
葛承雍

在清初期到中期這個表面繁榮平靜、實際開始頹唐沒落的年代,敏感的知識分子在得風氣之先的文化領域里,盡管還表現或抒發著當初文人那種孤獨、寂寞、傷感和悲哀之情,但已經透露出一種強烈的內在激情。他們以狂放怪誕、突破常格的書法外在形象吸引著人們。書法成了他們不屈不撓人格的主觀情感象征。這在當時秀潤工整、溫文恬靜的筆墨世界里無疑被人視為“怪”,這種在行為上不合時俗之見,在藝術上另辟蹊徑的先驅者,就是“揚州八怪”中的金農和鄭燮。
金農,號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等,單從別號上看就是一個疏放情性、超塵拔俗的文人。他曾以布衣被薦舉博學鴻詞科,但入京未試而返,或許是他對這種讓隱士文人就范的特殊仕途有所反悔,或許是他覺察到官場的黑暗而擔心墮落成貪官污吏,總之他再也沒有投身政壇。他浪跡海內,中年后寄居揚州,鬻詩文,賣書畫,直到去世。他在當時朝野風靡帖書的時候,提出擺脫帖學、師法漢碑的觀點,是頗具膽識的。有人認為他“儲金石千卷”是“好學癖古”,也有人認為他于碑學是“學而不倡”,實際上并非如此。金農《魯中雜詩》云:“會稽內史負俗姿,字學荒疏笑騁馳。恥向書家作奴婢,華山片石是吾師。”可知他是力求以古樸雄健的漢隸去改造日趨圓熟、靡弱的帖書。
金農學習漢隸《國山碑》和皇象《天發神讖碑》,追求質樸率真、魄力宏大的風格,因而他“分隸小變漢法”,并把這兩種碑石所具有的轉折方勁的特點加以發揚,表現出大膽革新的個性。金農不受前人束縛,剪去毛筆的尖毫,用齊頭筆去寫楷書,具有用刷漆的刷子寫字的效果,既方整斬截,又魄力沉雄,特別是作擘窠大字,具有蒼古奇逸、自創一格的氣度。金農用同樣的方法來寫行、草書,也很有古拙沉郁的特色。像他的行楷書頗類似北朝魏書,筆方道粗,體緊勢側,橫畫嚴格地疊緊,直畫一般較細而帶隸意,在平正中夸張某一部分所占的地位大小,造成清奇質實、無拘放浪的形貌。而他的隸書,橫畫粗長,豎畫細短,體勢欹斜,骨力深藏,似有返璞歸真、無所羈絆的情趣。

金農書法作品
金農這種側鋒方筆的運筆,不僅表現出沉著痛快、入木三分的功力,而且傳達出天真野逸的山林氣息。因此,我認為金農的書法風格主要是“疏野”。疏,側重于他內心的思想基礎和人生態度;野,側重于他外在的行為舉止和不拘的性格。這種“疏野”,不僅有別于正襟危坐、心滿意足的“館閣體”,也與隨緣自適、高雅嫻靜的“曠達體”有所差別。如果說曠達往往以自我解嘲、及時行樂的方式來擺脫眼前的苦悶,多出現于“達則兼濟天下”而遭遇暫時受挫的在朝官員中,那么疏野則采取超塵脫俗、不拘禮俗的方式,來淡化人世間的煩惱,多產生在“窮則獨善其身”后而脫離仕途的在野文人中;如果說曠達只是表面的、暫時的或萬般無奈的內心矛盾苦悶,仍可使人感觸到一顆被名利枷鎖牽累的寸心,那么疏野往往是經歷了仕途風波后,對榮華富貴無牽無掛的態度。所以,金農的“疏野”風格是對儒家禮教綱常的一種蔑視;不是文人士大夫失意時的達觀情態,而是甘愿身居市井、淡薄功名利祿的疏放情致。它的妙處在于既超脫塵囂,又不離現實;既不茍茍營營,又非不通人情;既安于守拙,又帶生活氣息,從而以清新樸素的格調直抒胸臆,以一種自覺或不自覺的人生態度對抗和揭露當時社會的黑暗。這也恐怕是當時人們對金農“性逋峭,世以迂怪目之”的主要原因。
關于鄭板橋,人們已經把他作為“揚州八怪”的突出人物作了說不完道不盡的高度評價,但無論是風雅說、怪道說、入畫說、狂魔說、玩世不恭說,似乎都沒有很好地把握住他那種具有深刻根基的批判現實主義思潮在強烈的書法個性里的升華。其實,正是這種與黑暗現實社會不協調的個性反抗,使其書法帶有粗豪放浪、憤世嫉俗的異彩。
鄭燮早年家境清貧,“時缺一升半升米”的窮困生活使他對社會的不均和人民的痛苦產生了憤慨,雖然他苦讀經史,希望通過科舉仕途去“立功天地,字養生民”,但直到乾隆元年(1736)他五十四歲時才考取進士,按理應點翰林,卻又因書法不合館閣體而外放知縣。從他所用“康熙秀才”“雍正舉人”“乾隆進士”“十年縣令”“七品官耳”等印章里,可以看出他因這種腐敗政治和黑暗社會而產生的內心痛苦。在他任山東范縣和濰縣知縣時,因幫助農民勝訟及辦理賑濟而得罪官紳受到打擊,終于在六十一歲時罷官而歸。他回到揚州后無以為生,只能靠賣字畫度日,唯不與權勢豪富和官紳來往,而廣泛交結在思想感情和精神氣質上有共通之處的文人學者,因而形成了不滿現實、傲岸不馴的“怪”。
經歷了仕途煩惱后的鄭板橋,帶有一種“久在樊籠里,復得返自然”的喜悅感,但更重要的是他對黑暗社會的控訴和批判,盡管這種批判是通過“倔強不馴之氣”的書畫來體現的,但卻時時閃爍出某種思想解放的光輝。正是在這種半隱半貧的生活中,使他的作品一方面不脫文人雅士那種豁達超脫的風格,另一方面又有反映民間疾苦、生活艱辛的現實主義色彩。思想情趣的兩面性和剛正不阿的做人之道,成為鄭板橋從事書法創作時審美意念的憑借。
鄭板橋號稱有三絕,即在三方面造詣極深的畫、詩、書,結成一個完整的藝術整體,形成所謂“三真”:真氣、真意、真趣的特色。他的書法別具一格,字中有隸法,有楷法,正式的隸書鮮見,秀麗工整的楷書也少見,瀟灑處像行書,縱橫處像草書,參用隸、楷、行、草、篆諸體字形,再加入蘭、竹畫法的用筆,創造出與眾不同的書體。這種板橋體,隸多于楷,行楷又融合,照他自己的解釋是八分隸法只剩下六分半了,因此“自號六分半書”。由于他的書法真正將五體熔于一爐,使得人們在分析時往往撲朔迷離,很難區別。或說他“少工楷書,晚雜篆隸,間以畫法”;或說他“狂草古籀,一字一筆,兼眾妙之長”;或說他始學《瘞鶴銘》、黃魯直(山谷),后以分書入行楷;或說他“以篆隸之法闌入行楷,蹊徑一新,卓然名家,而不知者或以野狐禪目之”。從書法技巧上看,這些分析都有道理,他的字多在橫畫上用力,似有黃山谷家法;結體多帶扁,轉折較重,善用蹲筆,又比蘇東坡瘦硬活潑;在強調左右欹斜抱合的結構基礎上,參以長字長畫,窮極外形變化,因此布局生動活潑,疏密有致,有偏有正,有寬有窄,甚至東倒西歪都是一氣呵成,大有“亂石鋪街”“星落銀河”之勢。

鄭板橋書法作品
鄭板橋的書姿變板滯僵硬為龍蛇飛動,不僅真行俱帶篆籀意,如雪柏風松,挺秀出塵,而且波磔之中,帶有石文蘭葉,古秀獨絕,引人入勝。與其說“板橋作字如寫蘭,波磔奇古形翩翻”,毋寧說“如灌夫使酒罵坐,目無卿相”。與其說他“蟬蛻龍變”“領異標新”的書法獨創精神來源于蘭竹畫意,毋寧說他“狂狷不羈”“怪道奇生”的隨意揮灑正是出于對館閣、帖學盛行的逆反。他的字正是與其倔強傲岸的個性相通,也是他沖出枷鎖敢于破格的最好注腳,使人有清新之風撲面而來的感覺。

鄭板橋繪《竹石圖》
然而,我不同意把鄭燮這種個性解放和師法造化的書意,解釋為怪杰聰穎過人的表現,或故作驚人的“野趣”的顯示。雖然有人認為鄭燮的書法“如秋花倚石,野鶴戛煙,自然成趣”;也有人認為他“亂玉鋪階”“墮魔入狂”,是以“野狐禪”來表現自成一家的疏野之致。但鄭板橋筆法縱橫馳騁、豪爽奔放,強調的是性靈的發揮;墨法酣暢淋漓,隨機應變,注重的是不受成法束縛的創新;于清新疏放的文人形式里,呈現的是鄙棄禮法、悲慨峻切的率真風格。這與一味追求幽峭寒僻、孤寂清冷的隱士生活情趣截然不同,更與清心寡欲、與世無爭的失意官宦思想格格不入。可以說,在鄭燮雅謔可掬、諧趣橫生的文字背后,包含著對世俗無情的揭露和譏刺,蘊含著因無法濟世愛民而對黑暗政治的猛烈抨擊。與其說他多少還有些儒家入世的積極思想,不如說他對現實生活的苦痛使其批判現實主義氣息更加濃厚。也正因為如此,他那絕少雕琢而清新自然的書法墨跡才具有長久的生命力,既以明快豪放乃至荒率奔突的特點而獨樹一幟,又預示著清代書風將在館閣、帖學的陰影籠罩里出現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