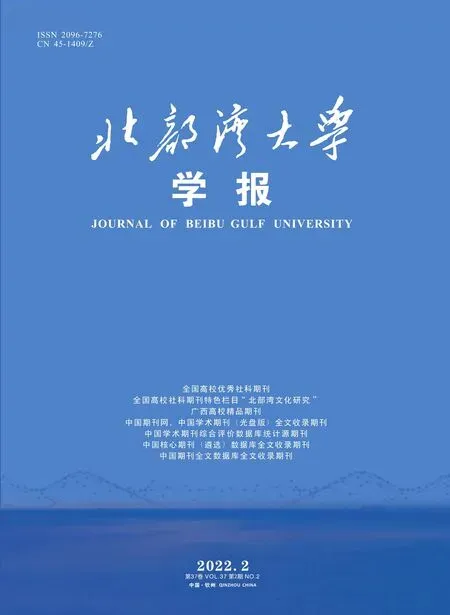重點海域救助船布置位置的選擇
李成海,俞啟軍,文 峰
(1.山東交通職業(yè)學院 航海系,山東 濰坊 261206; 2.自然資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山東 青島 266011;3.東營港引航站,山東 東營 257000)
0 引言
為了提高海難船舶救助的成功率,各國救助站采用科學布置救助船選址的策略,為船舶海上航行保駕護航。但是,由于海區(qū)廣闊以及救助船數(shù)量有限,往往存在救助效率低和救助不及時等問題。為了改變這一狀況,救助專家提出了在重點海域科學布置救助船的理念和最大效率地利用現(xiàn)有救助力量的救助策略。在傳統(tǒng)的理念中,需要大量的救助船對海區(qū)洋面進行全方位覆蓋,這對大多數(shù)國家的海難救助來說是不現(xiàn)實的,因此如何使現(xiàn)有救助站的救助力量實現(xiàn)效率最大化是遇險船救助決策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現(xiàn)有關于海難救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救助策略上。林婉妮等[1]根據(jù)巡邏船密度數(shù)據(jù)確定救援船舶的概率分布,分別計算風向影響下東海特定水域的海上救助效率。朱小林等[2]研究了海上應急救援系統(tǒng)中應急資源位置—分配決策問題,建立了基于事件類型的應急物資與船舶分配多目標模型,確定不同目標分量權重下合理的船舶、物資分配方法。郭國平等[3]利用P-中位建立了應急救助站點選址的數(shù)學模型,目標函數(shù)在滿足設置的約束條件下取最小值(即救援用時最少或救援距離最短)。吳曉林等[4]建立救助船模糊相似優(yōu)選模型,根據(jù)各指標的優(yōu)選結果對所有待選船舶方案進行綜合排序,選擇最合適的救助船參與救助行動。李洪成等[5]以系統(tǒng)的時效性、安全性和經(jīng)濟性作為優(yōu)化目標,建立多目標規(guī)劃模型,并給出了模型的求解方法。黃敏東[6]通過對海上救援時間進行分析,論述海上黃金救援時間以及科學制定搜救措施等對提高海上救助成功率的影響。楊衛(wèi)東[7]基于GIS并結合貪心算法,提出了連續(xù)設施選址問題的求解方案。
已有的研究成果為救助船救助的布置位置奠定了基礎。但與以往的設施布置方案相比較,救助船的布置位置具有特殊性。所以,針對海上救助重點水域的覆蓋問題,亟須在模型的構建和計算方法上進行改進。
1 救助問題
1.1 救助問題的分析
救助船的布置位置問題實際上是救助船停泊位置選址的問題。為提高救助成功率,應將救助船布置在最佳的救助位置。但是,由于救助船的數(shù)量有限,不可能全海域覆蓋,所以只能有針對性地在重點海域安排現(xiàn)有的救助力量,從而實現(xiàn)切實可行的區(qū)域救助方案。研究的思路為:提出假想模型、精確構建模型、確定救助船位置選址,對影響救助結果的因素進行定性分析。
根據(jù)已有的研究成果確認影響救助結果的因素有以下4個。
(1)船速。船舶的類型不同航速也不同。以集裝箱船為例,如果集裝箱船大小不一、配置不同,則航行速度亦有較大差別。接到警報后,若對遇險船的位置信息掌握不全,會導致在整個海域投放救助船的位置出現(xiàn)偏差,延誤救助時間。
(2)航線。如果遇險船是貨輪,雖然其航線比較固定,但是航區(qū)范圍很大。由于貨輪航線的變化會導致救援時間不同,也會影響救助船的位置布置[8]。
(3)求助時間。遇險船發(fā)出求救信息的時間不同,留給救助船的救助時間也會發(fā)生很大變化。越早求救,救助船就越早采取救助行動,遇險船的損失就越少。
(4)遇險船的數(shù)量。若遇險船有多艘,且都出現(xiàn)在同一救助船的救助海域內(nèi),顯然,一艘救助船無法兼顧多艘遇險船,故而,救助成功率會很低。但是,由于船舶集中發(fā)生海難的可能性不大,所以在模型中假設該情況不發(fā)生。
1.2 模型假設及參數(shù)
根據(jù)對影響遇險船救助因素定性分析的結果,在建模時有以下假設:
(1)遇險船類型相同,救助船噸位也相同,船舶間的差異主要體現(xiàn)在船速上[9]。
(2)所有船舶均勻速航速。
(3)救助船的救援目的地為預計遇險船與救助船相遇地點(即根據(jù)遇險船航行路徑估算出的救助位置),并非遇險船的實時位置。
(4)只有當遇險船進入搜救指揮中心搜尋范圍內(nèi)才可能被發(fā)現(xiàn),并通知最近的救助船開始施救[10]。
(5)一艘遇險船至少需要一艘救助船救助,即一艘救助船不能同時給多艘遇險船提供救助。
根據(jù)上述假設,使用數(shù)學語言對救助行動進行描述。
設:在航區(qū)航行的船舶有m艘,記為B=(b1,b2,b3,…,bm),遇險船為f艘,記為A=(a1,a2,a3,…,af),救助站有救助船t艘,記為D=(d1,d2,d3,…,dt)。
基礎參數(shù):



Ra為遇險船的航行半徑,n mile;
Rd為救助船的航行半徑,n mile;
T為以遇險船遇險時刻為起始時間,救助船開始向遇險船位置方向航行所需的準備時間;
Tji為從第i艘遇險船駛入第j艘搜救船舶搜救范圍始計,至被第j艘搜救船發(fā)現(xiàn)并確認遇險船所消耗的時間;
Tjh為從第h艘救助船接到第j艘搜救船的求助信息始計,至第h艘救助船抵達遇險船位置所消耗的時間;



2 構建模型
依據(jù)救助程序,可將該過程分為選擇遇險船,搜救船發(fā)出遇險船的求救信息,救助水域救助船的位置選擇,構建救助站救助船布置位置選擇模型。
2.1 目標遇險船的選擇與救助模型

(1)
實際上,處于救助范圍內(nèi)船舶的數(shù)量通常不能確定,而對于遇險船來說,被救助越早越好,因為等待的時間越長,救援成功的可能性會越小,所以遇險船會第一時間報警,離其最近的救助船會對其施救[11]。
在確定被救助的遇險船后進入救助階段,現(xiàn)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救助時刻用圖1表示。

圖1 救助階段示意圖
救助可分為4個階段(如圖1所示),圖1(a)表示遇險船信號發(fā)出。圖1(b)表示救助船向遇險船駛去,但遇險船還沒有進入救助中心發(fā)布的搜尋范圍。圖1(c)表示遇險船進入搜救范圍,救助船發(fā)現(xiàn)遇險船,同時也向附近的船舶發(fā)出求救信號。圖1(d)表示救助船適時地趕到遇險海域,成功地救助遇險船[12]。
為了便于利用數(shù)學語言描述救助過程,需建立直角坐標系。假定遇險船的航行路線是沿y軸正向,如圖2所示。

圖2 遇險船與救助船航線圖
假設遇險船為貨輪,以遇險船發(fā)出求救信號時刻為起始時間,g點為遇險船的遇險地點,f點為貨輪航行的起始點,若沒有救助船救助,貨輪會按圖2所示航線最終進入搜尋海域。

(2)
(3)
(4)

(5)
(6)
其中,d1=d2=
最后,聯(lián)立式(5)和式(6),積分后得到遇險船航向函數(shù)表達式為:
(7)

(8)
因為已經(jīng)假設貨輪航向與y軸平行,所以x橫坐標是恒定的。將x代入遇險船航向函數(shù)可求得救助船趕到出事海域時的縱坐標。據(jù)此可計算出救助船搜尋遇險船的時間。
(9)
2.2 遇險船求救及救助船救助模型
計算遇險船從遇險到進入搜尋范圍的時間,從而求出救助船最大可用救助時長。
當遇險船進入搜尋范圍時,兩船間達到警戒半徑距離,其數(shù)學表達式為:
(10)

(11)
(12)
然后求得:
(13)
求解式(12)后得到多個結果,導致式(13)也有多個結果,在此,選取最小的t′作為觸發(fā)遇險船警戒的解,得到救助船的最大可用救助時間為:
tji=t-t′。
(14)
2.3 重點海域全覆蓋的救助位置選取模型
對遇險船的目標選擇過程與救助過程進行分析模擬后,可得到最可能發(fā)生險情的遇險船航行地點。因為遇險船的始發(fā)港及航線有不確定性,所以需要多次模擬分析,計算出從不同港口出發(fā)、不同航線的船舶險情多發(fā)海區(qū)地點,從而選取出重點海域。
(15)
推導得到救助船的救助時間為:
(16)
將tjr、tjh做差得到
Δtjih=tji-tjh。
(17)
假設用變量Zi來衡量救助效果,并令其取值范圍為[0,1]。當Δtjih≥0,表示救助船會及時趕到事發(fā)海域,科學施救。完成一次成功救助時,則Zi=1;如果Δtjih<0,救助失敗,則Zi=0。同時,為了提高海上救助策略的成功率和抗風險能力,Δtjih的數(shù)值越接近1表明救助協(xié)調(diào)中心處置突發(fā)事件的能力越強。為此,設置一個合理預留時間量,使Δtjih大概率地大于該預留時間量。假設用變量ωi表示救助預留時間量,其取值范圍為[0,1],若Δtjih=0,則ωi=1,反之ωi=0。
所以,遇險船舶的目標方程可定義為
(18)
(19)
這是一個兩航段的海區(qū)位置選擇模型,在第一航段θ不變的前提下,首先以式(18)作為遇險船的目標方程進行求解,然后以該初解結果對式(19)進行求解。
2.4 模型分析
基于重點海域覆蓋的救助站的救助船布置位置模型可采用以下5個步驟進行構建:
第一步,根據(jù)搜救中心數(shù)據(jù)平臺獲取的遇險船和事發(fā)海域附近船舶的位置坐標及航速的最新信息,隨機生成遇險船事發(fā)地的救助船位置作為模型的初始數(shù)據(jù)[13]。
第二步,根據(jù)遇險船目標的選擇與事發(fā)地海域附近船舶模型,將第一步獲取的數(shù)據(jù)代入第二步,計算出事發(fā)海域多艘船舶中最可能的目標遇險船及其船位,給出救助站的救助船可利用的最大趕往事發(fā)地的救助時間。
第三步,將所選取的事發(fā)海域按一定長度間隔劃分成網(wǎng)格,以式(18)為遇險船的目標方程,運用遺傳算法求出該海域救助站多艘救助船的最優(yōu)救助位置,使救助點覆蓋率達到100%且救助站位置為最優(yōu)。
第四步,根據(jù)遺傳算法求解的結果,采用貪心算法進行改進,統(tǒng)計小于最優(yōu)的結果經(jīng)改進后是否能提高救助點覆蓋率,從而實現(xiàn)重點海域救助范圍的全覆蓋[14]。
第五步,在第四步遺傳算法求解結果的基礎上,計算所有Δtjih的結果。若該結果大于救助預留時間,則計算結果為模型最優(yōu)結果;若結果小于該時間,則以式(19)為救助目標方程運用貪心算法進行改進,直至ξ的值接近0。
3 案例分析
選取威海成山角附近海域作為實例研究區(qū)域,按照構建模型的假設,選取37°23′N,122°42′E作為坐標原點,以向東方向作為角的始邊,沿逆時針方向轉(zhuǎn)98.32°后的終邊作為y軸方向,采用n mile作為坐標軸的基本單位。選取2018年8月8日12:00位于該水域的船舶作為研究對象,根據(jù)成山角交管中心(VTS)統(tǒng)計數(shù)據(jù),最終確認42艘船舶的信息數(shù)據(jù)符合模型條件,在該基礎上進行案例研究。
在多發(fā)海難事故的報告線以南海域隨機抽取成山角海域100個縱坐標,選擇縱坐標對應的海域位置為遇險船船位。生成的縱坐標對應成山角VTS報告線內(nèi)、外水域的位置。
按照1 n mile的長度間隔在所建坐標區(qū)域劃分網(wǎng)格,從已有備選海域選擇救助船初始位置,運用遺傳法(變異率為0.05,交叉率為0.3,迭代數(shù)為200次),利用MATLAB軟件進行計算,從救助站選取1艘救助船船位為始點,逐步增加救助船分布范圍內(nèi)的數(shù)量,求得該救助站多艘救助船情況下的最佳救助效果,計算結果如表1。從表1看出當救助站在該海域部署4艘救助船時,救助覆蓋率為97%,當部署5艘救助船時,救助覆蓋率100%。

表1 利用遺傳法計算得到的救助船艘數(shù)與救助覆蓋率

(20)
為了提高救助范圍覆蓋率,基于案例中改進計算方法的原則對救助站位置進行改進,計算結果表明,在救助站布置4艘救助船時,該海域救助覆蓋率仍然是97%,因此要想將救助成功率控制在最高水平(100%),救助站需部署5艘救助船才能實現(xiàn)及時救助。
另外,可以根據(jù)改進策略的第二點,提高救助船駛抵事發(fā)地點的預留處置救助時間。選擇一組遺傳算法初始計算結果(6,145),(3,72),(2,-8),(25,353),(15,226),(5,275),(35,297)進行改進,經(jīng)過改進后的救助船位置為(5.009 5,140.054 7),(2.986 7,74.590 5),(2.058 3,-9.238 5),(25.108 6,354.026 4),(16.824 2,228.813 3),(6.894 6,274.918 5),(34.604 6,297.858 8)。對比救助船的初始和改進后的位置,發(fā)現(xiàn)救助站救助船的布置位置略微有了調(diào)整。
將救助船的初始位置和改進后的位置相比較發(fā)現(xiàn),如果采用初始的救助站救助船布置位置,將使最大救助時長與實際救助時長差值保持在0.1 h以內(nèi),從而給救助站救助船的實際施救工作造成很大壓力。而經(jīng)過改進后的救助船布置位置可以使救助行動的施救時間小于最大可用救助時間(0.1 h),這充分證明該模型和算法具有一定的可靠性和實用性。
4 結語
針對海上救助這一難題,構建基于重點海域覆蓋理論的救助站救助船位置布置模型,將遺傳算法和貪心算法相結合,用于救助船船位選擇,提出適用救助船選址的新的計算方法,采用威海成山角海難事故多發(fā)水域作為案例進行計算,獲取案例海域需要布置的救助船艘數(shù)及其相應的位置。結果表明建構的模型及算法均具有合理性與可靠性。
因為海難救助受到諸多因素影響,尚有許多變量需要引入,因此,構建考慮更多影響因素在內(nèi)的更加合理的救助站救助船位置布置模型是今后深入研究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