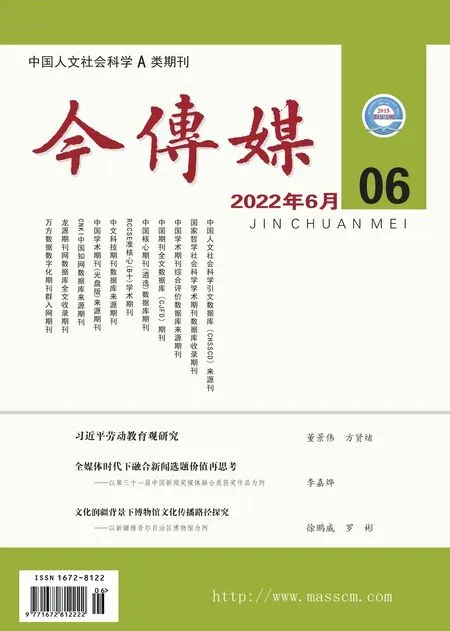美麗鄉村建設中的傳統手工藝再生創作
——以華縣皮影為例
張瀟娟
(西安美術學院,陜西 西安 710065)
鄉村是每一個中國人生存成長的根基,源遠流長的農耕文明土壤里蘊藏著博大精深的傳統文化資源。對于鄉村建設一系列問題的關注是一個歷久彌新的話題,早在19世紀末就出現了有識之士關于農村建設的多種倡導,結合當時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實際,先后提出了重農、重工、農村工業化等不同的鄉村建設思路。新中國成立以后,計劃經濟體制下土地集體制的農村,為中國的工業化、鄉鎮化發展提供了保障。1978年,通過鄉村改革開放解決“三農”問題,人民的生活開始從溫飽逐步向小康社會邁進。2015年提出的 《美麗鄉村建設指南》使得鄉村建設標準化、規范化。黨的十九大提出鄉村振興戰略,中國鄉村的經濟、文化建設隨著時代的發展再次面臨著新的挑戰與機遇。當代科技生產力的飛速發展,給城市帶來的發展變化是空前的,與此同時,中國城市與鄉村間的差異性也愈加明顯,因此,鄉村建設是打破城鄉差異的有效途徑,也是美麗中國建設的必然所在。
一、美麗鄉村與手工文化
鄉村是生發中國傳統文化的原點,美麗鄉村的建設是對中華民族根基的維護。建設美麗鄉村的維度是寬泛多元的,鄉村環境建設是最基礎的建設內容,但又不僅僅是民居排列整齊、鄉村道路平坦干凈、房前屋內潔凈敞亮、衛生情況的改進或公共設施的健全;當代鄉村的美麗更應是人與自然的和諧共處,是鄉村整體生態環境的平衡與可持續發展。只有良好的自然生態才是鄉村獲取財富的源泉,即“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深刻內涵。當下,把鄉村當作城市的垃圾場等事件時有發生,城市“搶奪”了鄉村的青壯勞動力,在鄉村建造粗放型工廠,城市文明消費下的遺棄物填埋在鄉村的溝壑。鄉村自己也在過度損耗自然生態,田間地頭的塑料薄膜隨手遺棄、農藥化肥的超標超量使用,采石、取沙、伐木往往隨意而為,等等。事實上,鄉村應該是中國城市化建設、打造美麗中國道路上的無憂后花園。
農耕文明孕育著中華民族的博大,傳統手工文化的根脈深深根植于此。中國幾千年的農耕文明中孕育了一部燦爛非凡的手工藝發展史,散落在鄉村的手工藝彰顯了中國勞動人民的造物觀、審美觀、價值觀。美麗鄉村建設呈現出積極健康的精神風貌,傳統手工藝中凝結的文化自信也最能體現鄉土文化精神。因此,鄉村的美麗要建立在生態環境基礎上,對其精神文化層面進行維護與建設;鄉村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對傳統手工文化而言,是至關重要的。生態環境失衡導致手工藝產品賴以存在的物質材料的匱乏乃至消失,是當下眾多傳統手工藝無法得到傳承發展的主要原因之一。在美麗鄉村建設中,傳統手工藝對生態環境的需求促使鄉村生態環境的良性發展,只有當鄉村各種物質條件充沛時,以傳統手工藝振興鄉村經濟、文化的路徑才能行之有效。
二、華縣皮影手工藝創作群體現狀
鄉村中的傳統手工藝通常是改善民眾生活現狀的一種謀生之道,在今天依舊可以通過“手工藝”改變生活現狀,進而提升鄉村經濟的發展水平。傳統手工藝在當代鄉村再次煥發生機,須從手工藝現狀入手,充分了解手工藝的優勢以及面臨的困境,了解民眾尤其是手工藝從業者的需求。華縣皮影歷史悠久,皮影制作在國內首屈一指,從保護、傳承、研究到創新發展皆具有一定的典型性,以此為例,可窺得傳統手工藝在鄉村建設中的重要性。
華縣皮影手工藝的保護傳承歸屬于當地文化系統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辦公室的調控管理,但更多是在官方政策下的自我發展。自我發展的方式主要有:以文獻史料展示兼傳統皮影演唱為主的華縣國際皮影博物館,以皮影影偶產業化商品銷售與皮影劇目創新的影子坊,以堅守傳統皮影造型制作與史料整理研究為主的蓆棚齋皮影博物館,華縣皮影國家級非遺傳承人汪氏入駐省城進行皮影商業銷售并與藝術家進行合作。華縣皮影的制作傳習在20世紀初曾一度風靡,還有零散分布于鄉村的傳承者。目前,各傳習藝人既有以皮影手工藝獲取經濟效益的,也有在時代背景下對從事多年的手工藝的自覺保護與傳承。
三、皮影藝人的傳承與創新
對皮影手工藝人而言,皮影創新的意愿既有來自市場的刺激,也有個人審美意識下的創新意愿。但由于皮影制作者本身學識的局限性,在創新中往往簡單直接,因此,提升手工藝人自身的學養、審美,是傳統手工藝傳承創新的一個重要任務。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皮影手工藝更多是影偶從幕后走到臺前,活態的影偶表演成為靜態的影偶展示。戲曲表演中的“偶”,由于曲詞唱腔與表演者的操縱,影偶是有血肉有精神的,當影偶脫離操縱者和幕布燈光,以工藝品的角色進入觀者的視野,它所承載的文化藝術信息會因語境的轉換而導致部分流失。
華縣皮影藝術從業者對于傳統的堅守與創新各有傾向,一種傾向是堅守傳統皮影造型、色彩、制作流程等,保持皮影藝術的“手工”特性。市場上甚至出現了以純手工制作作為影偶銷售價碼重要條件的現象,對非專業的民眾而言,其辨識度并不明顯。傳統皮影本身就是一門具有獨特魅力的雕刻藝術,手工藝的藝術價值試圖通過經濟價值來體現本無可厚非,但是,當市場上出現以機器制作的產品來壓低售價的現象時,對堅守傳統的藝人而言,其從業道路就會更加困難。
華縣皮影藝術的另一種傾向則是大膽創新,試圖通過現代的工具材料打破傳統皮影的固有狀態,比如造型、尺寸、題材內容,甚至是相應的演出形式。皮影制作藝人的創新通常是使用最簡單的方法,將動態影偶靜態化處理或將獨立影偶組合以敘事性場景再現。在傳統皮影中,人物的軀干、四肢等是可以活動的,尤其是人物和動物組合的坐騎類,正是由于傳統影偶關節的可活動性,在表演中才能表現出馬上對陣廝殺或奔跑的舞臺效果。創新影偶通常將馬與人物全部固態化處理,在平面展示中具有便捷性,但是,整體造型的靈活性則需要保留與呈現細微處的變化。小物放大也是皮影制作藝人常用的方法。通常在一些定制作品或活動作品中使用,放大后的影偶與傳統演出影偶的造型、裝飾、著色一致,但在視覺上產生了極大的不同。此外,藝人們根據皮影造型、裝飾的規律與特點,從其他藝術形式諸如剪紙、工筆繪畫等中借鑒構圖與內容,轉化為皮影藝術語言,或者說將參考圖以牛皮材料制作并進行著色處理。但是,筆者認為這些簡單的置換方式,既削弱了皮影藝術的本體語言特征,又不能滿足大眾的審美需求。
在市場需求下,華縣皮影藝人也嘗試進行相關文創產品的設計與制作,但是一般都是用皮影直接轉化,缺少設計與獨特性。常見的皮影文創產品多見于牛皮制作的書簽、擺件、影偶伴手禮等。
四、藝術家介入傳統手工藝的再生創作
當代,藝術家介入傳統手工藝是不容小覷的力量。當藝術家走進鄉村、探尋文化本源,獲取藝術創作更多可能性的同時,也為傳統手工藝注入了新的創造力量。藝術家介入鄉村建設、對鄉村原有傳統藝術進行再創作,既是中國鄉村文化復興的一種表現形式,又是美麗鄉村重建的文化自覺。
在傳統手工藝的再生創作中,成熟藝術家的帶動力量是巨大的,鄔建安、邱志杰等藝術家與華縣皮影制作者的跨界合作,使得華縣皮影在“威尼斯雙年展”得以展示,并在國際上引起了不小的轟動。在華縣皮影文創產品設計中,西安曲江明清皮影博物館堪做楷模,擔任館長的任華老師是一位設計師,因其藝術家的審美與經驗使得皮影文創產品精彩紛呈。蓆棚齋皮影博物館的皮影年歷及周邊衍生品,也是由專業設計師進行設計開發的,從產品設計到包裝應用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
藝術家借助傳統皮影手工藝進行的再生創作,既是個人藝術創作觀念的體現,也是對華縣皮影的宣傳與推動。但是,這種“走出去”的方式對鄉村文化自身建設的推動力不及“請進來”的力度明顯,比如,渠巖老師發起的“許村計劃”、武小川老師發起的“忙罷藝術節”等,同時,通過作品展示出鄉村的歷史、文化、自然的獨特魅力,也展示出鄉民的生活狀態與精神面貌;為鄉村民眾的物質生活帶來了經濟效益,是對鄉村民眾精神世界的維護。
在美麗鄉村建設、鄉村文化振興的契機之下,傳統手工藝需要藝術家的介入,藝術家們心系鄉村、走進鄉村、融入鄉村,用藝術再生創作修復鄉村日趨式微的文化價值,構建新時代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的美麗鄉村。
五、地方高校教育反哺鄉村文化建設
傳統手工藝文化對地方高校藝術專業的滋養是必然的,西安美術學院公共藝術系長期以來立足傳統,在當代與傳統之間不斷尋求契合點,開設了 《傳統文化考察》《傳統語言轉換》課程,從田野考察、資料收集整理到語言轉換,并就地域性傳統手工藝進行再生創作形成了較為成熟的教學體系。近年來,以西安美術學院公共藝術系“考工集藝”為學科目標,對陜西傳統手工藝,尤其是皮影藝術進行了考察研究,并將皮影藝術再生創作納入多門課程中。
在教學中,針對傳統手工藝的再生創作趨于兩個方向:一是以藝術創作為目的,學生在傳統手工藝中發現材料、技藝的創新點,完成從傳統到當代的轉化;二是針對傳統手工藝的文創產品設計,最終以作品回歸于傳統手工的生產銷售路徑,為傳統手工藝的發展帶來經濟效益。在此創作路徑中,學生通過對華縣皮影文史資料的梳理,對藝術本體深入分析并進行結構重組,并以平面、立體裝置、動畫、衍生品等再生創作形式進行了大膽的嘗試。因此,學生與鄉村、與鄉村手工藝之間還需加強有效連接,可通過學校與地方政府合作、建立高校實習實踐基地等,進一步推進高校教育在鄉村文明建設中的作用。高校藝術專業教育針對地域傳統手工文化的復興發展,實為通過專業實踐活動反哺社會、反哺鄉村,促進鄉村文化建設。
華縣皮影的再生創作以及在鄉村文化建設中取得的成績是顯著的,在地方文化形象打造、吸納從業人員緩解地方就業、老藝人生活保障等問題上皆有成效,同時為中小學、高校提供了豐富的研學項目,對傳統手工文化的宣傳、民族文化自信心的樹立都是有益的。但是,在華縣皮影手工藝再生創作中,也存在一些需要解決的問題。比如,鄉村傳統手工藝不應該僅僅被當作獲取元素的對象,其再生創作既需要創作主體的堅持,也需要外圍力量的支撐,只有多方凝力才能重塑傳統手工藝傳承發展的新路徑;傳統手工藝的持續性、漸進式發展需要在民眾需求的基礎上,在審美、應用層面進行引導,通過再生創作,在傳統文化與當代消費群體之間搭建橋梁,彰顯傳統手工藝與當代手工藝創作觀念的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