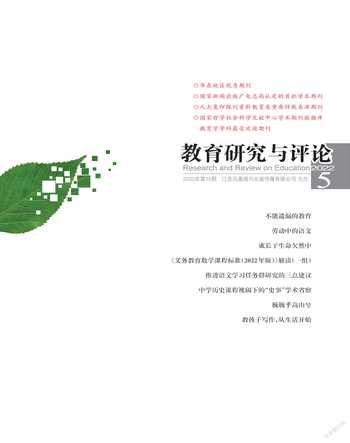追問:一種深入解讀文本的密碼


摘要:文本解讀是閱讀教學的起點。將追問作為深入解讀文本的密碼,能讀到別人目光所不及、思想所不到之處。以追問深入解讀文本,可以問在與常理相悖處,問在言語表達獨特處,問在情感轉折處。
關鍵詞:追問;文本解讀;閱讀教學
文本解讀是閱讀教學的起點。如果把閱讀教學比喻成登山,把教師比作導游,那么文本解讀的程度就決定了導游能帶著游客登到山的何處。教師拿到一篇文本,如何能找到深入解讀的密碼?讀到別人目光所不及、思想所不到之處呢?
一、 將追問作為深入解讀文本的密碼,源于與徒弟的一次對話
徒弟要執教四年級上冊的《西門豹治鄴》,我問她:“西門豹是怎么治鄴的?”她說:“西門豹先向老大爺詢問民情,得知是巫婆和官紳害得老百姓流離失所,便想辦法懲治了他們。最后帶領百姓興修水利,讓鄴縣得到了發展。”“嗯,文章內容概括得不錯!這是老師和學生都能看見的內容。”我繼續問:“再想想,你還讀到了什么大家看不見的內容?”徒弟語塞。
相信徒弟的困惑也是許多年輕教師的困惑——拿到一篇文章,了解了故事情節,知道了語文要素,明白了課后習題的要求,便以為讀懂了文本,于是自信滿滿地走進課堂,和學生聊得不亦樂乎。殊不知,自己的解讀未見得比學生的高明,未見得能給學生帶來更多的啟發和思考。甚至有些時候,教師在課堂上是被學生啟發的。
我一直覺得,語文教學中,教師要用心、靜心解讀文本,并將自己的解讀巧妙融入恰當的引導中,帶著學生訓練語言、發展思維,探究文本言語背后的秘密,步步攀爬,終到恍然大悟,“一覽眾山小”。恰當引導的前提,是教師對文本深入的理解。如何深入?追問,是一條路徑。
當我把自己的想法和徒弟交流時,徒弟又有了新的困惑——“要在哪里追問呢?”對此,我沒有急于告知,而是拿出一支筆,圈畫出了文中的一些詞語(如圖1所示)。
圈畫完詞語,我讓徒弟讀一讀這些詞語,想一想能提出什么問題。下面便是我們的一番對話——徒弟問:“西門豹為什么故意拖延時間呢?”我反問:“你說呢?”
“因為他想給其他官紳一個下馬威。”徒弟答。
我緊接著問:“要治官紳,抓起來就好了呀,干嗎要如此拖沓,大費周章呢?”徒弟答:“因為他要向老百姓驗證有沒有河神。”
我追問:“他為什么要驗證有沒有河神?”徒弟答:“他要讓老百姓相信河神的說法是迷信。”
我進一步問:“他為什么要大費周章地讓老百姓相信河神是假的呢?”
徒弟恍然大悟:“哦,我知道了!因為老百姓如果不相信,還繼續迷信的話,即使西門豹把巫婆和官紳懲治了,等西門豹一走,還會有新的巫婆和官紳來殘害老百姓。”
我笑了:“嗯,已漸入佳境了!那西門豹治鄴到底是怎么治的?”
這一次,徒弟胸有成竹地答道:“治官紳,更要治民心!治官紳容易,治民心難。民心治好了,即便后面西門豹不來了,老百姓也不會被巫婆和官紳騙了。”我欣慰地點點頭:徒弟悟出了文本的真意。
徒弟在我的層層“逼問”中逐步窺見了人物行為的妙處,也體會到了文本這幾處語言的妙處,并忍不住感慨:“原來,解讀文本這么有意思!能讀出這么多的趣味來。”
解讀完畢,徒弟問我:“師父,你是怎么能看到這幾個詞的呢?為什么我讀的時候就注意不到呢?”
二、 追問,如何問到點子上
一篇文章,要從哪里追問,才能問到點子上,才能把文本問出厚度來呢?
(一) 問在與常理相悖處
常理是人之常情,人之常想,人之常行。當一個人的情感、想法、行為和別人不一致時,這個人便是獨特的存在。我們在解讀文本時,要抓住人物言行悖于常理的獨特之處,通過追問,走近人物、發現人物、理解人物。
《西門豹治鄴》一文中,西門豹從老大爺那里得知巫婆和鄉紳害人。按常理來看,一般官員就會把鄉紳和巫婆抓起來治罪,但西門豹卻沒有按常理出牌,而是設了一個局,一次一次地耐心等待“河神”上岸。這就是西門豹行為與常理相悖的地方,讀到這里便可追問:“他這樣做的目的是什么?”學生通過進一步思考,便能感受到西門豹一石二鳥的智慧。
對人物的解讀,最怕“貼標簽”。譬如,教師問學生:“通過閱讀,你覺得西門豹是一個怎樣的人?”學生答:“我覺得他是一個聰明的人。”至于聰明在哪里,學生答不出所以然,或者淺嘗輒止。這就是貼標簽式的解讀。問在與常理相悖處,讓解讀指向對有效問題的探究,疏通、矯正與常理相悖處,學生的思維才能在逐步質疑、分析、判斷和推理的過程中走向深處,直至觸及文章主旨。
(二) 問在言語表達獨特處
語言是思維的外顯。獨特的語言必然存在于獨特的語境和思想中。教師解讀文本時如能發現文本獨特的言語形式,并據此追問,定能從思考中窺見文本表達的秘密。問在言語表達獨特處,可以是對關鍵詞語的推敲,可以是對某個字的斟酌,還可以是對人物對話的研讀,等等。
對關鍵詞語的推敲,仍以《西門豹治鄴》一課的教學為例。一般情況下,教師會以課后習題為牽引,先讓學生結合文本說一說西門豹治鄴的方法好在哪里,再啟發學生以文本線索為依托進行復述,體會西門豹的智慧。之所以這樣做,是基于對語文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理解——復述被理解為工具性,體會西門豹的智慧被理解為人文性。這其實是對文本的肢解。竊以為,發現言語表達獨特處,并據此追問,能讓學生順暢解讀出人物的獨特,快速達到言意一致。多讀幾遍西門豹懲治巫婆和官紳的情節,教師不難發現,文本中有許多關于“等”的語匯,如“等了一會兒”“站了很久”“再等一會兒”。這些言語的運用,既符合“等”這一思維邏輯,又表現了文本言語的獨特性——不斷重復。對此,教師便可追問:“西門豹為何要等?還要等那么久?這‘一等’‘二等’‘三等’背后又有怎樣的思考?”通過對這類獨特言語的層層追問,學生的思維層層遞進,便能感受到西門豹為治民心的良苦用心,感受到他的深謀遠慮。
對某個字的斟酌,古詩最有代表性。例如,二年級下冊《古詩二首》的《村居》中有一句“草長鶯飛二月天,拂堤楊柳醉春煙”。很多教師會關注到其中的“拂”字,讓學生做做動作、看看圖片,以促進理解。但僅止于此遠遠不夠,還要將解讀的視角拓寬一些:“拂”是擬人化的表達,表示楊柳接觸堤岸的一種狀態,用在此處形象生動,簡潔準確,很有畫面感,換作其他的字未必合適。如此,可以緊扣此字追問:“為什么不用‘觸’‘碰’‘掃’,而用‘拂’呢?”聯系上文的“二月天”,學生就會延伸思維:此時是早春時節,楊柳剛長出嫩芽,柳條很嫩、很輕,加上春風也是輕輕柔柔的,一個“拂”字,不僅表現了早春時節楊柳的特點,而且生動再現了春光的蓬勃爛漫,體現了作者對早春的喜愛之情。扣住這個獨特的語言點追問,就能讓學生感受到,原來情到濃時,連語言都是活潑的。
對人物對話的研讀,以四年級下冊的《“諾曼底號”遇難記》一文為例。其中有一段船長與機械師簡短有力的對話,堪稱經典——“洛克機械師在哪兒?”
“船長叫我嗎?”
“爐子怎么樣了?”
“海水淹了。”
“火呢?”
“滅了。”
“機器怎樣?”
“停了。”這段描寫沒有一個提示語,一個小節幾個字,實屬獨特的言語表達形式。在針對文本整體表述的基礎上追問“作者為什么這樣寫?”,會敦促學生聯系上下文思考,慢慢找出答案:簡短的對話是迫于當時緊急危難的情境,更能表現出哈爾威船長面對危險時的沉著、冷靜、有條不紊。此處針對言語表達獨特處的追問,提醒學生,解讀文本時,不僅要關注言語的表達特點,還要探究言語表達背后的思維與情感。
(三) 問在情感轉折處
劉勰在《文心雕龍》一書中寫道:“夫綴文者情動而辭發,觀文者披文以入情,沿波討源,雖幽必顯。”作家創作,必有感而發。閱讀文章的人,沿著文辭必能找到文章的源頭。文本解讀時,關注作者情感轉折處的言辭并進行追問,能讓學生順利找到潛藏在文本背后的創作者意圖、編者意圖,實現與文本、與創作者、與編者的多重對話。
情感轉折處往往潛藏在幾個詞、幾句話里。仍以《西門豹治鄴》一文為例。文中,西門豹對待巫婆、官紳頭子和對待普通官紳的情感是不一樣的——對待巫婆和官紳頭子時的用詞都是“麻煩你去”,結果是“架起巫婆,把她投進了漳河”“又叫衛士把官紳的頭子投進了漳河”,而對待普通官紳時的用詞是“請你們”,結果是“起來吧。看樣子是河神把他們留下了。你們都回去吧”。這樣的表述,凸顯了情感的變化與轉折。據此,教師可在之前提問的基礎上繼續追問:“西門豹對待巫婆、官紳頭子和對待普通官紳的態度為什么不一樣呢?”順著西門豹的顯而不露的情感線索,學生置換角色,走進西門豹的內心世界:擒賊先擒王,殺雞給猴看,既然已經起到了敲虎震山的作用,就沒有必要趕盡殺絕。至此,學生洞見西門豹處理事情的智慧也就水到渠成。
再以四年級上冊的《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一文為例。文中,魏校長問同學們為何而讀書,大家紛紛發表看法。當魏校長聽到周恩來說“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時,為之一振。此處的“為之一振”便是情感轉折處——在別處沒有迸發的情感,在這里產生了。讀到這里,教師就可以問:“魏校長為何聽了周恩來的話為之一振呢?”學生對比文中“同學們”的回答,不難發現,周恩來的回答顯示出一個孩子難能可貴的胸懷和抱負。至此,教學不能止步,教師不妨追問:“為何為國家讀書就能讓魏校長為之一振呢?”此時,學生的解讀視角就要從關注文內表述轉向對文章歷史背景的考證。通過考證,學生定能發現:當時的中國內憂外患,處于被人欺凌的境地,老百姓有怒不敢言,有冤無處訴,旁觀者也只能明哲保身。而周恩來——一個十二三歲的孩子,卻立志“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讓魏校長不僅看到了這個孩子的胸懷和抱負,更看到了民族的未來和希望,他當然會“為之一振”。解讀到這一層,就把書讀“厚”了,就由周恩來的志向讀到了那個年代無數有志青年的志向,就會理解:正是因為有無數個像周恩來這樣的孩子,中華民族才得以在無數次苦難中堅挺、屹立不倒。
情感轉折處還常常外顯于層次分明的行動上。《梅蘭芳蓄須》和《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出自同一單元。《梅蘭芳蓄須》一文結尾有一句話:“他的民族氣節更令人敬佩!”什么是“民族氣節”?學生不理解。結合文本來看,梅蘭芳一次次拒絕給日本人演戲這件事體現了他的民族氣節。可學生依然不理解:為什么拒絕給日本人演戲就叫有民族氣節?循著學情,深入文本,沿波討源。按照時間的順序,文章層次分明地表現了梅蘭芳拒絕的行為:1937年,藏身租界,躲避糾纏;1941年,面對逼迫,蓄須明志,賣房度日;日軍慶祝“大東亞圣戰”,要求必須上臺,他設法生病躲避。不妨畫一個簡單的示意圖表現梅蘭芳行為的轉折與遞進(見圖2)。
以上是文本的框架,教師梳理后緊扣人物行為,可以展開兩級追問。第一級,從日本人的角度追問:“為什么日本人非梅蘭芳演戲不可?”第二級,從梅蘭芳的角度追問:“為什么梅蘭芳如此堅持拒絕演戲?”基于這兩個角度的追問,啟發學生聯系當時的現實背景延伸思維,學生會了解到:日本人的堅持,一是因為梅蘭芳是杰出的京劇藝術家,可以作為藝術界的代表人物;二是因為梅蘭芳的登臺,能夠證明中國藝術界對日本的屈服。在這種情況下,梅蘭芳的拒絕,就不僅代表著個人的尊嚴,更代表著藝術的尊嚴和國家的尊嚴。梅蘭芳從躲避到蓄須、賣房,再到設法生病,險丟性命,這番堅持,正體現了孟子口中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氣節。可見,在情感外顯的行動處追問,人物的形象會更加飽滿、立體,學生理解的難點也能迎刃而解。
宋代禪宗大師青原行思提出參禪的三重境界:參禪之初,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禪有悟時,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大徹大悟時,看山仍是山,看水仍是水。文本解讀的過程也是教師引領學生參悟的過程:拿到一篇文本,讀了一遍又一遍,看到的是文本本身的內容和語言;在恰當的地方追問,且讀且思,能跳出眼前的“山水”,看到言語的秘密、情感的密碼。至于大徹大悟的“看山還是山,看水還是水”的境界,非一朝一夕之功,需要不斷修煉,結合課堂實際進一步反思,方得漸悟。
(姚賽巾,江蘇省南京市曉莊小學。著有《熊孩子唐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