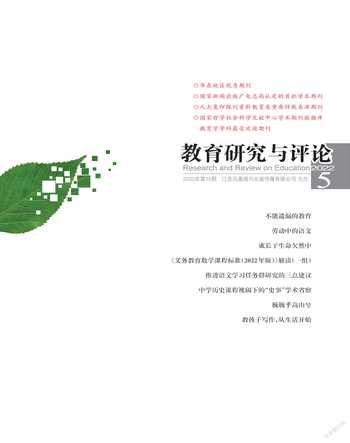每個人都需要一個“惠子”
惠子是著名的“杠精”,在政治、學術等各個層面與莊子相對立,在情誼上卻是莊子唯一的契友。惠子去世后,莊子曾跟隨從講過一個郢人斫堊的故事。這一故事從教育教學上來說,意味深長。
故事第一重,敘述郢人與石匠之關系。郢人心理素質高絕,面對鼻端揮動的大斧,可“立不失容”;石匠技藝精絕,揮斧運斤有著令人驚嘆的分寸感。郢人面對斧頭,無限信任,唯有一念:他會削去白堊。匠人面對郢人,無限自信,也唯有一念:我能削去白堊。兩人相知久矣,郢人知石匠之技藝,石匠知郢人之膽識。這是將遇良才,棋逢對手,是高峰對決,
是華山論劍,其間毫厘之差,結局不是淪為笑柄便是慘不忍睹。
故事第二重,敘述宋元君與石匠之關系。宋元君聽說石匠本領,便想一試。但,宋元君與石匠之間沒有郢人與石匠之間的默契與相知。石匠依然是石匠,技藝未落,素養猶在;宋元君不是郢人卻以為是郢人,自作多情,謬托知己。宋元君與郢人有著巨大的素養落差,他與石匠在境界上是不對等的,因此面對邀請,石匠以“臣之質(對手)死久矣”回之,言外之意“你不配質”。石匠知道自己的知己是郢人,而非宋元君,斷然回絕這種沒有任何意義的測試;重要的是,石匠的回絕是一種自傲,也是對知己的一種訴求。身懷絕技之人,比常人更渴望得到一個旗鼓相當的對手。
故事第三重,敘述莊子與惠子之關系。這是故事的落腳點。莊惠之間,既針鋒相對,又相愛相殺。他們爭執不休,渴望能駁倒對方,是對手;互相抬杠,互為對方的另一面,又是最好的朋友。他們在切磋中成長,在打磨中提升,始終是齊頭并進的競爭對手。如果莊子是刀子,惠子則是他的礪石——惠子之存在不僅測試莊子之學識,也磨礪莊子之哲思,在惠子弘揚正名、辯明邏輯之時,莊子也成就了大道無為之思想。他們的抬杠、斜杠、反杠,贏得了彼此的尊重,也贏得了中國思想史的永恒點贊。惠子去世時日越長,莊子愈加體會到孤獨與無趣。“吾無與言之矣”,這位“獨與天地精神往來”,活得逍遙灑脫的莊子,言語之間袒
露的竟是獨孤求敗式的無邊的傷感與凄涼!后世為莊子之哲思鼓與呼,不吝贊美之辭時,也應對惠子投去欣賞的一瞥,沒有他,也就沒有今天所看到的莊子。
一個人在某個領域無人可敵,開始或許喜悅,接著無趣,而后一定失落、悲哀。“高處不勝寒”,是有人與自己爭奪高處的戰栗,也是獨立高處無人抱團取暖的孤獨,前者可笑,后者可敬。莊子經過惠子之墓,思念之情油然而生,此情有著不一樣的厚重與悲哀。世人眼中,莊子是大學問家,是深不可測的海洋,只有莊子自己知道,自惠子死,學問正僵化,海洋正縮小,生命將燃盡。
世間多少學科都有類似情形:一個學者提出某種理論,總有另一個站出來,或駁斥,或爭辯,或修正,不斷與之抬杠,終使理論完善。在機遇(有機會比拼)和壓力(競爭卻又不相上下)的碰撞下,他們站在了各自領域的頂端。
峙,山旁,表示聳立、屹立。“對峙”即如兩座參天高峰在云煙之上競逐爭高,永無止境。此等境界,雙方只有彼此,再無別者。或許只有當山之巔峰俯瞰眾生之時,方可明白自己的高聳入云與對手的彌足珍貴。
惠子之存在告訴我們,每個教育工作者甚至每個人,都需要一個“惠子”。沒有磨礪與砥礪,沒有誰能走得很遠。你追我趕,對手往往能化為并肩的知音,一同“致千里”。
(江雪松,江蘇省天一中學,特級教師,正高級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