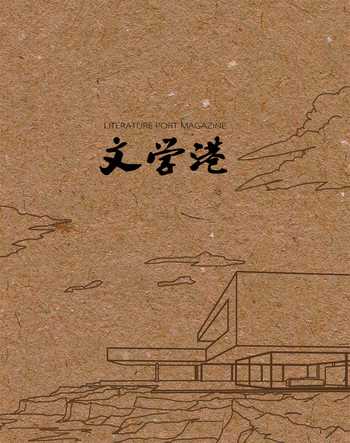創(chuàng)作談:鏡子中
李晁
《月色照人》里的故事發(fā)生在西南的鎮(zhèn)子里。鎮(zhèn)子的存在是尷尬的,它難以提供可以養(yǎng)家糊口的工作,因而人口流失是必然的。鎮(zhèn)子里的成年人大多去了遠(yuǎn)方,因?yàn)閷?duì)比鎮(zhèn)子,遠(yuǎn)方提供了更多的機(jī)會(huì)。這背景不需多言,這是幾十年來中國的現(xiàn)實(shí)。“未來”這個(gè)詞是屬于遠(yuǎn)方的,它們大多帶著城市的烙印,尤其經(jīng)濟(jì)發(fā)達(dá)的城市;而困守偏遠(yuǎn)鄉(xiāng)鎮(zhèn)的人,要么老到無法再出門工作,要么小得不足以工作;另一種狀況來自少部分青年人(應(yīng)該指出他們?yōu)閿?shù)較少),他們出于各種原因仍生活在鎮(zhèn)子里,在這個(gè)被稱作家的地方,繼續(xù)彰顯他們或隱或顯的存在。他們?yōu)槭裁戳粝聛恚@是我感興趣的。他們中的人也許到過遠(yuǎn)方,也許最遠(yuǎn)只到過所在省份的省城,但他們或多或少地接觸了外部世界,甚至參與了當(dāng)代社會(huì)里的勞作,譬如品嘗工廠流水線帶來的機(jī)械般的復(fù)制體驗(yàn)。可以想象,這掏空大腦的工作不符合他們對(duì)遠(yuǎn)方的真正期許,而報(bào)酬也足夠低廉,這是反感的源頭,所以他們回到了最初的地方。是什么讓他們放棄了金錢的誘惑(那聊勝于無的金錢),是對(duì)家鄉(xiāng)的單純依戀?認(rèn)為在那里可以持續(xù)獲得他們曾受到的庇護(hù)?這庇護(hù)產(chǎn)生的合理性必須打破他們當(dāng)初離家的期許,即認(rèn)為鎮(zhèn)子沒有希望,無法盛放理想的人生;可認(rèn)識(shí)很快得到重塑與刷新,他們發(fā)現(xiàn)在新的地方同樣沒有希望(且永遠(yuǎn)不屬于自己),在一個(gè)一切都要依靠個(gè)體且沒有固定居所的地方,生活的根基是搖搖欲墜的,這使得家這一概念變得脆弱。他們會(huì)在午夜夢回時(shí),想起那個(gè)并不富裕但仍然可以提供固定房間的家么?這一類似因素的疊加使得他們的回歸變得具有說服力——不在于說服別人,而在于說服自己。可我想說的不是這個(gè),至少不是《月色照人》這篇小說想要告訴讀者的。它直接面對(duì)的是仍生活在鎮(zhèn)子里的青年人,至于他們那小小的人生前傳,被敘述擱置起來。
既然生活在家鄉(xiāng),家庭和家族的影響便會(huì)籠罩居住其間的人,不論這人是否受到了外部世界的思想沖擊,即人與人的關(guān)系可以是最低限度的不相關(guān),進(jìn)而是冷漠的。在熟人社會(huì),一切關(guān)系都比置身陌生環(huán)境緊密,這是知根知底的連接,它提供了內(nèi)部的和諧共生;不是說此種聯(lián)系沒有矛盾,而是這矛盾沒有那么尖銳,或者被視作習(xí)以為常。這種生活更突顯了日常對(duì)人的影響。而家庭之外的生涯,便是工作,這兩部分的組合幾乎是當(dāng)代人面對(duì)的全部人生,不論是在城里還是鄉(xiāng)下。《月色照人》的寫作便對(duì)準(zhǔn)了這兩個(gè)部分,讓兩部分獨(dú)立呈現(xiàn),又產(chǎn)生各自的連接,即考察個(gè)體在家庭與工作中展現(xiàn)的不同面貌,而又達(dá)成的某種人性上的合一性。當(dāng)代都市生活給人帶來的分裂變得愈發(fā)明顯,一個(gè)人可能在工作中是一種形態(tài),在家庭里又是另一種,兩種形態(tài)各自在人性的一頭,卻不是平衡的關(guān)系,而是撕裂的關(guān)系。那么,在我所感興趣的小地方,一種小型城鎮(zhèn)里的人,他們的生活更多表現(xiàn)的是同一性,即他們很少被所謂的職場所影響,因?yàn)楣ぷ鞯牟环€(wěn)定性與松散性,無法讓個(gè)體在面對(duì)工作環(huán)境時(shí)做出相應(yīng)的調(diào)整與改變。久居小城鎮(zhèn)的人在從事與他們“相匹配”的工作時(shí),仍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他們在家庭中、在熟人社會(huì)里所塑造的人格形象。他們并不因此完美,甚至保有某種頑固的不良習(xí)性,但作為整體考量,他們身上卻具有一種單純的直接的個(gè)體魅力。這魅力也許是低沉的,或許還帶著對(duì)人生的過早放棄,但這一進(jìn)程里,每個(gè)人的具體困境都讓他們無法松懈,且最重要的是,他們對(duì)此并不察覺。
我想到安妮·普魯?shù)摹稊啾成健罚顝?qiáng)烈的感受還是來自人物,兩個(gè)毫無希望的鄉(xiāng)下男孩的故事看到最后,竟然一腳踢開了那個(gè)紛雜的時(shí)代(我們常常掛在嘴邊的時(shí)代)。杰克和恩尼斯,兩個(gè)來自貧瘠地域且沒受過多少教育的少年,初識(shí)時(shí),不到二十歲,待到杰克三十九歲不幸去世,二十年的時(shí)光就這樣被甩掉了。鮮少有短篇小說表現(xiàn)著長篇的時(shí)間跨度,并對(duì)此根本不在意。感動(dòng)也來自這里,是什么樣的生涯和心境或者說情感,足以消弭時(shí)間帶來的洶涌而又龐雜的影響,是什么讓我們深深領(lǐng)悟到,原來這是兩個(gè)如此單純的少年,他們幾乎從未長大。還記得杰克的心愿么,他只是希望和恩尼斯能經(jīng)營一家農(nóng)場,可以推斷,他們對(duì)世界的欲望早在童年時(shí)代就被打消了……換作電影,尾聲處,恩尼斯去到杰克家里,這一段的枯燥再次顯現(xiàn)了小說的自由、電影的無能為力,恩尼斯的內(nèi)心活動(dòng)無法得到有效表現(xiàn),會(huì)發(fā)現(xiàn)電影營造自然的獨(dú)特功能(譬如畫面),起到了相反的作用,它如此地虛弱,僵硬的言行,不足以表達(dá)恩尼斯來到杰克的成長之境,感受他曾經(jīng)存在的氣息。是什么讓人覺得這一刻如此重要,還在于仿佛恩尼斯在此刻變作了小小年紀(jì)的杰克,面對(duì)著陰郁的父親和壓抑的母親,替他重新生活。在今日這樣的氛圍里——讓人無限分心而又高度聚焦自我的時(shí)代——看杰克和恩尼斯如同兩個(gè)怪物,兩人竟只看重“這一點(diǎn)點(diǎn)”的情感,對(duì)不到二十歲的相遇如此眷念,對(duì)未來——包括職業(yè)和金錢等俗世目標(biāo)——如此熟視無睹,對(duì)這個(gè)世界蠻不在乎,這難道不足以挑動(dòng)我們的神經(jīng)?一個(gè)人要怎樣地存活于世,如何看待生活,杰克和恩尼斯做了“力所能及”的表現(xiàn)。他們要的東西實(shí)在有限,這恰又是世上最大的奢侈(別的我再也想象不到),一如小說里沒有詳說的兩個(gè)人的童年……他們出現(xiàn)時(shí)便那么用力,且這一點(diǎn)力保持到最后,仿佛這是他們僅有的東西,而情感的重量,是在于雙方使出的能量,在這個(gè)愛惜能量、把它視作自我寶貴財(cái)富的今天,有幾個(gè)能讓戥子的另一端微微顫動(dòng)?
這么提到《斷背山》其實(shí)和《月色照人》無關(guān),這是兩個(gè)截然不同的小說(前者是我心中完美的當(dāng)代短篇小說),唯一的聯(lián)系是,《月色照人》里的人物同樣是“毫無希望的鄉(xiāng)下孩子”,除此之外,小說不提供與愛情有關(guān)的任何深度內(nèi)容。
我希望這篇小說像一面鏡子,照出人的樣子,而非僅僅提供故事或者任何明顯的前后人物變化。因?yàn)椋谖业睦斫庵校麄冊诓恢挥X中早已是如今的模樣。當(dāng)然,最大的可能是,我沒有能力寫出這樣的變化來。5C182B28-95CB-4A42-A834-CFE1A1F0560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