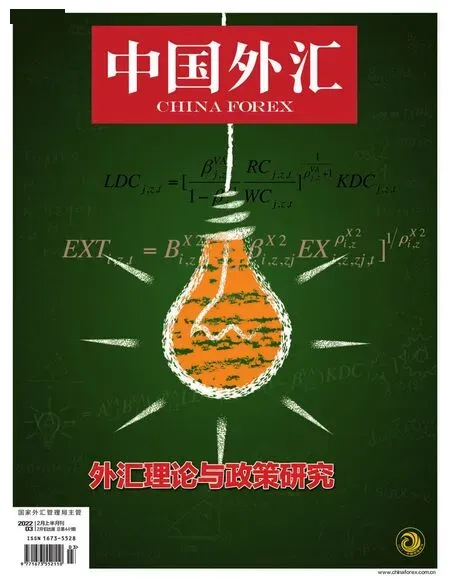貨幣國際化與國際金融治理地位:基于跨國面板數據的實證檢驗
文/戴金平 甄筱宇 曹方舟
一、引言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危機頻繁爆發,由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帶來的危害更是堪與19世紀30年代大危機相比——金融危機后世界經濟陷入長期衰退。世界各國長期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在催生資產泡沫的同時,也加劇了貧富分化。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再次引發全球性的、規模更大的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全球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推動的需求膨脹與疫情引致的供給收縮正在推高全球性的通貨膨脹(IMF,2021),并進一步集聚國際金融風險。國際金融體系的動蕩與危機彰顯了當前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內在矛盾與沖突,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迫在眉睫。
我國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的努力由來已久。2007年12月我國首次向世界銀行軟貸款窗口國際開發協會捐款3000萬美元,從世界銀行的資金受援國轉變為資金捐助國。2009年以來我國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的份額和投票權不斷提升。我國積極推動二十國集團(G20)替代七國集團(G7)成為國際金融治理的多邊治理機構,并在G20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倡導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重點服務于“一帶一路”建設,積極參與金磚銀行建設推動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盡管如此,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中的地位還十分有限,無法匹配我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和國際金融地位(戴金平和曹方舟,2021)。為此,“十三五”規劃明確了我國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目標與方向;十九大明確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十四五”規劃則將“推動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全球經濟治理體系”作為重要內容。而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變革,為國際金融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方案,關鍵是要提升我國在國際治理體系中的地位。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基本原理。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是上層建筑,哪些因素決定了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中的權利分配?換言之,一國的國際金融治理地位由哪些因素來決定?這是本文要回答的基本問題。
國際貨幣體系是國際金融體系的核心,美元體系是國際貨幣體系的核心,美元霸權是國際貨幣體系和國際金融體系內在矛盾沖突的根源。美元危機的頻繁爆發不僅沒有降低國際金融體系對美元的依賴,反而強化了美元體系,進而使全球經濟面臨巨大的不確定性(王達和高登·博德納,2020)。美元體系治理成為國際金融治理的難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既是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的重要內容,又是國際金融治理體系變革的物質基礎。在研究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地位時,本文在充分考量一國經濟實力、政治軍事實力、國家治理水平、幣值穩健性等因素的基礎上,重點研究貨幣國際化對一國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地位的影響。
本文選取國際貨幣體系中的5個主要主權貨幣——美元、歐元、英鎊、日元、人民幣和發行主權貨幣的7個國家——美國、德國、法國、意大利、英國、日本、中國(將歐元區國家簡化為德國、法國和意大利),通過構建貨幣國際化指數和各國國際金融治理地位,在引入國家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國家治理水平、幣值穩健性等控制變量的基礎上,實證檢驗了一國貨幣國際化對其國際金融治理地位的影響。本文的貢獻在于,揭示了影響一國國際金融治理地位的因素,尤其是貨幣國際化對國際金融治理地位的決定性影響。
二、模型與指標構建
(一)模型構建
本文基于中國、美國、日本、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7個國家2008—2018年的面板數據,構建了以國際金融治理地位為被解釋變量、以貨幣國際化程度為核心解釋變量的如下計量模型:

(二)變量選取與說明
1.國際金融治理地位測度
一國的國際金融治理地位是指該國在全球金融治理體系中的地位,而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是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國際清算銀行(BIS)、區域開發銀行等全球金融治理機構以及由這些機構制定的一系列全球金融規則、目標價值體系與制度體系構成。因此,一國的國際金融治理地位由該國在國際金融治理機構的話語權和影響力來決定。由于國際金融治理機構的重大決策往往由各成員國投票決定,本文參考了戴金平和曹方舟(2021)的研究,用一國在國際金融治理機構中的加權平均投票權來衡量該國的國際金融治理地位。
表1列出了主要國家國際金融治理地位指數。可以看出,我國國際金融治理地位指數從2008年的3.5247%增長到2018年的5.9823%,十多年間增長了近70%,說明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中的地位和影響力不斷增強,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盡管如此,與美國、日本、德國等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國際金融治理地位仍處于較低水平,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發揮的作用依舊有限。

表1 主要國家國際金融治理地位指數(單位:%)
2.貨幣國際化程度測度
貨幣國際化,就是一國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承擔交易媒介、記賬單位和價值儲藏職能。由于國際貨幣體系是國際金融體系的核心,一國的貨幣國際化程度能夠反映該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地位,貨幣國際化程度越高的國家,其國際金融地位越高。已有文獻表明,主要有兩種測度貨幣國際化程度的方法。其一,用一國貨幣承擔單一國際貨幣職能的程度,如用該貨幣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份額(鐘陽和丁一兵,2012)、在國際債券和票據中的份額(李稻葵和劉霖林,2008;白曉燕和鄧明明,2013)、在央行外匯儲備中的份額(韓劍,2011;甄峰,2014)等來反映該國貨幣國際化程度。這種方法僅能反映一國貨幣具體承擔國際貨幣某項職能的程度,無法全面測度一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其二,選取一國貨幣履行國際貨幣三大職能的多項指標,通過將這些指標加權平均得到綜合的貨幣國際化指數(彭紅楓和譚小玉,2017;戴金平和甄筱宇,2020),該方法解決了單一指標的局限性問題,因而能全面測度出一國貨幣的國際化程度。
基于此,本文選取了人民幣、美元、日元、英鎊和歐元履行國際貨幣職能的二級指標,具體指標體系描述見表2所示。需要說明的是,二級指標大多為季度數據,為保證數據頻率的一致性,用quadratic-match方法將年度數據轉化為季度數據。此外,全球外匯交易的貨幣份額由BIS每三年公布一次,本文用插補法對空缺數據進行補充。

表2 貨幣國際化程度指標體系的描述和數據說明
在權重設定方面,由于各個二級指標反映一國貨幣履行單一貨幣職能的程度,其對一國貨幣國際化程度的重要性不同,在無法對其權重做出準確判斷時,采用主觀權重設定會影響貨幣國際化指數的準確性和可靠性,而主成分分析法通過降維將多組高度相關的變量轉化為一組互不相關的變量,并通過賦予這些變量權重計算出最終的指數,該方法能夠很好地解決主觀權重設定的問題,因此本文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對各個二級指標賦予權重,計算出綜合的貨幣國際化指數。具體而言,假設由時間區間為的個反映貨幣國際化程度的二級指標組成的指標體系矩陣為為該指標體系的協方差矩陣,記該協方差矩陣的第個特征值為、第個特征向量為,由此第個主成分可以表示為,并且。根據各主成分對一國貨幣國際化程度的貢獻性,構造出一國加權平均的綜合貨幣國際化指數:

表3列出了用于測度貨幣國際化程度的二級指標的最終權重,可以看出,央行外匯儲備的貨幣份額(RCR)以及全球對外信貸的貨幣份額(GFCCR)對一國貨幣國際化程度的影響最大,說明價值儲藏職能對于一國貨幣國際化非常重要,高水平的貨幣國際化最終通過價值儲藏職能的發揮來實現。通過將這些二級指標加權平均可以得到主要國家的貨幣國際化指數,各主要國家和地區貨幣國際化指數見表4和附圖。

表3 貨幣國際化程度指數的最終權重

表4 主要國家和地區貨幣國際化指數(單位:%)

附圖 主要國家和地區貨幣國際化指數(單位:%)
從表4和附圖中可以看出,近年來我國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不斷提高,從最初的1.0590%到2018年的3.4221%,人民幣國際化程度提升了3倍,但與美國、歐盟等相比,人民幣國際化仍處于較低水平,我國仍需進一步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除此之外,雖然近年來世界各國對以美元為主的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的呼聲日益明顯,但從目前來看,美國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仍處于強勢地位,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仍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3.控制變量
一國的國際金融治理地位不僅是該國國際金融地位的彰顯,更要有該國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政治地位作為基礎,還要有幣值的穩健性作為保障。因此,本文借鑒已有研究,引入國家經濟實力、治理水平和幣值穩定性等控制變量:(1)國家經濟實力,用一國國內生產總值占比(gdpr)和國際貿易占比(tr)來衡量;(2)軍事實力(military),用一國軍費開支占GDP的比重來表示;(3)國家治理水平,用政治穩定性程度(stability)和政府有效性程度(gorvance)來衡量;(4)幣值穩健性,用一國通貨膨脹率(inflation)、實際利率(rrate)和匯率水平(exchange)來衡量。具體變量定義和描述性統計見表5。

表5 變量說明及描述性統計表
三、實證檢驗與分析
對于模型(1),本文采用廣義最小二乘法和固定效應進行估計,估計結果見表6所示。表6中第(1)、(2)列僅考慮了一國貨幣國際化程度對其國際金融治理程度的影響,可以看出,一國貨幣國際化程度的提升可以顯著促進該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地位;第(3)、(4)列引入國家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治理水平以及幣值穩健性等控制變量后,貨幣國際化的系數仍顯著為正,說明一國貨幣國際化程度越高,該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地位越高。在控制變量方面,一國GDP占比越高、匯率越升值、政治越穩定、政府效率越高、軍費支出越大,該國國際金融治理地位越高。此外,廣義最小二乘法估計和固定效應估計的估計結果基本一致,說明了估計結果的穩健性。

表6 模型估計結果
從估計結果中可以看出,一國的貨幣國際化程度是影響該國在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地位的重要因素。就我國而言,隨著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人民幣貿易結算、記賬單位以及價值儲藏職能的不斷發展使得世界各國對人民幣這一全球金融公共品需求的不斷增加,降低了世界各國對單一信用主權貨幣的依賴,緩解了美元“特里芬兩難”困境,人民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影響力不斷提升,從而使得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地位不斷提高。與此同時,在人民幣國際化不斷推進的過程中,人民幣境外清算制度進一步優化,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等金融基礎設施建設不斷完善,亞投行等國際性多邊機構的全球金融服務作用進一步擴大,我國向世界提供金融服務和治理的能力和效率不斷提升,從而促進了我國國際金融治理地位的提高。
除此之外,一國的國際金融治理地位與該國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政治地位和幣值穩健性相關聯,經濟實力是一國進行國際金融治理的基礎,政治和軍事實力能夠鞏固該國的國際金融治理地位,幣值穩健則增強了世界各國對該國參與國際金融治理的信心。近年來,我國經濟、軍事實力不斷增強,國家治理水平不斷提升,這些都為我國積極參與國際治理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我國在國際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地位不斷提高。
四、結論與政策建議
本文探究了一國國際金融治理地位的決定因素,尤其是研究了貨幣國際化與其國際金融治理地位的關系。首先,本文構建貨幣國際化指數和國際金融治理地位指數,研究發現近年來我國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不斷提升,并且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但與美國等發達國家相比,人民幣國際化程度仍處于較低水平,同時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相對較弱;無論是貨幣國際化水平,還是國際金融治理地位,都無法與我國的國際經濟地位相匹配。其次,本文基于跨國面板數據,實證檢驗一國貨幣國際化、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國家治理水平和幣值穩健性等因素對其國際金融治理地位的影響,研究發現一國貨幣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可以顯著提升其國際金融治理地位,并且一國經濟實力越雄厚、軍事實力越強、國家治理水平越高、幣值越穩健,該國國際金融治理地位越高。概括來說,一國的國際金融治理地位不僅是該國國際金融地位的彰顯,更要有該國的經濟實力、軍事實力和政治地位作為基礎,還要有穩健的幣值作為保障。
基于以上研究結論,我國要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推動國際金融治理體系改革,為國際金融治理體系貢獻中國方案和中國智慧,關鍵是要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中的地位。而要提升國際金融治理體系地位,就需要堅定不移地推動改革開放,推進高質量發展,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體工作思路可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其一,堅持高質量發展,培育經濟發展動能,提升我國經濟實力,堅持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升國家治理水平,為我國參與國際金融治理提供強有力的經濟和政治保障;其二,繼續深化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有序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完善金融市場發展,擴大金融市場對外開放,夯實人民幣國際化基礎;其三,推動人民幣國際化向更高水平發展,完善人民幣國際化基礎設施,提高人民幣支付和清算效率,加強我國與其他國家的雙邊貨幣合作,發揮人民幣在國際貨幣計價、結算、儲備中的作用,積極為世界各國提供人民幣這一全球金融公共產品,從而提升我國國際金融地位,打破美元“一家獨大”局面,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其四,以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SDR)貨幣籃子為契機,繼續增加我國在國際金融機構中的份額,提升我國在國際金融機構的話語權,積極推動國際金融體系變革,為國際金融體系改革提供中國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