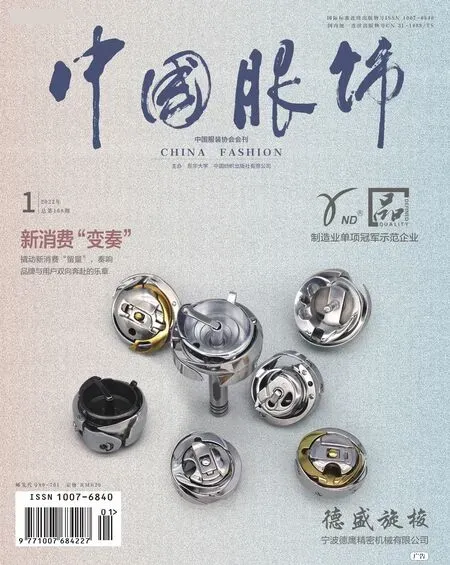“大扣”威風
文 | 邵瑩 邵新艷
粵劇武將戲服“大扣”中的“門道”
“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粵劇舞臺上,沒有塞外的風霜雪雨,沒有冰冷的刀光劍影,卻能讓觀眾身臨其境,感受將帥征戰的氣勢恢宏。
粵劇“大扣”巧妙地融合了古代武將的服飾特征,跳脫于生活中的原始狀態進行夸張、變形、美化,烘托人物氣質的同時極大程度地裝飾了舞臺。
“大扣”藝術特點
粵劇服飾在時代的發展中,既有對外來文化的海納百川、博采眾長,也借助嶺南地區的地理文化優勢進行更多元化的探索。粵劇“大扣”作為武戲中最夸張、最異于常態的戲服,有著與眾不同的藝術特點。
粵劇“大扣”是傳統戲劇中武將將帥的裝束,京劇中稱“大靠”。整體不貼身,圓領、緊袖口,扣身分前后兩片,長至足,主要由扣肩、扣身、扣裙和扣旗四大部分組成。扣肚部位硬闊凸起,夸張的形態搭配精美的刺繡格外突出,嚴陣以待的武將身背扣旗號令四方,盡顯英勇神武。整件“大扣”雖不具備實戰護身的作用,卻便于演員呈現大幅度動作,是戲劇服飾可舞性的體現。
色彩是粵劇“大扣”中極為重要的元素,主體顏色與圖案紋樣顏色常為冷暖相對,使彼此之間相互映襯,整體色彩和諧。每件“大扣”的主色調都是角色個性的象征,傳統衣箱講究“寧可穿破不可穿錯”,是戲劇中程式性、符號性的體現。如綠扣象征忠義勇猛,而白扣、粉扣則象征智勇雙全、年輕英俊。
此外,“大扣”上密布著千變萬化的刺繡紋樣。男扣的主體紋樣以龍紋或虎頭紋樣為主,而女扣則以鳳紋為主。扣地紋主要使用魚鱗紋、人字紋等模擬古代實戰鎧甲組織結構的紋樣,正中還繡有模擬鎧甲護心鏡的圓壽紋樣。“大扣”的四周常飾以雙層二方連續的邊飾紋,外層為大邊,內層為小邊,其種類較為豐富,大多以浪花紋為主,回紋、壽字紋、卷草紋等為輔,女扣中則綜合各種花卉的紋樣,形式多樣,富有裝飾性。線繡和盤金繡相搭配的形式將“大扣”上的圖案表現得活靈活現。
挖掘武將印跡
傳統戲劇服飾的設計離不開程式性、符號性、可舞性以及裝飾性四大特征,注重服務于角色、服務于舞臺。“大扣”的設計不是對現實生活的“照板煮碗”,而是對于典型整合后的進一步升華。
作為傳統戲劇中的武將服飾,“大扣”在由京劇傳入粵劇之前早已經過一番演變,從明朝雜劇中的“曳撒”到傳奇中的“甲”,進而到清朝宮廷大戲中的“靠”,在清朝宮廷戲畫中已呈現出與今極為相似的形制。

>>男扣結構

>>大扣配色
前人對“大扣”的設計來源這一問題的探討答案大致有三種結論:一是“大扣”源于明朝鎧甲,二是源于清朝鎧甲(亦稱清朝棉甲),三則不細說朝代,而是將“大扣”的來源直接歸結為古代軍戎服飾。在筆者看來,“大扣”給人的第一印象與清朝禮儀化后的棉甲的裝飾極為相似,但透過絢麗的裝飾看其結構部件,會發現其在形制結構上與清朝棉甲的結構出入較大,與明朝鎧甲的契合度更高。
通過選取“大扣”中典型的結構部件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大扣”在肩、胸、腹、下裙等多個部位的形制結構上均與明朝鎧甲有較高的相似度,如扣肩、吊魚等結構,甚至可以直接在明朝鎧甲上找到原型。典型部位如硬挺的扣肚,配以虎頭或是龍、鳳的紋樣裝飾,夸張、大氣,而在后身對應位置的長條狀后腰,通過細繩捆綁呈現虛抱人體的狀態。這樣的結構隱約與明朝鎧甲的腹甲及“抱肚”部位相似,并通過藝術化的夸張改造而成。粵劇“大扣”在形制結構設計上一定程度地保留了明朝鎧甲的特點,降低了其結構在實戰防御上的實用性,對經典結構加以設計升華,增強其整體氣勢。
“大扣”設計中所運用的裝飾元素,如虎頭、鎧甲紋樣、星片等,是綜合歷來軍隊戎裝中具有代表性的武將元素,并以更為輕便、精美的形式呈現在戲服上。這些元素不再拘泥于抵御刀槍或驅寒保暖等實戰作用,更多地是取其屬于戰場英武豪邁的氣質,再加以一定程度的藝術性夸張設計,作為“大扣”的裝飾而呈現。從唐朝、宋朝至明朝時期的戎裝,常見在胸腹、肩頭等顯眼的部位飾以饕餮、獅虎等獸首的鎧甲,借助神獸的靈性與神性增強軍士的信念,護身勵志的同時震懾敵軍,“大扣”中扣肚與肩頭上的形似鎧甲上“獸吞”的半立體虎頭紋樣,正是借鑒的典型。
當戲劇中武將處于戰爭狀態時,身背扣旗,演員對扣旗的控制張弛有度,扣旗隨演員的舞動灑脫飛揚,二者相融盡顯武將的威儀。扣旗源于古代的傳令旗,但僅是其在戲劇中極致的藝術夸張設計,并不具有實際的傳令作用。扣旗在武將背部排開,一方面直觀地襯托其威風凜凜的氣勢;另一方面扣旗代表武將手握兵權,由于扣旗是現實中令旗的轉化,一支扣旗代表一支軍隊,身背四支扣旗便代表武將手握四方軍隊,在形象上更顯其驍勇善戰,威風百面。
“大扣”的設計植根于中國古代不斷沉淀積累的鎧甲戎裝,形制結構與裝飾元素的應用相融合,突破了時間、空間的限制,對現實元素進行藝術加工,使屬于武將的元素從現實的實用性向戲劇服飾的特征轉變,是武將服飾在戲劇中綜合性的藝術升華。融入嶺南文化的“大扣”,借助嶺南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嶺南居民海納百川、開拓創新的精神,在呈現方式上更加大膽、活躍,獨具嶺南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