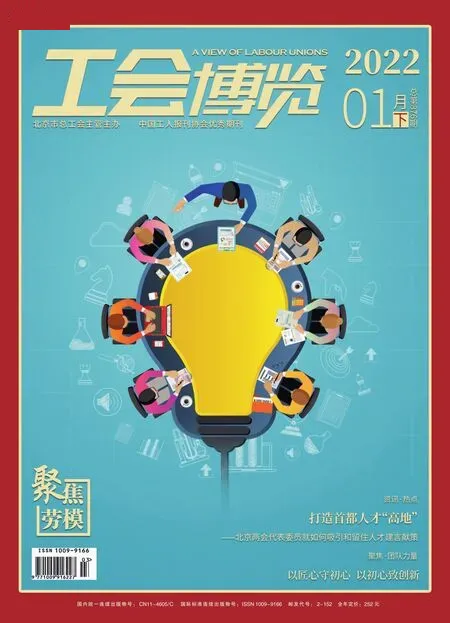幸運的當代青年
——《激蕩十年水大魚大》有感
□李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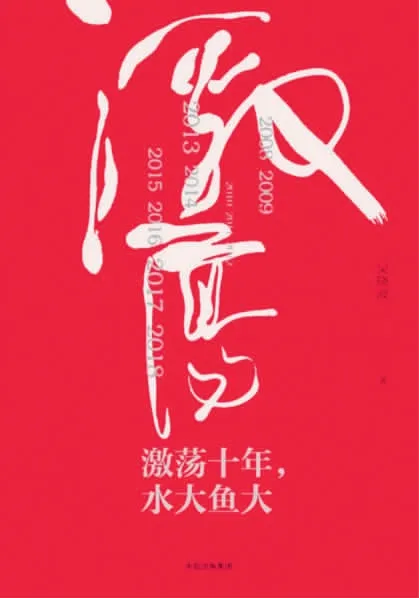
最近公司工會向全體會員推薦了一本書《激蕩十年,水大魚大》。該書深入淺出地通過具體時間以編年體的形式向讀者展現了改革開放40 年的近十年,我國經濟發生的重大變化。
十年前,我在一家人力資源中介機構工作。很長一段時間里,我覺得我在同屆的大學同學里算是工作找得比較理想的,比如在當時看來較為體面的職位,較為穩定的工作環境,而我不知道的是,我僅僅是剛剛踏上了一輪國進民退的洪潮。
改革進入下半場。延續了《激蕩三十年》 一貫的風格,《激蕩十年,水大魚大》 保持了吳曉波力求客觀中立的還原歷史、保持克制理性的思考評論和刻意保持距離的觀察記錄。以每一年度為章節,對2008 年到2018 年的中國企業大事件進行了回顧,每一個年度抽選年度最有代表性的事件或思潮或社會形態自成一個畫龍點睛的主題。
十年,很長,很短。
長到讓人在一個個經濟周期里經歷大起大落,世相悲歡;短到讓人感覺發生迅猛商業迭代就在昨昔。如果換一個角度,從市值來比較的話,則會看見另外一個真相。
在2007 年,全球市值最高的十家公司分別是:艾克森美孚、通用電氣、微軟、中國工商銀行、花旗銀行、AT&T、荷蘭皇家殼牌、美國銀行、中石油和中國移動。
而十年后的2017 年,榜單赫然已面目全非,十家公司分別是:蘋果、谷歌、微軟、臉書、亞馬遜、伯克希爾-哈撒韋、騰訊、美國強生、梅克森美孚、阿里巴巴。
中青年一代已經開始接管世界商業浪潮的主導權,因為他們更懂得這個變得面目全非的新時代。即便在缺乏長期性頂層設計的前提下,仍可見過往十年中國經濟變革的動力來自四個方面:
一是制度創新。中國一直在探索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和作用,兩方利益主體也一直來回博弈,反復,仿徨。但與其他市場經濟國家不同的是,中國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國有資本在國民經濟中的控制力,這也成為制度創新的最大不確定因素。
二是容忍非均衡。中國改革的非均衡特征和“灰色治理”,是打破計劃經濟體制的獨特秘訣。它包括“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東南沿海優先發展、給予外資集團的超國民待遇,甚至還有對環境破壞的長期容忍,對農民工群體的利益剝奪,以及民營企業家對現行法律的突破。因為改革的漸進性,制度邊界的來回摸索,讓一部分人“近水樓臺先得月”,也讓一部分成為改革的犧牲品。這里面很難用對錯來簡單判定。但是隨著一些領域的不均衡已快到臨界點,已不可持續。
三是規模效應。中國已經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2025 年超過美國指日可待。龐大的人口和市場規模為中國的創業者提供了巨大的成長紅利和規模效應,也會各種類型的創造提供巨大的試錯空間,但同時也讓各種野心膨脹者的犯錯成本無限放大。
四是技術破壁。技術的不可逆性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團的準入性壁壘,從而重構產業范式,并倒逼體制內改革。這一特征在改革的前三十年并不突出,然而,隨著互聯網的崛起,很多產業的原有基礎設施遭到毀滅性破壞,帶來了競爭格局的煥然一新。在可以預見的未來,技術的破壁能力將在更多的領域持續發酵,尤其是人工智能、生物基因、新材料、新能源等領域。
未來會如何?作者沒有給出答案。只提到對于這一段尚未結束的當代史,必須擺脫歷史宿命論,承認歷史發展的戲劇性和人的主動性。我們更應該相信科學史家伯納德·科恩的看法是對的,他說:“對那些與事先設計的模式不相吻合的事實,要予以特殊的注意。”創造意味著背叛和分離,也就是說,新的發生總是伴隨著不適感和不確定的可能性。前者說明這是必經的過程,后者則意味著希望。人類的一切創造,都來自于不確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