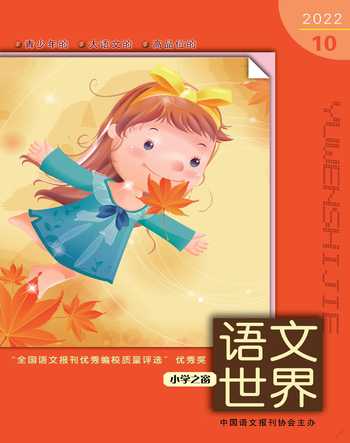淺談“天”字教學策略
宣瑩
“天”字先是出現在《識字1》“天地人”中,接著在《識字2》的“天地照古今”中復現,隨后在漢語拼音教學中以“藍天”的詞語出現,并在《語文園地一》中與“人”字放在一起,讓學生讀一讀,比一比。進入課文學習后,第1課《秋天》出現了“秋天”“天氣”“天空”等帶“天”字的詞語,第4課《四季》出現了寫“天”字的要求。對于這樣的安排,教師該怎樣根據“天”字的特點進行教學呢?
一、“天”字的字理解讀
“天”字是中國人最常見也最常用的漢字之一,與小學生的生活密切相關。一年級的學生,他們每天抬頭低頭之間都能看到“天”,而且在他們的口頭語言中,也常常有“今天”或“明天”之類的說法。可是,這兩個意義上的“天”字,都不是“天”的本義。
我們可以聯系甲骨文來理解“天”的本義。甲骨文的“天”,下面都是正面的人形,不同的是上面表示人頭的符號,有的像不規則的“口”,有的寫成兩橫指事符號;整體形象是一個正面站立的人,長著大大的腦袋。它的本義正是與那個大腦袋緊密關聯,表示頭頂。《說文解字》里有這樣的注釋:“天,顛也。至高無上。”即:天到頂了,到了無法再上加的部位。“天”的這個本義是怎樣引申出其他意義的呢?對人而言,最高的地方無疑是頭頂,對于大地上的萬物而言,最高的地方自然是頭頂上的天空,“天”字由此引申出天空的意思。在日常生活中,日出東方,月落西方,白天和黑夜交替,這樣一個周期的變化被稱之為一天。與之相連的,一年之中出現四時變換,出現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天”字由此引申出時間、季節的意思。還有氣候的不斷變化,產生各種氣象如雨、雪等,相關的晴天、雨天中的“天”字就有氣候、天氣的意思。在梭羅的《瓦爾登湖》里,有這樣一則資料:“在印度的普里人看來,表示昨天、今天和明天可以用一個字,而在表示不同意義時,他們一邊說這個字,一邊做手勢,手指后面的算昨天,手指前面的算明天,手指頭頂的算今天。”這與我們上面分析的“天”有著某些巧合和神似。其實,“天”在甲骨文中就是一個常用字,用法比較靈活,因此,它的引申用法很多也就不足為奇了。
二、“天”字的教學策略
筆者認為,對于剛入學的一年級學生來說,最重要的是培養他們的識字興趣,最好的方法是讓他們簡單、便捷地學習生活中早已熟悉讀音卻不認識字形的字。編者把“天”字排在學生識字任務的第一關,正是這個道理。如果采用字理識字教學法,教師先要引導學生學習“頭頂”,無形之中就設置了一道學習屏障,與學生很熟悉的“天”就隔了一層。這對于以感性為主的一年級學生來說就會直接失去學習的興趣。如果采用聯系生活識字的方法,教師不需要過多講解,學生就能主動地把“天”與天空聯系起來理解,形和義的理解一步到位。
統編教材還提倡在語境中識字。教材第1課《秋天》中出現了“秋天”“天氣”“天空”三個帶“天”字的詞語,而且意義不同,從語境上說非常適宜安排進一步學習“天”字,但教材卻安排在第4課《四季》中來學習“天”字的寫法。在《四季》中,雖然有“春天”“夏天”“秋天”“冬天”這些詞語,但是它們在課文的語境中表示的都是相同的意思。這就產生了一個問題:教材對“天”字的編排真的合適嗎?筆者在仔細研讀教材后發現,在第1課的寫字學習中,已經安排了“了”“子”和“人”“大”四個字,可能編者考慮學生的學習負擔等因素,只安排學生學習4個字,且“了”和“子”“人”和“大”成對出現,形成對比,體現了由簡單到復雜的書寫順序。但是,如果我們換個角度來看,“天”字與“人”“大”兩個字更是屬于一個系列的,將它們安排在一起學習,一方面可以練習“人”在不同字中的基本寫法,另一方面滿足了學生學習“天”字的語境要求。此外,編者把“天”字放到第1課后面進行進一步學習,不需要對其他課文內容進行變動,只要把“了”與“天”互換一下,就可以達成這樣的學習目標。
總之,教師采用什么方法來教學“天”字,安排學生在什么樣的語言環境中學習“天”字,都需要深思。如果教師只是以簡單的方法來教學“天”字,對一年級的小學生而言,將難以收到應有的學習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