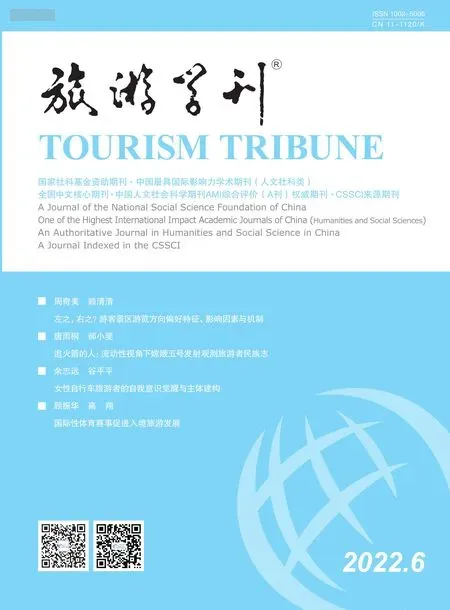追火箭的人:流動性視角下嫦娥五號發射觀測旅游者民族志
唐雨桐,郝小斐




[摘? ? 要]新流動性范式的提出使流動性研究更加注重流動背后所建構的社會意義。文章以嫦娥五號發射事件作為研究切入點,通過對奔赴海南文昌觀看火箭發射游客的民族志研究探討基于實地觀看火箭發射的流動特征。研究發現,“追火箭”旅游的流動性體驗超脫于火箭發射的具體時空場域,從出發前開始,延伸至回程后仍不斷持續,且基于“追火箭”的旅游流動過程強化了旅游者的國家認同、喚起了旅游者的自我認同。此外,研究對象呈現出循環新部落的特征,虛擬流動與現實移動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一方面,虛擬流動通過出行前的信息流動與社交互動為現實流動奠定了社會關系基礎,另一方面,現實流動深化了虛擬流動建立的社會關系層次,并為流動回虛擬世界后的情感聯結持續加強夯實了根基。研究認為,“追火箭”旅游通過火箭升空、探索宇宙這一具有人類浪漫主義傾向的目標,引領旅游者的“精神流動”,體現出在對“天”的構建和探尋中人類精神的歷史性和延續性。
[關鍵詞]流動性;“追火箭”旅游;國家認同;嫦娥五號;民族志
[中圖分類號]F5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5006(2022)06-0079-15
Doi: 10.19765/j.cnki.1002-5006.2022.06.011
引言
自新流動性范式[1]提出后,地理學對流動性的研究不再僅聚焦于簡單的物理空間移動表象,而是更注重流動過程中的意義生產,探索其背后引申出的社會建構意涵[2-3]。基于對新流動性范式理論的進一步探索,Cresswell將流動性劃分為以下3個層面:第一,從一處至另一處的物理移動;第二,物理移動建構的共享意義的表征;第三,物理移動產生的具身實踐與體驗[4],這為流動研究轉向聚焦流動的社會意義夯實了根基[5]。作為以流動為基本特征的行為方式,旅游中的流動性研究在學界愈來愈受到重視[6-7],其不僅僅是物理空間的位移,旅途的行為實踐也不斷提升著旅游者的社會互動能力與自我價值[8],進而增進人類幸福感[9]。而信息技術的發展使得旅行時間的有效利用率攀升[10]、旅行成本降低[[11]]以及基于信息的虛擬流動帶來的旅行視野開拓,更使得物理流動增加[10,12],也為旅游中虛擬流動性的研究拓展了空間。
Urry將旅行過程中基于交通方式的身體移動、基于商品流通的物品移動、基于信息建構的旅游者幻想中的旅行以及基于技術的虛擬旅行體驗歸納為旅游流動性的4個方面,書寫了流動性的空間與社會實踐[13]。隨著通訊技術的發展,Urry又將基于通訊媒介與網絡媒體的信息的虛擬流動納入了流動性的框架[14],成為第五大核心流動性。雖虛擬與現實流動的關系已有探討[15-16],但大多從宏觀層面分析其相互的影響[17],缺乏基于個體層面的微觀分析[18],更疏于揭示虛擬流動性與現實流動性交織下的旅游情境背后的社會意義建構,因而,對于將虛擬與現實流動置于一個框架中來分析日常旅行行為的呼吁也愈發強烈[17-18]。
在后現代主義所解構的社會中,流動隨著社會進程的高速運轉而不斷增強,人們逐漸習慣依托于時空壓縮的介質進行社會互動,基于傳播媒介的信息交流建構了流動中新的社會含義[19]。在這種情境下,傳統的旅游時空格局被打破,信息技術、社交媒體的浸入擴展了旅游者的旅游時空范疇,使得在家與離家的體驗不再涇渭分明[20-22]。孫九霞等將旅游流動性的時空意義進行延展,闡明旅游體驗并不是抵達目的地的時刻才開始產生,而是在出發前便已通過報紙、網絡、電視和書籍等各種形式勾勒了它的輪廓,離家之前,旅游體驗便已經開始建構[2]。同時,旅游體驗也并不是隨著回到出發地便結束,基于網絡的虛擬信息流動與社會交互使得旅游體驗在日常生活中仍能得以持續[23]。因此,Cutler等提出的去程(travel to site)、在場(on site activities)返程(return travel)的三維框架[24]在當今新流動性范式下的適用性值得商榷。此外,日常生活中的科技應用與媒體社交逐漸涉入旅游者的旅游過程[25],旅途中通過社會化媒體與原初社會關系網絡的持續聯絡,使得虛擬空間與實體空間能夠在同一時間共存,推動了旅游者的身份建構[26-27]。虛擬與現實不再是二元對立的關系,而是相互交融、互相滲透的存在[28],因此,在虛擬流動與現實流動交互相融的當下,對旅游流動過程的研究有必要拓展到離家前以及回程后的網絡信息流動和社會交互對旅游體驗的建構中來,從而進一步延伸流動性的時空框架,如探討虛擬信息流動與現實空間流動之間的交互關系[29],挖掘其背后更深層次的意義生產與社會建構的意涵。
人類自古以來就是觀星者,凝望宇宙是人類亙古不變的寄托,探索頭頂的浩瀚寰宇是人類前仆后繼、矢志不渝的追求。自遙遠的古希臘,人們便著手研究星象,從星空銀河中發現其獨特的規律和奧秘以揭示人類的命運[30]。近現代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火箭的發明為人類探索宇宙提供了可能。隨著2016年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的竣工,人們不再只能從電視中瞻仰火箭飛向宇宙的壯麗景象,而是可以奔赴現場去追逐火箭的發射。2016年6月25日,長征七號火箭在海南文昌實現首飛,發射當天文昌共接待游客15萬人次;同年11月,長征五號的發射是中國航天里程碑式的一次跨越,標志著中國航天邁入了新的征途,此次發射迎來了12萬人次現場觀測[31]。兩次發射觀測人次共計27萬人次,彰顯了我國航天旅游市場的龐大潛力。然而,國內外關于航天旅游的研究卻鮮少有之。國外關于航天旅游的定義更多集中于“space tourism”(太空旅游),意指駛向太空的旅程,其探討的多是以國際空間站為目的地的旅行以及對人類未來探索太空的展望[32-33];而國內對航天旅游的研究也是鳳毛麟角,且側重于火箭發射基地對目的地的旅游經濟帶動作用以及目的地的旅游發展戰略[31,34],對于火箭發射觀測群體的旅游相關研究極為稀缺。
本研究基于2020年11月24日凌晨在文昌進行的嫦娥五號發射事件展開。2020年12月17日,習近平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祝賀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的賀電中指出,“嫦娥五號任務作為我國復雜度最高、技術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統工程,首次實現了我國地外天體采樣返回。這是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攻堅克難取得的又一重大成就,標志著中國航天向前邁出的一大步,將為深化人類對月球成因和太陽系演化歷史的科學認知作出貢獻。”1一方面,嫦娥五號發射成功標志著我國探月工程“繞、落、回”三步走的收篇,實現了我國航天史上的“五個首次”,其中,最重要的是首次從月面鉆取最年輕的月壤樣本返回2。另一方面,嫦娥五號圓滿完成任務既是終章也是序章,標志著我國未來將踏入載人登月返回的新的航天征程3。因此,嫦娥五號的發射,不論是對于中國航天科研還是人類探索宇宙都是具有歷史性意義的邁進,其重要性空前,因此吸引了來自五湖四海的游客前往觀看。此外,央視新聞于2020年11月22日18:00在文昌發射塔進行“陪你追嫦娥”微博直播,共收獲了850萬線上觀看量。因此,由追逐觀看火箭發射引起的流動性,不僅包含著現實物理空間的流動性,還包括虛擬空間流動性,并潛藏著宏大的敘事框架。由此引出了本研究關注的問題:(1)從萌生動機到奔赴目的地展開實地觀測的流動行為、到回程后旅游體驗的持續,虛擬與現實如何建構的“追火箭”旅游流動全過程?(2)“追火箭”對于旅游者來說具有什么樣的社會意義?(3)傳統流動性框架何以通過“追火箭”這一特殊的旅游方式得以延伸?基于此,本文以流動性為理論框架,將其延展至虛擬移動性與現實流動性的范疇來界定流動的全過程,主要采用流動民族志的方法,通過對2020年11月海南文昌“嫦娥五號”發射事件的參與式觀察以及對火箭發射觀測者的深度訪談,就上述問題進行了解釋。
“嫦娥五號”為我國建設航天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再立新功,是人類和平利用太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的開拓性貢獻1,對這一重大歷史事件所引發的旅游流動性問題的探索,不僅契合新流動性理論研究的需求,還對火箭發射地空間發展與航天旅游的探索具有極強的現實意義。
1 研究案例地
文昌位于海南島東北部,毗鄰海口,是我國繼西昌、酒泉、太原后第4個航天發射基地。2007年9月,文昌航天發射場項目正式被批準立項,拉開了文昌航天旅游的序章[31]。文昌被公認是世界上第二佳位置的發射場地,僅次于南美洲圭亞那庫魯發射場2。對比過去中國最重要的航天發射場西昌基地,文昌的近海地理優勢可使火箭發射殘骸墜入海里而不是掉落地面,不至于對人類造成危險,從而具有可接近性和可參觀性[35],為渴望親眼觀看火箭發射的人群提供了良好的契機。依據國家政策的導向,文昌發射場的發展要朝著商業發射場的目標前進[36],文昌以其發射地理位置的理想性,有志于在未來成為有世界影響力的航天旅游城市。
文昌希爾頓海灘位于文昌市龍樓鎮銅鼓嶺國際生態旅游區淇水灣畔的魯能希爾頓酒店附近,可同時容納約4000人觀看火箭發射3,是觀測位置最佳的海灘。海灘無需門票,不設圍欄,但設有旅游指示標識,并于火箭發射時期設有火箭觀測主題廣告標牌,旅游者自發聚集于此,因其優越的地理位置和廣泛聚集的人流,研究者將其選作參與式觀察的主要案例地。
此外,本研究案例的場域還包括基于微博、bilibili平臺、微信群、微信朋友圈的線上空間,這些線上空間的研究內容都緊密圍繞2020年11月的海南文昌嫦娥五號發射事件與關鍵人物展開,與現實案例地共同構成了本研究聚焦的流動性時空架構。
2? 研究方法與數據收集
Urry等歸納并提出的新流動性范式下研究方法的四大要點:觀察、同行、問卷調查和文本分析[3,37],要求研究者深入目的地觀察以及深度參與到目標群體的文化活動中,因此本研究采取流動民族志方法,研究者與研究對象一起參與、體驗并記錄這一流動全過程[38],試圖深度挖掘“追火箭”旅游的流動特征及其內在意義建構。本研究基于流動民族志的研究設計,結合實地參與式觀察、網絡觀察(虛擬民族志)、深度訪談和文本分析的質性研究方法。(1)流動民族志。研究者于2020年11月18日晚通過微博聯系到視頻博主K,其作為短視頻自媒體的一條火箭文昌發射實地參觀記錄視頻在bilibili平臺收獲了57.9萬的播放量,系火箭發射系列視頻影響力最高的自媒體;獲得其聯系方式及訪談的初步同意,并于2020年11月21日晚進入了其組織的結伴去參觀火箭發射的微信群。研究者通過與微信群群友積極互動,先后添加20名互動較積極群友,將其作為潛在訪談對象。2020年11月23日晚,研究者按照約定時間抵達文昌市龍樓鎮希爾頓海灘(火箭發射主要觀測地之一),與“追火箭”群友進行了線下的會晤,自2020年11月23日晚上11點到24日凌晨4點半火箭發射,研究者全程位于研究現場,與現場等待見證火箭發射的游客處于同一場域;其間通過一系列互動與“追火箭”群友建立良好的社交聯系。(2)深度訪談。為了使樣本足夠豐富,返程后,研究者在實地接觸的群友中通過目的性抽樣選取了具有差異性的11位作為訪談對象進行了線上微信電話訪談。受訪者的性別分布為男性9人,女性2人,基于航天愛好者男性居多以及結伴微信群的男女比例為57:10,選取該比例的受訪者較為合適。受訪者年齡分布從21歲到33歲,所在行業與人生歷程大有不同。研究者于11月27日至12月21日期間對受訪者分別進行了25分鐘到45分鐘不等的深度訪談,在征得受訪者同意的前提下進行了錄音,共產生了381分鐘的錄音資料,后續整理成共計84 275字的轉錄文檔,用最后兩位受訪者的文本檢驗樣本飽和度,得到基本飽和的結果,即終止訪談,訪談者基本信息數據詳見表1。此外,本研究于2021年7月7—26日間對部分受訪者進行了回訪。7月7日,研究者奔赴杭州,邀請R11博主K進行面訪,訪談時長108分鐘,并將訪談記錄返回受訪者進行了核實;7月12—13日,研究者赴淄博對擁有5次追火箭經歷的受訪者R06進行了當面回訪,共收錄28分鐘的錄音資料并轉錄了共計6605字的訪談材料;7月26日,對SpaceLens1的創始人之一、受訪者R07進行了線上回訪,二次訪談數據詳見表2。(3)文本分析。分析采用歸納法,借鑒流動性理論框架,對訪談文本進行時空順序歸類以及話語內涵歸類,得出本研究實證的四大主題。本研究還采用了虛擬民族志的方法進行了網絡觀察,觀察對象包括視頻博主K兩條火箭發射視頻的彈幕及視頻自述話語、本研究受訪者產出的關于此次旅程的視頻、朋友圈日志、微信群內互動發言等。在日常生活越趨媒介化的當下,虛擬民族志被視為體現研究對象深度內心感悟與真實生活軌跡的材料,被廣泛地運用于虛擬與現實相結合的現象的研究中[39],而本研究具有線上、線下的雙重流動性,適用于虛擬民族志的分析。為了驗證分析結果的效度,研究者將流動民族志觀察數據、訪談文本和虛擬民族志文本進行了三角驗證。
3 研究發現
3.1 流動的序曲:線上集聚,一起送“嫦娥去月亮”
3.1.1? ? 視頻喚起的追火箭動機
本研究的受訪者大部分都是被視頻博主K 2020年5月14日在bilibili平臺發布的在文昌“追火箭”視頻吸引,從而萌生了親自去“追火箭”的動機,通過聯系博主K進入微信群,并于11月23日左右奔赴文昌實地進行觀看火箭發射,其行為本質上屬于影視旅游的范疇。影視旅游是通過影視作品對旅游者刺激、吸引從而激發其旅游需求,并促成旅游者前往影視場景拍攝地的旅游行為的過程[39]。影視作品擅長通過情緒渲染來調動觀眾的情感體驗,如懷舊影視可以喚起人們的感性情感、身臨其境的體驗和情感聯系[40-42],但對影視旅游的探討亟須在旅游者出游行為背后的情感支撐和社會意義層面上進行理論和案例拓展[43-44]。近年來,隨著影視旅游者群體的細分趨勢愈加明顯,影視旅游也逐漸與聲望、自我認同和國家認同聯系起來[45],但相關討論和案例尚處于萌芽狀態。在視頻博主K火箭視頻的彈幕中,“將來一定要去”“我也想親眼看火箭發射”等字眼頻頻出現,可見該視頻對旅游動機的激發作用。視頻博主K的視頻對旅游動機的喚起基于以下兩個方面:第一,視頻通過為旅游者提供信息增強其感知可進入性,不少受訪者表示,在看了視頻博主K的視頻之后,才獲悉火箭發射可以實地觀看,“我以前一直以為這個地方肯定是一些軍事禁區什么的,然后一般人是進不去的,沒有想到原來這么近就可以看得到。”(R03,視頻博主)第二,視頻通過文案、剪輯、彈幕講述了一個動人的故事,從感性層面喚起旅游者強烈的情感共鳴,從而激發了旅游動機,“(看完視頻)覺得很牛很震撼。很感動,還哭了呢。”(R09,運營推廣)在視頻里火箭發射的時刻,彈幕頻頻出現“淚目”“感動”等詞匯,情緒的渲染喚起了旅游者實地體驗的欲望(圖1)。不容忽略的是,彈幕作為影視作品中的用戶生成內容(user-generation contents,UGC)文本,被認為具有互動參與和情感表達的功能[46-47],在影視旅游領域的相關研究中,彈幕也被認為具有強化對目的地積極形象感知的作用,觀眾對出游的渴望也體現著情感的共鳴[48]。在視頻博主K火箭視頻的彈幕中,“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愿祖國繁榮昌盛”等內容凸顯了觀眾對國家認同的共情,而“將來一定要去”“我也想親眼看火箭發射”等字眼也頻頻出現,渴望情緒在互動參與中擴散,驗證了視頻內容和彈幕文本共同影響旅游動機[48]。
然而,有研究表明,影視作品只是激勵出游的部分因素[[49]],本研究也印證了這一觀點:“追火箭”旅游者本身具有潛在動機,視頻博主K的視頻只是起刺激與催化作用。“這種事情(火箭發射)是那種很神圣的”(R06,大學生),“對這種東西(宇宙)覺得很浪漫、很喜歡”(R09,運營推廣),“感覺是見證了國家的(進步)”(R10,視頻博主),“想出去放松一下”(R08,民航飛行員)等,這些因素都成了航天旅游的動機。可見,火箭不僅象征著探索太空的機器,還擁有國家富強的見證、宇宙的浩瀚等一系列符號表征。
3.1.2? ? 通過意見領袖流動進入網絡部落
新部落(neo-tribe)理論由法國社會學家Maffesoli率先提出,指后現代社會下人們由共同情感、愛好自發聚集而成的群體[50]。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網絡新部落的概念逐漸形成,意為以共同價值觀、興趣偏好聚集而成的基于網絡的社群組織[51]。視頻博主K于2020年11月21日建立“追火箭”約伴微信群,并在微博號召此次去文昌“追火箭”的粉絲入群,網絡部落就此建立。“我就想干脆直接把大家都召集在一起,大家一起看好了,那樣也更有氛圍會更有意思。”(R11,視頻博主K)提及建群的初衷,視頻博主K坦言是希望通過建群將愛好者聚集到一起,共享一段旅途。進群的粉絲也都是基于對航天的熱愛、對火箭發射的向往以及對視頻博主K的仰慕而聚集,其興趣愛好、價值觀念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線上社交進行得非常順利,“大家的目標就非常一致,所以交流起來就很融洽很和諧。”(R02,企業管理),且在互動中,“又系你”“康喲喂百大”等視頻博主K視頻里的標志性話語的頻繁出現象征著粉絲們同源情感的聯結[44],進一步了活躍了社交的氛圍。而在網絡部落形成初期,因群內粉絲之前并沒有建立情感關系基礎,其尋求結伴的行為多是帶著功能需求動機[52],“而且像自己拍不到的一些東西,可以通過他們的鏡頭,他們的視角(來看到)”(R06,大學生),“可以認識到更多的大佬”(R07,《視覺中國》簽約攝影師),“我剛開始應該是因為我第一次去看火箭,肯定希望有熟悉的人可以帶我”(R03,視頻博主),其需求多是以尋求領路人、結識牛人、消除孤單情緒等自身利益為出發點。而來自五湖四海的旅游者通過互聯網匯聚,結成一個擁有共同目標的組織,其實質上屬于信息的潛在流動,這種以非物質形式呈現的流動也一定程度上建構著社會意義,影響著旅游者對目的地的感知和旅程的期許,因此可將其視為流動性的一環。
3.2 流動的前夕:從虛擬到現實的流動
3.2.1? ? 旅途流動中的際遇
進入火箭發射的現實場域——文昌時,旅途的際遇開始建構旅游者的感知。“單純從文昌地方來說,風景很好,然后基礎建設也很好,然后到處都會覺得很淳樸、很質樸,也不算很發達的地方,有時候又覺得很神秘兮兮的。農耕和科技交錯在一起的一個比較特別的地方,挺矛盾的一個地方,但是又感覺沒有什么違和的,很和諧。”(R11,視頻博主K)在對主體目標——“追火箭”強烈的渴望和期待下,旅游者將在途中經歷的事物通過聯想與火箭形成關聯,比如,受訪者R07將他在旅途中邂逅的彩虹視為預示火箭發射成功的吉兆,而受訪者R04又為旅程中經歷飄雨而對火箭發射產生擔憂。同時,在旅途中,旅游者的物理空間在向火箭發射的主體場域靠近,內心也逐漸進入對火箭等待的應激狀態,緊張情緒下,發生的任何事都會被放大,從而影響等待火箭的心情。“在公交車上就是大家雖然素不相識,但是還有小姐姐跟沒有訂到旅店的人說,我知道在網上訂不到的旅店,可以帶你去。然后還有阿姨熱情地問大家一起去做客嗎,我覺得很暖。”(R08,民航飛行員)受訪者R08因公交車上陌生人溫暖的舉動而消解了長期以來壓抑的情緒,從而對火箭發射的等待報以更平靜的態度。“對,所以最后我跟小伙伴在我們快將近絕望的時候,我們遇到的一些希望,而且希望幫我們圓了夢。”(R02,企業管理)受訪者R02為了近距離拍攝長征五號而與警察發生一場“逾矩”,這趟經歷反而成為他整趟旅行中最難忘的體驗。值得一提的是,與其他旅游形式不同,基于火箭發射參觀的旅游者在出發之前就擁有高昂的情緒,并在流動的過程中也伴隨著緊張和持續激動的狀態,且一直延續到旅程結束。
3.2.2? ? 線上流動到線下的節點
線上虛擬社交到線下相聚的節點,是視頻博主K組織在飯店的一次聚餐。“因為剛加群大家都不熟悉的時候,你就只能通過他們說話的方式,還有(通過)他們的昵稱頭像來對他們說話的每一個人來建立第一印象。”(R06,大學生)見面之前,旅伴在他們印象里是扁平的、陌生的頭像以及能稍微凸顯其社交性格的聊天文字,而見面之后,對旅伴的形象感知變成了生動的面孔和神態,整體的感染力提升使得社交情誼的聯系逐漸深化。“如果有一次線下的見面以后,知道了每一個人,然后切實地看過樣子、聽過所有的聲音,就感覺這個人比較親近了。”(R06,大學生)基于共同愛好的新部落群體特征也使旅游者在線下的相處很融洽,因此,社群在基于線上社交的功能性需求逐漸弱化,基于線下交往的群體歸屬感增強,“我感覺就是大家一起線下見面后,感覺大家是一個團體,相當于就是所有人都相互認識到,相互開心,這樣子,然后一起看火箭可能挺爽的、挺浪漫的。”(R01,視頻自媒體)通過線上社交的建構,旅游者內心形成了對旅伴的潛在形象刻畫,而線下的流動節點又通過深化旅游者的情感聯結,實現了伙伴形象的再建構,從線上虛擬流動到線下實際流動的轉換過程中,通過共同目標和同源情感的聯結,社群對于他們的意義也實現了從功能性需求到情感需要的轉化。
3.3 流動的高潮:體驗閾限下的共鳴和感動
3.3.1? ? 沙灘流動場域的氛圍營造
進入參觀火箭發射的主要場域——希爾頓海灘后,旅游者的情緒進一步被感染。空間的演進使得周圍的事物經過一步步的篩選,最后鎖定至一個穩定統一的范圍,在這個范圍內,聚集了為同一個目標——火箭發射而等待的人,空間里的任何事物也與火箭發射息息相關。深夜11點的希爾頓海灘人群熙攘,“我有看到很多很多類型的(人),有比如說度假,然后順道來看的,然后有航天科研的工作人員就是在海灘邊守候的,還有一些一家老小就帶著專門過來玩,像我一樣專門過來都有。但還是比如說家長帶孩子來的可能會相對多一些。我覺得這是一種愛國教育的一種體現。”(R06,大學生)非同尋常的是,熬夜觀測火箭發射的群體并不僅僅是航天愛好者,沙灘場域內,有抱著孩子坐在駐扎帳篷里等待的親子群體、有圍坐在一起唱黨歌的夕陽紅旅游團、有因學校組織而列隊聚集的大學生群體、有特地前來的航天工作人員。場域的同一性烘托著濃烈的氛圍,旅游者在場域中流動,難免因所見所聞產生強烈的情感共鳴。面對五湖四海趕來海灘等待火箭發射的游客,受訪者們紛紛發出了深刻的感慨,甚至將自己與他人看作一個共同體,因共同的目標而等待渲染著他們的感性情緒,引發他們對家國、對信仰的無限遐想,“年輕人來我覺得還是挺好的,因為我覺得中國的東西是很需要推廣的東西,年輕人相信祖國,祖國才有未來。”(R03,視頻博主)
流動場域持續縮小并固定在沙灘上的一塊礁石附近,線下相聚的群友在這里再次重聚,一起等待最重要的時刻來臨。沙灘雖是開放的空間,但群友們因社群歸屬感而自動終止了流動,使礁石空間的性質變為一個相對密閉的無形空間,這一空間也是他們主要的社交場域。“坐在礁石上,一開始是聽他們聊天,然后看他們倆表演,然后后來是因為你開始拿出你的琴(‘你’指研究者1),然后開始彈琴玩,然后我就覺得好浪漫,還會有人在沙灘還彈尤克里里。”(R06,大學生)在這一場域內,通過社交,旅游者的疲憊被遣散、緊張得到緩解,甚至開始享受共處帶來的非慣常的情感體驗。
“凌晨兩點,四下寂寥,海灘上散布著零零星星少許人,大部分疲倦的游客已紛紛進入休息狀態來養精蓄銳,只有攝影師們堅守在礁石上,守護著拍攝機位,遠方的發射塔在沙灘視角下只是一顆白色的光點,火箭的形態依稀可見。凌晨3點半,沙灘開始人頭攢動,游人紛紛從帳篷里出來,尋找觀測點,氛圍漸趨熱鬧。凌晨4點,沙灘上的人群已經摩肩接踵,四周沸沸揚揚,人們紛紛舉起手機等待著,目光聚焦在遠方的發射塔上。”(研究者1的民族志筆記)“我記得很早4點,它定了在12秒開始點火,然后旁邊基本都幾百人,每個人都特別期待,在那個時候心情就開始激動起來了,就開始緊張起來了。”(R03,視頻博主)隨著時間的流逝,火箭發射越來越臨近,人流不斷涌上沙灘等待,私密的社交場域逐漸被打破,受訪者們逐漸從社交中放松的狀態重新回到對火箭等待的狀態,緊張情緒重新被喚醒。
3.3.2? ? 發射:集體歡騰下的旅游體驗共睦態
“‘8!7!6!5!4!3!2!1!發射!’ 12月24日凌晨4時20分12秒,在沙灘群眾集體的倒數聲中,火箭發射升空。遠方的發射塔炸開一團火紅的云煙,一只火球沖了出來,帶著燕尾般的尾焰劃破夜空,似一顆太陽般冉冉升起,發出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沙灘的群眾開始沸騰,所有人尖叫著、驚呼著、歡呼著鼓掌,情緒高漲的呼聲里夾雜著一句齊聲吶喊:‘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火箭躍進云層,在云翳的縫隙下若隱若現地穿行,尾焰映紅了整個天際。”(研究者1的民族志筆記)“宛若盤古開天辟地。”(R02,企業管理)當火箭徹底消失于人們的視線的那一刻,人群中迸發出了響徹云霄的掌聲,幾乎所有的受訪者在描述火箭發射的感受時用了“震撼”“激動”“感動”的字眼。“震撼啊,就覺得很牛很厲害,然后特別是穿過云層,被云層吸走之后,其實我們耳朵里面還能聽到就會耳鳴,看聲浪還挺震撼的。”(R09,運營推廣)火箭的升空超越了他們日常生活的一切見聞,是一種超然現象,人類對自身難以企及的超然現象充滿著敬畏與獵奇,因此感受到強烈的震撼。“很激動,當然很激動,對吧?我相信大家都是一樣的,一定是很激動。你想想一兩代航天人的努力,然后成為這么一個龐然大物,然后載著全國人的希望,對吧?往36 000多千米的星球外奔去,這個還是非常了不起的。”(R02,企業管理)火箭發射使受訪者聯想到祖國的航天事業極其艱辛的發展歷程,作為中國人,愛國情懷使受訪者與場域下的集體情緒高漲,激動不已。“然后還有大家一起在大喊,然后經過會特別感動。”(R06,大學生)火箭發射瞬間,場域內所有人達到旅游體驗共睦態[53],人們向著火箭集體吶喊,集體歡騰氛圍的渲染使每個人的情緒與身邊的人互相感染,人們為人類共同的熱愛、為中國人共同的希冀所感動。
3.4 流動的余音:集體記憶下的社會關系再建構
3.4.1? ? 旅游流動體驗的持續性
有學者指出,流動性并不只包含物理空間內的流動這一層意涵,其更重要的是背后折射的社交網絡和身份建構[3],而旅游體驗也不僅僅是旅游場景與時序下的體驗,更是一種生命體驗,與生命的歷程具有共在性[54]。嫦娥五號發射結束后,旅游者們離開文昌,回歸自己的日常生活中,但流動與旅游體驗并沒有停止,網絡的虛擬空間延續了物理空間的流動性,虛擬社區的互動使人們不斷建構著旅游的感悟,因此旅游體驗仍在持續[55]。回程后,受訪者們不斷在群里進行火箭話題的互動討論,并在朋友圈抒發自己的感觸,經研究者觀察,其感悟一直延續到2020年12月17日火箭返回艙的降落,仍余音繞梁、意猶未盡。因此,再次回味火箭發射的場景,受訪者仍難以掩抑激動的情緒,“我現在每次說起(追火箭)我的心情還是蠻激動的,蠻厲害的,說實話對不對?對,太難忘了,尤其是火箭進入云層以后,你還記得嗎?太震撼了。”(R02,企業管理)此外,旅游體驗的持續性與嫦娥五號的旅程也息息相關。有受訪者提及:“因為其實對于我們來說,它上升的那一刻都結束了,大家都走了,其實這也是它的旅程剛剛才開始。”(R10,視頻博主)嫦娥五號在太空的行程受到了廣泛關注,尤其是參與見證火箭飛向宇宙的旅游者對嫦娥五號的回歸更是滿懷著期待,通過不斷跟進新聞來追蹤嫦娥五號的太空旅程。這實質上是嫦娥五號在宇宙空間的流動,在網絡媒介通過信息與圖像的虛擬移動的形式,建構了旅游者持續的旅游體驗感知。更深遠的是,這一“追火箭”旅游的案例揭示了旅游流動從傳統的時空流動、虛擬到現實之間的流動延展到基于想象的精神流動的維度,人類亙古以來對宇宙的遐想與仰望在如今寄托于火箭,流動到人們身體難以企及的太空中。這也進一步證實,基于火箭觀測的航天旅游的獨特魅力在于其高強度的情感氛圍以及持續性的旅游體驗。
3.4.2? ? 循環新部落:線下流動到線上后的社交關系
從實地社交回歸虛擬社群后,流動再一次經歷從線下到線上的轉換,社群內旅游者的情感交互得到進一步的強化和持續。群友在返回之后紛紛發出自己制作的旅行記錄短視頻,視頻里一般包含火箭發射當晚社群內好友在一起娛樂的場景,該場景使社群伙伴感受到自己的參與感,從而產生積極反饋,在交互中進一步促進了友誼的升溫。“在發射之前可能就是說大家給我的感覺好像大家都是為了一個目的聚在一起的網友,對大家其實沒有一個比較立體的認識,但是當在追火箭的過程中,然后發現大家其實都還蠻好玩的。對大家的立體刻畫就更細致了一些,然后等到發射結束之后,看他們發的照片視頻,又感覺他們好像又不一樣了,反正每個層次都更深入一些。”(R04,英語專業大學生)社群內的互動交往形式演變成了一種循環新部落[56],經歷從線上交互到線下的流動再回歸線上的持續建構,這個過程中,集體記憶的共享使群友的情感聯結不斷強化、對火箭動態的持續關注又使情感的歷程在時間上得以延續。隨著嫦娥五號返回艙成功降落地球,微信群里又迎來一場新的集體歡騰。即使嫦娥五號的旅程結束了,受訪者之間的社交聯結卻仍未停止,因其心中強烈的重游意愿,未來的火箭發射,一群伙伴仍有機會再次集結,上演循環新部落的重復相聚。
3.5 基于“追火箭”時空流動的意義
3.5.1? ? “追火箭”的特殊意義
雖然當下信息技術發達,在各媒介平臺觀看火箭發射直播也能為人帶來情緒上的震蕩,但實地觀看火箭發射仍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意義。首先,火箭發射本身的諸多因素為其賦予了神秘的內涵,發射事件的稀有性、受天氣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的發射時間不確定性、發射場面的視覺震撼性、火箭太空征程的未知性都在堆疊著親身實地觀看火箭發射的特殊意義。“印象里火箭可能我們都(線上)看過,但是很少聽到它發射的聲音。我印象里就是‘轟’,但是實際上,你也聽到它的聲音‘咚咚咚咚咚咚’……跟拖拉機一樣,更驚訝的就是你看見了,然后跟印象里不同的時候就感覺會有驚喜,因為我們發現了新大陸。”(R01,視頻自媒體)其次,火箭發射時刻在場的具身體驗給人帶來的感官沖擊力是屏幕觀看不可取代的,聽聞著同一陣轟鳴聲、注視著同一個目標、呼喊著同一句口號……同一場域下旅游者的行為烘托著強烈的現場儀式感,高濃度的具身體驗也在意識里拉近了人與宇宙、航天等事物的聯系:“追火箭拉近了我跟遙遠的、宏偉的事物的聯系,比如說拉近我與中國航天的關系,因為親眼見證,所以親切感倍增,覺得自己與航天有著千絲萬縷的隱秘關聯。”(R11,視頻博主K)以一個親歷者的角色參與其中,感受到了火箭發射事件更強的賦能效應,且在往后的生活中,對祖國的航天事件也抱有更高的關注,實地觀測的意義由此得以升華。同時,與其他虛擬與現實結合的旅游形式不同的是,觀看火箭發射這一旅游形式通過虛擬與物理的流動孕育出更強的精神流動意義。從虛擬的向往到實地的兌現,“追火箭”需要克服距離以及時間上的困難,且與作息時間相悖的發射節點也需要人忍受生理的疲憊,而火箭發射又是轉瞬即逝的,人們甘愿付出時間、精力以及金錢,懷抱著堅定的信念去見證這一瞬間,是基于強烈的國家認同的基礎上萌生出來的對祖國航天偉業的“朝圣”。
3.5.2? ? 國家認同
實地觀看火箭發射,喚起了受訪者強烈的國家認同。在文昌目送嫦娥五號成功飛向宇宙的現場,有人興奮地擊掌,有人擁抱著跳躍,有人的眼里泛出淚花,“大家不應該說看著火箭發射就為了看它照亮天空,而應該是一種信仰,看火箭發射是為了看祖國越來越富強,看祖國的文化越來越復興。”(R03,視頻博主)火箭發射證明了中國的科技力量,是受訪者眼中對國家的信仰,同時,國家認同的強化也建立在將中國的過去與現在作比較以及將中國與世界別國作比較的基礎上。“以前想著以后可能有機會的話多去國外看一看,但結果發現自己回來之后就覺得自己國家的發展速度還是蠻快的,有一種民族自豪感。”(R08,民航飛行員)火箭的成功發射,是中國向世界證明自身綜合國力的契機,是中國航天在世界地位不斷上升的表現,而身為中國人,民族自豪感也油然而生。“我覺得也是非常有意義的,包括雖然不能為航天事業做事情,但起碼我自己可以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宣傳。給更多人宣傳到讓更多人認識到航天這個事情,我覺得也是我現在唯一能做的一件事情。”(R07,《視覺中國》簽約攝影師)同時,受訪者R05將對國家的認同內化為對航天事業的認同,并以具身視角,提出為航天事業做貢獻的期望。此外,國家認同的喚起也無形中強化了受訪者與國家之間的感知關聯,比如火箭發射的成功使受訪者R04感到自己的前途也更加光明,而受訪者R01與R06通過見證嫦娥五號飛向宇宙感到自己是祖國航天發展的見證者甚至是參與者,作為未來航天事業的建設者的R05表示出強烈的對未來參與祖國航天事業的欲望,而R03則感到對航天的熱愛的敬仰和傳承是自己以及同輩年輕人的責任。“我覺得一切都是非常有價值的。現在是這些辛苦,包括兩天兩夜沒合眼,我也是覺得非常值得。”(R04,大學生)“我覺得最樸素的感受就是我這一趟來文昌是來得值。”(R02,企業管理)而火箭喚起的國家認同,也消解了受訪者流動過程中奔波忙碌的疲憊,盡管跋山涉水、歷經艱難險阻來到文昌,僅僅為一睹短短幾十秒的發射,受訪者也因親眼見證了祖國的豐功偉績,認為流動過程中歷經的一切艱辛都值得。
3.5.3? ? 自我認同
在兩個火箭視頻的彈幕文本中,除了對火箭發射的情感抒發、對國家的祝福外,更多的是觀看者的許愿,表示對自身未來的期許,而這種對愿望實現的渴望在實地“追火箭”的過程中更為強烈(圖2)。超過8成的受訪者表明這趟旅程使他們更加堅定自己的理想信念,因此,伴隨參觀火箭發射的流動的是自我認同的升華。“我覺得追火箭的旅程會讓我去更堅定地去實現一些想法。我覺得有些東西其實沒那么難。我腦子里有一些可能有意義的想法或者說向往,在一定的條件下,我覺得我能更加堅定地想要去做,去實現,做一些更有意義的東西。”(R01,視頻自媒體)一方面,火箭象征著人類對太空的征途,在人類力所難及的范圍,這種超然的神圣性使火箭發射事件得以賦魅,從而在旅游者凝視中成為一種朝圣。“感動我們的不只是升空的火箭,而更是放下了平凡的生活,不顧一切地來到這里,點燃心中火焰的自己,這不也正是航天精神的浪漫所在。”(視頻博主K在第二條“追火箭”視頻中的自述)因此,“追火箭”的旅程也成為超脫世俗的經歷,當他們完成對家國信仰的朝圣后,也對自己賦予一種完成超越自身能力事物的感知,從而對自我產生一種肯定,這種自我認同體現在他們對自身選擇、對理想信念信任的強化。此外,大部分受訪者都抒發了自己強烈的重游意愿,“后續如果還有(追火箭)這一類的事情,我應該不會猶豫了,如果有時間我就會去。”(R08,民航飛行員)
不論是基于對國家成長的見證渴望還是對自我身份的建構欲望,都說明“追火箭”這一流動性的時空實踐具有極強的賦能效應,通過激起旅游者強烈的心流體驗和情感共鳴而增強其對國家和自我的認同,這種認同又轉化為一種內生性力量,化作旅游者面對未來的信心與動力。因此,超越一般影視旅游“懷舊與依戀”[57-58]、“擬真情景”[44]的體驗特征,此次基于視頻引致的“追火箭”旅游的特殊價值在于,其在精神層面為旅游者構建了精神流動更強烈的旅游體驗與更深刻的生命意義。
4 結論與討論
4.1 結論
在科技日益進步、流動日趨頻繁的現代化社會,對流動性的探討不應止步于物理空間內的流動,而更要探索其背后具身體驗的意涵以及社會意義的建構[26],同時,對流動性的研究也不應停滯于現實空間內的流動,虛擬流動已經成為一股不容小覷的力量,其與現實流動之間影響的交互值得重視[5]。本研究選取“追火箭”旅游群體為研究對象,采用流動性的理論分析框架,通過深度訪談以及參與式觀察,對“追火箭”旅游群體的流動過程及其內在意義建構進行深入分析,探討流動性框架在虛擬與現實移動之間的延展性,以及基于“追火箭”旅游探索區別于傳統流動性框架的新流動性范式。
研究發現,“追火箭”旅游作為一種特殊事件旅游,其過程體現出如下特性。
超越旅游流動體驗性框架的去程、在場和返程的三維框架[24],“追火箭”旅游的旅游體驗從出發前便已開始,延伸到回程后仍在不斷持續,且旅游體驗狀態呈現出全過程情緒高漲的特征。還未啟程,“追火箭”的流動已經成為旅游者心目中“重要的”“神圣的”“夢想的”向往,而通過與媒體交互產生的共鳴,旅游者感知自身離實現“航天夢”的距離越來越近。出發后,基于物理空間流動的旅途也不斷更迭著旅游者的情感體驗,場域范圍的逐漸縮小以及時間的臨近使旅游者的情緒愈發高漲,也使其將對旅途的關注點逐漸聚焦到火箭,以至通過周身一切事物建構對火箭的聯想。最終,火箭發射時刻,在宏偉壯觀的升空場景與集體歡騰的場域氛圍烘托下,旅游者達到體驗共睦態,其激動、震撼、感動等情緒也經歷不同程度的迸發與釋放。回到日常生活場域后,旅游者通過自身回憶及社交媒介的互動不斷建構其旅游體驗,以至于在與研究者再次回憶此段旅程時,仍用激動的語氣以及一系列擬聲詞表達其持續的情緒高漲。
基于“追火箭”的旅游流動過程喚起了旅游者的國家認同與強化了其自我認同。一方面,火箭的發射使旅游者聯想到祖國的航天事業,進而對中國航天從落后到崛起一路的艱辛歷程產生強烈共鳴,其“為祖國驕傲”“光榮啊,我們的中國”“民族自豪感”均是基于國家認同的最自然、樸實的情感流露。另一方面,旅游者為了觀看火箭發射跋山涉水、風雨無阻,而這一流動的旅程又以火箭排除險阻最終成功發射作為勝利標志,雙重險阻使得旅游者感知自我見證并完成了一件非同尋常的大事,從而更堅定了其對理想的追求、對信念的堅守,火箭成功發射化為內生性力量鼓舞了旅游者,強化了其自我認同。
研究還發現,基于虛擬到現實、再從現實回到虛擬的循環流動對旅游體驗以及背后的社會關系建構有重要意義。首先,以視頻博主K的火箭視頻為信息源,以微博、微信等社交媒體平臺為媒介,虛擬的信息流動使得素昧平生的旅游者最終匯聚成一個網絡新部落——“去月亮”微信群,在此新部落中,傳統地緣關系的界限被打破,同源情感以及共同目標的驅使使得旅游者在線上的信息交換以及情感交融一路順暢。此后,隨著五湖四海的旅游者們紛紛啟程去文昌,虛擬移動轉換為實際物理空間的流動,網絡部落群體功能需求性的社會關系也進一步轉化為集體情感歸屬的現實伙伴關系,結伴流動至火箭發射場域并共同等待發射的過程中,通過一系列的社會交往互動,新部落群體的成員友誼不斷升溫,社會交往影響著旅游者等待火箭發射的心情。最后,旅游者在觀看完火箭發射后流動回全國各地,但社會關系仍隨著虛擬的流動不斷被建構,通過主動或被動參與到伙伴的視頻、游記、朋友圈日志里,新部落的情感聯結未降反增,地理空間的區隔被弱化,并通過對嫦娥五號的太空旅程的持續追蹤,社群內仍然保持活躍的互動氛圍,并萌生了未來再次結伴去看火箭發射的約定,社群也形成了可重復性的線上與線下流動的循環新部落。與一般的新部落體驗的短暫性與網絡部落的匿名性特征不同的是[59],本研究對象的新部落群體體現出持續的聯絡性、體驗的可重復性以及由網絡部落演進到現實社群的去匿名性,這一點與研究音樂節的循環新部落特征相似[56],但與之區別的是,本研究樣本中的新部落群體的線下交往與融合并不需要類似于音樂節的“大旗”“文化服飾”等物質的符號表征物的支撐,其對視頻博主K視頻的同源情感、對火箭發射背后的家國情懷使得線下聯結持續順暢,但不論是物質的表征還是集體情感的象征,都指向符號是構成的新部落的特征體現,并與行為一起構成了新部落的兩大特征元素,這一點也支持了前人的研究[60]。綜上,本研究的理論貢獻在于基于微觀個體層面將虛擬流動納入旅游流動性的框架中進行實證研究,擴展了旅游研究中流動性的時空邊界,探討了流動背后的社會關系網絡與意義建構,驗證了旅游中的虛擬流動與現實移動是一個相互影響的過程:一方面,虛擬流動通過出行前的信息流動與社交互動為現實流動奠定了社會關系基礎,另一方面,現實流動深化了虛擬流動建立的社會關系層次,實現了社會交往身份形象從扁平到立體的層層進階,并為流動回虛擬世界后的情感聯結持續加強夯實了根基。
此外,本研究探析了“追火箭”旅游者的流動過程(圖3),延展了傳統旅游流動的時空界限,認為在時間維度,旅游體驗在離家前便已開始建構,在返家后仍能不斷延續;在空間維度,旅游流動不再局限于線下的實體空間,還包含線上虛擬空間的流動,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的相互切換也建構著流動的意義。
接下來,本文將對“追火箭”旅游這一研究案例中涉及的“物理流動”“虛擬流動”和“精神流動”的關系進行探討。火箭發射在航天領域屬于科學事件,是人類用科技的力量探索未知的偉大征程,而對于萬千個實地觀測的旅游者來說,他們的凝視為其賦予的含義卻不盡相同,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色彩。“航天其實是人類對宇宙星空的一個向往之心,這是我們人類對未知探索的一個本能。火箭它說到底它只是一個交通工具而已,它有一些什么實質意義?它就單純是一個交通工具。但是為什么我們這么熱衷于追求火箭呢?因為它相當于是一個載體,承載了我們所有人類對未知的一個向往之心,對于浩瀚宇宙的一個向往之心,所以我們才這么熱愛火箭這個東西。”(R07,《視覺中國》簽約攝影師)浪漫主義主張對人與世界關系表達的無止境的向往與渴望,提倡通過永恒的行動去探索我們之外的巨大的、不可捕捉的、不可企及的事物,雖然探尋的結果可能只是發現世界的無限性,但它更注重這一價值創造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人的意志和動機大于結果[61]。實地觀看火箭賦予人一種精神流動的空間,這種流動以火箭的箭身為載體,承載著跨越時空的精神,一方面承載著亙古以來人類文明對宇宙星河的探索與求知精神,另一方面寄托了人類對我們所在的地球到我們之外的太空征途的厚望。宇宙無邊無際,人的好奇心也無窮無盡,于是探索成為人類永恒的命題,成為潛藏在每個人內心深處的浪漫主義的種子,這顆種子在凝視火箭升空的過程中發芽,將對未知的想象隨著火箭涌流到遙遠的外太空,最終完成對頭頂這片難以企及的寥廓空間的“朝圣”。精神流動的輪回又體現在“追火箭”增強了人們探索未知事物的意志,這種循環的精神賦能激發人的不斷創造,是浪漫主義的核心體現。因此,“追火箭”旅游將旅游者身體的“物理流動”與當下傳媒媒介所建構的“虛擬流動”相交融,并通過火箭升空、探索宇宙這一具有人類浪漫主義傾向的目標,引領“追火箭”旅游者的“精神流動”1,超越物理所見天空的界限,體現出在對“天”的構建和探尋中人類精神的歷史性和延續性。
4.2 討論
值得探討的是,本研究揭示了在媒介化的現代生活里,社會關系屬性和空間概念也發生了“脫域”式的變革[62]。基于共同根源的地方空間的概念被逐漸淡化,人們逐漸從以地緣關系為基礎的互動聯系中脫離出來,融入網絡社會這一新的時空架構中,在這個時間同步、高速運轉的“流動的空間”里尋找新的歸屬[63]。視頻博主K的短視頻,實質上為觀看者們提供了一種“虛幻的流動性”,重構了他們的生活空間[64],使他們通過凝視視頻博主K的“追火箭”視頻構建他們自己腦海中的幻想影像,通過這種幻覺來萌生奔赴文昌“追火箭”的決策判斷[65]。而“追火箭”旅程中這一線上與線下相融合的互動行為,也被Castells詮釋為個人和群體通過網絡化方式重構社交的過程[66],以共同興趣為出發點,也使得他們在現實空間與虛擬空間的互動切換流暢自如。基于線上的虛擬社區雖然不能代表現實社區,但卻逐漸成為傳統社區有利的補充[67]。媒介構造了一個分享經驗的領域,在這個領域里,人們擺脫了傳統的地域空間的限制,實現了社會交往的“再嵌入”,并且通過此過程構建了身份認同與群體認同[68],在線上社區中,人類以一種煥然一新的狀態將自身同時安放于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中,安置于多重社會關系網絡中[69]。因此,在返回日常生活后,旅游者們仍然可以通過虛擬社區進行持續社交,線下的結伴旅行為他們奠定了牢固的社群意識和歸屬感,共同愛好又能為他們提供線上持續的經驗共享契機,他們身處不同的實體空間中,卻可以因為共同的虛擬空間和共享的時間來持續社會實踐。
本研究還發現了“追火箭”旅游置于時空流動之外的一種精神的、想象的流動性,與最新的理論研究相印證①,即旅游者賦予了“嫦娥五號”感官寄托,使其在想象中幻化成眼睛和身體,承載著期盼與渴望,流動到人們難以觸及的宇宙世界中,這種從吾之所至吾之外的流動性在一般旅游中無以為寄,是觀看火箭發射所獨具的一種流動性,且這種想象的流動性在人類的文明歷程中更為悠久、恒常。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言:“人類探索太空的步伐永無止境。”2從夸父追日的神話到追逐火箭的實踐,跨越時空,人類對頭頂那片浩瀚寰宇的向往永不止息。這一蘊含家國情懷、宏大敘事的流動,不僅為流動性理論的發展提供了更為豐富的案例,也為將來人類的流動空間不斷拓展的研究奠定了根基,隨著嫦娥五號返回艙的順利降落,人類流動至更廣袤的太空領域的征程指日可待。
需要強調的是,基于火箭發射觀測的航天旅游具有極強的精神賦能效應,無論是終極目標還是終極結果,觀看者的精神流動都是“追火箭”旅游不容忽視的特殊意義。自古以來,人們就擁有探索頭頂浩瀚寰宇的好奇心,西方的星座、星象以及東方的星宿、歷法無不與璀璨星空息息相關。“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窮處。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1宇宙的無窮性,從古代“宇宙”這一概念萌生時便得以彰顯,此后,自道家把“宇宙時空的無限性”納為思索目標[70],漢代的宇宙觀更是容納了“天道自然”的精神境界[71],人類對天地的探索欲造就了恢弘的時代格局的壯闊的精神氣象。近現代以來,隨著交通技術和探測水平的飛速發展,人們對宇宙的探索堆疊演化成“太空”“星球”等具有科學韻味的詞匯,盡管如此,浪漫主義精神無時不刻浸入在這類科學中,實地“追火箭”便是一種典型的體現。航天是表達人與宇宙關系的一種探索,歷經時代的更迭,人對無盡的宇宙強烈的探索欲生出的種種新的探索方式都是創舉,世界是人類永無止境的自我創新的體現,宇宙的概念、實體都是人的意識創造的結果,是人的選擇和創造定義了“于我之處”的世界和“于我之外”的宇宙。因此,實地“追火箭”的觀測者產生的精神流動在本質上也屬于從世俗進入神圣境域的精神流動,但有異于古代中國思想流派朝圣和西方的宗教朝圣,“宇宙”這一超驗的實體既蘊含了科學的意味,又因其神秘性帶給人無限遐想,同時,這類特殊的“朝圣”是人的身體難以企及的,因此需寄情于火箭,以其為媒介來完成人們意象中的太空探索之旅。
此外,研究者通過研究全過程的具身觀察和體驗以及資料的收集與分析發現,基于火箭發射觀測的航天旅游具有強大的發展潛力。首先,本研究超過8成的受訪者都自發表達了強烈的重游意愿,其中有基于對火箭發射場景在場體驗的深度迷戀、有對火箭發射事件“重大”且具有“強時令性”性質的追逐傾向、有對國家航天事業發展的持續見證意愿,不論是出于哪一種動機,都充分證明火箭旅游給旅游者帶來了旅游者極高的滿意度,且在此旅游市場并未被充分挖掘、產品與營銷尚未興起的當下,旅游者的滿意度很大程度上出自對過程本身的暢爽體驗。實際上,“去月亮”微信群里有群友在完成嫦娥五號“追火箭”之旅后啟程去觀摩了2020年12月17日四子王旗的嫦娥五號返回艙降落與2020年12月22日文昌的長征八號發射。其次,隨著中國的綜合國力不斷增強,其年度火箭發射次數與成功概率也漸趨上升,世界上只有8個能夠獨立發射火箭的國家,中國2021年航天發射次數共計55次,位居世界第一2,而文昌作為地理位置極佳且可公開觀測火箭發射的目的地,是一片基于火箭觀測的航天旅游發育的肥沃土壤。硬件設施達標的前提下,軟件設施也在不斷發展。互聯網的飛速發展、視覺傳播媒介的興起使得航天的科普得以在虛擬的社會互動中實現,在嫦娥五號發射至返回期間,新華社、澎湃新聞等媒體不斷用“仙女降臨”3“帶土特產回家”4等擬人化詞語將嫦娥五號發射事件祛魅,使其更加日常化從而滲入大眾的視野,一眾網友也通過觀看直播等形式持續關注嫦娥五號在太空的“旅程”。因此,航天旅游的營銷者可以尋找合適的切入點,將“軟件”引發的對火箭發射的關注轉化為實地追逐火箭發射的動機,并結合火箭發射目的地的硬件設施打造更為成熟、優質的航天旅游產品。航天旅游具有深遠的愛國教育意義以及基于個人特殊生命體驗的自我身份建構意義。
本研究也存在以下不足。第一,研究樣本基于視頻博主K微信群內的群友展開,普遍年輕化,而沙灘上觀測火箭發射的旅游者還包含青少年、親子、老年人群體,本研究結果對解釋整個“追火箭”旅游者群體是否具有普適性還有待商榷。第二,研究采用民族志方法初步揭開“追火箭”旅游的神秘面紗,未來“追火箭”旅游體驗及意義建構的研究還有待實證研究進一步深化。第三,研究者發現基于本研究樣本的“追火箭”群體表現出極高的重游意愿,甚至部分旅游者已經實施了重游,“追火箭”的重游意愿在更廣大群體中的特征、重游意愿的內在驅動力以及重游體驗的感知在未來的研究中值得探討。最后,本研究還發現,觀測火箭發射的旅游者有極其激昂的情緒感受,此種持續高昂的情緒背后的形成機制可在后續研究進一步探討。
致謝:感謝匿名審稿專家對本文提出的寶貴修改建議。感謝所有訪談對象對本研究數據收集的支持與配合。最后,特別感謝bilibili平臺up主康喲喂對本研究開展的大力支持。
參考文獻(References)
[1] SHELLER M, URRY J. 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2006, 38(2): 207-226.
[2] 孫九霞, 周尚意, 王寧, 等. 跨學科聚焦的新領域: 流動的時間、空間與社會[J]. 地理研究, 2016, 35(10): 1801-1818. [SUN Jiuxia, ZHOU Shangyi, WANG Ning, et al. Mobility in geographical research: Time, space and societ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16, 35(10): 1801-1818.]
[3] 吳寅姍, 陳家熙, 錢俊希. 流動性視角下的入藏火車旅行研究: 體驗、實踐、意義[J]. 旅游學刊, 2017, 32(12): 17-27. [WU Yinshan, CHEN Jiaxi, QIAN Junxi. The experiences, practices and mean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train travel to Tibet[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2): 17-27.]
[4] CRESSWELL T. Towards a politics of mobility[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010, 28(1): 17-31.
[5] 朱璇, 解佳, 江泓源. 移動性抑或流動性?——翻譯、沿革和解析[J]. 旅游學刊, 2017, 32(10): 104-114. [ZHU Xuan, XIE Jia, JIANG Hongyuan. Mobility or liquidity? Translation, evolution and interpretation[J]. Tourism Tribune, 2017, 32(10): 104-114.]
[6] HANNAM K, BUTLER G, PARIS C M. Developments and key issues in tourism mobilitie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4, 44(1): 171-185.
[7] HALL C M. Reconsidering the geography of tourism and contemporary mobility[J]. Geographical Research, 2005, 43(2): 125-139.
[8] 韋俊峰, 明慶忠. 打工度假旅游者的流動性實踐及身份認同建構——廈門馬克客棧案例[J]. 旅游學刊, 2019, 34(10): 127-136. [WEI Junfeng, MING Qingzhong. Self-identity construction and the working-holiday tourist: A case study of mark hostel in Xiamen[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10): 127-136.]
[9] MITAS O, YARNAL C, ADAMS R, et al. Taking a“peak”at leisure travelers’positive emotions[J]. Leisure Sciences, 2012, 34(2): 115-135.
[10] LYONS G, URRY J. Travel time use in the information age[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2005, 39(2/3): 257-276.
[11] MOKHTARIAN P L.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ravel: The case for complementarity[J]. Journal of Industrial Ecology, 2002, 6(2): 43-57.
[12] KENYON S. The‘accessibility diary’: Discussing a new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to understand the impact of Internet use upon personal travel and activity participation[J]. Journal of Transport Geography, 2006, 14(2): 123-134.
[13] URRY J. 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 Mobilities for the Twenty first Century[M]. London: Routledge, 2000: 49-76.
[14] URRY J. Mobilities[M]. Cambridge: Polity, 2007: 22-33.
[15] SALOMON I.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ravel relationships: A review[J].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A General, 1986, 20(3): 223-238.
[16] SENBIL M, KITAMURA R. Simultaneous relationships betwee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activities[C]. Lucerne: 10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Travel Behavior Research, 2003: 10-15.
[17] HAZARIE S, BARBOSA H, FRANK A, et al. Uncovering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between physical and virtual mobility[J]. Journal of the Royal Society Interface, 2020, 17(168): 20200250.
[18] KONRAD K, WITTOWSKY D. Virtual mobility and travel behavior of young people—Connections of two dimensions of mobility[J]. Research in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2018, 68: 11-17.
[19] 黃佩, 王文宏, 張蓁. 網絡中的背包客: 從流動中尋求認同[J]. 旅游學刊, 2014, 29(11): 87-94. [HUANG Pei, WANG Wenhong, ZHANG Zhen. Backpacker online: Seeking identification from mobility[J]. Tourism Tribune, 2014, 29(11): 87-94.]
[20] GREEN N. On the move: Technology, mobility, and the mediation of social time and space[J].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2, 148(4): 281-292.
[21] WHITE N R, WHITE P B. Home and away: Tourists in a connected world[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07, 34(1): 88-104.
[22] PARIS C. Flashpackers: An emerging subculture?[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2): 1094-1115.
[23] MOLZ J G. ‘Watch us wander’: Mobile surveillance and the surveillance of mobility[J]. Environment & Planning A, 2006, 38(2): 377-393.
[24] CUTLER S Q, CARMICHAEL B. The dimensions of the tourist experience[M]//MORGAN M, LUGOSI P, RITCHIE J R B. The Experience of Tourism and Leisure: Consumer and Managerial Perspectives. Bristol: Channel View Publications, 2010: 3-26.
[25] MACKAY K, VOGT 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everyday and vacation contexts[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3): 1380-1401.
[26] CRESSWELL T. Mobilities I: Catching up[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0, 35(4): 550-558.
[27] CRESSWELL T. Mobilities II[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012, 36(5): 645-653.
[28] FRITH J. Splintered space: Hybrid spaces and differential mobility[J]. Mobilities, 2012, 7(1): 131-149.
[29] HANNAM K, SHELLER M, URRY J. Editorial: Mobilities, immobilities and moorings[J]. Mobilities, 2006, 1(1): 1-22.
[30] 盧白羽. 莎德瓦爾德和他的《古希臘星象說》[J]. 中國圖書評論, 2008(4): 123-124. [LU Baiyu. Schadwaldt and his Ancient Greek Astrological Theory[J]. China Book Review, 2008(4): 123-124.]
[31] 楊璐. 文昌航天旅游發展戰略研究[D]. 海口: 海南大學, 2018. [YANG Lu. A Study on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Space Tourism in Wenchang[D]. Haikou: Hainan University, 2018.]
[32] LELE A. Asia and space tourism[J]. Astropolitics, 2018, 16(3): 187-201.
[33] CHANG E Y. From aviation tourism to suborbital space tourism: A study on passenger screening and business opportunities[J]. Acta Astronautica, 2020, 177: 410-420.
[34] 于世豹, 胡家銘, 陳小林, 等. 鄉村振興背景下的特色小鎮智慧旅游建設路徑研究——以張掖航空航天特色小鎮為例[J]. 智能建筑與智慧城市, 2020(8): 103-105;108. [YU Shibao, HU Jiaming, CHEN Xiaolin, et al.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smart tourism characteristic tow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Taking Zhangye aeronautics and astronautics characteristic town as an example[J]. Intelligent Building and City Infomation, 2020(8): 103-105;108.]
[35] 李玲麗, 齊真. 我國航天發射的新搖籃——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J]. 國際太空, 2016(7): 13-15; 88. [LI Lingli, QI Zhen. Overview of Wenchang satellite launch center[J]. Space International, 2016(7): 13-15; 88.]
[36] 國防科學技術工業委員會. 航天發展“十一五”規劃[J]. 航天器工程, 2008(1): 1-6. [National Defense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dustry Committee. “Eleventh Five-Yar Plan”for space development[J]. Spacecraft Engineering, 2008(1): 1-6.]
[37] BUSCHER M, URRY J. Mobile methods and the empirical[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Theory, 2009, 12(1): 99-116.
[38] 曹晉, 孔宇, 徐璐. 互聯網民族志: 媒介化的日常生活研究[J]. 新聞大學, 2018(2): 18-27;149. [CAO Jin, KONG Yu, XU Lu. Digital ethnography: Research on mediated daily life[J]. Journalism Bimonthly, 2018(2): 18-27;149.]
[39] CONNELL J. Film tourism-evolution, progress and prospects[J]. Tourism Management, 2012, 33(5): 1007-1029.
[40] OH J E, KIM K J. How nostalgic animations bring tourists to theme parks: The case of Hayao Miyazaki’s works[J]. 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 Management, 2020, 45: 464-469.
[41] KIM S, KIM S, PETRICK J F. The effect of film nostalgia on involvement, familiarity, and behavioral intention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19, 58(2): 283-297.
[42] SWALE A. Miyazaki Hayao and the aesthetics of imagination: Nostalgia and memory in spirited away[J]. Asian Studies Review, 2015, 39(3): 413-429.
[43] BEETON S. The advance of film tourism[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lanning & Development, 2010, 7(1): 1-6.
[44] 郝小斐, 張驍鳴, 麥娉恬. 圣地巡禮旅游者的行為特征及其同源情感研究——以動漫電影《你的名字。》為例[J]. 旅游學刊, 2020, 35(1): 95-108. [HAO Xiaofei, ZHANG Xiaoming, MAI Pingtian. Anime pilgrimage tourists’ behavioral patterns and their homologous affection: Taking anime film Your Name. as an example[J]. Tourism Tribune, 2020, 35(1): 95-108.]
[45] POOKAIYAUDOM G, TAN N H. The Buppaesanniwas phenomenon: ‘Thaines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s a film tourism motivation[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20, 18(5): 497-513.
[46] 龍耘, 王蕾. 誰是青年: “Y世代”在中國語境中的解讀[J]. 中國青年社會科學, 2015, 34(4): 11-16. [LONG Yun, WANG Lei. Who is the youth: An interpretation of‘Y generation’ in Chinese context[J]. Chinese Youth Social Science, 2015, 34(4): 11-16.]
[47] 鄭飏飏, 徐健, 肖卓. 情感分析及可視化方法在網絡視頻彈幕數據分析中的應用[J]. 現代圖書情報技術, 2015(11): 82-90. [ ZHENG Yangyang, XU Jian, XIAO Zhuo. Utilization of sentiment analysis and visualization in online video bullet-screen comments[J]. New Technology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 2015(11): 82-90]
[48] HAO X F, XU S J, ZHANG X M. Barrage participation and feedback in travel reality shows: The effects of media on destination image among generation Y[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19, 12: 27-36.
[49] MACIONIS N, SPARKS B. Film-induced tourism: An incidental experience[J]. Tourism Review International, 2009, 13(2): 93-101.
[50] MAFFESOLI M. The Time of the Tribes: The Decline of Individualism in Mass Society[M]. London: Sage, 1996: 6; 15-21; 76; 95-98.
[51] ADAMS T L, SMITH S A. Electronic Tribes: The Virtual Worlds of Geeks, Gamers, Shamans, and Scammers[M].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8: 11-20.
[52] 于朋艷. 大學生參與旅游虛擬社區結伴同游動機與阻礙研究[D]. 武漢: 中南民族大學, 2018. [YU Pengyan. The Study of the Motivations and Obstacles of Traveling with A Compan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in the Tourism Virtual Community—Taking Colleges in Wuhan as An Example[D]. Wuhan: South-Central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2018.]
[53] 謝彥君, 徐英. 旅游體驗共睦態: 一個情境機制的多維類屬分析[J]. 經濟管理, 2016, 38(8): 149-159. [XIE Yanjun, XU Ying. The communitas of tourist experience: A multi-dimensional category analysis of situational dynamics[J]. Economic Management, 2016, 38(8): 149-159.]
[54] 孫九霞. 共同體視角下的旅游體驗新論[J]. 旅游學刊, 2019, 34(9): 10-12. [SUN Jiuxia. A new view on tourism experie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mmunity[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9): 10-12.]
[55] ONG C, CROS H D. The post-Mao gazes: Chinese backpackers in Macau[J]. Annals of Tourism Research, 2012, 39(2): 735-754.
[56] 吳少峰, 戴光全. 迷笛音樂節中循環新部落的聯結與交往特質[J]. 旅游學刊, 2019, 34(6): 74-84. [WU Shaofeng, DAI Guangquan. Attributes of cyclic bonding and association amongst neo-tribe members at the Midi music festival[J]. Tourism Tribune, 2019, 34(6): 74-84.]
[57] KIM S. Extraordinary experience: Re-enacting and photographing at screen tourism locations[J]. Tourism and Hospitality Planning & Development, 2010, 7(1): 59-75.
[58] KIM S, KIM S, KING B. Nostalgia film tourism and its potential for destination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Travel & Tourism Marketing, 2019, 36(2): 236-252.
[59] NORMAN M. Online community or electronic tribe? Exploring the social characteristics and spatial production of an internet hockey fan culture[J].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2014, 38(5): 395-414.
[60] HARDY A , GRETZEL U , HANSON D. Travelling neo-tribes: Conceptualising recreational vehicle users[J]. Journal of Tourism and Cultural Change, 2013, 11(1-2): 48-60.
[61] 以賽亞·伯林. 浪漫主義的根源(修訂版)[M]. 呂梁, 洪麗娟, 孫易, 譯.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11: 17; 104-107; 140. [BERLIN I. The Roots of Romanticism(Revised Edition)[M]. LYU Liang, HONG Lijuan, SUN Yi, trans. Nanjing: Yilin Press, 2011: 17; 104-107; 140.]
[62] 安東尼·吉登斯. 現代性的后果[M]. 田禾, 譯. 南京: 譯林出版社, 2014: 18-25. [GIDDENS? A.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M]. TIAN He, trans. Nanjing: Yilin Press, 2014: 18-25.]
[63] 曼紐爾·卡斯特. 網絡社會的崛起[M]. 夏鑄九, 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06: 355. [CASTELLS M. The Rise of Network Society[M]. XIA Zhujiu, tra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06: 355.]
[64] 秦朝森. 脫域與嵌入: 三重空間中的小鎮青年與短視頻互動論[J]. 現代傳播(中國傳媒大學學報), 2019, 41(8): 105-110. [QIN Chaosen. Delocalization and embedding: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young people in a small town and short video in a triple space[J]. Modern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2019, 41(8): 105-110.]
[65] URRY J. The Tourist Gaze[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2: 3.
[66] 曼紐爾·卡斯特. 傳播力[M]. 湯景泰, 星辰, 譯.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018: VIII. [CASTELLS M. Communication Power[M]. TANG Jingtai, XING Chen, trans.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8: VIII.]
[67] 簡·梵·迪克. 網絡社會——新媒體的社會層面[M]. 蔡靜, 譯. 北京: 清華大學出版社, 2015: 178-179. [DIJK J V. The Network Society: Social Aspects of New Media[M]. CAI Jing, trans. Beijing: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2015: 178-179.]
[68] 施蒂格·夏瓦. 文化與社會的媒介化[M]. 劉君, 李鑫, 漆俊邑, 譯. 上海: 復旦大學出版社, 2018: 39. [HJARVARD S. The Mediatization of Culture and Society[M]. LIU Jun, LI Xin, QI Junyi, tran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18: 39.]
[69] 孫瑋. 微信: 中國人的“在世存有”[J]. 學術月刊, 2015, 47(12): 5-18. [SUN Wei. WeChat: Chinese“existence in the world”[J]. Academic Monthly, 2015, 47(12): 5-18.]
[70] 劉振永. 道家和道教的生命宇宙觀[J]. 美與時代(下), 2010(11): 49-51. [LIU Zhenyong. Taoism and Taoist view of life and cosmology[J]. Aesthetics, 2010(11): 49-51.]
[71] 李曉敏. 中國古代“天人關系”說的發展演變[J]. 華中人文論叢, 2013, 4(2): 97-99. [LI Xiaomi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the ancient Chinese theory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J]. Huazhong Humanity Forum, 2013, 4(2): 97-99.]
Rocket Runners: A Tourists’ Ethnography of the Chang’e-5 Laun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TANG Yutong, HAO Xiaofei
(School of Tourism Management,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275, China)
Abstract: The paradigm of mobility has shifted to encompass the social component of mobility. Now that virtual and real mobility are interactively integrated, it is necessary for researchers to extend the mobile period from before tourists leaves home to after they return there. To extend the space-time framework of mobility trips, it is essential to consider how virtual mobil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ourism experience. The present study examines the Chang’e-5 launch: we investigated the mobility characteristics of space tourism based on field observations of the rocket launch through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network observation, and in-depth interviews of tourists who traveled to Wenchang to watch the launch. To determine the far-reaching impact and potential value of “rocket-chasing” tourism, we continuously tracked the participants’ WeChat Moments, videos, and blogs about rocket chasing from December 2020 to July 2021. We found that the travel experience of rocket chasing began before the participants’ departure and continued after their return home; throughout the process, the travel experience was associated with high emotions. That tourism experience enhanced the tourists’ national identity and reinforced their self-identity. We also observed that virtual and physical mobility in tourism exerted a mutual influence on each other. Through information flow and social interaction before travel, virtual mobility established a foundation of social relations for physical mobility. Conversely, physical mobility deepened the level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established by virtual mobility, and it changed the identity of social interaction from a 2-D to a 3-D structure. Levels of advancement created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ongoing reinforcement of the emotional connection after the return to the virtual world. Tourists in different physical spaces can continue social interactions owing to the sharing of virtual space and time. We also identified a spiritual and imaginary mobility outside time and space with rocket-chasing tourism: the participants endowed Chang’e-5 with sensory sustenance; in their imaginations, it transformed into their eyes and bodies; it conveyed their expectations and desires; it flowed into an unreachable universe. This mobility from where the subject exists to where they do not is a unique feature of rocket-chasing tourism, and it is very different to general tourism. Such imaginary mobility has been a constant feature in the history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e launch of Chang’e-5 made a new contribution to China’s aerospace industry, and it helped achiev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ountry. Chang’e-5 was a pioneering achievement in the peaceful exploration of space and in promot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In this study, we investigated how tourism mobility triggered by the launch of Chang’e-5 broadened the theoretical boundary of mobility research; we interpreted the core meaning of spiritual mobility in rocket-chasing tourism. Spiritual mobility in tourism is a very important topic, and it deserves follow-up research. From a practical perspective, we found that rocket-chasing tourism has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n patriotic education and in developing self-identity based on a special life experience; that has strong practical implications for constructing rocket launch sites and developing space tourism.
Keywords: mobility; roket-chasing tourism; national identity; Chang’e-5; ethnography
[責任編輯:周小芳;責任校對:王? ? 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