畢奐午與《掘金記》
張建智

畢奐午
一
重讀詩人畢奐午的詩集,正是暮春時節。網上看到,武漢大學空蕩蕩的校園,珞珈山道沒有了學子游人紛擾,只有櫻花依然燦若云霞,落花空階前,伊人春無跡。讓我想起老詩人生前每到春時,會給老友們群發詩柬,邀請他們一聚,共同賞花,詩柬也寫得別致而饒有意趣:“這么些天總是風風雨雨,但在雨絲風片中花還是要開了,春天還是要來了。又到了桃花、櫻花的時節,又到了我們老人也擠在年輕的人叢中看花的時節。你們哪天來呢?我們每天都在盼望,等候……等候仙子和詩人的降臨。”老詩人的家在武大珞珈山二區宿舍。如候鳥般來了又走的武大學子們,只記得曾經的武漢大學中文系主任畢奐午是個爽朗憨厚、愛書成癡的老頭,卻很少了解他年輕時是與艾青、何其芳齊名的詩人,他的詩作曾在大江南北廣為傳誦,激發一代愛國青年的熱血。如今再查找畢奐午的資料,卻發現老詩人除了早年出版的兩部詩集,幾乎沒有任何文集問世,連零散的報刊文章都稀見,完全成了詩壇、文壇的“失蹤者”。這不禁讓我好奇,詩人究竟經歷了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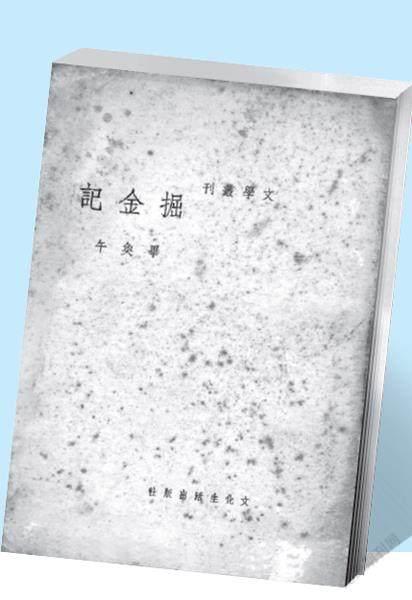
《掘金記》畢奐午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6 年初版
二
畢奐午,原名恒武,后改奐午。曾用筆名畢篥、李福、李慶、魯牛等。一九○九年生于河北井陘縣賈莊,一個太行山東麓礦區的小山村。畢奐午父輩和家庭出身已不可考,零散的資料基本都只寫到他的童年是與祖母一起度過的,祖母知書識字,給畢奐午很好的啟蒙教育。畢奐午小小年紀便已能背誦《唐詩三百首》和《古文觀止》,祖母給他講的《聊齋志異》《封神演義》的故事也給他埋下了文學創作的種子。畢奐午在賈莊當地的新式小學念書,畢業后考入北平師范學校,這所學校是北京最早的師范學校之一,歷史非常悠久,老舍便是這所學校早期的畢業生。畢奐午就讀北師時的校長是王西徵,他是位卓越的教育家,曾與陶行知一起創辦曉莊師范學院。王校長引領下的北平師范學校,文化藝術氛圍非常濃厚,師資也多是聘請當時文壇、藝術界和思想界的名師。國文教師于澄宇、高滔,音樂美術教師李苦禪、趙望云、汪采白等,讓畢奐午受益終身。在北師的六年,他對文學、音樂、美術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最終選擇了以文學作為一生的志業。特別是國文課上教師布置的新詩題,讓畢奐午開始了詩歌的創作。
一九三一年畢奐午從北師畢業,但當時的北平局勢紛擾,一介文學青年,要謀一職業并非易事,但他也不想回到老家,便在北平逗留。那年正值國立北平圖書館正式開館,正醉心文學的畢奐午,大部分的時間都泡在圖書館里。他與王西徵一起合作,為《世界日報》編輯了文學副刊《慧星》。《世界日報》創辦于一九二五年,由成舍我創辦,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變之后,《世界日報》主張抗日,反對國民黨當局的不抵抗政策,并精心編輯副刊,發行量一度高達一萬多份。畢奐午編輯了二十多期《慧星》,發表了不少傳誦一時的新文學作品,并最先發表了蘇聯詩人馬雅可夫斯基的《怎樣寫詩》的中文譯文。這一時期,畢奐午通過辦刊、翻譯讓自身的詩歌創作日漸成熟,而內憂外患的時局,讓畢奐午無法只沉浸在純文學的園地中。現實中底層人民的流離失所、掙扎苦難給他帶來極大的觸動,他決心用筆刻畫人間疾苦,由此奠定了他詩歌創作上現實主義的底色。

《雨夕》畢奐午著文化生活出版社1939年版
在北平逗留了三年后,畢奐午于一九三四年經過考試,成為天津南開中學的教員。當時的天津南開中學的教員隊伍囊括了李堯林(巴金的三哥)、何其芳、高遠公(王國維、梁啟超的學生)、李苦禪等,畢奐午與他們志趣相投,時常詩文切磋,成為一生的摯友。盡管日本侵華戰爭的陰云已籠罩華北大地,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七年這一段時期,可謂是京派文化的繁榮期。這一時期各種高質量的文學副刊匯聚,如巴金與靳以主編的《文學季刊》,卞之琳主編的《水星》,楊振聲、沈從文又從吳宓手中接過天津《大公報》的文藝副刊,由蕭乾主編,給文學新人開辟了發展的空間。畢奐午作為詩人也正是在這個時期嶄露頭角,正式登上文壇。
而對畢奐午影響最大的,是他通過同事李堯林結識的巴金。一次巴金來南開看望三哥李堯林,恰遇上畢奐午,得知畢奐午正在寫新詩,巴金在看了他的幾首習作之后,很是欣賞,便鼓勵他多多創作。之后畢奐午的第一部詩集《掘金記》(1936)、第二部詩集《雨夕》(1939)均是在巴金的支持下得以出版問世的,說巴金是畢奐午文學上的伯樂和引路人一點不為過。兩人從青年時代至耄耋之年,長達近七十年的友誼,也令人十分動容。
詩集的出版,讓年輕的畢奐午成為詩壇一顆冉冉上升的新星,然而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一介書生的畢奐午被日軍投入了監獄,并受到了非人的屈辱和摧殘,精神肉體遭到極大損傷,甚至一度喪失記憶。現存的資料已無法得知畢奐午入獄的原因和細節,但從他之前的經歷來看,畢奐午可能很早就作為一名黨員投身地下工作了。早在北平師范學校求學期間,畢奐午就曾與當時的同學王榮庭(之后成為極負盛名的“西部歌王”王洛賓)一起結伴輾轉來到哈爾濱,希望經哈爾濱奔赴紅色圣地莫斯科。但由于各種原因,他們未能順利成行,在哈爾濱流浪了三個月后,仍返回北平。
畢奐午的第二部詩集《雨夕》出版于一九三九年,巴金在詩集后記中提到,上海“八一三”事變以后,完全失去了畢奐午的消息,他惦念友人,也為了不讓詩人的手稿空駐在黑黑的書架上,便一力促成了詩集的出版。艾青在評價畢奐午詩作時也寫道:“詩人似乎就一直生活在已經淪陷了的城市里,除了讀到他這樣痛苦的詩之外,從來沒有得到他的消息。”6D0E3CBC-C729-45DE-8B96-A1B6951A7527
由此可以看出,“八一三”事變后畢奐午可能就已經被秘密逮捕入獄了,而巴金等一眾友人并不知情。至于畢奐午何時出獄,現有的資料也都難以查證,只知道他在一九四六年由巴金和李健吾介紹,被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朱自清聘請為助教。所以很可能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畢奐午才被釋放。入獄期間,畢奐午完全停止了創作,出獄之后,仿佛詩神忽然遠離了他,僅有少數詩文發表,而他的獄中經歷也沒有太多回憶見諸文字。一九四八年,畢奐午調赴華中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的主要前身)任講師。翌年畢奐午便晉升為副教授,后又升為教授。解放戰爭爆發后,畢奐午也跟許多愛國志士一樣投身“反饑餓、反迫害、反內戰”的民主風潮中,這期間,他作為大學教員,全力地支持青年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與當時清華大學、華中大學兩校從事地下活動的中共黨員學生,保持著密切的關系,他的家也成了學生黨員地下活動的場所和掩護所。
新中國成立前夕,畢奐午出席了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會,并先后擔任中南文聯、第一屆湖北省文聯、武漢市文聯、湖北省文化局等機構的領導職務。應該說,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初,他在湖北文化界地位頗為重要,但之后卻因為一些子虛烏有的原因,被打入另冊,調離領導崗位,來到武漢大學成為一名普通教師。“文革”十年,畢先生無法再上講臺,藏書也被抄走,他被下放農場勞動。畢奐午生性豁達樂觀,十年牛棚歲月,他還給自己起了個雅號叫“喚牛”。“文革”結束,畢奐午重新回到武漢大學,并出任中文系主任。
改革開放之后,畢奐午沒有再創作更多的作品,除了寫下《初出牛棚告白》發表在《詩刊》上,幾乎沒有其他作品問世。但畢老并沒有閑著,從東湖的牛棚搬至武大宿舍,畢奐午把自己全部的精力投入到了教學和科研上。他一人帶五名研究生,還時常為中青年教師提供資料、審讀論文著作,為慕名求助的文學青年看習作,解答各式各樣的問題。為人修改書稿、引見編輯,甚至尋找工作單位,這些為他人作嫁衣之事,耗費了大量精力,但他卻甘之如飴。他自謂不是作家,更不是學者,也不是詩人,只是希望把教師作為畢生志愿:“站在講臺上講課,我是體力不支了。但我可以像珞珈山上的拾柴人,多撿一些枯枝落葉,供中青年教師們燒火煮飯,做出美味佳肴來。”
三
我收藏的畢奐午的《掘金記》,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是印數甚少的精裝本,屬于“文學叢刊”系列。“文學叢刊”自一九三五年底至一九四九年初,由巴金主編,陸續出版達十集,每集十六種,包括小說、散文、詩歌、戲劇和評論,均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可謂是民國期間,出版時間持續最久,內容最豐富廣泛,作品思想藝術水平相當高的一套叢書。“文學叢刊”在書裝上的特點是自始至終都采用一樣的三十二開本,一式的封面設計,素白封面,全無裝飾,只印上書名、叢刊名、作者名和出版社,極其樸素,卻自有一種簡潔大方。“叢刊”每集十六種,每集詩集并不多,僅一種或兩種,但被“文學叢刊”選中出版的詩集,往往都成了中國新詩史上的經典,如第一集卞之琳的《魚目集》、第三集臧克家的《運河》、第四集胡風的《野花與箭》、第五集曹葆華的《無題草》、第六集鄒荻帆的《木廠》和王統照的《江南曲》、第十集陳敬容的《盈盈集》等。《掘金記》是“文學叢刊”第二集中唯一的一本詩集,該集另有長短篇小說十四種,劇本一種,作者陣容包括靳以、蕭軍、沙汀、蘆焚(師陀)、荒煤、周文、柏山、蔣牧良、歐陽山、陸蠡、麗尼、悄吟(蕭紅)、何其芳、巴金和李健吾。其中蕭紅的《商市街》和何其芳的《畫夢錄》,都是兩位作家的散文處女集,且日后皆成為新文學史上的經典之作,可見主編巴金敏銳的文學品位和扶持新人的獨到眼光。
盡管詩人畢奐午和《掘金記》今天已淡出人們的視線,但詩集甫一出版,在當時新詩界可是激起一陣浪花,好評如潮。京派評論家李影心在詩集剛一出版時,就在《大公報·文藝》發表書評給予高度評價: “《掘金記》的作者又重新燃起我們對氣魄濃郁好詩的期望。”同為詩人的何其芳,對畢奐午的詩也十分欣賞,他認為畢奐午的詩有臧克家現實主義的張力,且“筆力粗強似甚于臧克家”。到了二十世紀四十年代,作為新詩理論家的聞一多編《現代詩鈔》時,《掘金記》已被列入“待訪”詩集,當時畢奐午身陷日軍監獄,聞一多以讀不到畢奐午的詩為恨。
《掘金記》分為兩輯,第一輯收十首詩,第二輯則包含四篇散文,書中沒有詩的寫作時間,但作者在書前的序言中寫道:“這里面的文字,一大部分是我在上中學的時候寫的。春城,村莊,田園……這些都就是當時國文先生在講堂上出下的題目……四篇散文,寫的時期略微靠后,是兩年前吧。我從中學畢業了,趁暑假回到我那位置于一個大礦山附近的故鄉去一趟。在那里我看見不知有多少的人是遭遇著像《冰島漁夫》里面所描述的人物的同樣命運—潘堡爾壯丁們的生命是都被大海吞噬了。于是我便描了這樣幾幅小畫。但它們并沒有把河泊山下居民的哀愁的萬分之一申訴出來。”
由此可見,詩集的兩輯恰對應詩人兩段人生經歷,由純真懵懂的文學少年,到進入社會大學更深刻思考社會痼疾的青年文人,而細讀兩輯中的文字,也會發現詩人文風從輕靈變得雄渾。第一輯中,除了與詩集同名的《掘金記》一首,多是短小的詩,我最喜歡的是《春城》和《田園》兩首,均來自詩人初中國文課堂的習作。新詩歷史上,中學生的習作收入詩集的例子并不少見,如汪靜之的《蕙的風》、陳敬容的《盈盈集》中,都有數首中學時的習作,但課堂作業直接作為成熟的創作,公之于眾,倒并不多見。而且畢奐午這兩首詩從詩的語言、意象、韻律,都堪稱完美,如果不是詩人在序中言明,絕難想象是出自稚嫩學生之手。《春城》一首,以一句“也是春天”的極短句開篇,既點出了全首的季節背景,又給讀者留下了一點懸念,又一個春天來臨,該是勾起詩人年年歲歲春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的感想。之后作者則以洗練而靈動的筆觸,通過一連串底層勞動人民的形象,勾畫出一幅初春的城市風情卷:趕馬車進城送貨的車夫、游蕩在城街間尋營生的人們、縷麻編草鞋為生的鞋匠。詩人以“永不戴手套的鄉下人”“帶著菜色的黑眉男子”“摸索于人類之足底”這幾個細部描寫,寥寥數筆,底層人民饑寒掙扎的卑微生活,便畢見紙上。然而詩的色調,又不是一味的灰暗,“冒著杏花雨”“沒有一棵苜蓿花,沒有一棵金鳳花”,讓人讀后,感受到春日花開的亮色,但慢慢回味,卻又涌起一種莫名的哀傷和凄婉,全詩以“向炎夏走去”結尾,正恰與開篇呼應。整首詩,景與人物交融,意象生動,明暗色交織,情感流暢而細膩。6D0E3CBC-C729-45DE-8B96-A1B6951A7527
畢奐午詩中,意象的營造,頗為大膽,也獨具特點,如另一首《田園》中,詩以“新的鞋子/踏著舊泥土”起首,新與舊的對應,鞋子與泥土兩個意象,虛實間似有無窮的隱喻,后兩句“到五月的海洋/眺望田間的麥浪”,海洋和麥浪形成一種自然的互喻,舒暢而繁榮的氣象油然而生;緊接著詩人又以蕪菁、石榴花和晚霞比喻農女廚邊通紅的火焰,火光絢爛,把整首詩飽滿的情感推至頂峰。
又如在《牧羊人》中,詩人寫道“黃金色的米粒,價值/等于幾瓣殘紅”“三月的太陽/空照銀齒的鐮刀”“春雷,如失意的老人/在陰沉的天空/隱隱呻吟”,這些意象的營造,使整首詩彌漫一種優美而蕭索的徒勞感,將讀者緊緊包圍,深陷其中,仿佛走進了詩人筆下營造的村莊和田野。《秋歌》一首,詩人寫催征壯丁的喇叭,響徹田間的緊張感,卻用了一種十分詩意閑適的筆調,結尾處“赤臂的苦力,肉搏/西風,落葉,黃花”,這兩組反差極大的意象,產生驚人的張力,讓人不禁生出這些征戰的人們在浴血奮戰,而終將如黃花落葉般灰飛煙滅,隨風而散。
畢奐午對中國當時社會現實的深沉思考和悲憫,也體現在他的詩中,使他的寫景和抒情詩有了思想的深度。他在《村莊》中寫道:“我們曾把自己的谷子/一大排,一大排的割倒/我們曾換得一個錢票/小而又小。”在《牧羊人》中他寫道:“可憐的歲月是如此凋零”,“汗水與塵土/再不能塑成/美麗的幻夢了”。詩人對社會不公與黑暗的控訴在《掘金記》這首長詩中達到頂峰,整首詩共九十三行,不分節,酣暢淋漓,一氣貫注。全詩記述了太行山民的一次掘金狂潮。
一九三四年,太行山區山洪暴發,隨之傳聞金礦大量流失,千千萬萬饑民懷揣僥幸的希冀,成群結隊,背井離鄉,瘋魔一般地涌向太行山掘金,不分男女老幼,都用最原始的工具,拼命地希望哪怕挖到半點金沙。詩人用強健的筆力,描繪出這既魔幻又現實的場景:隨急風在天空飛起白云,隨鍬鋤在地面流著石火,隨著人堆上的勞作怒潮,每一顆心都想收獲新果。人們為了爭奪一星半點的金沙,以命相搏,殺傷流血:太行山的空氣,像不夠人們呼吸,每個人都用方言叫囂、懊惱、焦灼,往往為一粒細沙,不惜用鐵鍬爆濺血花。詩人準確抓住在掘金狂潮中各色人等的特點和心態,他們中有多年在塞外販馬的來客、有平山草地田野勞作鑄就鐵骨的農民、有兇頑野蠻的山民、有盲從發財夢的城市居民。但最終真正得利的是一些城市內的銀樓業老板,他們精于算計,散布流言,乘機壓低黃金收購價格,大大地撈了一把,而付出血與汗甚至生命的掘金者們,到頭來只是被流言欺騙,白白做了一場夢,只剩痛苦的回味。
這首《掘金記》奠定了畢奐午現實主義詩人的地位,詩人通過這一并不知名的社會事件,毫不留情地揭示出當時中國社會底層人民迫于生計的無助和愚昧,無良奸商唯利是圖,最終陷入人吃人的怪圈。不同于前幾首輕靈的小詩,長詩這種形式適合表現宏大的敘事和壯闊的感情,也更顯詩人的功力,詩人投槍匕首般鋒利的語言和深沉的悲憫融合得恰如其分。詩人選用這首詩為整部詩集命名,說明他對這首詩的看重。盡管,我更偏愛詩人早期的短小詩作,但不可否認《掘金記》一詩,在現代詩歌中的地位。
畢奐午在序言中有言: “對于什么是詩或怎樣寫詩等類的文字,在那時自然有些看不懂;但我也總沒有留心過。幼時對于幾種玩具,如木馬,布老虎……是那樣渴望地想知道它們肚子里裝的是什么;對文學理論則從未發生半點興趣。”由此可見,詩人對新詩理論并不感興趣,也并未下功夫,他的詩更多是自然的流露,而較少雕琢。詩人的目光緊緊地注視著苦難深重的中國大地,在藝術風格上,他也不盲從于當時新詩壇流行的新月派唯美主義,也不附庸于現代派的象征主義,而形成現實主義的詩風。
何其芳曾讀到畢奐午的《火燒的城》一詩,詩中有這么幾句:“是誰被拋棄于腐朽,熟睡/如沉臥于發賣毒液的酒家/在那里享受著夢境無涯?/歡樂的甜蜜,吻的溫柔誰不期待?/但那帶著枷鎖的苦痛的手指/將推你醒來……”何其芳讀后,曾感慨地對畢奐午說道,是的,我們不能再做夢了,而應該如詩中所言,讓戴著枷鎖的苦痛的手,把我們推醒、搖醒了……
《掘金記》第二輯中的四篇散文,《人市》《下班后》《潰敗》和《幸運》所描寫的皆是礦區人的生活日常,與其說是散文,不如說更接近于微型小說。如《下班后》中在礦里工作十個小時的蘇保,卻無法讓妻子吃上飽飯,而妻子為生計只能成為暗娼,蘇保受不了工友的冷嘲熱諷,但望著空空的米缸和餓得哀號的兒子,只無可奈何地嘟囔一句“長大,還不是得提安全燈,背拖鉤……鉆黑洞去”。作者用極短的篇幅,沒有設置太多的故事情節,只是白描式地展現一系列小人物在艱難困苦中求生的場景。詩人筆下的礦區只是中國社會的一個縮影,社會的黑暗和不公,像一個巨大的輪回,埋葬一代代礦區民眾的希冀與生命。太行山礦區,對自小生于斯長于斯的畢奐午,那些山民、礦工、家庭婦女,他是再熟悉不過的了,所以寫得非常真實,力透紙背。而創作這一系列短篇的緣起,可能是他與王洛賓在哈爾濱流浪的三個月里,兩人住進了高爾基筆下那種“夜店”式的雞毛小店里,房間是地下室,窗戶比馬路還低。在這里,他接觸到了當時最底層的生活和最下層的人物:賣苦力的、無家可歸的逃亡者、白俄浪人、小偷、乞丐、下等妓女,等等。這些親身經歷為他后來的寫作儲備了素材。令人不免惋惜的是,《掘金記》之后,畢奐午的創作幾乎中斷了。
一九三七年巴金將畢奐午的一些新詩和小說,編輯成《雨夕》,同樣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原書作者后記已輾轉丟失,所以巴金親自為書補寫了后記。詩人這時正身陷囹圄,巴金也不知老友在何處,但覺得有義務把這本存在他處的稿子付梓出版。《雨夕》初版本稀見,之后也沒有單獨重印,只在一九八八年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將《掘金記》與《雨夕》合為一冊,命名為《金雨集》重印了二百冊。除了兩本詩集,畢奐午再也沒有出版任何作品。以畢老坎坷波折的人生經歷,與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多位大師的交誼,從年輕時便顯露的文學才華,他本可留下更多有價值的文學作品,然而他最好的創作年華都在監獄和牛棚里度過了。如今老詩人離世已二十個年頭了,武漢大學,櫻花掩映的小樓里,曾經陪伴林淑華、蘇雪林直至畢奐午的青燈早已熄滅。那些曾經來賞花的老友們,都已離開人世,來求教的青年學子們,也已快到了相識時畢老的年紀。真似李輝所說的:“遙想當年,畢奐午先生清晨牽著牛,穿過草叢,向遠處走去。頭上,漫天星辰……”
然而,《掘金記》這部薄薄的詩集,其價值所在恰如一星微光,給身處黑暗的人們,帶來一點文學的溫度和慰藉。我想,只要是光,它總會在夜空中閃爍,于讀者心中流動。一如梵高畫中的“星空”— “沒有眼睛能看見日光,假使它不是日光性的。沒有心靈能看見美,假使他自己不是美的。你若想觀照神與美,先要你自己似神而美。”我想,今日讀者讀畢奐午的詩,同樣要有這么一顆心靈。6D0E3CBC-C729-45DE-8B96-A1B6951A75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