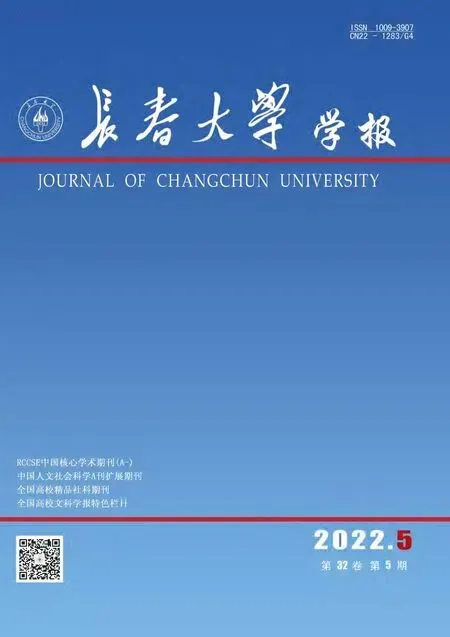摩梭人“走婚”的文化邏輯與觀念秩序
許瑞娟
(云南民族大學 南亞東南亞語言文化學院,昆明 650504)
摩梭人是生活在中國西南部川滇兩省交界瀘沽湖周邊地區自稱為“納”或“納日”的古羌人后裔,迄今仍較為完整地保留了母系社會形態。元朝以降,摩梭人接受了從藏區傳入的苯教與藏傳佛教,受到藏族文化的深度影響,晚清以后,又與父系傳統濃厚的漢族、彝族有著密切的交往,此后歷經種種社會變革和歷史激蕩,仍未動搖母系制的根基。摩梭人獨具特色的母系家庭與兩性異居走訪制(“走婚”)構建了摩梭文化的獨特性[1]。遺憾的是,“外界媒體在報道摩梭人時,都把焦點放在了走婚習俗上,把摩梭村寨渲染成原始的性樂園和性天堂,許多游客懷著好奇心來到瀘沽湖”[2]。大眾傳媒對“走婚”的誤讀,嚴重地破壞和褻瀆了極具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價值的獨特民俗文化事項。
在以往的研究中,學者們多局限于對摩梭人“走婚”存續原因的討論,忽略了摩梭文化系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多元婚姻現象,忽略了“走婚”獨特的功能和結構,也忽略了“走婚”的文化和社會支持因素。事實上,“走婚”只是摩梭社會“多元婚姻”體系的一部分,其背后的根源隱藏在摩梭人的觀念邏輯與日常生活秩序結構之中。本文將“走婚”與摩梭人的其他婚姻形式區別開來,試圖闡釋“走婚”的獨特文化價值以及摩梭文化中頗具象征性的傳統理念。人類學關于親屬制度研究的“交換理論”(exchange theory)從兩性之間的社會交往關系出發來看不同群體、不同地域之間的連接點。莫斯與葛蘭言都指出,以社會性別為中心的交往是社會構成的主要機制;列維·斯特勞斯則延伸到整個親屬制度、神話和宇宙論的研究,強調了不同群體之間兩性交往對于超地方社會形成的重要意義[3]。從中我們可以獲得一個啟示:在探討摩梭社會獨具特色的社會形態與家庭結構時,聚焦摩梭社會兩性關系所呈現出的獨特文化實踐與形塑力量,并以此反窺摩梭社會的文化制度,是一種可行的研究進路。因此,對摩梭人的兩性關系與婚姻形態進行再研究顯得非常有必要。
一、學者視野中的摩梭“走婚”
20世紀五六十年代,以宋恩常、宋兆麟、嚴汝嫻、詹承緒、王承權、李近春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對分布在云南寧蒗彝族自治縣永寧鄉、拉伯鄉和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鹽源縣瀘沽湖鎮、前所蒙古族鄉以及木里藏族自治縣、屋腳蒙古族鄉等自稱為“納”“納日”的族群展開了社會歷史調查,撰寫了一批有影響力的調查報告和論文,將川滇邊境鮮為人知的摩梭人推向了公眾的視野。囿于時代學理的局限,學者們試圖將永寧納西族的婚姻制度與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提出的觀點進行比較,將摩梭人異居走訪的婚姻形態視為早期母系氏族的縮影,認為“走婚”保留了若干血緣婚和群婚的實例,并且正在經歷由母系制向父系制的過渡[4]6。這些觀點問世不久后便成為極具爭議性的話題。
20世紀80年代以后,摩梭研究有了新的進展。留美學者施傳剛使用“走訪制”來表述摩梭語中對兩性關系的指稱,并指出“走訪制”是摩梭社會占首要地位的戀愛生育制度,它與婚姻的不同之處在于“非契約性、非義務性和非排他性”(1)源于施傳剛美國斯坦福大學1993年博士學位論文The YongningMoso: Sexual Union, Household Organization, Gender and Ethnicity in a Matrilineal Duolocal Society in Southwest China(永寧摩梭:中國西南一個異居制母系社會的性聯盟、家戶組織、文化性別與民族認同)。。留法學者蔡華介紹了一個社會在既無丈夫又無父親的情形下的運行情況,指出世界上不是只有一種單一的婚姻模式(2)源于蔡華法國巴黎第十大學1995年博士學位論文A Society without Fathers or Husbands: the Na of China(中國納人:一個無父無夫的社會)。。香港學者周華山從社會性別的角度剖析了“走婚”是一種以母系血緣為核心的兩情相悅而非獨占式的婚俗[5]。和鐘華將“走婚”的存留與演變視作民族自身歷史演進的結果[6]。陳柳指出,摩梭社會內部傳統文化的力量與外部的國家力量不斷交織與平衡,形塑了摩梭人婚姻變遷的軌跡[7]。趙鵬在新的歷史語境下對摩梭及其走婚文化進行了分析和審視[8]。趙心愚指出,“走婚”世代延續是長期堅守為其明確的范圍與界限的規矩,其中最關鍵的是嚴禁血緣婚[9]。
國外學者則傾向以跨文化比較的視角來看待摩梭人的婚姻制度。美國學者孟徹理(C.F.Mckhann)指出,摩梭人的家庭是一個關鍵的組織單位,它的延續是通過包括各種婚姻形式和居住習俗在內的多種方式來完成的,“母系”和“父系”的問題在歷史上和結構上都是次要的(3)源于孟徹理1998年文章Naxi, Rerkua, Moso, Meng: Kinship, Politics and Ritual on the Yunnan-Sichuan Frontier(滇川交界處的納西、阮可、摩梭及蒙的親屬關系、政治制度及宗教儀式)。。法國克里斯蒂娜·馬休(Christine Mathieu)指出,摩梭人的民族特色主要通過各類宗教儀式及家庭結構表現,封建制度與當地風俗融合后形成了特有的民族特征(4)源于克里斯蒂娜·馬休法國木爾多赫大學1996年博士學位論文《失去的王國和被遺忘的部落:中國西南部納西族和摩梭人的神話、宗教儀式及母權制》。[10]。蘇珊·克內德爾(Kn?del, Susanne)指出,摩梭社會是母系社會和異居制社會,獨特的親屬制度是摩梭人的族群標志(5)源于蘇珊·克內德爾1998年文章YongningMoso Kinship and Chinese State Power(永寧摩梭的親屬制度與中國政府機構的權力)。。伊麗莎白·許(Hsu, Elizabeth)提出,以“家屋為中心”的觀點來理解摩梭社會的親屬制度與婚姻制度更為合適(6)源于伊麗莎白·許1998年文章Moso and Naxi: the House(摩梭與納西:住屋)。。
學者們對摩梭社會“走訪制”的關注引發了關于婚姻與家庭的普遍性爭論,彰顯了摩梭個案獨具特色的人類學與社會學價值。正因為獨特,“走婚”往往難以得到主流社會的認可,“文革”期間,母系家庭和“走婚”習俗被斥為“四舊”予以革新。歷經了種種社會動蕩,“走婚”習俗依舊頑強地保留了下來,且一直延續至今。這就不得不讓人追問:究竟是什么強大的力量在背后支撐著“走婚”的延存?對此問題的討論,學者們各執己見。
有的從歷史溯源著手研究并指出,南詔建立鐵橋節度后,強制性的移民措施使瀘沽湖地區的摩梭人所剩無幾,為了生存繁衍下去,他們將歷史上殘存的“父名母姓”“貴婦人,黨母族”傳統復活起來,出現了家庭與婚姻的逆轉[11]。有的認為,只有理解摩梭母系意識,才能解釋摩梭人為什么實行走訪制[12]。有的指出,“摩梭社會沒有婚姻和家庭,只有按照母系傳承的血緣和財產關系,以及母系親族居住在一起的社會結構”[13]7。有的認為,“走婚”是摩梭人生存和文化的一種選擇[6]62。有的指出,“走婚”是適應摩梭家屋體制的文化產物,加上過去摩梭馬幫貿易盛行、喇嘛遠赴藏區求學等客觀原因,半數摩梭男人長期在外,不可能實行一夫一妻制,“走婚”便成為鞏固和延續家屋的睿智之舉[5]110。有的認為,“走婚”的出現與長期延續,除與摩梭人居住地的特殊自然、地理環境有關外,也與其族源(古羌人)有關,是川滇之間歷史上曾存在的“母系文化帶”的文化遺存[14]。還有的認為,永寧壩區普通人家的“走婚”是摩梭上層階層為維護其統治地位而制造出來區分等級的制度[15]35-36。上述觀點似乎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卻又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局限性。
二、“走婚”:制造“輕松和諧”還是“海枯石爛”?
大量的民族志資料以及客觀事實告訴我們,“走婚”并不是摩梭人在兩性關系中的唯一選擇。20世紀60年代初期,在拉伯的一些村落中,正式結婚的夫婦比例高達59.2%[16],如今永寧壩區結婚的比率也呈逐年上升的態勢,辦理銀行貸款、子女落戶入學等都需要提供結婚證,現實需求迫使許多年輕人選擇結婚,在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就職的摩梭人,幾乎無一例外地選擇結婚。不可否認的是,“走婚”在摩梭社會中實行了幾百年,直至今日選擇“走婚”的也不在少數。摩梭語將“走婚”稱作thi se se。se se的意思是“走走”,thi相當于一個動態助詞,表達“走”這個動作持續著的一種狀態。盡管在田野工作中獲得這個詞并不費周折,卻鮮有學者從詞法上對其語源進行仔細探究。se的本義是“走”,從詞性上來說是一個動詞,se se從詞形上來看是動詞的重疊形式,語義為“走走”;從語法上來講,當表示可持續動作行為的動詞重疊時,一般有短促動作的動量小或時量短或嘗試、輕松等意義[17]。
通過對“走婚”詞義與詞法的分析,已經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在摩梭社會中,“走婚”是基于雙方感情基礎的兩性關系,名分、地位、經濟、責任等外在因素對兩性關系的促成沒有必然影響。“走婚”持續的時間往往有一定的期限,短暫的可能一兩夜,長久的幾十年,但絕沒有漢語中“海枯石爛”“天長地久”“一生一世”的語境與文化寓意,促使“走婚”最直接的動因是兩性之間的相互愛慕。相互喜歡就在一起,感情淡了就好聚好散,一切自然而然。由于不需要考慮經濟、責任等外在因素,“走婚”從一開始便是男女雙方在輕松與和諧氣氛里的情感釋放。有的人難以理解并對其“污名化”,對摩梭人而言,兩性交往中相互喜歡是關鍵因素,物質、名分并不十分重要。
外界對摩梭人“走婚”過度關注,卻對其背后隱藏的文化機制漠不關心。有學者指出:“男女兩性間的‘走訪式關系’只是摩梭人眾多社會關系中的一種,是摩梭文化中很小的一個部分。”[13]7筆者在田野調查中也發現,摩梭人尤其忌諱在血緣親屬面前談論“走婚”,平日里也極少刻意評論,何況,人世間真摯、美好、純粹的感情本來就不是拿來在光天化日之下曝光的。摩梭諺語形容“走婚”的男女就像天上飛翔的鳥兒一樣來來往往,一切自然而然。“走婚”不是如外界所傳言的“性自由”“性解放”,而是有一套內在的規約機制的。比如不能與三代之內有母系血緣關系的親戚“走婚”,不鼓勵與實行一夫一妻制的異民族結婚,不能與“養蠱”的人家“走婚”,不應與名聲不好的家庭“走婚”[4]142。對于不遵守規約而胡亂“走婚”的人,會被眾人唾罵為“在電線桿下隨便抬起腳來亂撒尿的狗”,遭到厭惡與鄙視。一個人若沒有好的名聲,為家屋蒙羞,這在摩梭社會無異于最嚴重的懲罰。“走婚”避免了婆媳、姑嫂、妯娌相處的矛盾,最大限度地維護家庭成員之間的和睦,而和諧是摩梭社會最核心的觀念秩序。“走婚”是摩梭人文化觀念中合乎情感邏輯的一種表達方式,體現了摩梭人生存智慧的主觀能動性。
三、“走婚”的文化邏輯
2016—2019年,筆者多次前往摩梭傳統文化習俗保留得較為完整的永寧鎮溫泉鄉瓦拉別村進行田野調查。調查中發現,該村80戶摩梭家庭分屬于“潘咪、窩夫、包若和格則”四個斯日,每個斯日由幾家或十幾家母系家戶組成,摩梭人將同一個斯日的成員視為“一個根骨”,三代以內的同一斯日成員之間禁止“走婚”。斯日是有母系血緣關系的親屬聯盟,規定著母系血緣親屬間的性禁忌,并在“祭祖”與“葬禮”儀式中勾聯著各個母系家戶對于祖先的記憶與認同。筆者在田野調查中的一項工作,是繪制各個斯日不同家戶的族譜,從中可以找到一些關于“走婚”的文化邏輯與觀念解釋。
原則上,男女雙方“走婚”所生子女應屬于女方家庭,如果選擇結婚,所生子女既可以屬于女方家庭也可以屬于男方家庭,一切均可根據各家庭的現實需求以及雙方協商的結果來定奪。ZL家屬于窩夫斯日,從族譜(圖1)中不難發現,摩梭人的婚姻形態是多元的,既有“結婚”也有“走婚”。“走婚”所生子女屬于女方家庭。結婚則分兩種情形:男子娶妻與女子招贅所生子女屬于自己家戶,男子上門與女子外嫁所生子女屬于對方家戶。如ZL家第二代成員MZZ外嫁、第三代成員ZD、BG、MB入贅上門,所生子女均屬于對方家戶。為了應對現實生活中的不確定性,家中成員都能接受靈活變通的兩性關系模式,最終目的都是為了大家庭的延續。筆者在訪談中獲知,不論選擇什么樣的婚姻關系,都體現了摩梭人共同的婚戀觀,即兩廂情愿、結合自由、解除容易、性愛為主、遵守血緣禁忌、非獨占性特點。

圖1 ZL家的族譜圖
QA家,在瓦拉別村是一個極具代表性的大家庭(圖2)。

圖2 QA家的族譜圖
QA家屬于包若斯日,是典型的母系大家庭。QA家女兒多,除了MD外嫁,其余幾個女兒均選擇“走婚”。“走婚”又分兩種形式:一種是男女雙方各居母家,夜晚由男方到女方居所走訪;另一種是男女雙方不經過結婚儀式,女入男方家居住或者是男入女方家生活。由于家庭成員較多,家中最能干的女兒MZ便與長期固定的走婚對象單獨組建了一個家庭,從大家庭里分家出來,新建的小家庭除了MZ自己親生的兩個兒子EC與LC外,還有其妹妹的孩子MDS、CL、MDL和MDZ。傳統摩梭社會并不鼓勵分家,但如果大家庭因人口多而難于管理,便會分一個小家庭出去。分家出去的一般都是有能力的人,QA家建立小家庭的MZ,是云南省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在當地是知名人物。固定專偶“走婚”之后獨立組建小家庭,減少了昔日“走婚”的不穩定性,如今已成為摩梭社會盛行的婚姻模式。
現今環瀘沽湖周圍以及永寧壩子選擇“走婚”的摩梭人仍然占多數,結婚的也不少。但無論摩梭人的婚姻關系如何變化,最終仍逃不開母系血緣紐帶這條主線。摩梭人婚姻與家庭形態的靈活性,反映了各家戶根據現實需求在社會生產和再生產過程中進行的有效調節,若家中無女就娶妻,若家中無男就招贅,也可以過繼。摩梭人沒有太多結婚和生育的壓力,找不著對象或不愿意找對象,沒有生育能力或不愿意生育,都不會受到家人的責怨與鄰里的恥笑。
男性“走婚”所生子女屬于女方家庭。筆者在記錄族譜的過程中發現,父親記不清子女年齡的情形非常普遍,“走婚”男性所在家戶成員記不住其子女姓名的情況也很常見。梳理族譜時,報告人的習慣幾乎無一例外都是先從女性始祖開始,后代的排序也習慣于從女性開始,把男性放在后面,并不按照實際年齡的大小來排序。盡管摩梭人的親屬關系是雙系的,但是在繼承權、家庭權威以及情感方面,卻有著強烈的母系偏向。摩梭社會流傳著一句諺語:“親戚之間的關系就像木頭一樣牢固,而斯日之間的關系卻如鐵鏈一般堅固。”(7)筆者根據2017年2月在永寧扎美寺訪談GJHF的筆記整理。諺語通過形象的比喻說明斯日關系比親戚關系更加牢固,在摩梭人的傳統觀念中,真正牢固不變的關系是母系血緣親屬,而非通過“結婚”“走婚”等方式建立起來的親戚關系。摩梭語將人的脊柱稱作“斯俄”,“斯日”與“斯俄”共同的語素“斯”揭示了兩個詞在詞源上的密切關聯(8)筆者根據2016年10月在大落水村訪談摩梭民族博物館RHDJ的筆記整理。。“斯日”如同人的脊柱支撐人體軀干一樣,將無數個有著母系血緣關系的家戶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維系并協調著母系血緣紐帶的運轉與延續。
“走婚”最根本的意義在于解決社會的再生產以及個體的生理需求。摩梭語含蓄地把走婚稱作“走走”,如此輕描淡寫的表達足以反映摩梭人對此并不十分重視,“走婚”屬于個人隱私,當事人沒有說的義務,家人也沒有過問的習慣。摩梭人最在意的是與母系親族間其樂融融、和睦共處的關系,有摩梭諺語說:“兒女不知道母親的祖先,就像飛在高空的孤雁。”靈活多樣的選擇雖然使某些摩梭家戶內母系親屬的血緣關系不再“純粹”,但這樣做的根本目的是為了維護和延續母系制的傳統,體現了母系親屬為生存和繁衍作出的選擇與讓步。事實上,“走婚”一直在逐步適應不斷變化的社會條件的過程中改變著話語與實踐,但萬變不離其宗,母系血緣親屬是摩梭社會主導性的親屬結構,也是摩梭人用來區分人際網絡關系親疏遠近的最重要的標尺。
四、“走婚”的觀念秩序
盡管摩梭社會多樣性的婚姻形態廣泛存在,但從傳統的思想觀念來說,摩梭人強烈地表現出對于“走婚”的青睞。究竟是什么樣的文化機制使“走婚”長盛不衰?有學者試圖從藏傳佛教對摩梭社會的影響來詮釋“走婚”。歷史上,永寧土司規定,有兩個兒子的家庭,必須有一個去當喇嘛。解放前,永寧地區喇嘛的比例大約占到成年男子比例的30%,再加上很大一部分的摩梭男性長年在外趕馬經商,這就是為什么摩梭百姓家庭以“走婚”作為兩性交往最主要的方式[15]36。毋庸置疑,這的確是“走婚”盛行的一個原因,持續不斷的社會流動的結果,促使摩梭人在盡可能的范圍內選擇合適的婚姻形態。
元末明初,以藏傳佛教為核心的藏文化深入瀘沽湖地區,對摩梭社會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摩梭貴族階層極力推崇藏傳佛教及藏文化。“走婚”是否受到藏族婚姻制度的影響,或者更確切地說,摩梭社會是否與藏族社會的某些文化邏輯、意識觀念存在著共同之處?
有學者研究發現,云南藏區多偶家庭的大量存在,與他們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的資源環境有著密切的關系。藏族傳統觀念認為,同是一對父母所生之兄弟“應生在一起,長在一起,永不分離”。這種觀念為兄弟共妻提供了傳統思想基礎[18]31-32。
有學者研究表明,“在藏族社會中,理解‘肉’的親屬(母系親屬)關系極具重要性,這種關系與吐蕃女子特別的獨立特點和地位是同時存在的,無論是從經濟角度來看,還是從兩性關系方面來論述,吐蕃的女子們是非常自由的”[19]。摩梭社會女性優勢的傳統觀念表現出與藏族社會高度的一致性,女性有著充分的性自由權利以及對家庭經濟命脈的掌控力,摩梭女性強大的靠山來自于她的母家,地位崇高的舅舅、慈祥的母親以及親密的兄弟姐妹都是她堅強的后盾。有關藏邊社會的民族志資料也指出:“地處西藏與尼泊爾的藏邊社會定日,導致家戶經濟方面危機的因素是勞動力而不是有限的自然資源的貧乏,家庭的團結具有帶來更多的經濟效益的功能,定日人認為,家中人口多一些會使家庭繁榮。這種關于家庭人口的觀念使每戶人家在社會中都具有強烈的社團性質。……在討論定日的社會階級結構和經濟組織時,人們可以看到血統觀念在這些結構中并不是決定性因素,把一切社會關系聯接起來的不是血統觀念而是家庭觀念。”[20]就此而言,摩梭人對于家庭與血統的觀念與藏族如出一轍。
“走婚”還有一個重要原因,是依附于家庭與土地之上的客觀因素。歷史上,摩梭土司曾以家庭為單位征收賦稅,人單勢薄的小家庭完全沒有能力來應付沉重的苛捐雜稅,唯一的指望與依靠便是大家庭,家庭的和睦與團結在這種時候顯得尤為重要,不引入非血緣關系的人到家戶里生活,“走婚”便是最佳選擇。在摩梭社會中,“走婚”對緩解人地關系緊張,解決生產方式與勞動力的矛盾,限制人口增長以及保持較好的生活水平等,都有著十分重要的調節作用[18]36。
摩梭人的傳統文化觀念總是可以在達巴經中找到追根溯源的解釋,吊詭的是,筆者訪談了幾位資深達巴,均證實經文中沒有關于“走婚”的描述,只在《創世紀》中尋到一些隱晦的線索。相傳摩梭人的始祖曹直里依依娶了天上的仙女柴紅吉吉美為妻,此舉遭到仙女姐姐的嫉妒,她便使盡各種手段讓曹直里依依長年昏迷不醒,并指使公猴與妹妹結為臨時伴侶,生下半人半猴的兩男兩女。后來曹直里依依得到菩薩的解救,回到家里砍死了公猴,因考慮到自己年歲已大,遂不忍殺害半人半猴的兒女,后來這兩子兩女相互婚配,繁衍了今天的摩梭人。《創世紀》中暗含了兩個關鍵的隱喻:一是摩梭人的女始祖是天上的仙女,一出場就賦予了比男性高的身份地位;二是兩性關系是自由的,除結婚外還可以臨時挑選伴侶過同居生活。神話中的隱喻為摩梭人踐行“走婚”提供了“歷史”依據。
摩梭人舉行葬禮時,達巴要念誦一段叫作《斯克》的經文,講述的是這樣一件奇事:遠嫁他鄉的姐姐與弟弟重逢時竟然沒認出來,弟弟一氣之下頭也不回地走了。知道真相后的姐姐悲痛欲絕,沒過多久便離世了。奇怪的是,遺體在火化時燒了幾天幾夜燒不化,后來兒子負荊請罪找回舅舅,舅舅在棺材上放了一條披氈、加了一根柴火,阿媽的遺體瞬間化成骨灰。老達巴說,“摩梭人從此不再把女兒嫁出去,不愿再忍受骨肉分離之痛,兄弟姐妹共同生活在母親身邊,從那時開始實行母系家庭和走婚”[21]。達巴經中還有許多歌頌母親功勞的表述。有一段經文講述了母親懷胎九月生下孩子并含辛茹苦將其養育成人的不易。在新生嬰孩的誕生禮與年滿十三周歲的少年成丁禮上,達巴都要念這段經:“裝在肚子里九個月,抱在懷里七個月,摟在胸口上喂奶,(媽媽)用嘴巴(幫孩子)擦鼻涕,(媽媽)用手(幫孩子)擦屁股……。”(9)筆者根據2017年1月在麗江訪談拉伯鄉白埡村達巴WLWDZ的筆記整理。達巴經中也常以子女的口吻表達對母親的感激之情,尤其在母親的葬禮上,達巴會念道:“人都會有老的一天,所以要養兒防老;人都會有肚子餓的時候,所以要播撒種子;母親老了,子女有贍養她的義務;母親不在了,子女有送終盡孝的責任。”(10)同①母親臨終前,兒女們要爭著把母親抱在懷里,把事先準備好的口含(11)里面放有酥油和少許碎金銀。放到母親嘴里,直至母親咽下最后一口氣,并竭盡所能地為她操辦一場體面而隆重的葬禮。母親與子女臍帶相連,臍帶就如一根無形的繩索,是有形刀斧切不斷的特殊紐帶,握著這根繩索的是母親,母親通過臍帶將兒女們聯結在一起,延續著一份永恒的情感。過去,摩梭家庭的孩子脖子上都系著一個繩子,上面拴的是臍帶。倘若兄弟姐妹間發生爭執,其中一方便會將臍帶從懷里掏出來,拿著質問另一方:“這是什么?”(12)同①。這時,無論多么激烈的爭吵都會戛然而止。爭吵的終止體現了母親在摩梭人心目中的無上權威。
文化傳統對民族心理的規約與形塑,是無形且根深蒂固的,摩梭傳統文化造就了摩梭人對母舅的高度尊崇,并體現在摩梭社會的方方面面,摩梭人對兩性走訪關系的青睞,終極目的是使大家庭團結和睦,生而在世的人們將“取悅母親、舅舅與逝去的祖先”作為人生價值的永恒追求。有學者用“生活的充實性”來詮釋西南地區少數民族重要的價值觀念,這一觀念與摩梭人崇尚“家庭和諧”有著顯著的共同特征[22]。摩梭人對祖先的敬畏、對母舅的尊崇、對家屋和諧的追求,是“生活充實性”的重要體現,也是作為一個摩梭人的終極意義所在。這一文化內驅力的影響,促使摩梭人在兩性關系與婚姻制度中不斷地尋求著平衡的調劑,摩梭人重視家屋中男女比例的和諧,缺男或少女對于任何一個家屋而言都很尷尬,他們會通過“抱養”“過繼”“招贅”“娶妻”等各種辦法讓家屋男女比例保持平衡。正常情況下,他們選擇并傾向于“走婚”,這樣可以避免因引入外來血緣成員而產生種種誤會與矛盾[23]。達巴經里還有兩句經文這樣說道:“嫁出去的女人過不上好日子,帶回娘家的只有眼淚;不出嫁的女兒,即便是哭泣,眼淚也淌在父母的手掌心里”;“留在家里的女兒,哪怕只是一塊鐵耙最終也會變成金子,即使開出來的是銀花最終也會結出金子般的果實;嫁出去的女人,即便是一塊銀子最終也會變成石頭”(13)筆者根據2020年8月在麗江訪談拉伯鄉白埡村達巴WLWDZ的筆記整理。。
若放眼從中國西南到西藏甚至到東南亞、南亞廣袤的跨喜馬拉雅地區,不難發現有兩個非常重要的“本土觀念意識”,即“以家屋為中心的社會”和“以聯盟為目標的思想意識”,常常被用來解釋構成這些地區多樣性親屬制度與婚姻形態的社會制度。跨喜馬拉雅地區族群特有的“地方性親屬觀念”在摩梭社會也同樣具有解釋力。社會流動劇烈的結果使男女兩性有更多的性自由;依附于家庭與土地上的客觀因素使摩梭人不得不作出極具現實性的決策,以家庭為中心并盡可能地強調生活中的“社團意識”;傳統文化通過各種儀式在達巴經中被反復強調,形塑了摩梭人“女性優勢、尊崇母舅、重視母系親屬”的觀念意識。總而言之,“走婚”是摩梭人為了生存繁衍并使母系親屬以及家屋團結和諧而采取的權宜之計與文化策略。
五、余論
隨著對摩梭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我們越發覺得,要想勾勒出一幅完整、全面、逼真的摩梭社會生活圖景,還有大量艱巨的工作等待我們去做。摩梭社會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不同的群體踐行著不同的婚姻模式,分布在不同地域的摩梭人因所處的地理環境差異以及受周邊族群文化影響程度的不同,呈現出文化慣習上的差異性,永寧摩梭、蒗渠摩梭、拉伯摩梭、左所摩梭、木里摩梭因所處地域的差異而呈現出不同的差異。在已知的人類文化中,摩梭文化的獨特性使其閃耀出珍稀的光芒,摩梭文化所包含的人類學、社會學意義及其學術對話空間是極其豐富和廣袤的。迄今為止,對分布在不同地域的摩梭人的文化特性進行聚焦性比較研究的成果仍然比較有限。摩梭人所創設的文化邏輯與觀念秩序是如何系統地、始終如一地規范著摩梭人的社會組織?摩梭社會獨特的“走婚”制度可以歸結為文化選擇的結果,這一選擇符合摩梭人的心理和感情需要,反映出摩梭人如何概念化自己所處的社會和世界。對摩梭人的“走婚”制度進行再研究,是深入了解摩梭人觀念世界的一個很好的路徑。研究表明,摩梭人偏重“母系親屬”的文化觀念,并以家屋的和諧作為“生活充實性”與人生終極意義的追求。
但是,或許這還并不是研究摩梭人“走婚”制度的最終結論,只是在通往摩梭文化終極研究道路中某一個視角所賦予的結論。2020年10月,騰訊視頻上映了一部取材于摩梭人口述的紀錄片《納人說》,紀錄片結束時有這樣一句旁白:“我們既要接受彼此的不同,但更多地,我們還將看到,你我何其相似,并相互聯結。”如果將摩梭人的“走婚”作為跨喜馬拉雅地區多元婚姻形態中的一個個案,這也正是筆者在這篇文章里試圖闡明的一個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