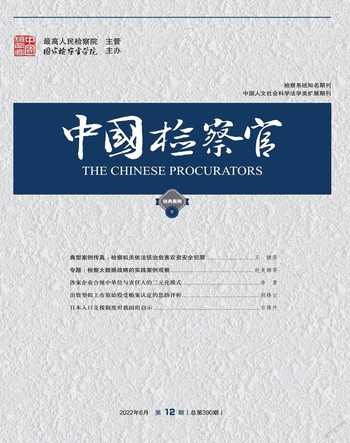走私犯罪對象認識錯誤的定性與處理
陳鹿林
摘 要:走私案件中,行為人具有走私的概括故意,或者只是對走私對象出現具體的認識錯誤時,應按實際對象定罪處罰;出現抽象的認識錯誤時,應在故意的內容與客觀事實重合的限度內確定合適的走私罪名。事實認定方面,可以從四個維度區分概括故意和認識錯誤:一是結合貨物的自然屬性;二是結合行為人的分工、角色和獲利情況;三是結合行為人是否履行必要的核實義務;四是結合行為方式、運輸工具與貨物的匹配度。基于從嚴打擊走私犯罪的政策導向,在遵循主客觀相一致原則的基礎上,總體上應從嚴把握認識錯誤的證據標準。
關鍵詞:走私犯罪 概括故意 具體認識錯誤 事實認定
一、走私犯罪對象認識錯誤的定性爭議
[案例一]2018年5月以來,葉某龍以310-450元/件的包稅價格向境外貨代人員攬收貨物。貨代人員以偽報品名、低報價格、虛構收件信息的方式填寫、交寄郵包,葉某龍又找到李某花負責接收、核對,李某花則委托黃某華,由黃某華提供其工作的郵政公司某營業部派送范圍的收貨地址用于接收上述郵包。截至2018年7月,葉某龍等3人采用上述方式郵遞境外貨物入境共1000多件,其中109件郵包郵寄入境時被查扣,內有一批普通貨物,偷逃應繳稅款72萬余元;還有5件象牙制品,價值24萬余元。3名被告人辯解,只知道包裹內是日常用品,不知道內有珍貴動物制品。一審法院認定上述3名被告人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二審法院認為,3名被告人對走私珍貴動物制品不具有走私的概括故意,不構成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僅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1]
[案例二]2016年4月10日中午,徐某林、馮某文受人糾集,共同駕駛一艘摩托艇從廣東省中山市前往香港。當晚7時許,二人到達香港一碼頭裝載一批用蛇皮袋包裝的穿山甲鱗片,駕艇返回中山市,途經民眾鎮田基沙水閘附近水道時,被公安機關查獲價值199萬余元的穿山甲鱗片77袋。徐某林辯解老板委托其走私凍肉入境,不知實際貨物為穿山甲鱗片。一、二審法院均認定徐某林構成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2]
走私罪屬于類罪,我國刑法根據不同對象進一步將其區分為走私普通貨物罪、走私武器、彈藥罪等13個具體走私罪名。司法實踐中,行為人對具體走私對象認識不清甚至發生認識錯誤的情形比較常見。對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海關總署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走私案件意見》)第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主觀上具有走私犯罪故意,但對其走私的具體對象不明確的,不影響走私犯罪構成,應當根據實際的走私對象定罪處罰。但是,確有證據證明行為人因受蒙騙而對走私對象發生認識錯誤的,可以從輕處罰”。該條規定了概括故意與認識錯誤的法律適用問題。從字面含義理解,無論概括故意還是對象認識錯誤,都按實際走私對象定罪處罰,對象認識錯誤不影響行為定性而只影響量刑。
然而,從司法實踐看,當行為人對走私的貨物(包括物品)[3]發生認識錯誤時,并非當然按照實際貨物定罪處罰。案例一中二審法院就認定行為人只構成走私普通貨物罪,不構成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那么,上述規定該如何理解,發生認識錯誤時,什么情況下并非簡單地按實際貨物定罪處罰?當然,法律適用的前提是準確區分概括故意和認識錯誤,判定當事人是否確實發生認識錯誤,這就涉及概括故意與認識錯誤的識別問題。對此,本文將圍繞上述兩個問題對走私犯罪對象認識錯誤問題展開分析。
二、走私犯罪對象認識錯誤的法律適用
單純從字面含義理解,《走私案件意見》第6條并沒有區分概括故意與對象認識錯誤,但這種理解顯然忽視了概括故意與對象認識錯誤之間的區別。前者是指行為人對其行為對象認識模糊,實際對象沒有超出其認識范圍而在其認識之中,此時按實際對象定罪處罰,符合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的原則。后者主要是對其行為對象在認識上出現錯誤,而非認識模糊,實際行為對象超出其認識范圍而在其認識之外。[4]在發生認識錯誤的情形下,能否按實際走私對象定罪,需要結合主客觀相一致的基本原則作具體分析。
對象認識錯誤屬于事實認識錯誤的一種,可以分為具體的認識錯誤和抽象的認識錯誤。具體的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在主觀上認識的對象與實際實施的對象雖然不一致,但具有相同屬性,沒有超出同一犯罪構成的范圍,即行為人只是在某個犯罪構成范圍內發生對象認識錯誤,在此情形下不影響行為定性。例如,某被告人非法攜帶300多個非洲獅爪、獅牙、豹牙等動物制品入境時被查獲,訴訟中被告人辯解以為都是獅牙,應以獅牙價值作為定案金額。[5]然而,無論是獅牙還是獅爪、豹牙,都屬于珍貴動物制品,這種認識偏差屬于具體的認識錯誤,仍應定性為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罪,且犯罪數額應以實際物品進行核定。
抽象的認識錯誤是指行為人所認識的事實與現實中所發生的事實分屬于不同構成要件的情形。[6]在此情形下不能直接根據實際對象認定犯罪,而應在故意內容與客觀事實相符的范圍內認定犯罪。具體到走私罪中,雖然刑法根據不同對象規定了13個具體走私罪名,但不同對象之間可能存在一定重合,出現認識錯誤時,應在故意的內容與客觀事實重合的限度內認定走私犯罪主觀故意,確定合適的罪名。[7]以走私仿真槍為例,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5條第2款,走私的仿真槍經鑒定屬于槍支,構成犯罪的,通常以走私武器罪定罪處罰。然而,“如果行為人認為自己走私的仿真槍不具有槍支功能,就缺乏走私槍支的故意,即使事后鑒定為槍支,也應當認定為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物品罪”[8]。這是因為普通仿真槍與槍支在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這一范圍內是重合的。
值得探討的是,如果主觀認識對象與實際貨物不存在重合,特別是當行為人只有走私普通貨物的主觀故意,而實際貨物中卻有違禁品時如何處理?比如本文案例一中,根據二審法院的認定,葉某龍等人主觀上只有走私普通貨物的故意,但是客觀上走私了珍貴動物制品(象牙),而珍貴動物制品與普通貨物(涉稅貨物)又不存在重合。對此,筆者認為,可以將本案中走私珍貴動物制品的行為評價為走私普通貨物未遂,與其他走私普通貨物既遂行為一并處理。當然,如果實踐中行為人只有走私少量普通貨物的主觀故意,實際上卻都是違禁品,一般不宜按犯罪處理。而如果行為人缺少走私犯罪的主觀故意,例如在正常進口普通貨物過程中,確實因受蒙騙而實際包含了違禁物品的,不應以走私罪評價。
三、走私犯罪概括故意與認識錯誤的識別
前面主要分析了走私犯罪中概括故意與認識錯誤的法律適用問題,但法律適用的前提在于準確識別概括故意和認識錯誤,判定當事人是否確實發生認識錯誤。
走私犯罪概括故意分為兩種類型:一是完全概括故意型走私,即行為人具有走私的犯罪故意,且無論走私何種貨物都未超出其主觀故意,但對具體走私對象認識模糊;二是部分概括故意型走私,即行為人具有走私某一類型貨物的主觀故意,但在該種類之下具體是何種貨物在所不問,或者認識模糊。
在完全概括故意型走私中,行為人對具體走私何種貨物不聞不問或者放任不管,可以直接按實際對象定罪處罰,因此不需要判斷是否發生認識錯誤。但司法實踐中,完全概括故意型走私的情形比較少見,更為常見的是部分概括故意型走私,此類概括故意與認識錯誤的區分比較容易混淆。當然,在分析行為人是否發生認識錯誤時,既包括對某種對象是否有明確的認識,也包括是否有認識的可能性。如果某類走私對象的出現,不能排除行為人有認識的可能性,仍然屬于概括故意的范疇。但如果沒有認識的可能性,完全超出其認識范圍之外,則屬于認識錯誤。具體而言,可以結合以下幾個因素進行綜合考量。
(一)結合貨物的自然屬性分析判斷
認識錯誤,意味著對貨物的種類、屬性出現了誤判。而針對貨物的種類、屬性,可以從自然屬性和法律屬性兩個維度來把握。自然屬性不考量法律特別規定,而是立足于生物特征、物理特征等自然視角區分不同類型的貨物。例如,動物與植物,陸生動物與水生動物,書籍與食品等,通常基于自然屬性可以做出合理區分。法律屬性則是根據法律特別規定或相關規范性標準來區分不同類型的貨物,例如來自疫區的動植物產品、禁止出口的木炭等。
當行為人辯解其主觀認識的對象與實際對象出現偏差時,如果其本身具有走私犯罪的主觀故意,應當立足于自然屬性的角度來分析判斷是否有認識可能性,是否發生了認識錯誤。而法律屬性屬于法律認識問題,對于法律認識問題只需要達到具備違法性認識即可,不需要達到在法律上明確知道具體屬于何種貨物的程度。例如,在走私凍品案件中,涉案凍品可能來源于疫區,也可能并非來源于疫區,前者定性為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罪,后者一般定性為走私普通貨物罪。對于行為人而言,其只要認識到涉案貨物系凍品,即便其沒有認識到系來自疫區,也不屬于認識錯誤,應按實際對象定性為走私國家禁止進出口的貨物罪。
當然,實踐中有些貨物屬性的認定,需要同時考量自然屬性和法律屬性,例如對珍貴動物及其制品、文物、淫穢物品、槍支彈藥的認定,一方面需要以它們的自然屬性為基礎,另一方面又離不開法律所規定的具體標準。在此情形下,應當首先立足于自然屬性判斷認識的情況,然后結合經驗、常識分析其對涉案物品的法律屬性是否有認識的可能性。
(二)結合行為人的分工、角色和獲利情況判斷
共同走私中,行為人的分工、角色對于判斷其對走私對象的明知程度有重要參考價值。貨主作為走私犯罪的直接驅動者和最大獲利者,走私對象的不同直接影響其非法獲利的多少,一般可以認定貨主對實際走私對象明知。貨源組織者因直接與供貨商聯系,同時也多是貨主與上游供貨商之間的聯系紐帶,在二者間傳遞信息,一般情況下也對走私對象明知。而單純運輸、裝卸、付款人員的主觀狀態則需結合具體情況綜合判斷。比如,對于繞關走私成品油案件,因運輸、裝卸人員需用油管進行接駁,貨物特征比較明顯,一般足以認定行為人對貨物種類有概括的認識。而對于書籍、光盤等通常有外包裝且須根據內容來判斷是普通貨物還是違禁品,則需要有更充足的理由和證據來認定是否有認識的可能性。
以本文案例一為例,二審法院認為,上訴人葉某龍、李某花、黃某華相互間口頭明確約定不寄違禁品,寄件人在郵包中混雜珍貴動物制品的行為,已超出上訴人的主觀認知范圍,其對走私珍貴動物制品不具有走私的概括故意。筆者認為,從葉某龍等3人在本案中主要扮演攬貨、包通關的角色角度看,結合其事前確實約定只走私普通貨物,排除走私違禁品,認定行為人對郵包內的象牙制品發生認識錯誤更為合理。
(三)結合行為人是否履行必要的核實義務判斷
在貨物進出口中,行為人避免發生認識錯誤最直接的方式是核實涉案貨物。如果行為人在有了解、核實條件的情況下,卻未履行必要的核實義務,說明其有認識的可能性但予以放棄,體現其放任涉案貨物走私的心理狀態,實際走私何種貨物并未超出其認識的范疇。
例如本文案例二,徐某林辯稱老板委托其走私凍肉入境,不知實際貨物為穿山甲鱗片,但法院認為,徐某林作為一名有社會閱歷的成年人,應當知道老板利用載貨量較小的涉案摩托艇走私凍肉而向其與馮某文每人支付6000—7000元高額報酬并不符合常理,且其在接貨時已經猜測到并非凍肉,但卻未核實貨物的真實情況、未終止實施走私行為,而是為了謀求高額回報,繼續將涉案貨物走私入境。可見,徐某林對于走私貨物的品類、社會危害性持放任的態度,對其應當根據實際的走私對象即穿山甲鱗片定罪處罰。本案中,法院就是結合行為人獲取不尋常報酬、未履行必要核實義務等情況,綜合認定涉案貨物并未超出行為人概括故意的范疇。
(四)結合行為方式、運輸工具與貨物的匹配度判斷
在具體作案過程中,行為方式、運輸工具屬于比較宏觀的范疇,更容易被行為人所感知,一般情況下行為人會有比較明確的認識,或者這種認識程度比較容易查實。與之相反,貨物則屬于更加微觀的范疇,通常隱藏于具體行為方式、運輸工具之下,外人對其認識的清晰度往往較低,行為人發生認識錯誤的概率較高。在此情形下,行為方式、運輸工具與貨物的匹配度可以作為區分概括故意與認識錯誤的重要依據。
一般而言,運輸工具與貨物的匹配度越高,行為人的主觀認知越明顯。比如大宗貨物往往使用大容積的運輸工具,毒品則多采用人肉攜帶、行李夾藏、郵寄等方式。對于裝載對象相對有限的運輸工具,可以通過對運輸工具的認知情況,進而判斷其對實際貨物的認識情況。以走私凍品為例,凍品運輸過程中需要配備相應的冷藏設備,可以通過論證行為人明知使用冷凍集裝箱裝載貨物,進而推斷其對集裝箱內裝有凍品具備認識的可能性。
在行郵渠道(個人攜帶或郵寄等)走私中,對于發現毒品、槍支或者淫穢物品等違禁物品的,違禁物品與走私方式基本能夠相對應,可以更多地推定主觀明知。反之,在大宗貨物中夾帶毒品、槍支或者淫穢物品或少量其他貨物的,受委托人員對于夾帶貨物的認識能力相對有限,對于此類小型違禁貨物主觀明知的判斷應當有更高要求。
四、余論
走私犯罪具有特殊性,一方面走私犯罪往往參與人員眾多,犯罪鏈條很長,實踐中能夠將同一次走私的所有參與者一網打盡的情形很少見;另一方面,走私案件涉及境外證據和事實的認定,大量事實很難查清。正因如此,司法實踐中行為人以認識錯誤為由作出罪抗辯的情形較為常見,且多是真偽難辨的“幽靈抗辯”。從案件認定的角度來看,如果過于強化認識錯誤作為出罪事由,勢必導致大量案件無法處理,容易形成放縱走私的傾向,難以發揮刑法一般預防的效果,也不利于維護國門安全;但如果不考慮認識錯誤因素,一律按實際走私對象定罪處罰,又有違刑法主客觀相一致的基本原則,容易導致罪責刑不相適應,或者不當擴大打擊面。
因此,走私案件的具體處理需要在打擊犯罪與保障人權之間尋求合理的平衡點,這就離不開實體法和程序法(證據法)兩個維度的綜合考量。從法律適用角度來講,應區分概括故意、具體的認識錯誤、抽象的認識錯誤等作不同處理。而從事實認定的角度看,總體上應從嚴把握認識錯誤的證據標準,特別是在繞關走私、職業化偽報品名走私(俗稱“特報”)中,在足以認定行為人有走私故意的情況下,一般推定其有走私的概括故意,并按實際走私對象定罪處罰;只有當確實有比較充分的證據或比較充足的理由認定當事人出現認識錯誤時,才能以此為由將部分或全部行為出罪。
*浙江省寧波市人民檢察院第三檢察部副主任、四級高級檢察官[315040]
[1] 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判決書,(2019)粵刑終1600號。
[2] 參見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19)粵刑終155號。
[3] 走私罪中貨物與物品有一定區別,但從認識錯誤角度看,二者沒有明顯區別。為敘述簡潔,本文統一使用“貨物”。
[4] 參見晏山嶸:《走私犯罪案例精解》,中國法制出版社2014年版,第404頁。
[5] 參見福建省高級人民法院刑事裁定書,(2016)閩刑終249號。
[6] 參見張明楷:《刑法學》,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第277頁。
[7] 參見南英主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走私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理解與適用》,中國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334頁。
[8] 同前注[6],第749頁。